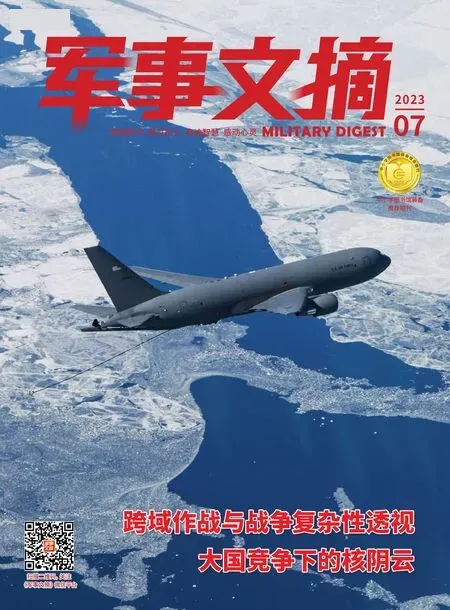跨域作戰復雜性問題探析
孔 光 畢自昌 韓 宇

戰爭是人類最復雜的實踐活動,其復雜性隨著各種高新技術、高技術裝備在戰爭中的運用和作戰域的不斷拓展呈指數級增長。如果從跨域的視角看,人類戰爭大體經歷了三次跨域融合,即基于無線通信的協同作戰、基于信息鏈路的精確作戰和基于跨域融合的混合作戰,對抗的重心也從兵力火力、精確作戰逐步過渡到跨域融合能力。跨域混合作戰使作戰評估、作戰籌劃和指揮控制更為復雜,但人在現代戰爭中的參與程度和決定性作用更加突出,作戰重心向認知聚焦。
跨域作戰是人類活動空間和軍事技術融合發展的必然結果。近年來的軍事實踐中,無論是多維聯合作戰,還是非常規混合戰爭,戰爭所涉及的政治、經濟、科技、社會因素日趨復雜,戰場對抗正從陸、海、空、天、電磁等物理域的搏殺向網絡、認知和社會域延伸,作戰領域的拓展和作戰要素的疊加導致戰爭復雜性不斷增強。
戰爭形態演進中的跨域作戰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科技進步促使人類戰爭的領域不斷拓展,而戰爭的形態也隨著作戰域的拓展而日趨復雜。

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提升了不同平臺之間的協同性
基于無線通信的協同作戰。冷兵器戰爭時期,武器作用范圍有限,士兵數量和身體機能是取得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到了機械化戰爭時期,各類武器平臺的出現極大地拓展了作戰空間,戰場范圍為由幾百平方千米擴大到上百萬平方千米,作戰空間由陸、海平面戰發展為陸、海、空的立體戰場,但作戰行動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物理空間。無線電技術的發明和運用使跨域作戰成為可能,從1837年美國莫爾斯發明電報、1897年意大利馬可尼實現遠距離無線電通信,無線電技術逐步運用到各類作戰平臺。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日軍通過無線電監控俄軍艦動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軍坦克部隊配備了車載電臺,不同平臺間可實現作戰協同,作戰效能極大提升,作戰控制的復雜性也隨之提高。作戰重心從正面戰場轉移到與無線電緊密相關的密碼破譯和通信干擾方面,通信和機動也成為至關重要的作戰要素。
基于信息鏈路的精確作戰。隨著衛星導航、雷達、成像、網絡等技術的應用,構建了集成偵察監視、指揮控制、導航定位功能的信息鏈路,使信息與火力的結合異常緊密,作戰空間由實體空間向信息空間拓展,“發現即摧毀”的精確作戰成為可能,橫跨不同作戰域的信息要素成為各方關注和運用的重點內容,甚至在部分戰爭過程中,出現了后方信息分析和指揮人員多于前方作戰人員的新現象。信息域成為牽引其他作戰域的主導因素,指揮信息系統成為聯結各作戰要素體系的紐帶,信息流成為取得作戰要素快速流轉的動力源。軍事對抗的重心由物理域向信息域轉移,作戰機理也由火力制勝發展到信息制勝。
基于跨域融合的混合作戰。網絡技術和網絡媒體的普及使得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加之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融合賦能,促使虛擬空間行動對物理系統、認知領域的滲透性越來越強,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間)使用武力的頻率和規模逐漸下降,物理攻擊和虛擬攻擊、軍事手段和非軍事手段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從而催生了“灰色地帶”“混合戰爭”等一系列綜合戰爭理論,美軍也先后提出了“多域戰”“全域戰”等作戰概念。現代戰爭的作戰范圍拓展到更多的無形空間,在傳統戰爭中清晰的敵我界線,在新形態中變得逐漸模糊,其中不僅包括普通物理學意義上的自然空間,還包括網絡空間、心理空間等,戰爭手段也由傳統的軍事手段,向政治、經濟、金融、文化領域延伸。綜合看,混合作戰是打破原有領域界限,發揮跨域融合的非對稱優勢,擊敵要害、破敵體系,以改變敵認知為中心的作戰樣式。
跨域作戰催生復雜性戰爭
科技和作戰理論的持續發展深刻改變著世界,同樣也改變著戰爭。跨域作戰作為現代戰爭的典型特征,也是催生戰爭復雜性的根本原因。
跨域作戰力量多元,交戰雙方作戰能力難以評估。以火力為中心的戰爭評估可以通過兵力和火力數量統計達成,以信息為中心的戰爭評估可以通過技術和平臺發展來衡量,跨域混合作戰因力量多元、組合多樣造成能力評估甚為復雜。首先,認知、網絡、太空等新興領域作戰能力涉及各類軟性指標,難以進行標準化計量。其次,常規與非常規戰爭的混合,軍事和非軍事作戰手段的混合,形成一整套多層級的系統性組合,作戰樣式譜系更為復雜,各種力量運用也更為捉摸不定。
跨域作戰體系復雜,作戰行動指揮控制難度加大。按照“OODA循環”理論,當觀察、判斷、決策、行動四類作戰要素形成閉環時,即可完成一次作戰行動。在現代作戰體系中,依托先進軍事通信網絡能在任意人員(裝備)之間建立聯系,從而形成無數可能的作戰組合及對應作戰方案。但是每增加一個作戰單元,其作戰體系可能的構成就會指數級地增加,其復雜性也必將對應地增加,這就極其考驗信息傳輸網絡的可靠性、決策算法的自動化水平。跨域作戰使作戰體系的復雜性和指揮通聯的難度陡然增長,這對指揮員的籌劃、決策和協同能力形成巨大的挑戰。
科技發展迅猛,給跨域作戰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無人作戰、激光武器、高超聲速武器等一系列新軍事技術、軍事武器的持續涌現正在對傳統作戰樣式、作戰進程產生極大影響,并不斷顛覆人們對戰爭的認知。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數據技術可以以某種程式化或深度學習的迅捷方法,將大量人(物)構建到一個復雜的邏輯中,并以人類難以企及的速度與遍歷能力實現要素組合、重組、優化。具有智能特征的各類高端武器的組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機動性、殺傷力和震懾力。我們無法預測基因技術、量子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會給戰爭帶來哪些顛覆性的沖擊,但可以確認的是技術發展必然會給未來戰爭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人工智能、高超聲速武器等前沿技術正在顛覆戰爭形態

不同域的組合以及軍事與非軍事手段的結合,使得跨域作戰成為一個復雜性系統
積極應對復雜性戰爭挑戰
戰爭本身是一個超級復雜系統,具體運行過程中既不是理想模型也不可精確預測,而是隨著作戰域的不斷拓展,作戰要素的組合和協同關系也更為廣泛和復雜。但毋庸置疑人在現代戰爭中的參與程度和決定性作用更加突出,只有把握戰爭發展脈絡,于撲朔迷離中掌握更多的確定性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加快推進新型作戰力量建設。新型作戰力量是軍事能力、乃至國家現代化水平和國力的重要體現,“以新制勝”也歷來是世界軍事發展的重點和焦點。新型作戰力量所對應的新作戰需求、新技術支撐和新型作戰能力在解決跨域作戰所帶來復雜性方面具有先天的主動性和后天優勢,是在未來戰爭中提升整體作戰能力、贏得戰爭主動的重要前提。新型作戰力量發展建設的核心在于持續加大人才隊伍的建設力度,基礎在于高技術裝備的發展應用。在新型作戰力量建設運用中,我們應始終重點關注高技術裝備與高素質人才隊伍這一對基本組成要素,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加快培養具備未來戰爭所需信息素養、作戰指揮能力的新型作戰力量人才;持續推動高新技術裝備研發、使用與戰斗力生成研究;搭建能夠給予新型作戰人才充分培養鍛煉的體系平臺,全面促進新型作戰力量形成新型作戰能力,以奪取未來作戰中的主動權。
大力推動跨域作戰體系建設。實行跨域作戰的核心目標就是通過構建跨域作戰體系實現高效的跨域資源融合、相互支援、密切協同,使整個體系的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發揮。跨域作戰體系是通過按照作戰需求組合運用跨域作戰要素而構成的作戰體系,而絕不是多個作戰域的作戰要素和作戰能力的機械疊加。跨域作戰體系能夠通過作戰信息的跨域流動、作戰要素的跨域使用來實現作戰能力的互補或倍增。為了實現某一作戰目標,跨域作戰體系要能夠快速、動態且靈活地構建基于任務要求的作戰體系,其中包括任務所需的殺傷網、感知要素、指揮要素、行動要素等,相關要素的跨域協同也能夠根據規則執行,形成高效的“感知-決策-行動”跨域殺傷鏈路,為指揮員提供多套跨域作戰方案選擇,以最優方案達成作戰目的。

戰爭形態正逐步由消耗戰向認知戰方向轉變
持續開展新作戰領域研究探索。現代戰爭由分域協同向多域融合、跨域聯合轉變已成為基本趨勢,世界各國作戰力量建設正呈現出向新領域持續加速拓展的趨勢。1935年,英軍因無線電技術優勢掌控了電磁空間的絕對優勢,依此實現對英國領空監視,并成功擊敗德國,贏得了不列顛之戰;1991年,美國依托網絡技術優勢形成了在網絡空間的整體優勢,在“海灣戰爭”中顛覆性地發展了精確作戰模式。而當前跨域混合作戰儼然已成為各國研究的重點領域,且戰爭形態正逐步由消耗戰向認知戰方向轉變。
從跨域的視角不難發現,人類戰爭先后經歷了從有形空間向電磁域的跨越、從物理空間向信息空間的跨越、從軍事領域向非軍事領域的跨越,而戰爭的復雜程度也隨著作戰域的拓展而不斷提升。戰爭實踐表明,每當作戰行動拓展至新的領域時,早期開展相關理論和技術研究的國家更容易形成先發優勢,我們只有形成關鍵領域技術的突破和理論的創新,才能在未來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