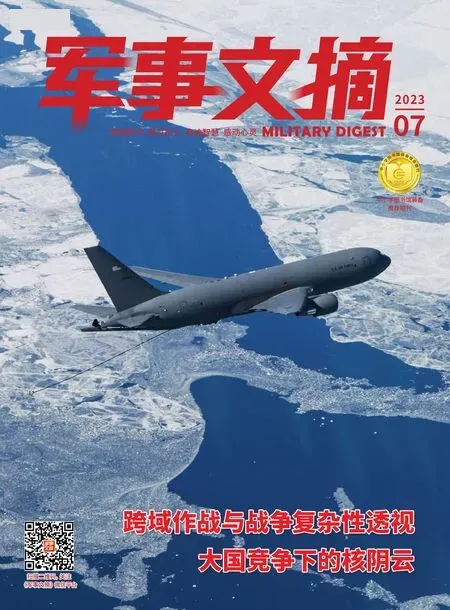隱形空間對抗:論復(fù)雜性戰(zhàn)爭的新形態(tài)
賀 璐 李寶玲 王 新

戰(zhàn)爭是人類最復(fù)雜的實(shí)踐活動,戰(zhàn)爭復(fù)雜性與社會的進(jìn)步、科技的發(fā)展緊密關(guān)聯(lián),隨著人類活動空間和軍事技術(shù)融合發(fā)展,跨域作戰(zhàn)正在成為現(xiàn)代沖突對抗的必然結(jié)果。網(wǎng)絡(luò)空間、電磁空間、認(rèn)知領(lǐng)域等“非接觸式”的隱形空間,是鏈接陸、海、空等實(shí)體空間的核心地帶,是實(shí)施跨域作戰(zhàn)的“神經(jīng)”樞紐,逐漸成為大國角力博弈的重要戰(zhàn)場。隱形空間對抗方式多維多樣、手段隱蔽無序、疆域模糊難辨,逐漸演變?yōu)橐环N新型戰(zhàn)爭形態(tài)。
隱形空間對抗的方式
復(fù)雜性是戰(zhàn)爭的本質(zhì)屬性,隱形空間強(qiáng)調(diào)“戰(zhàn)爭形態(tài)由兵力火力消耗戰(zhàn)向跨域精確破襲戰(zhàn)轉(zhuǎn)變”,對抗貫穿“情報(bào)偵察、指揮控制、聯(lián)合打擊、綜合保障”全過程。隱形空間對抗是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從近幾場沖突看,隱形空間對抗的運(yùn)用越來越常見,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方式,而是根據(jù)不同對手、不同強(qiáng)度,靈活運(yùn)用不同空間、不同手段組合發(fā)力,形成利于己方的戰(zhàn)略態(tài)勢或者戰(zhàn)場優(yōu)勢。
低強(qiáng)度隱形空間對抗。低強(qiáng)度對抗博弈是指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處于合作和競爭關(guān)系,雙方政治、經(jīng)濟(jì)、外交、軍事等多領(lǐng)域保持一般性競爭性互動。此態(tài)勢下,隱形空間對抗重在掌握信息、保持存在,主要表現(xiàn)為兩種方式。一是隱蔽突破滲透。競爭雙方運(yùn)用網(wǎng)絡(luò)偵察手段,持續(xù)、隱蔽對對手政治外交、軍事及關(guān)鍵基礎(chǔ)設(shè)施等網(wǎng)信體系目標(biāo)偵察滲透,長期竊取對手關(guān)鍵領(lǐng)域信息數(shù)據(jù),在核心節(jié)點(diǎn)預(yù)先設(shè)置“暗樁”,強(qiáng)調(diào)保有隱形空間的局部優(yōu)勢。二是持續(xù)偵察監(jiān)視。競爭雙方依托陸、海、空、天、網(wǎng)等偵察資源,構(gòu)建針對對手的偵察預(yù)警探測體系,常態(tài)保持高頻度偵察狀態(tài),奪取和保持隱形空間信息優(yōu)勢。在雙方利益攸關(guān)區(qū)域,雙方結(jié)合練兵備戰(zhàn)行動,主動設(shè)計(jì)突防突擊、情報(bào)偵搜等科目,誘導(dǎo)對方電磁目標(biāo)活動,借機(jī)搜集掌握對手核心數(shù)據(jù)。
中強(qiáng)度隱形空間對抗。中強(qiáng)度對抗博弈是指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之間保持合作和競爭狀態(tài),但競爭成為雙邊關(guān)系主旋律,雙方圍繞核心關(guān)切展開全方位對抗較量。此態(tài)勢下,隱形空間對抗重在警示攻擊、威懾施壓,主要表現(xiàn)為三種方式。一是非接觸精準(zhǔn)破襲。競爭雙方圍繞戰(zhàn)略目標(biāo),運(yùn)用“非接觸式”武器手段,通過隱形空間精準(zhǔn)攻擊對手核心網(wǎng)信目標(biāo),直接或間接影響對手實(shí)體空間目標(biāo),令對手吃“啞巴虧”。2010年8月,美國運(yùn)用“震網(wǎng)”病毒精準(zhǔn)襲擊伊朗布什兒核電站,迫伊擱置核發(fā)展計(jì)劃,就是隱形空間精準(zhǔn)破襲的典范。二是實(shí)戰(zhàn)性干擾檢驗(yàn)。競爭雙方在利益攸關(guān)區(qū)域,強(qiáng)調(diào)運(yùn)用隱形空間對抗裝備手段,試探性、警示性干擾攻擊對手主戰(zhàn)武器裝備等,驗(yàn)證裝備作戰(zhàn)能力,相互試探對手底線,威懾教訓(xùn)對手行為。三是敘事性認(rèn)知較量。競爭雙方依托網(wǎng)絡(luò)信息和現(xiàn)代媒體技術(shù),圍繞全球戰(zhàn)略格局走勢的思想博弈和政治塑造,相互試探闡述己方核心訴求,依據(jù)自身利益提出不同主張,制造對方負(fù)面國際形象,誘導(dǎo)網(wǎng)絡(luò)輿論走向,爭取國際輿論主導(dǎo)權(quán)。
高強(qiáng)度隱形空間對抗。高強(qiáng)度對抗博弈是指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合作溝通渠道基本斷絕,競爭雙方在隱形空間對抗日趨白熱化,并慫恿主導(dǎo)發(fā)動“代理人戰(zhàn)爭”。此態(tài)勢下,隱形空間對抗博弈重在介入支援、殺傷懾止,主要表現(xiàn)為三種方式。一是持續(xù)攻擊遏控。競爭雙方著眼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biāo),靈活運(yùn)用網(wǎng)絡(luò)攻擊、電磁干擾等隱形空間對抗手段,持續(xù)攻擊破壞對手軍事信息體系,大規(guī)模癱瘓關(guān)鍵基礎(chǔ)設(shè)施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懾止對手可能冒險(xiǎn)行為或支援“代理人”實(shí)體空間作戰(zhàn),奪取和保持隱形空間優(yōu)勢。二是高技術(shù)外部支援。主導(dǎo)發(fā)動“代理人戰(zhàn)爭”一方,運(yùn)用隱形空間資源和人工智能技術(shù)介入支援,采取提供實(shí)時(shí)戰(zhàn)場態(tài)勢、重構(gòu)作戰(zhàn)體系、遠(yuǎn)程指揮行動、指引火力打擊,以及賦能“代理方”武器裝備等方式,提升“代理方”整體信息化水平,跨域式躍升其綜合防抗能力。三是占控認(rèn)知領(lǐng)域高點(diǎn)。競爭雙方圍繞占控隱形空間資源,采取信息轟炸和信息遮斷等手法,針對目標(biāo)國進(jìn)行戰(zhàn)略敘事,以特定事件極度渲染、歪曲敘述,進(jìn)行標(biāo)簽化定性,通過觀念塑造、輿論操控等構(gòu)建對對手不利的負(fù)面情感認(rèn)同,占據(jù)義理制高點(diǎn),為其行動提供道義和法理依據(jù)。

2010年8月,美國運(yùn)用“震網(wǎng)”病毒襲擊了伊朗布什兒核電站
隱形空間對抗的特點(diǎn)
伴隨戰(zhàn)爭形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戰(zhàn)爭特征也呈現(xiàn)多樣變化。隱形空間對抗,作用效能由虛擬空間向?qū)嶓w空間、認(rèn)知領(lǐng)域滲透,作戰(zhàn)手段由單一方式向多維融合、立體攻防拓展,對抗形態(tài)呈現(xiàn)指數(shù)級、爆炸性的復(fù)雜嬗變,衍生出許多獨(dú)有的戰(zhàn)爭特征。
疆域模糊傳統(tǒng)的陸、海、空、天等物理空間戰(zhàn)場,都存在一個(gè)比較清晰的防御疆界,比如人為以山脈、河流、島嶼或者關(guān)隘、城池等劃定界線,具有明顯的物理性距離感。隱形空間因?yàn)榻M成要素既有物理空間的人員和設(shè)備,也有虛擬空間的信息數(shù)據(jù)和交互規(guī)則,“實(shí)”與“虛”的交織混合,裝備與鏈路的靈活重構(gòu),人員與數(shù)據(jù)的聯(lián)通交互,決定其與陸、海、空等物理空間不同,無法用類似“山脈”“河流”“城池”等固定實(shí)體,劃定一個(gè)比較清晰的隱形空間疆域邊界。因此,隱形空間對抗不再關(guān)注傳統(tǒng)物理疆域爭奪,更多關(guān)注隱形空間運(yùn)轉(zhuǎn)的關(guān)鍵樞紐,這既可能在物理實(shí)體邊界外,也可能是傳統(tǒng)戰(zhàn)場腹地,這給布防帶來巨大挑戰(zhàn)。
平戰(zhàn)一體傳統(tǒng)作戰(zhàn)平戰(zhàn)界線分明,強(qiáng)調(diào)“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shí)”,平時(shí)重在集聚能量,重點(diǎn)是掌握對手情況、創(chuàng)新作戰(zhàn)運(yùn)用、專攻精練聚能;戰(zhàn)時(shí)重在集中釋能,重點(diǎn)是遴選對手核心目標(biāo),全面實(shí)施打擊釋能,實(shí)現(xiàn)作戰(zhàn)企圖。隱形空間對抗十分依賴對手體系脆弱性和漏洞,強(qiáng)調(diào)“養(yǎng)兵千日、用兵千日”,平時(shí)以不同形式、不同規(guī)模、不同空間悄然發(fā)生,重在偵察滲透和隱蔽潛伏。戰(zhàn)時(shí)則在平時(shí)滲透潛伏基礎(chǔ)上,運(yùn)用不同策略、不同手段、不同強(qiáng)度實(shí)施攻擊,重在全面攻防和破擊體系。因此,隱形空間對抗功在平時(shí)、用在戰(zhàn)時(shí),很難按照傳統(tǒng)戰(zhàn)爭屬性對其做出清晰的戰(zhàn)爭界定。比如“震網(wǎng)”病毒也是通過平時(shí)長期偵察滲透,最終通過病毒直接達(dá)成戰(zhàn)略目的。
技術(shù)制勝兵力規(guī)模、武器裝備是傳統(tǒng)作戰(zhàn)攻防優(yōu)劣的重要衡量因素,但隱形空間攻防優(yōu)劣主要依賴科學(xué)技術(shù)手段。一方面,隱形空間要穩(wěn)定高效支撐作戰(zhàn)體系,需要依靠量子密碼、可信計(jì)算、云計(jì)算、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學(xué)技術(shù),構(gòu)建可靠、穩(wěn)固、安全的作戰(zhàn)體系鏈接和分散部署的作戰(zhàn)單元,力避被對手降維打擊;另一方面,隱形空間作戰(zhàn)運(yùn)用的無線接入、遠(yuǎn)程接管、病毒程序、電磁擾壓、信息遮斷、輿論轟炸等手段,都是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電磁能、社會工程和人工智能等技術(shù)融合共生產(chǎn)物。對抗雙方誰有高敵一籌的技術(shù)手段,誰就能在隱形空間中先敵一步出奇制勝。比如,2007年以色列空襲敘利亞核設(shè)施基地,就是基于美軍長期偵察滲透敘軍預(yù)警探測系統(tǒng),針對性研制出“舒特”系統(tǒng),有效干擾了敘軍防空雷達(dá)網(wǎng)絡(luò),支援以軍戰(zhàn)機(jī)突入敘境轟炸并順利返航。

隱形空間是鏈接實(shí)體空間的核心地帶
軍民混合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和精神生活需要,網(wǎng)絡(luò)空間、電磁空間、認(rèn)知領(lǐng)域等隱形空間與民眾工作生活越來越密切,加之隱形空間的開放性、技術(shù)手段的通用性、疆域界線的模糊性,使得軍隊(duì)力量和民間力量參與的界限逐漸模糊,以軍掩民、寓軍寓民、軍民混合已成為隱形空間對抗的新常態(tài)。一方面,隱形空間對抗不再局限于軍事目標(biāo)還是民用目標(biāo),不再局限于虛擬空間還有認(rèn)知領(lǐng)域,決定對抗不再僅僅是軍隊(duì)責(zé)任,還需要軍民融合互補(bǔ)一體發(fā)力;另一方面,隱形空間對抗手段具有通用性,民間蘊(yùn)藏著豐厚的技術(shù)手段和物質(zhì)基礎(chǔ),決定軍隊(duì)力量需要民間力量提供強(qiáng)有力支撐,聯(lián)動奪取對抗勝利。2022年烏克蘭危機(jī)中,軍民力量混合參與隱形空間對抗較量,改變了對抗進(jìn)程,開啟了隱形空間軍民混合對抗的新起點(diǎn)。
隱形空間對抗的影響
隱形空間對抗看似實(shí)施持續(xù)低位攻擊,降低了沖突雙方高強(qiáng)度軍事對抗風(fēng)險(xiǎn),但從現(xiàn)實(shí)看,隱形空間對抗手段方式靈活難測、作用效能滲透轉(zhuǎn)化、行動力量軍民難分,引發(fā)戰(zhàn)爭形態(tài)快速嬗變,催生多種危機(jī)易發(fā)并發(fā),戰(zhàn)爭沖突呈現(xiàn)越來越多的復(fù)雜性趨勢,給遏控危機(jī)、打贏戰(zhàn)爭帶來很多風(fēng)險(xiǎn)挑戰(zhàn)。
危機(jī)管控挑戰(zhàn)更大。隱形空間對抗重在采取有限手段規(guī)模,長期隱蔽對對手實(shí)施持續(xù)低位攻擊,強(qiáng)調(diào)不過度刺激對手、不追求一時(shí)得失,旨在積累小事件形成雪崩效應(yīng),漸進(jìn)蠶食對手優(yōu)勢,確保戰(zhàn)略態(tài)勢始終保持利己方向發(fā)展。與傳統(tǒng)作戰(zhàn)領(lǐng)域相比,隱形空間攻擊由于沒有國際法規(guī)范行為準(zhǔn)則,對抗雙方時(shí)時(shí)刻刻都在博弈較量,一旦處置不當(dāng)極有可能發(fā)生“擦槍走火”,進(jìn)而引發(fā)危機(jī)升級甚至爆發(fā)武裝沖突。同時(shí),隱形空間“非接觸式”對抗解決不了本質(zhì)問題,反而“溫水煮青蛙”可能使矛盾越積越深,一旦造成雪崩效應(yīng),必然引發(fā)更為強(qiáng)烈反應(yīng),且不局限于單一領(lǐng)域內(nèi),給戰(zhàn)略危機(jī)管控帶來更大風(fēng)險(xiǎn)挑戰(zhàn)。
區(qū)域拒止難度更大。隱形空間具有跨域、賦能功能,“跨域”是因隱形空間與陸、海、空、天等物理實(shí)體空間相互重疊關(guān)聯(lián),物理實(shí)體空間的軍事信息系統(tǒng)和用頻武器平臺,需要隱形空間技術(shù)手段使廣域分布或機(jī)動部署的兵力兵器達(dá)成通信聯(lián)系,這是跨域作戰(zhàn)的基礎(chǔ)。“賦能”是指通過隱形空間能融合分析戰(zhàn)場情報(bào)、共享分發(fā)態(tài)勢信息、快速規(guī)劃作戰(zhàn)行動、科學(xué)消除用頻沖突,實(shí)現(xiàn)作戰(zhàn)力量信息共享、一體聯(lián)動。與傳統(tǒng)作戰(zhàn)領(lǐng)域兵力兵器支援相比,隱形空間介入支援可通過重構(gòu)作戰(zhàn)體系、共享情報(bào)信息、遠(yuǎn)程控制行動等遠(yuǎn)程方式,實(shí)現(xiàn)對低水平“盟友”的信息化“賦能”,從而彌補(bǔ)其綜合實(shí)力差距,極大降低了大國發(fā)動“代理人戰(zhàn)爭”成本,增加了“區(qū)域拒止”難度,促使有些大國更加肆無忌憚“拱火遞刀”,導(dǎo)致敏感地區(qū)“政局動蕩”、地緣政治發(fā)生巨變。

云計(jì)算、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學(xué)技術(shù)是隱形空間對抗的制勝法寶
體系作戰(zhàn)威脅更大。聯(lián)合作戰(zhàn)體系龐大、結(jié)構(gòu)復(fù)雜,關(guān)鍵是通過隱形空間將實(shí)體空間各作戰(zhàn)單元鏈接起來,利用信息處理技術(shù)逐級匯聚、逐級融合。隱形空間對抗核心就是對聯(lián)合體系中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和樞紐局部短時(shí)破壞,使其支撐或關(guān)聯(lián)的實(shí)體作戰(zhàn)目標(biāo)降能或失效,發(fā)揮以虛制實(shí)的作戰(zhàn)效能。與傳統(tǒng)作戰(zhàn)領(lǐng)域針對單個(gè)實(shí)體目標(biāo)摧毀性作戰(zhàn)相比,隱形空間對抗更加注重打擊聯(lián)合作戰(zhàn)體系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重在破壞整個(gè)作戰(zhàn)體系運(yùn)行功能,使分散部署的各作戰(zhàn)力量成為被割裂的孤軍,致使其信息流動受阻、指揮決策失準(zhǔn)、行動控制不暢,無法有效緊密協(xié)同行動,產(chǎn)生類似“降維打擊”的行動效果,迅速形成對對手高維度的絕對優(yōu)勢。由于隱形空間體系架構(gòu)設(shè)計(jì)缺陷,導(dǎo)致安全問題不可能徹底管控,聯(lián)合作戰(zhàn)體系在遵守跨域賦能增效的同時(shí),必然也面臨“降維打擊”風(fēng)險(xiǎn),無疑增加了體系作戰(zhàn)的不確定性。
社會領(lǐng)域?yàn)?zāi)難更大。隱形空間對抗是典型的“非接觸式”較量,具有平戰(zhàn)難分、軍民難辨的特征。從既往對抗案例看,對抗人員往往披著民間人員外衣,運(yùn)用比特流、電磁波等手段攻擊,肆無忌憚發(fā)動遠(yuǎn)程接管破壞或者抵近戰(zhàn)場干擾攻擊。與傳統(tǒng)戰(zhàn)場較量相比,隱形空間對抗由于行為體多元性和溯源的困難性,攻擊人員突破了傳統(tǒng)戰(zhàn)爭作戰(zhàn)法律界限,不僅僅對對手軍事目標(biāo)持續(xù)實(shí)施精準(zhǔn)破襲,還常常選擇對手關(guān)鍵基礎(chǔ)設(shè)施和支援保障作戰(zhàn)的民用目標(biāo)實(shí)施大規(guī)模阻斷攻擊。由于隱形空間攻擊目標(biāo)正在由軍事向軍民兼顧轉(zhuǎn)變,對抗雙方金融、能源、電信、電力、交通等基礎(chǔ)設(shè)施都是重點(diǎn)打擊對象,都面臨被癱瘓、被接管的體系性災(zāi)難,給沖突戰(zhàn)爭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隱形空間更注重打擊敵人作戰(zhàn)體系的重要節(jié)點(diǎn)
應(yīng)對策略
戰(zhàn)爭形態(tài)的深刻變化,直接影響戰(zhàn)爭機(jī)理的改變。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通過特點(diǎn)觀機(jī)理,認(rèn)真研究新復(fù)雜戰(zhàn)爭形態(tài)的復(fù)雜性,從復(fù)雜性的角度去研究戰(zhàn)爭問題,聚焦大國對抗博弈推進(jìn)戰(zhàn)爭準(zhǔn)備,掌握隱形空間對抗主動權(quán)。
推動構(gòu)建國際行為準(zhǔn)則,禁錮各方隱形空間行動。鑒于隱形空間與實(shí)體空間深度關(guān)聯(lián),放任隱形空間對抗必將加劇戰(zhàn)略對抗態(tài)勢,給大國博弈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因素。我們必須秉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主動承擔(dān)與我相適應(yīng)的大國責(zé)任,聯(lián)合世界各國和政治團(tuán)體,推進(jìn)全球多邊框架下討論隱形空間安全問題,積極推進(jìn)隱形空間國際治理進(jìn)程,重點(diǎn)圍繞隱形空間對抗平戰(zhàn)難分、軍民難辨,行動多元、溯源困難等現(xiàn)實(shí)問題,規(guī)范制定隱形空間有關(guān)條約,明確“使用武力”“武裝攻擊”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各方活動范圍、行為方式、制裁標(biāo)準(zhǔn)和行使自衛(wèi)權(quán)的尺度,劃出隱形空間對抗的紅線和底線,約束各方在隱形空間行為,力避有些國家憑借技術(shù)實(shí)力,在隱形空間長期肆意挑釁打壓,搶占主動權(quán)主導(dǎo)權(quán)。
強(qiáng)化積極防御能力建設(shè),對沖大國隱形空間挑釁。把握隱形空間對抗正在由軍事向民用關(guān)鍵基礎(chǔ)設(shè)施拓展特征,統(tǒng)籌軍事與民用關(guān)鍵基礎(chǔ)設(shè)施,加強(qiáng)體系冗余性建設(shè),預(yù)想最壞情況、做好最壞打算設(shè)計(jì)體系,確保體系反脆弱性。要強(qiáng)化軍民聯(lián)防,健全完善相關(guān)法規(guī)制度,明確軍地跨部門信息共享、多領(lǐng)域應(yīng)急協(xié)同、應(yīng)急指揮體系組建等內(nèi)容,明確聯(lián)合處置隱形空間事件流程,為軍地聯(lián)防提供法理依據(jù);要敢于打破桎梏,站在攻擊者角度審視可能攻擊來源、手段、途徑,通過調(diào)整防御策略做好“底線防御”,同時(shí)要主動前出狩獵、前置防御,常態(tài)追蹤溯源對手,從攻擊源頭反制敵攻擊行為;要大膽技術(shù)創(chuàng)新,加強(qiáng)區(qū)塊鏈、量子技術(shù)、人工智能、5G和擬態(tài)防御等新興技術(shù)運(yùn)用,創(chuàng)新構(gòu)建縱深網(wǎng)絡(luò)防御體系,縮短觀察、判斷、決策、行動的響應(yīng)時(shí)間,依據(jù)碎片化隱形空間行動事件,自動分析攻擊源和先攻特征,預(yù)測網(wǎng)絡(luò)攻擊行為,妥善謀劃應(yīng)對隱形空間行動應(yīng)對策略。
提高運(yùn)用軟硬實(shí)力能力,懾止隱形空間對抗。當(dāng)前大國博弈對抗進(jìn)入全方位角力階段,隱形空間對抗加劇大國競爭對抗,有國家在隱形空間惡意破壞和遏制打壓,無所不用其極。要贏得隱形空間博弈對抗勝利,必須拿起隱形空間對抗武器,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要深研對手既往案例,研究對手攻擊招式、追蹤對手攻擊路徑、搞清對手能力手段、預(yù)判對手可能行動,預(yù)置反制對手攻擊行為;要強(qiáng)化核心能力建設(shè),按照隱形空間作戰(zhàn)效能和對抗方式,重點(diǎn)研發(fā)定點(diǎn)破襲和集成攻擊兩類武器工具,推動武器工具定制化譜系化,達(dá)到根據(jù)隱形空間對抗態(tài)勢靈活實(shí)施反制行動,保持反制行動的有效性;要大膽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聚焦隱形空間機(jī)理特征、策略招法和手段樣式,成體系推出沖突形態(tài)、作戰(zhàn)概念、場景設(shè)計(jì)、戰(zhàn)法運(yùn)用等一攬子成果,引領(lǐng)斗爭準(zhǔn)備;要敢于亮劍實(shí)踐,把對手對我隱形空間懾壓挑釁行動作為“磨刀石”,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應(yīng)對行動、靈活運(yùn)用反制手段,在現(xiàn)實(shí)應(yīng)對中提升隱形空間實(shí)戰(zhàn)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