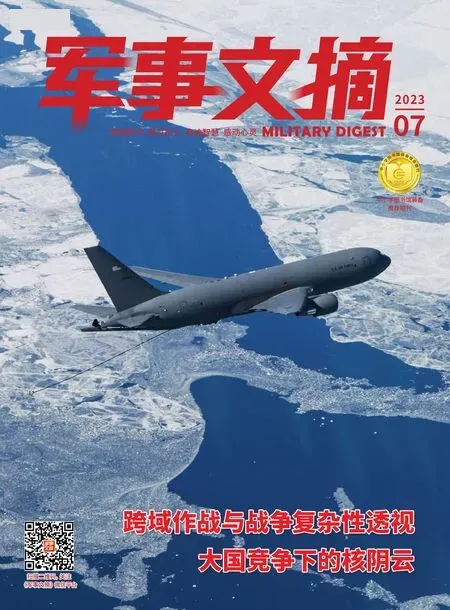從美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透視拜登政府核策略
曾 鵬 廖龍文

冷戰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均會根據自身對國際安全形勢和戰略格局的認識發布《核態勢評估報告》,評估美國核政策并調整核武器發展。自1994年克林頓政府發布首份《核態勢評估報告》以來,小布什政府(2002年)、奧巴馬政府(2010年)、特朗普政府(2018年)基本也都在執政次年發布了各自的《核態勢評估報告》。拜登政府上臺后,于2021年7月正式啟動核態勢評估進程,2022年3月,向國會提交了機密版《核態勢評估報告》,并在2022年10月發布公開版《核態勢評估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新版《報告》雖然充滿“一體化威懾”等隱晦或含糊的表述,但依然無法掩蓋美國本屆政府繼續維護其核霸權的真實意圖。《報告》將重點放在中國和俄羅斯身上,并明確將中、俄、朝、伊四國列為潛在的核對手,將中國定義為“步步緊逼的挑戰”;并一再重申美國對盟友和伙伴的承諾,為此沒有采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唯一目標”兩項核武器使用政策。對于未來,《報告》稱美國將減少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并謀求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
美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不變的基點
核武器作用:效果獨有、地位突出。《報告》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核武器將繼續為美國提供無法替代且獨特的威懾效果”,尤其是在使用核武器威懾和應對一些非核威脅方面能力獨特。
《報告》重申當前及未來美國核武器主要有三種作用:威懾戰略攻擊;為盟國和伙伴提供核安全保證;在威懾失敗時助力美國達成目標。這種定義類似于奧巴馬政府的表述,但后者還認為“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使核武器在美國家安全和美軍事戰略中的作用已大大減少”,新版《報告》缺乏這種認識。而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核力量應優先考慮威懾潛在敵人不發動任何規模的核襲擊,對盟國和伙伴提供保障,當威懾失敗時,仍可以為不確定的未來規避風險”,新版《報告》更像是對此表述婉轉的重申。可以預見,美國核武器將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保持這三種作用,持續為其軍事霸權提供獨有的威懾能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版《報告》稱美國正在“采取措施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但首先需要一定的“安全、政治和技術條件”,而俄羅斯和中國“對減少核武器的依賴興趣似乎不大”。因此,美國防部目前肯定不會考慮“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
核武器使用:舍棄承諾、模糊界限。對于核武器的使用,拜登在上臺前曾表示積極推動美國實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唯一目的”兩項政策。其中“唯一目的”政策是指美國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敵人對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使用核武器,并在必要時做出反應。這兩項政策是核武國家減少對核武器依賴的一個基本要素。但拜登政府最終未采納這兩項政策,也明確拒絕現在和未來很長時間內采取這兩項政策,認為上述兩項政策會“導致不可接受的風險”。這表明美國將延續“先發制人核打擊政策”,也為美國可能在沖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預留了充足空間,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門檻,加劇了核沖突風險。

F-35A正在進行B61-12投彈試驗
《報告》聲稱“美國只有在為保護美國或盟友、伙伴的重大利益的極端情況下,考慮使用核武器”。美國會對核武器的使用設置“非常高的標準”,且“不會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和遵守其核不擴散義務的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這一政策可以說延續了源自冷戰時期的延伸威懾戰略,強調“核保護傘”在管控盟友和推進地緣戰略目標中的特殊作用,但對“極端情況”缺乏明確界定。
核力量發展:實戰化、有序推進替換。新版《報告》幾乎全盤延續了前兩屆政府啟動的耗資巨大的“三位一體”核力量、核指控與通信系統以及核軍工基礎設施現代化計劃。《報告》明確表示美國“將繼續部署‘三位一體’核力量,并全力致力于在今后幾年陸續部署現代化系統”,隨著美國現有核力量逐漸達到預期壽命,相應“替換計劃正在有序進行。”同時,美國將增強核力量“對網絡、太空和電磁脈沖威脅的防護;加強綜合戰術預警和攻擊評估;改善指揮所和通信聯系;提供先進的決策支持技術”。
《報告》支持已部署的W76-2海基低當量核彈頭。W76-2彈頭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報告》中作為一項新的要求被提出,并在2019年迅速開發和部署。新版《報告》中稱W76-2彈頭提供了一個“阻止有限核使用的重要手段”,并明確表示該型彈頭可用于針對中、俄,是明目張膽的“核訛詐”。此外,《報告》還支持研發同樣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W93新型核彈頭,并會為哨兵洲際彈道導彈計劃和W87-1彈頭提供資金。
在發展核武器方面,新版《報告》也與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完全放棄了奧巴馬政府名義上的“不發展新核武器”的承諾。美國核武器相關國家實驗室充分利用這一機會,通過各種手段增強美國核武器的作戰能力。目前,美國核武庫正在進行大量的“改型”和“延壽”,將現有核武器的使用壽命延長幾十年,同時賦予其新的軍事能力。美國核武器現代化計劃完全違背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防止“縱向核擴散”的精神。這表明拜登政府延續了倚重核武器的老路,甚至希望通過發展小當量核武器來提高核武器的實戰性、確保核威懾的可靠性,實現核武器威懾作用最大化。
核武器綜合體現代化:保持彈性、恢復生產能力。為與核力量現代化配套,《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具有彈性和適應性的核安全綜合體”,尤其是要加強對“生產基礎設施、科學技術和工業基礎現代化”等核安全綜合體的投資,“確保其能夠及時應對安全環境的變化或美國核力量發展中出現的挑戰”。拜登政府明確要求國家核安全管理局“制定基于生產的恢復計劃,確保核安全綜合體能具備全面生產能力”,允許“定期和及時納入先進技術,以提高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隨著核武庫壽命逐步到期和新技術被引入核武器,美國核力量現代化已進入“移花接木”的關鍵時期。
钚彈芯的生產是核武器綜合體的核心任務之一。目前,美國計劃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和薩凡納河場地兩個地點建設钚彈芯生產廠,使兩個廠互為備份,計劃“2030年前達到每年至少生產80枚新钚彈芯的能力”。

核主導作戰環境
核試驗態度:保持開放、發展能力。《報告》表示“美國維持一個核爆炸試驗準備計劃,以應對技術不確定情況。美國不打算也不希望恢復核爆炸試驗。只有在總統明確指示下才會恢復核試驗。”這一說法與特朗普政府“美國除非是為了保證美國核武器庫的安全與有效性,否則不會恢復核爆炸實驗”如出一轍,也與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美國將不再進行核試驗”的承諾有天淵之別。
美國的確一直保持著在24個月內恢復全面核試驗的能力。從《報告》看,美國是否恢復核試驗主要取決于美國核力量現代化過程中是否會遇到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而隨著美國钚彈芯生產能力的恢復和擴大,其設計可能會與經過傳統核試驗檢驗的設計有較大差異,這些都增大了美國恢復核試驗的可能。
核與非核武器的關系:核常結合一體化威懾。新版《報告》貫徹了美《國家安全戰略》中“一體化威懾”的要求,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正致力于通過包括網絡、太空、信息和先進常規打擊能力在內更廣泛的軍事能力來增強其日益增長的核力量”,因此美國需要通過一體化威懾實現“聯合部隊以互補的方式整合核與非核能力,利用多域部隊的獨特能力,在可信的核威懾力量的支持下實現一系列威懾方案”,保證“聯合部隊能夠在化學、生物、放射性和核污染的環境中作戰并取得勝利。”
盡管多年來美國一直努力將核能力和常規能力整合到戰略威懾規劃中,但《報告》試圖進一步深化這種整合,使美國的軍事威懾更加靈活,還可以使美國的盟國和伙伴更深入整合到美國的軍事行動中。不過戰略威懾中更深層次的“核常一體化”容易模糊核戰爭和常規戰爭間的界限,使美國在常規作戰中增加可能動用核武器的信號,達到核脅迫的目的。
延伸核威懾:強化地區存在、核武前沿部署。《報告》認為美國“向盟友和伙伴提供可信的延伸核威懾是美國家安全和國防戰略的核心”。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都提出要美國建立一個最強大、最廣泛的國家聯盟和關系網絡,而“延伸核威懾是這個網絡的基礎”,也是“區域安全架構的支柱”,同時,公然推出美國在歐洲和印太部署戰略力量的詳細計劃。
對于歐洲,《報告》承認北約是一個核聯盟,美國致力于在歐洲實現核武器和運載系統現代化和維持前沿部署,包括部署新的F-35A聯合攻擊機和B61-12核炸彈。
對印太地區,《報告》要求美國在印太地區部署強大和可信的核威懾,以應對中國的核能力和導彈發展,以及來自朝鮮和俄羅斯的持續威脅。《報告》強調了與該地區盟國的合作,“重要目標是確定三邊(美、日、韓)或四邊(美、日、韓、澳)信息共享和對話”,并就繼續擴大威懾進行磋商,包括向該地區前沿部署戰略轟炸機、核常兩用戰斗機和其他核武器的能力。近年來,日本也拋出了與美國進行“核共享”的主張,并表示強烈支持新版美《核態勢評估報告》。
美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變化

美國地下核試驗準備
將國際態勢定位為“決定性的十年”。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拜登政府認為美國正處于“決定性的十年”。新版《報告》與《國家安全戰略》一脈相承,認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和潛在對手正在大量投資于新的核武器。到21世紀30年代,美國將首次需要威懾兩個主要核大國,這兩個大國都將部署現代化、多樣化的全球和地區核力量。”這種提法可謂比特朗普政府所宣稱的“美國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更加多樣化和先進的核威脅環境”更為明確。而且《報告》宣稱美國“將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核武器來應對這一風險”。
在美國所設想的“三極世界”中,由于害怕“漁翁得利”,各方誤判可能性增大且戰略決策必然復雜化,美國實現核威懾和核保證都將更加艱難。
對中國威脅提升,進行“明火執仗”核訛詐。《報告》指責中國正在對核力量進行雄心勃勃地擴張、現代化和多樣化改造,將建立一套新的“三位一體”核力量,并在2030年擁有至少1000枚彈頭。未來,中國“可以在危機或沖突之前和期間擁有更多核作戰選項,利用核武器達到核脅迫目的,甚至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伙伴進行軍事挑釁”。
《報告》明確表示將利用“W76-2低當量潛射彈道導彈彈頭、戰略轟炸機、核常兩用戰斗機和空射巡航導彈”等核力量反制中國的核威懾,以免中國“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使用核武器獲得優勢”。

美國核武庫發展里程碑

美國內華達試驗場地面彈坑
《報告》還表示:盡管中國不愿參與,但美國有必要與中國就一系列戰略問題進行接觸,重點是在軍事上消除沖突與通信危機、信息共享、保持克制、減少風險、加強新興技術和核軍備控制等。如果說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從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誠懇到特朗普政府的傲慢和指責已經算是巨大的倒退,那拜登政府在《報告》中將對抗中國的核力量明火執仗地“擺到桌面上”的行為更是走上了對中國進行核訛詐的歧途。
視俄羅斯為競爭對手。《報告》對俄羅斯的核力量發展進行了嚴厲的指責,特別是圍繞其入侵烏克蘭的行為,稱俄羅斯將核武器作為“對鄰國進行無理侵略的擋箭牌”。《報告》認為俄繼續在其戰略中強調核武器的作用,使其核力量現代化和擴大,并“使美國本土、盟國和伙伴處于危險之中。”
《報告》明確表示:美國“不會允許俄羅斯或任何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來實現其目標”,將利用“配備B61-12炸彈的F-35A核常兩用戰斗機;W76-2彈頭;以及遠程防區外導彈等武器”應對俄羅斯多樣化的核力量,避免俄羅斯“發動針對北約的常規戰爭和考慮在此類沖突中使用非戰略核武器”。
對朝繼續施壓、防止伊朗擁核。對于朝鮮,拜登政府將延續持續施壓的政策。《報告》稱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持續和不斷增長的危險”,并明確指出“朝鮮對美國或其盟國和伙伴的任何核攻擊都是不可接受的,將導致該政權的終結”,赤裸裸的威脅躍然紙上。
對于伊朗,《報告》認為“伊朗目前并不擁有核武器,而且美國當前也認為它并不追求核武器”,但對伊朗正在采取的、此前受《伊核協議》限制的動作表示關切。《報告》重申美國將與盟國合作,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

演習中試射民兵-3導彈
在軍控與裁軍上,考慮《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后續行動。由于軍控和核裁軍一直是美國合法探析其他有核國家核能力和打擊“核門檻”國家的有力武器,因此美國政府歷來對此態度積極,拜登政府這次也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表態。
《報告》承認僅靠威懾不能減少核危險,并重申了美國對軍控、減少風險和防核擴散的承諾,并將2026年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后續行動列為最高優先級。但俄羅斯曾在2021年延期《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時明確表示,除非美國接受對其導彈防御系統的限制,否則它不會進一步削減其戰略武器庫。
《報告》重申了美國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和《裂變材料禁產條約》的承諾,但并未像奧巴馬政府一般許諾“尋求《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獲批”。《報告》還對《禁止核武器條約》持否定態度,指出美國并不“認為《禁止核武器條約》是解決導致各國保留或尋求核武器的基本安全沖突的有效工具。”
取消新導彈研發、退役B83-1核炸彈。相較于特朗普政府,新版《報告》對美國核武庫規劃最主要的變化僅體現在取消了“未始即終”的海基核巡航導彈研發,并退役“行將就木”的B83-1核炸彈。
海基核巡航導彈研發計劃由特朗普政府倡議啟動,其目的是在亞洲和其他地方保持核存在,而不必要求盟友托管核武器,預計成本300多億美元。目前看來,該計劃甚至還沒有開始認真研發,因此該計劃還不是一種真正的核能力。
B83-1核炸彈是美國當前核武庫中當量最大的核武器,也是美國現存僅有的百萬噸級核武器。拜登政府認為B83-1炸彈的能力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且隨著壽命增加維護成本也在上升,因此決定將其退役,但沒有提供具體的時間表。后續,美國計劃用B61-12核炸彈替換B83-1核炸彈。當前B61-12延壽已進入全面生產階段,且原定于2023年春季交付的第一批B61-12炸彈已提前到2022年12月交付,加快了在歐洲部署B61-12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認為隨著B83-1炸彈退役,為了應對堅硬和深埋目標,美國將在近期內利用現有的能力增強對這種目標的打擊,或暗示美將發展一種新武器。
結 語
雖然美新版《報告》承認“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但拜登政府的實際做法卻與之南轅北轍,繼續大力推動美國核武器現代化,力圖保持“先發制人核打擊政策”的同時降低核武器使用門檻。可以說新版《報告》只是對美國的核武器政策進行了“細枝末節”的調整,“以核謀霸”的核心思維沒有任何改變。更嚴重的是,美國把這種冷戰思維加倍投射到中美關系上,對中國的核訛詐已“圖窮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