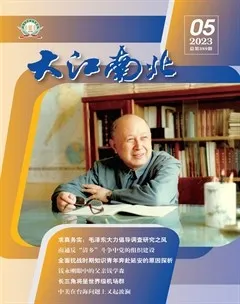錢永剛眼中的錢學森——一位既合格又不合格的父親
陳怡
一位盛名之下仍有遺憾的科學家
“在我眼中,錢學森不是一位合格的父親。他給我的教誨太少了!我上學他基本不管,尤其是我上初中的時候,物理老師水平不怎么樣,講課常常講不清楚。那時我別的功課都是5分,唯獨物理有點兒摸不著門兒,學起來費勁。后來我就和我爸開玩笑說:‘您這么大的一個科學家,那時要是能稍微向我播撒一點兒愛心,給我點撥點撥提示提示,那么今天我的本事可能就會大一點兒。但在我心目中,錢學森又是一位合格的父親。因為他教會了我許多做人的道理,尤其是讓我知道了,一個有作為、成大器、能夠為國家作出大貢獻的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舍。”
高級工程師、錢學森之子錢永剛日前接受了筆者的采訪,深情講述了父親錢學森一些鮮為人知的側面。
錢永剛說,中國航天事業初創時,除了錢學森一人知道火箭、導彈是怎么回事外,從全國調來的幾十位教授和100多名大學生都不了解,連火箭、導彈的樣子都沒見過。所以,當時錢學森即使想要找一個助手也找不著。成年后的錢永剛理解了,在那種情況下,錢學森不得不舍棄對自己兒女的教育,才能保證我國航天事業的順利發展。父親的這一精神特質對錢永剛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他深刻理解了“舍”、“得”之間的辯證關系——“只有勇于舍,才能保證得”。在這個意義上,他評價自己的父親“既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又是一個合格的父親”。
人民的滿意,是科技工作者最高的獎賞
在“舍”和“得”之間,錢學森的取舍標準是什么呢?《錢學森說》一書里記錄了錢老本人的一段話,揭示了他心底的指向:“我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后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的獎賞。”這是錢學森在得到美國的一個重大獎項后,回應別人祝賀他“得到了美國人的認可”時說的話。也正因此,他一生堅持加州理工學院的精神傳統,不管別人怎么看,只要自己認準的事,就堅持到底,如他自己所說——“事理看破膽氣壯”。
在得到黨和人民給予的高度認可及獎勵的同時,一種只有家人才會感受到的巨大孤獨感也伴隨了錢學森的晚年。在錢永剛的回憶中,“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這幾句中國古人的詞正是錢學森晚年心境的寫照:他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自身不斷進步,卻發現和自己談得來的朋友越來越少。早年經常到他家看望他、聊天甚至吃飯的朋友,到了錢學森晚年的時候,再提出去看望他時,基本都遭到了婉拒。因為錢學森覺得老朋友已經談不到一塊兒,共同語言越來越少,真正能夠理解他思想的人越來越少了。
“不過他在學術晚年的各個階段,總還是能找到一些談得來的人,而且很多是后來者。他的朋友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不是永久的。他在那個階段思考什么問題,和他有思想共鳴的人才是他的朋友。有時候他遇上一個談得來的年輕人,會高興好幾天。他是挑選朋友的。”錢永剛說。
被忽視的錢學森思想,可能對中國科技發展產生重大推動
孤獨者總有難以被理解的思想,當筆者問及錢學森最被忽視的思想是什么時,錢永剛講述了一段往事。1954年,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發表后,引起轟動。一位華裔科學家事后評論這件事,說錢學森的這本書出版后,美國人3年沒有讀懂。“美國是一個科技發達的國家,錢學森寫出來的書美國人沒讀懂,不是說錢學森的英文不行,而是因為錢學森表達的是一種全新的思維、一種全新的研究科學的方法。”錢永剛解釋說,“過去絕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都是探索如何通過改變物質的結構來改進和提升物質的特性、改進物質的性能和效率。物理、化學,都是研究這方面的;包括生物,通過雜交產生的新物種,其物質結構和雜交前是不同的。但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不談物質結構的變化,而是講如何在不改變物質組成結構的情況下,通過調整相關系統之間的關系,以及物質和環境之間的關系,來改變和提升物質的特性。”在錢永剛看來,錢學森思想中,外國人一下子沒讀懂的,正是這一點。錢學森其實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且鮮明的觀點——可以利用運行不那么可靠的元器件,組成可靠運行的系統。這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在《工程控制論》里只有一句話輕描淡寫地帶過。即便如此,明白的人已經可以明白。這為我國科技的發展,提出了一種嶄新的研究思路。
錢永剛記得,錢學森回國以后,在被詢問中國是否有可能造出自己的導彈時,他的答復非常肯定。當時有很多人不明白錢學森為什么敢這么肯定,香港的報紙聽說這個消息以后,寫道:錢學森在美國是一個受人尊重的科學家,但回國以后學壞了,學會了拍馬屁、說共產黨愛聽的話了。中國要造導彈,錢學森說中國人可以造,其實根本就不可能。當時,香港媒體認為錢學森是沒有本事為中國造出導彈的,可事實證明,錢學森和他的團隊經過艱苦的努力,造出了中國的導彈!這個過程中,錢學森正是充分運用了他那個許多人看不懂的觀點。
“錢學森晚年的學術思想,也是順著這個方向走的。你看錢學森晚年的學術著作,會覺得很好讀懂——里面沒有數學,我相信多數中國人看得懂。為什么?因為錢學森把他自己的這個思想——通過改善、調整事物之間的關系來制造新的物質——延伸到了他晚年關于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生命科學、地理科學、軍事科學、行為科學、建筑科學的思想中。”錢永剛說。他不無遺憾地指出,錢學森的這一思想不僅當時的美國人沒讀懂,錢學森的眾多中國同行到今天依然沒讀懂。“而這個沒有被讀懂的錢學森思想,恰恰是將來會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重大推動作用的。”
對“錢學森之問”,錢學森自有答案
錢永剛記憶中的父親晚年雖然孤獨,但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依然通過電視、廣播、報紙了解社會發展的狀況,而且是個敢想敢說的人。比如,錢學森認為在當今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情況下,科學技術必將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很多人現在感受不到,或者不敏感,但錢學森直接預測共產主義在200年后,也就是23世紀時,會在世界上實現。這種“事理看破膽氣壯”的純粹,也體現在錢學森在2005年溫家寶總理看望他時,提出的著名“錢學森之問”。
事隔多年,錢永剛認為有必要向公眾澄清,“錢學森之問”的本義并非如后來安徽教授改編的那樣,而是“為什么我國的大學總是冒不出有獨特創新的人才”這個問題,其實錢學森自己心中已有答案,錢永剛后來在整理時將之表述為:“所有設定的項目都需要由人來完成。沒有人,項目定得再好也沒有用。而關于人的問題,現在國內沒有一所大學是按照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模式來辦的。北大清華的情況我也知道一些,它們也不成。”據說,后半部分在發表時被刪掉了。
從小在由科學家父親與音樂家母親組成的家庭里長大的錢永剛,在談及教育對人的影響時特別強調:錢學森的一生證明了一個人的科學素質固然得過硬,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素養,而這正是當下國內教育所忽視的。“很多人以‘有用或‘沒用來衡量孩子的學習,把文化或形象思維的培養當作‘沒用的。形象思維相關課程很難打分,很難說作文87分和92分的區別在哪里,但要‘升學,就非要打成90分以上,80多分就不夠。就是說,我們的教育整體上是重邏輯思維、輕形象思維的。而錢學森認為,一個有創新能力的人在求學期間所接受的教育,一定是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并重的,這樣,這個人將來才可能做出新東西。”錢永剛強調說,錢學森認為真正誘發創新的,是形象思維的積累。
(編輯 鄭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