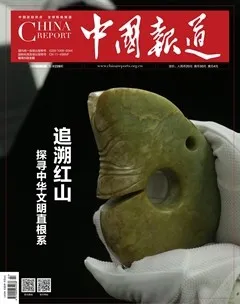“印太經濟框架”開始露出牙齒了嗎?
楊丹志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3日下午,日本東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國總統拜登、印度總理莫迪在東京都六本木的泉花園畫廊舉行“印太經濟框架”(簡稱IPEF)啟動儀式,其他初始成員國領導人或部長級官員通過視頻方式遠程參會。
“印太經濟框架”?(IPEF)第二次部長級會議5月28日在美國底特律閉幕。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會后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印太經濟框架”?14個成員國達成了使供應鏈更具韌性和安全性的協議。這是自2023年5月“印太經濟框架”?啟動一年來取得的首個具體成果,同時也是成員國在供應鏈方面達成的首個多邊協議。外界普遍認為,多邊協議的達成標志著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建設取得重要進展。
媒體也普遍關注到,關于“印太經濟框架”供應鏈的協議,拜登政府稱,是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出于遏制中國的需要
2022年5月23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東京宣布啟動一項新的亞太經濟伙伴關系——“印太經濟框架”。“印太經濟框架”共有13個初始成員國,分別是美國、澳大利亞、文萊、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13個成員國的GDP占全球40%。當地時間2022年5月26日,白宮網站宣布,斐濟成為第14個初始成員國,同時也是第一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太平洋島國。
2022年9月8日至9日,“印太經濟框架”在美國西部城市洛杉磯召開首次面對面的正式部長級會議。2023年5月的底特律部長會議,成員國在加強“印太經濟框架”建設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美國倡議并力推“印太經濟框架”,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推進2.0版“印太戰略”的需要。為了推進2.0版“印太戰略”,在安全領域,拜登政府積極推進美日韓安全合作,強化美日澳印四國機制(QUAD),建立美英澳三國機制(AUKUS),強化五眼聯盟成員間的合作,從而實現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的強化和升級。同時,美國還以幫助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加強海上能力建設為由強化與這些國家安全合作。但在經濟領域,美國對亞太地區,包括美國所強調的范圍更廣的印太地區的影響力相對不足。印太戰略作為美國力推的大戰略,不能只限于安全領域。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經濟框架”無疑可以使2.0版印太戰略補全經貿短板。
二是確立美國在區域經濟,特別是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領導權的需要。特朗普任內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給地區內國家造成美國從太平洋地區收縮,至少在多邊經濟合作中態度消極的印象,地區內一度出現“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說法。美國力推“印太經濟框架”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地區內國家在經濟方面對于美國的信心。美國也可以借此確立自己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領導地位。
從根本上講,美國推出“印太經濟框架”是出于遏制中國的需要。美國推行2.0版印太戰略,并在戰略設計中逐漸加大經濟議題的比重,一個主要目的就在于抵消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拜登政府之所以熱衷于構建區域合作新機制并確立美國對新機制的領導力,重要原因在于中國近年來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影響力日益提升,令美國相形見絀。美國需要通過建立“印太經濟框架”,提振印太國家對于美國在地區安全和區域經濟合作領域領導力的信心。
美國利益優先下的“排外圈子”
作為美國大力推動的區域合作新安排,“印太經濟框架”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是美國利益優先。自特朗普任內美國退出TPP之后,美國在亞太區域合作進程中的影響力逐漸弱化。拜登政府期待通過打造區域經濟合作新機制并掌控新創機制運行規則的制定權和主導權,確保美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權,進而維護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長久的機制霸權。與美國自身利益相比,疫情后地區經濟的復蘇和繁榮處于次要位置。
“印太經濟框架”側重4個關鍵支柱:互聯互通的經濟(貿易)、有韌性的經濟(供應鏈)、清潔的經濟(清潔能源)和公平的經濟(反腐敗)。任何一個支柱建設,都不能違背美國的意志,損害美國的利益。由于“印太經濟框架”所涉及的數字經濟、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和反腐在美國國內都較少有爭議,更容易被認可同時也無需國會批準。
其二是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凸顯。與亞太地區既有的區域合作機制相比,“印太經濟框架”摻雜了更多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意圖在新經濟領域構筑一個封閉、對抗性的供應鏈體系。缺少傳統意義上的自貿協定所包含的關稅減讓內容。既沒有給予成員國在自貿協定上的實際利益,不包括降低關稅或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談判,但是又想要制定在勞工、環境標準和貿易便利化方面的共同規則并迫使成員國共同遵守。

當地時間5月27日,“印太經濟框架”部長級會議在美國底特律召開,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發表講話。
其三是針對中國意圖明顯。防范、圍堵、遏制中國(特別是遏制中國擴大在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的政治意圖和戰略導向明顯。目前,美國和其他13個“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在確保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方面已經達成協議。所謂的確保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主要目的就在于使印太國家減少在此方面對中國的依賴,并為其提供一個中國之外的替代方案。從美國積極策劃推進“芯片聯盟”到此次達成“印太經濟框架”供應鏈協議,美國實則在策動與中國脫鏈脫鉤,構建“去中國化”的印太供應鏈同盟,維護封閉小圈子的利益,對中國則形成壁壘。國際貿易專家默卡里奧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為了抵制中國的所謂“重商主義擴張”,在“印太經濟框架”建設方面,美國必須用錢買來印太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合作。
從長遠看,“印太經濟框架”對地區經濟穩定起到消極破壞作用。在東亞乃至亞太區域,從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日韓合作、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中日韓分別與東盟的3個“10+1”合作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多個區域合作安排并存共舞。區域內多個國家是多個區域合作安排的成員。中國是多個區域合作機制的重要成員,也是確保這些機制運轉的重要驅動力。而“印太經濟框架”從一開始即將中國排除在外,實則是要“另起爐灶”打造美國主導的印太區域合作進程。隨著供應鏈協議等系列協議的簽署,域內國家與中國既有的合作關系不可能不因之受到沖擊和干擾,既有的區域合作機制也面臨弱化甚至解構風險。
此外,“印太經濟框架”各成員國達成的若干共識和簽署的協議,也會限制“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與外部之間的貿易流通和技術交流,加大“印太經濟框架”與其他貿易機制之間的鴻溝,實則制造新的經濟壁壘。從長遠看,極有可能導致經濟領域內的陣營對抗,加劇地區內部的分裂。
應當看到,從“印太經濟框架”(IPEF)創建伊始,成員國對這個新機制的質疑和不滿就一直存在。印度媒體指出,如果沒有對簽約國的市場準入條款,如何吸引足夠多的國家簽署“印太經濟框架”并作出意義重大的承諾?韓國前貿易部長呂漢豪也指出,傳統上多邊和雙邊貿易協定最重要的方面是高度的市場準入。印尼前貿易部長穆罕默德·魯特福認為,印尼已經將價值鏈提升至鋰電和電動設備,希望印尼的汽車能夠在美國行駛。實則表明印尼希望美國對印尼出口美國的汽車削減關稅。
“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基本一致批評在該機制運行中,缺乏美國對其他成員國的市場準入和關稅減讓。而如果沒有這兩方面的內容,美國與其他13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就存在巨大缺陷。目前,印度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是美國對印度商品的進口關稅的3倍,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也高于美國對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商品的進口關稅。“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總額比美國對這些國家商品的進口關稅總額高出47%。因此,美國不愿意再單方面放開市場。多個“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加入該機制,主要是想更順利地進入美國市場,而不是讓美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同時,這些國家也希望無需在與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中作出一邊倒的選擇。
在“印太經濟框架”底特律部長會議上,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強調了拜登政府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旨在使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最大化。戴的講話無視中小國家的利益,引起了中小國家的懷疑和不滿。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和工業部副部長劉鎮東說,他對美國的工人必須從貿易中受益的觀點表示同情。“但(這一政策)面臨的挑戰是這不能以犧牲我們(馬來西亞)的工人為代價”。
即使在美國國內,也有農業和工業團體抱怨“印太經濟框架”缺乏市場準入改善,認為這導致其在與其他區域貿易協定的競爭中處于劣勢。來自美國國內的不滿,也可能會影響其各項協議的落實。
中國如何應對“危險信號”?
隨著“印太經濟框架”底特律部長會議的召開,其機制化進程已經不可逆轉。未來中國可能面臨更多的風險和挑戰,需要做好應對準備。
一是要冷靜觀察,保持戰略定力。“印太經濟框架”畢竟在機制化建設、規范確立方面剛剛起步,是否會按照美國所期待的方向發展,仍然存在諸多變數。特別是,如果“印太經濟框架”不僅遲遲不能給美國之外的成員國提供實質性的、新的(美國)市場準入或者其他貿易特權,反而使其增加風險,錯失發展機遇,則上述國家作出重大承諾并予以兌現的動力就會不足。
例如,對大多數東盟國家而言,同時參與亞太自貿區和“印太經濟框架”本來并不相互抵觸,但當美國利用“印太經濟框架”在經濟、技術和外交政策方面對中國采取強硬措施時,作為“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的7個東盟國家實則難以采取觀望態度。因為一旦徹底選邊站隊倒向美國,必然會損及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業已成熟的經貿合作關系。因此,這些國家會審慎地作出選擇,避免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畢竟,中國是搬不走的鄰居,中國巨大的市場容量在現在和將來對東南亞諸國仍然充滿吸引力。因此,繼續打造中國—東盟關系鉆石十年,尋求與東盟的共同發展,有助于中國突破“印太經濟框架”的壁壘。
二是在復雜、困難條件下更要修煉內力。做好內循環,充分利用國內統一大市場,中國需要在半導體、芯片、數字經濟等領域加大資金、人力資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升級、做強中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同時,鼓勵和支持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
三是繼續推行開放的地區主義。現階段,中國需要繼續與包括“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開展經貿合作。同時,繼續推進RCEP框架內各項協定的具體落實,加強在金磚機制內合作,進一步推進中國—中亞、中國—拉美、中國—太平洋島國之間的合作,以此抵消、弱化“印太經濟框架”對中國的消極、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