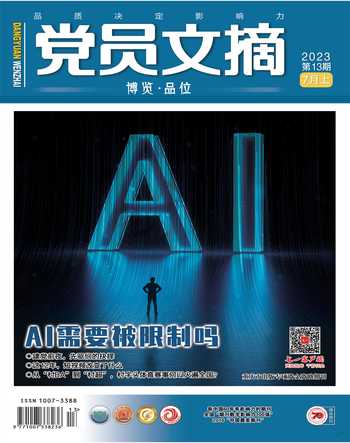七十余載“塵與土”:菲律賓軍事基地的“美國魅影”
吳健

2023年4月18日,美國防務博客網站報道,菲律賓最北端的巴丹群島,一艘菲軍登陸艇搶灘,將美軍M142火箭炮(音譯“海馬斯”)送上陸地,炮車在數分鐘內向30公里外的靶船打出6枚火箭彈后轉移。但靶船安然無恙,報靶的菲律賓士兵發出小聲哄笑。
這是美菲本年度“肩并肩”聯合軍事演習中的一幕,這一回創下兩國軍演投入兵力之最(共1.7萬余人),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親自觀摩,目睹了這尷尬一幕,但他依然與身旁的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卡爾森談笑風生。
2022年6月上任后,小馬科斯逆轉了前任杜特爾特“系統性瓦解菲美同盟”的做法,鼓吹依靠美國構建“最低限度可靠防御態勢”,最重要的內容除了組織聯合演習,便是開放更多基地給美軍。
“睡蓮”潛質
海馬斯“出糗”的巴丹群島,2004年首次被納入美菲“肩并肩”聯合軍事演習范疇,因位置太過敏感,雪藏到今年才再次“入圍”。
日本《防衛快信》雜志主筆中谷和義指出,“肩并肩”看似美菲例行演習,但在美國主導下,已成為其推行“一體化威懾”、裹挾地區國家選邊站隊的工具,“看看演習課目,就知道它瞄準誰”。
巴丹最北端距巴士海峽中心水道不過40公里,處在臺灣海峽周邊500海里(約900公里)半徑內,有充當美軍跳板的潛質。
巴丹面積雖小,卻控扼巴士、巴林塘海峽,監視從東海到南海的航線。它就像水生植物睡蓮,只需投入相對少的資金建立簡易飛機起降場和倉庫,就能成為美軍的戰力和介入通道備份,與諸如沖繩嘉手納等大型軍事基地互為補充,支持美軍快速應對危機事態。
而“睡蓮”只需要相對低廉的成本,意味著即使這樣的基地被菲律賓收回,比起當年美國被迫舍棄菲律賓克拉克、蘇比克這樣的大型基地,經濟上的損失也小許多。
福音?禍根?
1946年7月4日,美國在慶祝第171個獨立日之際,向世界“放出大招”——允許自己最富饒的殖民地菲律賓獨立。慶典上,美國參議員泰丁斯致辭:“這是彪炳史冊的最理想、最杰出的奇跡,是國際關系全新的范例。”當時的菲律賓總統羅哈斯的答謝卻很謹慎:“美國把我們抬舉得這么高,遠超我們能力所及。因為沒有強有力的權力,我們更需要‘世界公理的幫助。”
剝去漂亮的辭令,這番話至今都發人深省。中谷和義指出,長久以來,菲律賓只有“缺乏主權的獨立”,“強有力的權力”仍來自原宗主國。
“看一下菲律賓首屆政府名單就明白,總統羅哈斯是前駐菲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摯友,國防部部長康利克是西點軍校畢業生,80%的參議員為美國殖民政府工作過,而國家軍隊以美國豢養多年的雇傭兵為主體。”中谷和義說。
當然,光在菲律賓安插代理人是不夠的,美國還需要一副“霸權手套”——軍事基地。
1947年3月,羅哈斯與美國大使麥克納特簽署《軍事基地協定》,菲律賓同意美國免費使用22個海空軍基地(設施),期限99年,美國軍人享有治外法權。
冷戰時期,美軍在菲律賓實有固定設施不下40處,幾乎控制該國所有戰略地帶。然而,這并沒有給菲律賓帶來真正的安寧。
美軍的治外法權,讓菲律賓人深惡痛絕。經過多次談判,美菲于1966年達成協議,將1947年簽訂的《軍事基地協定》有效期縮短至1991年9月16日。1973年,美軍完全撤出越南,華盛頓在亞太實施戰略收縮,要求盟國分擔更多防務責任。
在此情形下,1979年,美菲談判確認,菲律賓對基地擁有主權,將美國軍事基地改稱菲律賓武裝部隊基地,基地內懸掛美菲兩國國旗,設立一名菲律賓司令官,作為基地名義上的最高首長。
1986年,伴隨奉行民族主義的阿基諾夫人執政,菲律賓國內要求美軍撤出的呼聲愈加強烈。此后,菲律賓在憲法中明確表示,《軍事基地協定》期滿后,任何外國軍事基地、軍隊或設施都不允許存在,除非就這一問題簽訂的條約得到菲律賓參議院2/3以上議員批準。
1991年,在此起彼伏的反抗美軍基地運動影響下,延長基地租約的議案在菲律賓參議院被否決,這標志著美國在菲律賓近一個世紀的駐軍史落下帷幕。
“軍事睡蓮”在泛濫
當1992年11月24日最后一批美軍離開菲律賓時,人們曾期待美菲將開啟不以軍事基地為核心的新關系,連蘇比克灣所屬的奧倫格波市也宣布將原基地變成自貿區,打造亞洲航運樞紐。
出人意料的是,菲律賓政府突然宣布自1993年1月1日起向美軍開放所有港口機場,涉及軍艦來訪、飛機過境、聯合演習等情況。
近年來,美國提出“分布式作戰”概念,菲律賓身處“第一島鏈”南端,其關鍵地理位置讓美國海軍無法割舍。但美軍不尋求在菲律賓建設永久性基地,而是在需要時進行補給、監視的“睡蓮小據點”的準入權。
耐人尋味的是,美菲軍事同盟正有序進入“美菲+”階段,即允許更多盟國使用菲律賓基地,目前菲律賓和日本正在磋商兩國《部隊訪問協定》,以便日本自衛隊員能像美國軍人一樣在菲律賓境內活動。
至于菲律賓能得到什么?菲律賓前空軍上校奧科爾在英國《簡氏國際防務評論》上說,那就是免費或廉價獲得“最低限度可靠防御態勢”。
別讓“兩個主角唱一臺戲”
除了“人為”激化菲律賓與鄰國在南海島嶼爭端,美國正試圖將盟友菲律賓引向別的地區熱點,與日本遙相呼應,在亞太方向制造緊張局面。
采訪過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英國《衛報》記者森夏恩·利肖科·德利昂指出,現實中的菲律賓,關于恩怨糾葛的美菲同盟,實際有兩套歷史敘事,一套來自上層,一套來自底層。前者由以富裕、西化、高知為特征的“民主派”社會精英構建,偏向強調美國“賜予”菲律賓獨立,構建民主政體和提供援助。而在底層的歷史敘事中,相比虛無縹緲的民主,人民更愿意知道誰能提供工作與面包。
展望未來,基于長久以來美國的霸權行徑,美菲戰略互信根基并不深厚。
美國《外交政策》曾援引菲總統小馬科斯當選時的承諾,菲律賓不應成為他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應獨立自主地制定外交政策。他還曾表示,當菲律賓處理與一個大國的關系時,貿然讓美國介入,等于“讓兩個主角唱一臺戲”,將注定失敗。當然,小馬科斯上述種種表態,目前只停留在口頭上,其未來對外政策,還有待觀察。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