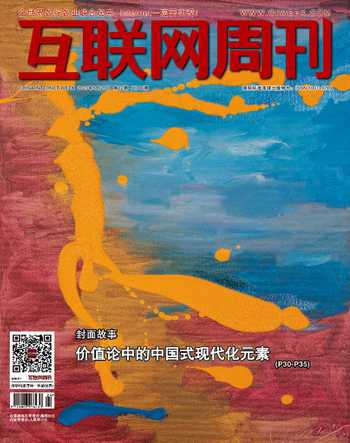價值論中的中國式現代化元素
姜奇平 于小麗
數字經濟學是信息時代的經濟學,其中包含了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轉變背景下的總的現代化范式轉變,我們把這種范式轉變概括為從西方式現代化范式向中國式現代化范式的轉變。前者是工業時代經濟學的文明范式,后者是信息時代經濟學的文明范式。我們此前在《經濟哲學的數字化與東方化》中進行過將文明范式具體化為經濟學范式后的東西方比較。下面進一步討論將經濟學范式具體化為價值論范式后,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元素,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它們是從哪里來的,要發展到哪里去。
總的觀點認為:經濟學價值論中的西方式現代化元素,主要是以利為中心,利在價值論中就是交換價值。以交換價值為中心,就是以錢為中心。而中國式現代化元素,則表現在義與利的統一上。義代表意義,是生產目的;利代表交換價值,是生產手段。經濟學價值論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轉向,反對的是為生產而生產,要求的是生產手段一定要符合生產目的。數字經濟中的“數字”包括數據和信息,就是用來表達意義的符號。數字經濟的西方化取向,表現在為技術而技術、為符號而符號,而中國式現代化取向中,數字經濟學的價值論旗幟鮮明地反對為符號而符號,主張以人為本,意義優先。當代世界的存在意義,就在于追求美好生活,而非人與人的各種戰爭。
一、從人的價值審視使用價值
(一) 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論的理論來源之一:中國古典經濟學價值論
1. 義利之辯:將意義價值置于交換價值之上
中國式現代化范式,要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首先要同中國古典經濟學中的優秀傳統結合。受西方影響,人們一般認為,中國不存在系統的經濟學。事實上,中國古典經濟學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八國聯軍反復折騰中國的過程中,才讓人們不自信,以為“不存在”。中國古典經濟學在價值論上具有完整的體系,這一體系的中軸主線就是義利之辯,即生產目的(義)的價值與生產手段(利)的價值之間的關系。中國古典經濟學中的各家各派,都把“生產手段要符合生產目的”作為價值論的核心取向。這一點與西方式現代化的經濟學價值論“唯利是圖”的取向正好相反。
利要合于義,猶手段需要契合于目的。管仲稱之為“宜”,這一點與孔子觀點相同。他說:“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義出于理,理因乎宜者也”(《管子·白心》)。宜,就是合目的性的存在如“利”“用”,要與目的性相符合。與西方經濟學相比,義不存在最大化的問題。因為最大最小都是過頭了,過猶不及。只有利才存在最大化的問題,比如效用。經濟系的學生一進課堂,聽到的就是最大化。相當于在舉行一個蒙目儀式,從此不問生產目的,做一個盲目的人。
從數字經濟是農業經濟的否定之否定,或者從隔代遺傳來講,數字化必然與東方化同源。中國古典經濟學中關于“用”的思想,固然是使用價值這一正題的主要內容,但從現代之后的角度看,儒學關于使用價值的經濟思想遠不止于此,還有關于意義價值這一生產目的內容,這是其超越魁奈的地方。這集中表現在義利之辯中。義利之辯是一個典型的價值論問題,問的是哪種價值更高,是義的價值更為優先,還是利的人更為優先。中國古代除了司馬遷等極少數人,絕大多數學者都以義為優先。而魁奈以使用價值這個正題,反對交換價值這個反題。
從現代性角度看義利之辯的傳統看法,以為義是指利他,利是指利己,因此義利之辯是利他利己之辯,以為儒家主張的是利他,實際這是一種錯覺。儒家對應利他的概念是善,而非義。實際上,義是指意義,利是指價值。因此從現代之后(如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義利之辯是意義(生產目的)與價值(生產手段)之辯。與現代性經濟相比,前現代性經濟學如中國古典經濟學,不是以價值論為起點,而是視價值(利)為手段論,將目的(義)作為價值論的前置邏輯,放在價值論的前面。
義利之辯,是中國古典經濟學頂層設計中的最上層框架,但這一點被長期誤解。中國古代經濟作為前現代經濟,與現代性經濟以利(價值)為體系之軸相比,實際是個“利—義”(價值—意義)雙軸體系。前者是一般等價體系,后者是“一般等價+非一般等價”體系。用這種邏輯進行梳理,中國古代經濟的邏輯就不再是不成系統,而是自成系統了。前現代(東方化)、后現代(數字化)的價值論,都屬于目的論系統,強調目的第一性、手段第二性;而現代性(西方化、工業化)價值論則屬于合目的論系統,強調手段第一性、目的第二性,而且總是把經濟目的視為經濟之外的所謂“倫理”問題,如道德情操問題,置于經濟學之外討論。
中國古典經濟學中的許多學派,都有成體系的“義—利”二元結構框架。它們是同源的,是從有易如伏羲易以來,自然形成的。儒學義利理論只是對這種實際運行的經濟體系的邏輯總結。
在孔子出生一百多年前,晉國大臣李克就說“夫義者,利之足也。”意思是,意義(義)是價值(利)這種手段要滿足的目的。晉國的這種思想非常普遍,后來傳到齊國,晏嬰說:“義,利之本也。”意思是,人是目的,錢是手段,意義是利益系統歸宗時,“以人為本”的本與宗。
管仲主張的“以義制利”說,成為一個系統化的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論框架。
管仲在談利之前,首先將義置于目的的高度,稱為“和”。《管子·五輔》說:“夫民必知義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調,和調乃能處安。”這里的“和調”,有社會分配均衡的意味。如果不講義,只講利,就無法達到廣義的均衡“和”,就不能“處安”,而始終處于手段與目的背離造成的波動之中。
管仲與儒家有一點相近,而與法家不同,在于強調“行之以仁義”(《管子·山至數》)。他說:“故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管子·白心》)。這里的儀,就是指義。
儒家的義利學說,是中國古典經濟學中最為系統的價值學說,主張意義先于價值。孔子這一體系,稱為義主利從論,這是趙靖《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對孔子經濟體系的定性。
說義指涉的是意義,而非利他,我們可以從《論語·里仁》原文來揣摩。孔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不可理解為這是在談利他,而是說把義放在最高層面來談論。無適、無莫,這是意義作為真值,符合還是不符合方面的特征,指既不過頭,又無不及,因此不存在最大化問題。君子的言行作為話語(能指),要符合仁這個真值(所指),能指對所指,既不能過頭,又不能不及,而要符合意義所在。關公“義薄云天”,也不是說他利他行善事,而是說他堅守初心,不計利害。而說一個人講義氣,也是說他在堅守意義與衡量得失之間,選擇前者,犧牲后者。
《論語·述而》中孔子還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作為不義的對比,“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是說價值上貧且賤,但一個樂字,是專用于意義的,是在說沒錢但快樂;而“富且貴”說的是價值上的充分,但一旦評價為不義,則在說意義缺失,對應有錢不快樂。
在這里,義都不可能是指利他,因為它的反義詞不義,是指無意義,而不是利己。孔子沒說過利己就是不義,否則子為父隱當如何講?
在宋明之前,義利與利他、利己之間的對應關系是不明顯的,并不一定義對應的是利他、利對應的是利己。以孔子和董仲舒為例。孔子在《里仁》中肯定富貴之欲,不能認為他主張利己,他觀點的重點是取之有道,即“以其道得之”,而不是利誰。董仲舒反對由公家“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漢書·食貨志》),則把公對應不義,認為公家與民爭利為不義,主張天下資源為民所用。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儒家的義,是在講利益的獲得方式是否正當,正當為義,不正當為不義,字面上是可以講通的,但正當不正當替換為有意義無意義,更加通順。正當不正當是指手段,有意義無意義是指目的。如果非要用正當解義,《論語·里仁》中孔子還說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并沒有說這個欲本身不正當。取之有道無道,才是正當不正當。然而,即使取得方式正當,難道就是義嗎?不一定,因為還有可能不仁。如果手段正當,但目的不仁,或目的是仁的,但手段不正當,就會產生悖論。例如,不義且仁,這可能嗎?不可能。所以,這里的“不義而富且貴”與“不仁而富且貴”是可以互換的。義就是當作意義來講的“仁”,當然“仁”還有別的含義。
現代性物極必反,造成了價值上的異化,所以要由以人為本的意義進行矯正。但對于前現代來說,這個命題也可能含有重農主義的意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落后”于現代性的。但在工業化完成之后,這一“落后”命題又可能螺旋式上升為先進命題。《論語》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可以重新解釋為:以人為本的人,是意義取向的;而以物為本的人,是金錢取向的。西方式現代化主要是“小人”的現代化,當然,“小人”比中世紀的神還是進了一步,而未來的中國式現代化要成為君子的現代化。
數字經濟實際就是一個隔代遺傳的義主利從的經濟體系。今天,義主利從的經濟體系,典型就是體驗經濟。體驗經濟在利上,是典型的高利潤經濟。它暗合了《大學》的一個奇異觀點,即“以義為利”。“做優”做的是利潤之優,恰恰來自意義的升值作用。這里的義,不是指正義(政治、社會角度的意義),而純指經濟上的意義,如能帶來“樂”這種體驗的意義。這種意義的財務含義,是“因為快樂,所以越貴越值”,與“有錢但不快樂”正好相反。
這樣一看,現代經濟學家對義主利從論的評價,就有可能被顛覆了。需要認真研究,其中哪些是可取的,哪些不可取。例如,前現代的義主利從,對利的抑制作用明顯,而后現代的義主利從,反而要求獲利更多且優。例如,數字經濟的穩定均衡點處于比工業經濟的一般均衡點更高的位置,具有更高附加值,這是歷史階段不同,經過現代化與沒有經過現代化所造成的。而且,儒家說的義是仁義,是在強調共同體的意義,這與數字經濟的生態文明背景也是一脈相通的。
2.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在以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的問題上,都不約而同具有以人為本的取向,這與經濟學的工業化、西方化傳統基本相反。
以人為本表現為以民為本,而非以商為本。這里的民本,表現在民用、民欲上,值得注意的是,將使用價值以及消費擺到了逐利之上的生產目的的高度。這里的使用、消費,都屬于高于交換價值的價值所在。
《尚書》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說法。這里的“天”,代表至高無上的價值判斷,在“利”這一工具理性之上,處在生產目的的位置之上。
什么是民之所欲呢?欲有雅俗之分。物質欲望是俗,禮義廉恥是雅。前者代表使用價值中低于交換價值那個方面,后者代表使用價值高于交換價值的方面。管仲把二者結合起來,構造出中國式經濟學的元價值框架。《管子·牧民》中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是中國經濟學的總綱。在“用—利—義”三元價值中,倉廩實、衣食足說的是“用”,即使用價值;而禮節、榮辱說的是“義”,即意義價值,如禮義廉恥。與工業化、西方化經濟學價值論基本結構的區別一目了然,它空過了“利”(交換價值)。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論倒不是說要空過利,相反還反對空過利,而是要強調在“利”這個二樓之上,還有“義”這個三樓存在。
管仲一方面主張“與俗同好惡”,說“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俗欲對應的是使用價值,即所要滿足的需求。工業化、西方化的經濟學中的效用概念,也是建立在物欲水平上的,但比管仲思想有所不如的是,西方經濟學為了突出“利”的主導作用,把需求、消費這些俗欲都限制在物欲水平,并進一步把包含生產目的的高級需求如精神需求,都還原到物欲水平;而管仲并沒有把使用價值限制于人的低級需求,而提出了禮節、榮辱這類屬于自我實現的目的層面的價值。這就擺正了“利”在總體框架中的位置。
凱恩斯有效需求概念已異化為指鹿為馬,把不是最終需求的東西當作需求,把投資說成是需求,把最終需求異化為中間需求,而把人本身真實的、最終的需求當作不重要的東西拋棄掉。這反映了現代性經濟學的通病,把“義”僅僅理解為經濟學之外的倫理問題,最多算是經濟倫理問題。
而在管仲和儒家的價值論框架中,不存在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兩分,表面上好像是倫理術語的義、禮,實際只是經濟本身的目的性而已,與倫理本身并沒有什么關系,如同胡塞爾堅持認為體驗與心理學無關,而就是哲學本身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經濟倫理”這個概念是不科學的,應改為“中國古代經濟目的”。只有當人失去經濟目的時,才會把經濟目的降格表述為倫理,意在推出經濟學之外,讓別的學科來管,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工業化、西方化的價值論的基本結構是“用利之辨”,由用(使用價值)與利(交換價值)構成的。對價值論基本框架進行一番東西方比較就會發現,工業化、西方化的“用—利”(以利為本)二元結構,缺失了一個重要環節,即價值的第三重性,代表價值的目的屬性的一環。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處在工業化、西方化的歷史階段,其通用特征是以現代性為核心范式,但中國式現代化將第一次在比現代性更高的現代化水平上,弘揚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新價值觀。不能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中用使用價值與價值概括商品二重性,就否認存在第三重價值。因為《資本論》分析的是工業化,具體到工業資本主義這種工業化,這種分析可以覆蓋以工業化為主的社會主義經濟,但對數字化與社會主義乃至更高發展階段的組合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更加適合。中國式現代化從中國古代“隔代遺傳”地繼承“義”這一價值維度,是構建克服勞動異化的頂層價值論框架的需要。需要完整準確理解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論,聯系馬克思所說工業資本主義結束后的自由勞動中,尋找第三重價值(義)的根據,即自由而全面發展。這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
3. 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在中國古典經濟學思想中,有將使用價值與人的價值并稱的說法,如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稱為兩全之美。《尚書·大禹謨》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就是物盡其用之意。《三國志·卷二十六》有“豫位止小州,招終于郡守,未盡其用也”,直接提及“盡其用”。西漢劉安《淮南子·兵略訓》“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有發揮人的潛力的意思。
《易經·系辭下》有“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有人將這里的“使民不倦”解釋為“保證民眾不會勞苦厭煩”,不通。因為《易經》上另有“互通有無,使民不倦”,是同一個意思。不能認為“互通有無”或“通其變”是為了“保證民眾不會勞苦厭煩”。“不倦”實際的意思是有為,不使無所事事,帶有人盡其力之意,指的是農商分工,使人各自專注于自己所擅長的事,不致因為滿足自用后就不再生產。《鹽鐵論》就是這樣解的,“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如果都自給自足,夠用后就不再產出,則別的行業的人就不夠用。《蘇軾集·補遺》中,專門有一篇《通其變使民不倦賦》,講得更清楚。
另外,中國古典經濟學說的“盡人之力”,與泰勒制對工人的壓榨是不同取向的。中國古典經濟學還沒有勞動與勞動力之分,從“百工盡其巧”(《管子·山至數》)來看,這個“巧”也在力的范圍,說明指的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本身,是一種對人的“使用”。而泰勒制對工人的壓榨,是針對勞動力而抑制勞動的,是不盡其巧、不盡其才,而僅把勞動者當機器使用,限制勞動者自我實現潛力發揮的。
在數字化中,“使用”(access)一詞,有與中國古典經濟學中人盡其才、隔代遺傳相同之處,開始從強調物用的使用價值,轉向強調人的價值的參與。而把二者統一在同一個概念之下,是一種兼顧物用與人才的“兩全之美”。其中的“使用”,也有相對于人的盡用之意。
(二)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論的理論來源之二:“使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
建立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論新范式的過程,有前后兩個視角。如果說中國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論,是從前天看昨天,其優點是沒有忘記生產目的,在經濟學中給了生產目的一個顯要的位置;缺點是比較嚴重地忽視了生產手段,形成了對現代市場經濟及工業化的阻力。另一個視角,是從明天看昨天,從西方后現代理論即后于工業化這個“現代”的理論的角度,將交換價值的“皇冠”摘掉,令其從屬于本質上是目的價值的更高的使用價值。更高的使用價值,把人的最終需求包括潛能釋放當作生產的目的,矯治有錢不快樂。
使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使抽象價值從屬于具體價值,作為學派一級成體系的思想,首推生態馬克思主義,這是其價值論的綱領性主張。生態馬克思主義具有“后”學派的特征,這個“后”就是在工業化之后。數字化正好就位于工業化之后,它們在價值論上具有完全相同的指向。
數字經濟學關于第三重價值即目的性價值的觀點,直接師承這種理論。數字經濟學提出的使用權中心論,其價值論前提就是“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抽象價值從屬于具體價值”。
詹姆斯·奧康納系統地提出“使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使抽象勞動從屬于具體勞動”這一價值論綱領,并以此作為“生態社會主義”這個術語的定義,指向的理論和實踐是“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潤來組織生產”[1]。
為了強調人是目的,尤其自主的勞動者是目的這一點,需要把使用價值的位置從“只扮演第二號的角色”提高上來,“使用價值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一定是與交換價值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的”[2]。事實上,使用價值的地位應比交換價值更高,“我們的研究重點就必須要從事物的交換價值的維度轉向其使用價值的維度。我們越是在理論上接近使用價值,在實踐中,我們就越能夠接近真實的實踐語境以及真實的、活生生的人們”[2]。
喬爾·克沃爾也提出“使用價值的解放”這樣的系統思路,“要將使用價值從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3]。他認為社會主義“不得不去打破資本和交換價值對我們的束縛,從而釋放使用價值”[4],生態社會主義社會要實現勞動力的解放,就要打破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邏輯,強調使用價值[3]。他還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場追求使用價值的斗爭,實現使用價值才能實現內在價值[3] ,“生態社會主義是為了使用價值,或者通過已經實現的使用價值,來為內在價值而斗爭的存在。”[5])。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中,使用價值獨立于交換價值而存在,使用價值是為了滿足而非控制人類和自然的需求而存在,是對內在價值的追求[3]。這里說的內在價值,指的是意義的價值,或者說生產目的的價值。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附錄一“傳統社會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的比較與對照”表中,對傳統社會主義(相當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生態社會主義(相當于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對具體價值與具體勞動態度進行對比,實際是在對比從資本主義沿襲某種人與自然不和諧、人與人不和諧的工業化傳統的社會主義,與真正體現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本質的社會主義,在價值取向上的區別。他把希望寄托在生態社會主義上,認為它才代表著克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社會危機)與生態危機(自然危機)的希望。這對于社會主義完成工業化之后如何轉移經濟重點,有積極的啟示。
在比較中給人印象深刻,對數字經濟學建立自己的價值論富于啟發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傳統社會主義關注對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定量批判,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使用價值的定性批判。
數字經濟學將通過平衡定量(Q)與定性(N)的整體框架,在均衡水平全面回應這一趨勢。如果說交換價值的計量單位是數量(Q)的話,使用價值的獨立計量單位將是品種(N)。數字經濟學沿著1977年D-S模型將品種內生進均衡與最優框架,將使用價值以質的方式全面體現在廣義均衡理論中。
二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在抽象勞動上的經濟剝削的關注,轉向生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在具體勞動上的生態剝削。
如果認為工資代表生存權,經濟剝削主要是對發展權的剝奪,那么生態剝削主要是對自我實現權利的剝奪。做出這種剝奪的,不是個人,而是生產方式。也就是說,除了改變生產方式,僅靠生產關系調整,無法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根據數字經濟學制度理論,生態剝削代表的主要是對勞動自主性、創造性的剝奪,以及對勞動自主與創造活動的分成權利的剝奪。這是通過任何二次分配福利都無法彌補的損失,只有通過以使用權為中心重建產權制度才有望實現。
三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對勞動力使用價值創造剩余價值的關注,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對勞動力使用價值“具有某些特定種類的具體勞動能力”的關注。
從數字經濟角度理解,具有差異化、多樣性特征的創新、創造能力,就屬于這樣的特定種類的能力。這種能力通過商品化、資本化,固然能夠轉化為剩余價值,但作為使用價值創造剩余產品的能力同樣不容忽視。例如,通過個人知識與技能,打造出令人回味無窮的工藝品,可以在成交之后,帶來與錢無關而只與快樂有關的體驗余味與創作喜悅,這些都不在剩余價值之內,卻是附加的價值。
四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對貨幣資本的使用價值生產利潤形式的交換價值的關注,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對貨幣“資本”的使用價值“具有生產使用價值的功能”的關注。
對數字經濟來說,貨幣“資本”不再是資本的交換價值,而成為由M2置換的“資產”,作為資產的使用價值繼續生產使用價值,并帶來增值的使用價值,這與貨幣資本的增值從傳統經濟中二者現值相等,變為在數字經濟中現值不等。這是由通用性資產特性,以及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決定的。這決定了數字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將發生以使用價值為中心的變化。凱恩斯式的資本理論有可能讓位給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后者更強調資本使用價值功能的同方向理論。
五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對經濟貧困的關注,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對生態貧困的關注。
在奧康納的對照表里,經濟貧困與生態貧困的對比出現了兩次,第一次談國際比較,第二次談國內比較,但原理是一樣的。經濟貧困容易理解,就是以貨幣衡量的貧困。而生態貧困,則更多指貨幣標準以外的貧困,包括機會不平等、文化與精神的貧困、社會資本的缺失,乃至自然生態中的利益損失等等。
數字經濟學最關心的生態貧困,是“有錢不快樂”這種綜合現象背后反映的質量型貧困。通過強調更高的具體價值與使用價值,探索包容性參與以及多樣化紅利對改變這種貧困的影響。
六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對生產資料國有化的關注,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對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關注。
只有數字經濟可以把這個問題從可以理解變為可以解決。因為一旦使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必然的推論將是在對應權利上使所有權從屬于使用權,從而將全民所有轉化為全民所用,即所謂平等使用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
七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對生產資料國有化以交換價值形式進行再分配的關注,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對生產資料社會化后使用價值的再分配標準的關注,包括前者對需求滿足的商品形式的關注,發展到后者對需求滿足的社會形式的關注。
這同樣是一個只有在數字經濟條件下才可以解決的問題。由于不能由使用價值主導,進而不能以使用權為中心來主導,再分配只能在生產資料與生產過程等方面之外的結果分配環節進行,即使再分配可以使結果顯得公平,但無法彌補使名義上的大多數所有者被排除在創造性活動之外而無法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一缺憾。數字經濟的解法,將是通過生產資料的有償共享,基于社會化后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的分配標準,來實現機會公平。這個標準的核心是有多少人可以分享生產資料使用權,從而降低創造財富的機會門檻。
數字經濟正好也對需求滿足給出新解,就是將生產性需求與非生產性需求,在生態化的市場經濟中盡可能地統一起來。這里數字經濟學與生態經濟學第一次有了不一致的地方。多數生態經濟學家鑒于工業資本主義將文化產業嚴重物化,而認為文化、娛樂、精神等需求應該是非市場化滿足的。而數字經濟學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市場機制到底能不能實現從價值優先向意義優先的轉變,或實現從抽象價值優先向更高的具體價值優先的方向演進。我們贊同萊斯關于需求多樣化的主張,但不贊成他將符號消費等同于虛假消費的看法。
八是從傳統社會主義“輕視具體勞動”,發展到生態社會主義“重視具體勞動”。
數字經濟學無疑會非常重視具體勞動,而且是從自主人假設出發來重新看待具體勞動。這就要求把勞動力理解為勞動者,補上其中工資與剩余分成這一差值。勞動的使用創造剩余價值,具體的勞動也創造具體的剩余使用價值。后者屬于前面所說的具體交換價值的范圍。關鍵是勞動者對分享其中的剩余,具有積極的權利。
九是從傳統社會主義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難以取得平衡,轉向生態社會主義上下協同,把官僚機構大眾化。
工業經濟在組織上的特點是采用委托代理結構,容易膨脹中間人,而激化國家與公民關系。民眾對官僚機構的不信任,通常通過民粹主義這種相反機制,發泄其不滿。數字經濟在實現組織生態化過程中,解決上下協同的思路,是實現去中間人化,并形成使勞動者P2P合作的生態結構。這有利于把民粹主義的破壞性力量,轉變為恢復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
十是從傳統社會主義建設基于交換價值計量的GDP導向的增長,轉向生態社會主義對土地使用、具體勞動、使用價值進行重新定義。
社會主義在工業化中繼承了工業資本主義的最大遺產,就是GDP系統。這一系統使社會主義在經濟增長中的表現,越來越像資本主義。但GDP本身卻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也可以說,自從《國富論》將笛卡爾理性這一哲學概念轉化為交換價值這個經濟學術語,從而明確了工業經濟的中心思想之后,一切都大局已定。
傳統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要從基于交換價值計量的GDP導向的增長中轉向高質量發展軌道,是由工業文明由數字文明(生態文明)接替這種歷史的新陳代謝機制決定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只是明智地指出了兩種不同文明間價值坐標上的分殊之點。
對具體勞動、使用價值進行重新定義,不僅是生態社會主義的要求,也是數字經濟發展內在的必然要求。數字經濟學以自己的方式如經濟計量的方式,用品種概念對具體勞動、使用價值進行了均衡水平的重新定義。在目前的各種學說中,只與生態馬克思主義吻合。
當然,奧康納談的是理想化中的社會主義,并沒有考慮在數字化、生態化過程中,真實世界中面臨資本主義政治競爭、文化競爭、經濟競爭、軍備競爭、科技競爭的現實壓力條件下,社會主義主權國家在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選擇方面受到限制這一點。盡管如此,中國既然明確選擇了生態文明與數字文明之路,從長遠發展計,確實需要認真考慮如何與西方國家相區別,走出一條不同道路的問題。
何萍針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建立以使用價值、消費為主線的歷史唯物主義范疇”“修改原有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評價認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提出異化消費、生態危機、虛假需求等概念,對社會的消費結構及其與生產結構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闡發使用價值、消費在當代人們生活中的主導作用,豐富和更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內容與結構[6]。
我們同意吳寧的評價,“奧康納的關于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抽象勞動以及具體勞動的命題,是馬克思主義商品二重性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的理論,在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市場成為社會主義資源配置形式的時代的一種發展。”
對儒學價值論與生態馬克思主義價值論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他們都一方面強調夠用就行,另一方面強調有意義的滿足。這不是偶然的,這是歷史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在起作用。二者對生產目的的強調,一個出現在異化之前,一個出現在異化之后,但都明顯有別于現代性價值論。
數字經濟學最主要的發展在于,在原有的商品二重性、勞動二重性之上,增加了一個高于交換價值、抽象勞動的第三重價值,即更高的具體價值與更高的具體勞動。這就指明了工業化基本任務完成之后,經濟發展向何處去的根本方向。至此,以《國富論》提出的交換價值、抽象勞動為標志的工業化的經濟運動,由于找到了使用價值、具體勞動這一明確的否定性的替代標志,才真正進入數字經濟的新時代。
參考文獻:
[1]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527.
[2]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204.
[3]吳寧.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簡論(下冊)[M].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5:283-284.
[4]喬爾·科威爾.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78.
[5]喬爾·科威爾.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77.
[6]何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作為哲學形態何以可能[J].哲學研究,2006,(1):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