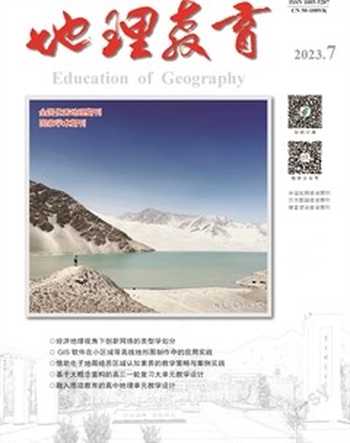經濟地理視角下創新網絡的類型學劃分
曹賢忠 呂磊 陳波



摘 要:創新網絡已成為經濟地理學重要研究領域之一。首先對創新網絡內涵及理論淵源進行梳理,通過系統比較分析當前研究文獻,從空間尺度、網絡功能、網絡資源、網絡知識以及技術權力等方面對創新網絡進行了類型學劃分。經濟地理學視角下,從空間尺度來看,可將創新網絡分為全球、地方(本國、本省、本市)、全球—地方創新網絡;從網絡功能來看,可分為聯系網絡和合作網絡兩種模式;從網絡資源構成來看,可分為社會資本主導型創新網絡和網絡資本主導型創新網絡;從網絡知識類型來看,可分為正式創新網絡和非正式創新網絡;從技術權力來看,可分為平等型、半層級型、層級型三類創新網絡。
關鍵詞:創新網絡;空間尺度;網絡知識;技術權力;經濟地理學
中圖分類號:K902? ?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5-5207(2023)07-0003-05
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Schumpeter)在其1912年出版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最早提出了創新理論。他認為在經濟體系中不斷地引入創新可促進經濟不斷發展。熊彼特認為創新是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和新的生產要素的組合。這種新組合包括五類情形:生產一種新產品、采用一種新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市場、掌握一種新原材料或半成品來源以及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形式[1]。熊彼特創新理論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創新對經濟周期的影響,明確了創新是改變經濟均衡的唯一要素,明確了企業家這一行為主體在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為研究創新提供了重要支撐[2]。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創新范式從傳統封閉式線性模式向現代開放式網絡模式轉變,科技創新與區域發展關系、創新網絡特別是不同行政區域之間創新主體的跨界協同創新等逐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前沿科學問題之一 [3-6]。創新網絡的相關研究有助于豐富和完善基于中國案例的區域創新系統理論體系,這也是當前我國學者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亟待理論探索和方法創新的領域之一[7]。因此,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程中,明晰創新網絡的科學內涵及其類型學劃分,對于經濟地理學學科發展以及創新驅動國家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價值。
一、創新網絡概念及理論淵源
Freeman[8]最早開展了創新網絡研究,并提出了創新網絡的概念,Cooke[9]在其基礎上,對創新網絡內部主體關系進行了界定。從創新網絡本質含義來看,可將創新網絡看作是一個聯系緊密的實體或系統,創新網絡是指政府、企業、高校、研究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等創新主體合作進行技術研發而形成的網絡組織[10]。實際上,區域創新網絡構建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單個企業知識匱乏、創新能力不足、創新資源有限,因而企業為了獲取知識、彌補自身的創新缺陷傾向于與其他企業合作創新[11]。隨著技術創新合作模式的不斷演進,創新網絡相關的其他網絡組織概念也受到了經濟地理學者的關注,如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12]、創新聯合體[13]、創新飛地[14]等。其中創新聯合體是個較新的概念,是指在政府倡導下,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通過聯合建立產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創新聯盟,共建工程中心、工程實驗室和技術中心等多種方式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形成的聯合體。創新聯合體能夠為企業進行跨界合作、創新生產模式提供新知識,有利于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15]。
創新網絡可溯源到區域創新系統理論。1992年,英國卡迪夫大學菲利普·庫克(Philip Nicholas Cooke)教授在深入研究國家創新系統的基礎上,發表了《區域創新系統:新歐洲的競爭規則》一文,首次提出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的概念,并在其1996年主編的《區域創新系統:全球化背景下區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書中指出,區域創新系統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與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等構成、能夠持續產生創新的區域組織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把創新視為一個系統、非線性、演化的過程,并且強調企業和其他機構間的相互聯系。Cooke[16]認為,區域創新系統內的研究機構、大學、技術轉移等機構,有利于提高區內企業創新效率。區域創新系統由知識應用及開發子系統、知識生產和擴散子系統、區域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外部因素組成,深刻地揭示了創新系統的本質(圖1)。
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創新主體主要包括企業、大學與科研機構、中介服務機構和政府部門,他們通過知識流動形成一個相互促進的網絡系統。其中,企業是區域創新系統中最重要的創新主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整個創新系統的創新能力。區域創新系統理論主要致力于解釋地區經濟布局以及區域高技術產業、科技園、創新網絡和創新項目政策的影響。區域創新系統理論認為區域是企業的“群”,這些區域由通過合作和競爭規則的企業網構成,且已形成全球競爭力[17]。
二、創新網絡類型學劃分
基于經濟地理學視角,現有研究主要從空間尺度、網絡功能、網絡資源、網絡知識以及技術權力等方面對創新網絡的類型進行劃分。
1.空間尺度的類型劃分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經歷了諸多思潮的演變。作為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研究對象,區位、空間與地方的內涵也隨著經濟地理學的變革而不斷演進,尤其是隨著彈性專業化、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及經濟全球化的興起,西方經濟地理學者在闡釋“空間”的概念時發生了分歧,相繼提出了制度轉向、文化轉向、關系轉向、尺度轉向和演化轉向等眾多轉向[18-19]。而Castells[20]認為空間逐漸分化成兩種不同的形式,即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與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 ,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距離的死亡”或“地理的終結”等論斷不絕于耳,這對基于距離的古典經濟地理學理論提出了巨大挑戰,經濟地理學必須要重新認識“空間”的概念。信息技術的進步引發了新空間形式的轉變,經濟活動從根本上變得非地方化,全新的“流的空間”已經取代傳統靜態的“地方空間”[21]。對于全新的“流的空間”而言,可看作是一個由創新網絡和企業網絡交織在一起的集合網絡,借助于該網絡知識與技術得以在地方、全球等不同空間尺度進行傳播,“流的空間”所構成的網絡節點之間的距離則已超越了古典經濟地理學所說的物理距離,是一種基于“關系”強弱決定的空間距離。關于“流的空間”和“關系”的探討,促使區域創新網絡逐漸成為經濟地理學界的核心研究領域。從古典區位理論開始,到全球生產網絡、區域創新系統、關系經濟地理和演化經濟地理等思潮演變,經濟地理學者們重點關注不同空間尺度的創新網絡研究[22]。
根據創新主體所在的不同空間區位,可將創新網絡空間尺度分為地方、全球和“全球—地方”三類,但由于中國特殊的行政區劃國情,若將本國看作地方,本國尺度還可細分為本省或本市、本省或本市以外的區域。因而,可進一步將不同空間尺度創新網絡細分為全球創新網絡、本國創新網絡、本市或本省創新網絡、“全球—地方”創新網絡四類,可將這一思想抽象化為圖2所示,其中,國家A和國家B只是一種抽象化的表達,代表本國和其他國家,企業1至企業4分別表示一國內部開展創新合作的某一類別企業的集合。在國家A內有四個不同的企業,其中企業1主要與本市或本省內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聯系,形成的網絡可看作是本省或本市創新網絡;企業4主要與本省或本市以外、本國以內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聯系,形成的網絡可看作是本國創新網絡;企業3主要和國家B內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聯系,和本國內的創新主體聯系較少或沒有聯系,形成的創新網絡可看作是全球創新網絡;企業2不僅與本國內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聯系,同時還與國家B內的創新主體有著創新聯系,形成的創新網絡可看作是全球—地方創新網絡[23]。
2.網絡功能的類型劃分
根據創新網絡基本功能的不同,可分為聯系網絡和合作網絡兩種模式,創新主體一般通過聯系網絡獲取知識,通過合作網絡進行合作創新。其中,合作網絡主要關注重復、持久或持續的互動或聯系,主要由正式的規則、制度與戰略安排形成的創新聯系組成[24],如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創新飛地、產業技術轉移轉化中心等;而聯系網絡則由組織間非正式的互動和聯系組成,會頻繁更新和改變組織間的聯系,引起網絡的動態演變[25],如臨時性展會交流網絡等。二者在結網目的、類型和空間尺度上存在顯著差異(表1)。
3.網絡資源的類型劃分
根據網絡資源類型的不同,可將網絡資源分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Huggins等[27]認為社會資本更加體現為非正式的交流,網絡資本則更加體現為正式交流。其中社會資本包括義務和期望,主要依賴于社會環境的可信賴性、社會結構的信息流動能力、處罰規則[28]。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可較好地用于分析如何在組織內外獲得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雖然社會資本概念從社會能力與社會化視角解釋了網絡投資,但對于經濟效果方面則缺乏有針對性的研究,難以從經濟預期方面解釋網絡投資[29],而網絡資本則可以解決這一問題。Huggins[30]首次提出了網絡資本概念,該概念彌補了社會資本在解釋網絡投資方面的不可計算性,基于網絡資本的可計算的和戰略性的網絡被認為可促進知識流動,且能幫助企業獲取競爭優勢。二者在投資來源、運行機制、主體對象以及對網絡收益的影響等方面均存在差異(表2)。
4.網絡知識的類型劃分
根據網絡知識交流的不同,可分為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知識一般包括隱性、可編碼化、科學、技術、文化、美學、表述和符號等類型[31]。其中,隱性知識(或緘默知識)和可編碼化知識在學界應用最為廣泛,二者在表達形式、交流方式、轉移難易程度、地理空間范圍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表3)。非正式社會交流被認為是本地隱性知識傳輸的重要方式[32],正式交流則是編碼化知識傳輸的重要方式[33]。
[特征 編碼化知識 隱性/緘默知識 表達形式 表達方式多樣 表達方式單一 交流方式 正式交流 非正式交流 轉移難易 容易 較難 地理空間 全球 本地/區域 / 全球和本地可互換知識 ][表3 創新網絡中編碼化知識與隱性/緘默知識特征][注:資料來源于曾剛等的論文[33]]
5.技術權力的類型劃分
根據技術權力,創新網絡可分為平等型、半層級型與層級型三類。技術權力是影響產業技術創新網絡和集群形成與發展的主導因子之一[34],這主要是因為創新網絡和產業集群中存在核心企業,而其主導了整個網絡和集群的發展,進而促使創新網絡產生權力關系,形成了平等型、半層級型與層級型三個類型[35]。但從演化機制看,企業間的水平、平等式競爭推動了集群和創新網絡的演進,技術權力影響集群創新路徑,重工業“集群式”建設方式亟待反思[36]。
三、結語
創新驅動已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大戰略選擇,創新網絡也已成為經濟地理學重要的研究方向。經濟地理學視角下,從空間尺度來看,可將創新網絡分為全球、地方(本國、本省/本市)、“全球—地方”創新網絡;從網絡功能來看,可分為聯系網絡和合作網絡兩種模式;從網絡資源構成來看,可分為社會資本主導型創新網絡和網絡資本主導型創新網絡;從網絡知識類型來看,可分為正式創新網絡和非正式創新網絡;從技術權力來看,可分為平等型、半層級型與層級型三類創新網絡。關于創新網絡類型的研究也主要呈現出三大特征,一是多集中對大型企業主導的創新網絡分析,缺乏對中小企業主導的創新網絡類型研究;二是多集中單一空間尺度不同類型創新網絡的結構及演化,缺乏對多空間尺度交互的不同類型創新網絡運行機理研究;三是多集中對論文、專利合作的虛擬創新網絡分析,缺乏對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創新聯合體和創新飛地的實體創新網絡分析。
展望未來,建議基于創新網絡的不同類型,綜合運用面板數據與實地訪談數據,重視對不同類型創新網絡的結構、演化過程、空間格局及作用機理的比較分析,并重視對典型區域的重點產業創新網絡案例的深入剖析,歸納總結不同類型創新網絡的規律性特征和效應,為豐富和完善創新網絡相關理論體系服務。
參考文獻:
[1] 約瑟夫·熊彼特. 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0.
[2] 韓振海, 李國平.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演變評述[J]. 科學管理研究, 2004, 22(2): 24-26.
[3] Fernandes C, Farinha L, Ferreira J J, et 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25 years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J]. Regional Studies, 2020(2): 1-14.
[4] Bathelt H, Cantwell J A, Mudambi R. Overcoming frictions in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flows: challenges of connecting, sense-making and integra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18(5): 1001-1022.
[5] 陸大道. 我國新區新城發展及區域創新體系構建問題[J].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 2018, 39(1): 1-3.
[6] 賀燦飛, 朱晟君. 中國產業發展與布局的關聯法則[J]. 地理學報, 2020, 75(12): 2684-2698.
[7] 林初昇. 去中心化和(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人文地理學的批判性理論探索與方法創新[J]. 熱帶地理, 2020, 40(1): 1-9.
[8] Freeman C. Networks of innovators: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J]. Research Policy, 1991(20): 499-514.
[9] Cooke P.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arriers and the Rise of Boundary-Crossing Institutions[M]. Academia-Business Links.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4.
[10] 王緝慈等. 創新的空間: 產業集群與區域發展[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9.
[11] Kogler D F. Relatedness as Driver of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A Research Agenda – a Commentary[J]. Regional Studies, 2017, 51(3): 365-369.
[12] Cao X, Zeng G, Ye L. The structure and proximity mechanism of formal innova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high‐tech ITISAs[J]. Growth and Change, 2019, 50(2): 569-586.
[13] 羅小芳, 李小平. 為什么要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N]. 光明日報, 2021-6-8(15).
[14] 曹賢忠, 曾剛. 基于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創新飛地建設模式[J]. 科技與金融, 2021(4): 36-41.
[15] 張赤東, 彭曉藝. 創新聯合體的概念界定與政策內涵[J]. 科技中國, 2021 (6): 5-9.
[16] Cooke P.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General Findings and Some New Evidence from Biotechnology Clusters [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2, 27(1): 133-145.
[17] 胡志堅, 蘇靖. 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的提出與發展[J]. 中國科技論壇, 1999(6): 21-24.
[18] 苗長虹. 變革中的西方經濟地理學:制度、文化、關系與尺度轉向[J]. 人文地理, 2004, 19(4): 68-76.
[19] 苗長虹, 魏也華. 西方經濟地理學理論建構的發展與論爭[J]. 地理研究, 2007, 26(6): 1233-1246.
[20]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21] 艾少偉, 苗長虹. 從“地方空間”、“流動空間”到“行動者網絡空間”: ANT視角[J]. 人文地理, 2010, 25(2): 43-49.
[22] 司月芳, 曾剛, 曹賢忠, 等. 基于全球—地方視角的創新網絡研究進展[J]. 地理科學進展, 2016, 35(5): 600-609.
[23] 曹賢忠. 基于全球—地方視角的上海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網絡研究[M].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19.
[24] Turkina E, Van Assche A, Kali R.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luster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aerospace industr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16): 1211-1234.
[25] Bathelt H, Cantwell J A, Mudambi R. Overcoming frictions in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flows: challenges of connecting, sense-making and integra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18(5): 1001-1022.
[26] 曹賢忠, 曾剛, 司月芳. 網絡資本、知識流動與區域經濟增長:一個文獻述評[J]. 經濟問題探索, 2016(6): 175-184.
[27] Huggins R, Thompson P, Johnston, A. Network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flow: how the nature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mpacts on innovation[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2(19): 203-232.
[28] Kemeny T, Feldman M, Ethridge F, Zoller T. The Economic Value of Local Social Networ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5):1101-1122.
[29] Huber F. Do clusters really matter for innovation practic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Questio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spillov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12): 107-126.
[30] Huggins R. Forms of network resource: knowledge access and the role of inter-firm netwo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12): 335-352.
[31] Pinch S, Henry N, Jenkins M, Tallman S. From ‘industrial districts to ‘knowledge clusters:a model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competi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3): 373-388.
[32] Whitfield L, Staritz C, Melese A T, et 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Upgrading, and Value Captur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ocal Apparel and Floriculture Firms in Sub-Saharan Afric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96(3): 195-218.
[33] 曾剛, 王秋玉, 曹賢忠. 創新經濟地理研究述評與展望[J]. 經濟地理, 2018, 38(4): 19-25.
[34] Bathelt H, Taylor M. Clusters, power and place: inequality and local growth in time-space[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02, 84(2): 93-109.
[35] 景秀艷, 曾剛. 從對稱到非對稱:內生型產業集群權力結構演化及其影響研究[J]. 經濟問題探索, 2006, 26(10): 41-44.
[36] 林蘭, 曹賢忠, 曾剛. 技術權力影響下重工業集群創新路徑研究——以上海臨港裝備制造集群為例[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 51(2): 152-16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