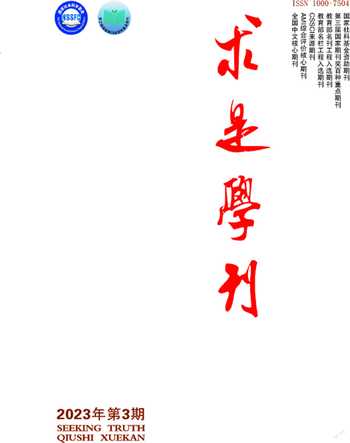論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研究
田巨為 魏義霞
摘要: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心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他立足于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分別從心學之社會作用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兩個維度對梁啟超的心學思想淵源進行了解釋,通過對思想與時代的相互作用考察了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發展邏輯與脈絡,進而又從宗旨與效果的辯證分析上對梁啟超心學思想之歷史作用進行評定。對于張錫勤先生這方面研究成果的學習,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張錫勤先生對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之問題意識和方法論原則,更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梁啟超心學思想之時代價值和當代啟示。
關鍵詞:張錫勤;梁啟超;心學
作者簡介:田巨為,黑龍江大學副研究員、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黑龍江? 150080);魏義霞,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黑龍江 150080)
DOI編碼: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3.005
張錫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近代哲學與文化以及中國倫理思想史的研究,學術造詣深厚,其對中國近代哲學與文化領域的研究在國內學術界具有極高的地位。張錫勤先生的學術研究較多關注于中國倫理思想史、近代文化史、倫理思想等問題,而以人物作為研究對象的作品較少,現今可見的專著僅有《梁啟超思想平議》一書。該書于2013年出版,但此時據張先生開始撰寫該書已經歷時二十多年。由此可見,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思想經過了長期的思考與深入的研究,并對原始資料進行了充分的整理比較,最終系統、完整地完成了這部著作。通過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哲學以及中國社會始終如一的熱愛。
一、社會與思想的雙重維度:對梁啟超心學思想淵源的揭示
張錫勤先生在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研究中始終強調特定社會意識是對特定社會存在的反映這一基本原則,分別從對明治維新心學動因的揭示、對陸王心學的崇信與鼓吹、對佛學和心學的綜合與創新三個維度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淵源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
(一)明治維新——梁啟超心學的實踐淵源
張錫勤先生認為,明治維新改革的成功是中國近代新學家謀求救亡道路的實踐樣本。梁啟超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樣,為了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廣泛地學習、分析了古今中外的典籍與實踐經驗,嘗試了各種方法與路徑,最終形成了對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經驗進行學習與吸收的觀點。張錫勤先生曾對近代思想家對日本經驗的推崇進行過分析:“在20世紀初,赴日留學成為一股潮流。通過對日本社會和思想界的皮毛了解,不少人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所以迅速成功,與王學、禪宗的影響有直接關系。”1梁啟超在對日本維新的分析中認為,“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為用也”2;“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學,即有得于禪宗”3。與梁啟超同時的章太炎也認為,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4,“日本資陽明之學以興”5。中國近代的新學家們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案例中,看到了陸王心學、禪宗思想在社會變革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這構成了梁啟超等人從日本的政治改良經驗中汲取心學養料的重要論據。
張錫勤先生認為,在近代新學家視野中,“王學乃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理論資源和精神支柱”,近代新學家們由對明治維新成功經驗的推崇,進而轉為對陽明心學的推崇,這“使他們更加崇信、親近王學,也使他們試圖通過提倡、弘揚心學來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6從這一點看,梁啟超是這一批近代新學家群體中的代表者,對心學的狂熱追求及其心學思想是其哲學思想和改革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毋庸置疑,這是張錫勤先生關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極具特色和個性的觀點,既體現了先生對于日本明治維新的深入思考,同時也為其揭示心學在中國近代思想史,尤其是梁啟超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前提和現實基礎。
(二)取法陸王——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理論淵源
張錫勤先生從中國近代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出發,指明了梁啟超思想受到的西方新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雙重影響。就中國古代哲學影響而言,心學和佛學的影響最大。張錫勤先生強調:“梁啟超是陸王心學特別是陽明學的忠實崇信者、鼓吹者。他稱王守仁為‘千古大師,認為‘王學為今日學界獨一無二之良藥,而致良知說乃是‘千古學脈,超凡入圣不二法門。他自稱,‘吾生平最好言王學。”7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學派,經過千年的發展,內部也呈現出了諸多派別。陽明心學源自于宋明時期的新儒學思潮,具有極強的變革意識與批判精神。在梁啟超的時代,經歷了清朝兩百余年的高壓統治,沉寂的思想界也正急需一股能夠革故鼎新的力量。梁啟超對陽明心學的推重,除了受日本維新的影響,同時也源自其對心學中自我覺醒、批判傳統等特點的肯定。
王陽明在理論上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等命題,強調主體對世界與社會的主宰作用。這種高揚的主體性無疑是梁啟超當時急需的思想力量,只有喚醒當時處于盲目無知狀態的普羅大眾與知識分子,才能夠產生足以推動社會變革的實踐力量。所謂“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意在說明沒有主體的參與,現實世界即不具有價值意義,主體的活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不斷地對外在世界賦予意義。這種創造活動必然需要主體的自覺、自為,而不是機械、消極的運動。心學這種對主體意志的強調,正契合于近代思想界的變革趨勢。
張錫勤先生通過深入系統的分析,揭示了梁啟超對陸王心學從推崇到以之為維新變法思想武器進行鼓吹的理論特征,應當說,這也突顯了梁啟超等近代新學家謀求心學近代化的思想特征。對于陸王心學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和救亡圖存的社會變革推動作用的強調是張錫勤先生學術生涯重點關注的課題和一以貫之的觀點,同時也是理解張錫勤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深入了解張錫勤先生對近代心學的思考和論述,就無法凸顯其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理論特色和思想貢獻。
(三)綜合佛學——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系統論證
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受佛學思想的影響高度重視,他認為:“佛學對梁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我們在評介梁啟超的哲學思想之前,首先當指明心學與佛學對他的影響。”1在梁啟超看來,客觀外物只是“感覺的客觀化”2,是“我們心理的表象”3,是主觀的產物。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又在論述佛學的幾篇論文中,進一步發揮、論證了這種客觀依附于主觀,是主觀產物的主觀唯心論”4。梁啟超心學思想是佛學和陸王心學的的綜合產物,對此,張錫勤先生總結說:“梁啟超的這套主觀唯心論乃是佛家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陸九淵的‘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的‘心外無物、‘乾坤由我在,陳獻章的‘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諸說的綜合。”5從而得出梁啟超和當時近代心學論者的共同點:“他們都否認意識乃是客觀存在的主觀映象,否認它對物質的依賴關系,最終得出了客觀依附于主觀,是主觀的感受、產物的結論。”6張錫勤先生通過對梁啟超思想對心學和佛學的系統分析,注重從主觀與客觀的關系角度對其心學思想進行性質界定,反映了張錫勤先生始終堅持特定意識是特定社會存在反映的基本立場,可以說,這是對唯物史觀的遵循,也是注重實事求是歷史精神的具體表現。
基于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實踐和思想淵源分析的基礎上,張錫勤先生還從時代變化和理論發展互動的維度,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演變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剖析。
二、時代與理論的互動:對梁啟超心學演變的剖析
梁啟超的思想一生多變,其心學思想亦是如此。張錫勤先生強調,梁啟超心學思想的不斷豐富發展和變化,始終是伴隨著中國近代革命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脈動的,基于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心學的演變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認為“境者心造”說標志著其心學的開啟,是梁啟超對生命哲學的思考,開啟了其心學研究的大門;以佛學溝通心學、豐富心學,是梁啟超心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心物合一”則是梁啟超對心學研究的升華,將心學內容與自己的思想體系相融合,從而在近代社會變革和政治革命的發展中提出自己有實踐性的見解。張錫勤先生看到了梁啟超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勇于探索的成果,也看到了其學術在時代中受限的不足,并且做出了全面又客觀的評價,這對我們今天探討心學思想的當代價值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境者心造”說——梁啟超心學思想發展的開端
1900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惟心》一文,強調“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7。所有外部環境都是虛幻的,只有心創造的“境”才是真實的,強調了心的決定作用和力量。通過梁啟超對譚嗣同《仁學》的評價,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的“境者心造”說借取和發揮了譚嗣同“世界因眾生而異”、人們“各自有世界”的觀點。梁啟超認識到心對一切事物有體悟和感知的重要性,如果缺少了心的發現,其他的存在都是不真實的。對待同一物境,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情也都有不同的感受。張錫勤先生在《梁啟超思想平議》中闡述:“梁啟超寫道,面對同一外境,由于各人處境、心情不同,各人的感觸、映象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余興;反之,‘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余悶。‘同一黃昏也,當‘月上柳梢頭之時,熱戀中的情人依約幽會,則感此黃昏無限美好;反之,閨中怨女‘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則感此黃昏無比愁慘。‘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當曹操統大軍南征之時,‘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則感此江景極為壯麗;反之,當白居易‘潯陽江頭夜送客之時,則感此江景無比凄涼。”1
梁啟超亦認為:“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那么,一切物到底是黃是綠、是苦是甜,‘果為何狀?他的回答是:‘一切物即綠即黃、即苦即甜。就是說,你說它是黃是綠、是苦是甜皆無不可。這是因為,所謂‘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2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梁啟超對心的決定性作用的極端肯定。這一思想傾向,為其后來心學思想的變化埋下了伏筆。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對心的理解給予肯定,認為其具有積極意義,并做出了客觀分析和評價。張錫勤先生斷言:“在《惟心》一文中,梁啟超揭示了人們對同一外境、外物的感受具有差異性的現象。這種差異性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的。由于處境、地位、經驗、關注點、心情的不同,人們對同一客觀對象的反映、感受是有差異的,人們的感覺是具有主觀性的特征的。”3這一論斷既符合梁啟超本人的思想特點,同時又揭示了其普遍性特征,有助于人們對于梁啟超思想傾向的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
(二)矯正“惟心”——梁啟超心學思想發展的樞紐
張錫勤先生肯定梁啟超對心的解釋有其合理性,也明確地指出其存在不合理的一面。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1900年發表的《惟心》和20年后的《非“唯”》進行充分的比較分析,發現梁啟超的心學思想具有不斷矯正和與時俱進的特點。
梁啟超在《非“唯”》中總結說:“總而言之,無論心力如何偉大,總要受物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力量很不弱。”4與此相對比,他早期在《惟心》中的觀點則是:“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5從梁啟超觀點的這種前后變化中可以看出,其心學思想經歷了一種質的變化,開始承認心之外物的存在。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前后變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說:“梁啟超看到,主觀唯心論如果貫徹到底,最終勢必要否認與我并存的他人,以至‘我自己身體內種種機官的真實存在,這就會‘發生奇謬,‘鬧出種種亂子來。這種回到日常生活常識的認識,較前自然是一大進步。但是,他對唯心論的批評,是以肯定‘心力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且具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為前提的。他雖已承認物的真實存在,但他只認為物是一種‘條件,并不承認物質第一性、決定性的原則。”6梁啟超在《非“唯”》中對“心力”作出了界定:“心力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并且含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人類所以在生物界占特別位置者就在此……若在心字頭上加一個唯字,我便不能不反對了。”7張錫勤先生指出了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特點:“人們反映的這種差異并不是主觀自生的,它同樣是對客觀的反映。人的意識雖是主觀映象,但卻是對客觀世界的主觀映象,其內容是客觀的。可是,梁啟超抓住意識的主觀性特征,卻否認意識所反映的內容的客觀性,否認外境的客觀性及客觀存在的確定性。……外界事物的一切屬性不是事物自身客觀固有的,而是吾心的主觀感受,是吾心賦予事物的。”8
隨著時間的推移,梁啟超對思想與存在的關系做了新的解讀,其心學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認為:“人類于橫的方面為社會的生活,于縱的方面為時代的生活。茍離卻社會與時代,而憑空以觀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動作,則必多不可了解者。”1從這里可以看出,梁啟超已經認識到主觀思想對客觀事實的依附作用,對主觀思想和客觀事實的主從關系有新的認識,從而為其心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指引。對于梁啟超這一階段的思想,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也看到了思想離不開存在的客觀事實,修正了先前的錯誤認識。”2張錫勤先生通過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發展路徑的分析,進一步擴展到對近代的社會進步和社會思想的主流變化進行全面的解讀,深刻地把握了近代歷史中從思想到社會、從理論到實踐的變革脈絡。
(三)“心物合一”——梁啟超心學思想發展之大成
1926年,梁啟超基于對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理解,提出了“心物合一”這一觀點。他認為,“有客觀方有主觀,同時亦有主觀方有客觀。因為主觀的意不涉著到客觀的物時,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觀的物不為主觀的意所涉著時,便失其價值,也等于不存在”3。
較之過去的觀點,梁啟超這時對物的存在和作用有了新的認知,但同時他并沒有削弱對“心”的重要作用的認識,反而強調“心”的偉大,提出心力可以改良或創造環境。梁啟超這樣批評唯物主義:“物之條件之重要,前文已經說過……若在物字上頭加一個唯字,我又不能不反對了。須知人類和其他動物之所以不同者,其他動物至多能順應環境罷了,人類則能改良或創造環境。拿什么去改良、創造?就是他們的心力。若不承認這一點心力的神秘,便全部人類進化史都說不通了。若要貫徹唯物論的主張嗎?結果非歸到‘機械的人生觀不可。”4張錫勤先生指出:“梁啟超是抓住了舊的機械唯物主義忽視意識能動性的缺陷。但是,他把機械唯物主義的這一缺陷夸大為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在內的一切唯物主義的共同缺陷,對整個唯物主義予以否定,并以強調意識的能動性為由為唯心主義作辯護。他再次把物質僅看作是‘條件,顯然他是離開物質的決定性來講意識的能動性的。”5梁啟超一方面肯定物質條件作為心力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又認為這種物質前提在心力面前的作用微乎其微。張錫勤先生得出這樣的結論:“不過,此時的梁啟超依然堅持認為心具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堅持認為‘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不‘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可見,他的根本立場并未改變。”6由此可以看出,張錫勤先生對于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研究充分體現了“先立乎其大者”的原則,即勇于拋開細枝末節和零散論述,而是在梁啟超紛繁復雜甚至是反復跳躍的觀點中強調其心學思想的核心問題和基本邏輯,撥開迷霧、朗現乾坤,這對于人們準確地把握梁啟超心學思想的實質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張錫勤先生能夠借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從特定的歷史人物承擔特定的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扮演的特定歷史角色這一視角去闡發梁啟超心學思想的變化。張錫勤先生指出:“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看,梁啟超的《非‘唯》較之二十多年前的《惟心》是有進步的。這表現在此時的梁啟超已承認外物的真實存在,看到了心要受物的制約。就此而言,《非‘唯》是對《惟心》的矯正。”7張錫勤先生堅持從唯物主義立場審視梁啟超心學思想的得與失,并深入時代背景分析了其心學思想轉變的社會存在動因。張錫勤先生講:“梁啟超之所以主動對《惟心》作矯正,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當時中國的客觀環境所決定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年代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勢力影響在中國思想領域此消彼長的態勢。”1
張錫勤先生更進一步從理論邏輯的角度揭示了梁啟超“心物合一”的成因。為了圓滿地說明心物關系,梁啟超在《非“唯”》中強調唯物論和唯心論對“物”或“心”的極端強調都有缺陷。2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在心物關系上的發揮符合王守仁的本意,“梁啟超反復強調心與物、主觀與客觀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相互決定,不能分離,無非是為了否定物質第一性。拋開物質第一性講心物關系,這是梁‘心物合一的要害。梁認為‘主觀的心不能離開客觀的物而單獨存在自然是正確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客觀的物是否也不能離開主觀的心而單獨存在呢?一切唯物論者對此是否定的,而梁啟超則是肯定的,這便是他所說的‘物要靠心乃能存在”3。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與王守仁的主張是一樣的,否定心外之物的存在,然后再講心物合一,只能說是將物合一于心。梁啟超堅持心是第一性、客觀的事物不能離開主觀心而獨立存在的觀點,便是主觀唯心論。4張錫勤先生通過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發展歷程的分析,從側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其心學思想的影響。
可以認為,張錫勤先生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于唯物史觀的強調貫穿其學術思想的始終。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梁啟超的心學思想,即體現了其對于唯物史觀的深刻理解和自覺運用,同時也為其能夠科學、準確地論述、分析和評價梁啟超心學思想提供重要了的理論保障和方法指導。
三、宗旨與效果的辯證分析:對梁啟超心學歷史作用的評定
任何思想的產生、轉變和發展都是離不開時代背景的。中國近代是一個社會變革、社會轉型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化革新、文化轉型的時代。因此,中國近代不論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文化領域都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作為近代重要的歷史人物,梁啟超的心學思想最終目的是喚醒人們的主觀意識,從自我之心開始喚醒沉睡的社會大眾。張錫勤先生從理論追求、社會效果和歷史局限三個方面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歷史作用進行了系統分析。
(一)凝聚意志——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理論追求
張錫勤先生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去分析梁啟超心學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從而還原當時因社會進步的需求產生的特定的歷史意識,并由此肯定了其心學思想對于促進思想啟蒙的積極意義。梁啟超說過:“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5張錫勤先生看到了這種意識決定論的價值:“20世紀初那個特定的年代,包括維新派、革命派在內的諸多變革者都在鼓吹這種意識決定論。……這反映了那時包括梁啟超在內的變革者們對思想啟蒙、觀念變革、文化革新的高度重視,而這種意識決定論在當時的確也起到了推動觀念變革的作用。”6
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這種心力“是希望形成一種共同的民族意志,由此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族合力……這是由中國近代的時代需要所決定的”7。心力在近代究竟是何含義,張錫勤先生認為,“‘心力就是人們的精神意志力……這種內在的趨動力顯現于外,便能轉化為巨大的外在物質力量。這種人人皆有的心力是一種偉大的潛能。人們成就、事功的大小,取決于這種潛能釋放、發揮的程度”8。梁啟超舉中西方諸多事例證明心力的作用,“心力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具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以西方為例,其社會的發展進步‘豈有他哉,不過最少數之仁人君子以其心力以與惡社會戰,而卒獲最后之勝利云爾。以中國為例,曾國藩之成功,‘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謀,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1。
張錫勤先生看到了梁啟超心力思想的最終目標,看到了近代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弘揚愛國熱情。“他們所以大力呼喚‘心之愛力,是為了激發國人愛群、愛國的意識,培育國人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呼吁激勵、增長心力,是欲使中國人心由冷而熱,由冷而愛,變消極為積極,變被動為主動,變依附依賴為奮發進取,改變中國‘民心弱的狀態,使中華民族起死回生,重新振作起來。概言之,他們的基本思路是:中國欲圖振興只有自強;而國家民族的自強是建立在民眾人人自強的基礎上的;人欲自強首當自強其心。由強心而強國乃是他們心力說的根本宗旨。……他們所主張的是一種心力救國說、心力強國說,其意圖、宗旨是至為鮮明的。”2
對“心力”說的重視和堅持代表了張錫勤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觀點,對于包括梁啟超在內的近代思想家關于“心力”的論述、辨析、比較是張錫勤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學術特色和理論貢獻之一,是人們了解中國近代思想史,尤其是戊戌維新前后思想變化和邏輯演進的一把鑰匙,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
(二)救亡圖存——梁啟超心學思想的社會效果
張錫勤先生看到梁啟超的心力思想與時代需求的息息相關性,并對其心學思想在激發近代國人救亡、變革的激情和熱忱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有充分肯定。梁啟超希望國人“萬其足,一其心;萬其心,一其力;萬其力,一其事……夫能齊萬而為一者”3。這反映了梁啟超希望基于共同的民族意志而形成一股巨大民族合力的理論宗旨。張錫勤先生認為,“心力說作為唯意志論的一種,本質上屬于非理性主義。但維新派思想家強調正確選擇,使心力‘用之于仁,進而‘一其心,一其力,又表現了理性主義的精神,這是由中國近代的時代需要所決定的”4。他對梁啟超的心學思想進行了理性與非理性的辯證分析,指出梁啟超試圖用心力把人的精神和實踐行為統一起來。張錫勤先生認為,“康、梁、譚等人論心與心力,雖然有時講得十分玄虛,其實他們是緊緊為現實斗爭服務的。他們并非有意談玄,所針對、所要解決的乃是當時中國的現實問題”5。張錫勤先生客觀評價心力的積極影響,“在近代,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再安于現狀、安于命運,不再任人宰割、聽人擺布,變消極被動為積極主動,由弱者成強者,心力說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雖然,這種心力說并不像它的提倡者所想像的那樣,是中華民族的回天再造丸,但它在當時的確起了一些積極作用。……心力說對造就一批批熱血沸騰、豪情滿懷的志士仁人,是有一定影響的”6。
張錫勤先生分析了心力說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他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代,也是一個歷史大轉折、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救亡和變革事業的宣傳發動者、領導者極力強調(以至夸大)精神意志力量的偉大,以激發人們投身于救亡、變革事業的熱忱,是自然且必然的”7。張錫勤先生進一步總結了心力說的主要觀點與目的:“人人皆有的心力是一種無有限度、止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偉大潛能,它顯現于外則形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心力成就一切,只要最大限度地釋放、調動、發揮心力,世間便沒有做不成的事。” 1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正是基于這種‘一切唯心所造、心是世界本原的主觀唯心論,他們奏出了一曲又一曲極度推崇心力的贊頌歌,并對心力寄予了無窮的期望”2。“心力所以偉大顯然是由于心的偉大。從理論上說,維新派的心力神奇說乃是他們自心造世界的主觀唯心論的必然邏輯”3。梁啟超的心力說在于調動人的能動性,樹立民眾的信心,從而進一步改造民族性。梁啟超強調:“天下事可為不可為亦豈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為,斯真不可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斯可為矣。” 4從理論上說,維新派的心力神奇說乃是他們自心造世界的主觀唯心論的必然邏輯產物,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有其積極的意義。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便是這種心力神奇說的鼓吹者。他始終認為,心力是最偉大的力量,是社會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5。在近代,中華民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國處于社會變革、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民族危機非常之嚴重,需要一種力量來激發人們去投身到救亡圖存、變革事業中去,梁啟超的心力救國論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并且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救亡圖存是中國近代社會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時代課題,構成了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中國近代思想家的核心關切。張錫勤先生從時代需求的背景出發探討梁啟超心學思想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因素,既符合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現實,同時也體現了張錫勤先生對于唯物史觀的自覺運用。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正是張錫勤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始終貫徹的核心方法。
(三)精神萬能——梁啟超心學思想的歷史局限
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現實狀況,心力說的盛行有其必然性。張錫勤先生講:“一批維新派、革命派的思想家、宣傳家都曾極力夸大心、心力的偉大神奇,一時間主觀唯心論在中國頗為盛行。”6這也是出于激發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以投身于救亡圖存、社會變革事業的需要。在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西方的科學價值觀開始在中國社會興起,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國內掀起了介紹、宣傳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潮。張錫勤先生認為,隨著“科玄論戰”的結束,“科學派對玄學派的勝利,實則是唯物論對唯心論的勝利”7;“科玄論戰”引起了從學界到社會的普遍關注,也加劇了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在當時思想領域的影響。此時的梁啟超也開始主動對《惟心》一文進行矯正,這充分說明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影響力。張錫勤先生認為,“從基本立場、傾向說,梁啟超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指責唯物史觀是‘命定主義”8。可以知曉,這是一種時代的烙印,是近代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的過程中維護中國傳統文化所做出的螳臂當車式的努力。張錫勤先生說:“這種指責似不純是誤解而是歪曲。因為是歪曲,因而梁的這些指責不可能對人們產生多大影響。”9
梁啟超的心學主張強調“一切惟心所造”,是對心力的無限夸大和神化,最終走向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梁啟超后來又接受西方哲學家叔本華的唯意志論思想,這就使他的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得以進一步滋長。張錫勤先生認為,梁啟超的意識決定論只“看到了意識的能動性,并對它作了一些說明……但是,他們對心和心力卻始終缺乏科學認識。……人在客觀世界面前,既是能動的,又是受動的。而在他們的哲學中,心力即精神意識的能動性是既不受客觀規律支配,又不受客觀條件制約的”1。“心力并不受客觀規律制約,甚至可以改變客觀規律。顯然,指望靠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心力去創造奇跡,取得成功,在現實當中就勢必要碰壁、落空。由此而產生的狂熱性、盲目性勢必要給中國的變革和建設事業帶來負面甚至破壞性的影響。這方面的教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不少的。只講能動,不講受動,這是近代心力說普遍存在的問題。”2張錫勤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心力說的弊端:“這種精神萬能論解決不了客觀世界的矛盾,并不能為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提供持久的動力。”3
通過以上分析,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的心學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梁啟超的心學淵源,來自陸王心學和佛學,將此二者融合統一;其二,梁啟超心學的演繹,從“境者心造”到“心物合一”不斷深化;其三,梁啟超的心力強國論,不僅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覺醒,而且在中國內外受困的情況下對近代政治革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張錫勤先生對于梁啟超心學思想的闡釋從其本源開始探究,對大量文獻資料進行貫通式的學理分析,從而發現其思想具有隨時代背景、社會思想變化不斷矯正的特點。張錫勤先生強調,梁啟超的心學思想始終圍繞著愛國、救國、激發民族斗志、不屈不撓地實現民族救亡的時代主題,其心學思想也使傳統心學實現了向近現代理論形態的轉化。探究張錫勤先生對梁啟超心學思想的闡釋,可以體會到其將時代意識融入具體問題研究的唯物史觀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既是對以史為鑒文化傳統的繼承,也是著眼于更好開創未來以理論方式回應時代需要的創新發展。
[責任編輯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