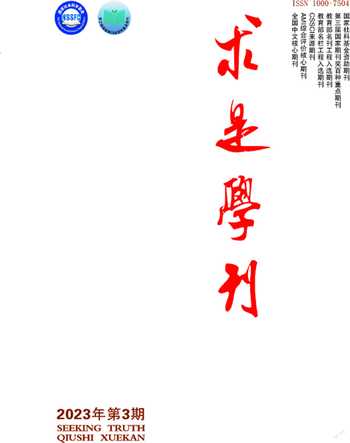錢謙益論詩詩對杜甫《戲為六絕句》的承傳與新變
摘 要:錢謙益所作論詩詩《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在承傳杜甫《戲為六絕句》的基礎上又產生新變。錢氏繼承了杜甫尊重前賢、別裁偽體的思想,以批評當時的詩壇流弊。錢詩延續了《戲為六絕句》“戲題”的自況心懷,但也增添了走出“嗤點前賢”的矛盾、消解諷刺的緊張等意味。錢詩與《戲為六絕句》都是以近代視野和當世視野為論述重點,但不同于杜甫對時人的包容態度,錢謙益以自己的詩學為標準,將時人劃分了陣營。《戲為六絕句》論述的內容可能不僅僅限于詩歌,這種現象在錢謙益論詩詩中更是蔚為大觀,他論述了文學家、批評家、書法家、畫家以及女性群體,且對后世論詩詩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錢謙益;論詩詩;杜甫;《戲為六絕句》
作者簡介:高明祥,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2)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詩人別集叢刊”(14ZDB076)
DOI編碼: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3.014
錢謙益在明崇禎十三年(1640)七八月間曾作《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這種以絕句來闡發文學主張的論詩詩體式,可以追溯到唐代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繼之頗為著名的是金代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后世出現的論詩詩體式大都受二者影響。據學者對清代論詩詩數量的統計,“就詩題徑直標明‘論詩仿效某人的情況來看,標明仿杜甫的有10家12個標題74首,而仿元者有31家34個標題1002首”1,可以看出杜甫與元好問兩家論詩詩的強大影響力,并且仿元詩的數量遠遠多于仿杜詩。但是,錢謙益的論詩詩呈現出與杜甫《戲為六絕句》更為緊密的聯系,而且由于時代的變換,更增添了新的內容。錢謙益的詩風學杜,已是學界共識,所謂“摹擬少陵,入其堂奧,自不待言”2。不過,這組詩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詩歌文本,又是詩學闡發的載體。那么,在論詩詩的體式與思想方面,錢謙益與杜甫又有什么相通與不同呢?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較為匱乏3,筆者試就此展開論述。
一、文本的互文與時代的困惑
錢謙益論詩詩存在諸多傳統論詩詩文本如杜甫《戲為六絕句》、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等的痕跡,由此形成一種互文性的關聯。不過,我們對互文性的關注,往往停留在字詞的比對與文本的相似方面,對其背后所隱含的主體、時代等之間的對話有所忽略。通過錢謙益與杜甫論詩詩之間的關聯,我們可以窺得互文性的這種更深層次的對話。
錢謙益一生服膺杜詩。他認為:“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于杜氏。大歷后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1這十六首論詩詩在字詞、句法方面都有著對杜詩的承傳關系。首先是字詞。2錢有“嗤點前賢豈我曹”(其二)3,“何事后生饒筆舌,偏將詩律議前賢”(其三),其中的“嗤點”“前賢”“后生”之詞與杜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4如出一轍。錢有“過都歷塊皆神駿,秋駕何當與細論”(其六),其中的“過都歷塊”當來自杜甫之“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5。錢有“麗句清詞堪大嚼”(其十六),亦來自杜甫“清詞麗句必為鄰”6。其次是句法。錢有“姚叟論文更不疑,孟陽詩律是吾師”(其一),來自杜甫《解悶》詩“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7。錢有“高楊文沈久沉埋,溢縹盈緗糞土堆”(其四),仿杜甫之“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8。錢有“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鐘譚作后塵”(其十一),來自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9。當然,其間還有對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的一些承繼。如錢有“昭容一語是天真”(其十一),似乎來自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其四“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10之句。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杜甫和元好問論詩詩數量的差異,杜甫是六首,元好問則是三十首。錢謙益論詩詩卻與數量較少的《戲為六絕句》形成更緊密的關聯,其中所展現的可能不僅僅是一種文本的呼應關系,更是對杜甫論詩詩背后精神的認同。換言之,錢謙益可能面臨著同杜甫更為相近的時代困惑。
唐代中期的詩壇有“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11的風氣,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稱當時情況是:“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秾莫備。”12杜甫論詩詩正是表達了對當時詩壇風氣的批判。《戲為六絕句》有“才力應難夸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1等句,俱是表達對時人妄自托大、不尊前賢的批評,亦即所謂的“好古者遺近”,于是杜甫指出“轉益多師是汝師”2的學詩途徑。黃生《杜工部詩說》云:“諸章備見公論文之旨,蓋因當時后生輕薄前賢,特發此論。大旨在篇末‘轉益多師一句。言博取自益,乃為善學,嗤點前賢,徒傷輕薄耳。”3錢謙益在箋注《戲為六絕句》時也發揮了這種精神:“‘不薄今人以下,惜時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正告之也。‘齊梁以下,對屈宋言之,皆今人也。不薄今而愛古,期于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為鄰則可耳。今人侈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后塵,不亦傷乎。”4
錢謙益論詩詩也表達了對時人嗤點前賢行為的不滿。其二云:“一代詞章孰建鑣,近從萬歷數今朝。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表明錢謙益對前賢建鑣詞章功業的認可,而后世不應隨意嘲諷。這種態度幾乎貫穿于錢謙益的一生,在他去世前一年即康熙二年(1663)所寫的《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九中,仍可見到他對時人妄議前賢的不滿:“詞場稂莠遞相仍,嗤點前賢莽自矜。北斗文章誰比并?南山詩句敢憑陵。昔年蛟鱷猶知避,今日蚍蜉恐未勝。夢里孟郊還拊手,千秋丹篆尚飛騰。”5其中“詞場稂莠遞相仍”與論詩詩主題“共論近代詞人”,“嗤點前賢莽自矜”與論詩詩“嗤點前賢豈我曹”都一脈相承。他開篇便批判當時的文壇仍是良莠不齊的局面,一些人為了夸飾自己不惜隨意貶低前賢。這種對“前賢”的執念,錢謙益可謂一以貫之。
而且,由于不滿時人嗤點前賢的行為,錢謙益還面臨時代帶來的新問題。“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堪稱這十六首詩的思想核心。那么,“大雅”是什么?錢氏《虞山詩約序》說:“諸子挾其所得,希風而尚友,揚扢研摩,期以砭俗學而起大雅。余雖老矣,請從而后焉。”6從這里可以看出,“大雅”是為糾正“俗學”之弊的一個準則。那么,“俗學”又是什么?錢謙益有相關論述:
諺有之,海母以蝦為目。二百年來,俗學無目,奉嚴羽卿、高廷禮二家之瞽說以為蝦目。而今之后,人又相將以俗學為目。由達人觀之,可為悲憫。7
少奉弇州《藝苑卮言》,如金科玉條。及觀其晚年論定,悔其多誤后人,思隨事改正。而其贊熙甫則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蓋弇州之追悔俗學深矣。8
時人沉湎俗學,掇拾饾饤,夸詡漢、魏、三唐,如以嚼飯喂人, 人徒增嘔噦耳。9
俗學謬種,不過一贗,文則贗秦、漢,詩則贗漢、魏、盛唐。10
從上述材料可知,錢謙益所言“俗學”固然有經學層面的意義,但在詩文層面主要是指復古派及其后學。第一則材料,錢氏反對嚴羽的“詩必盛唐”說,這也是復古派理論的濫觴。第二則材料,錢氏不惜炮制“弇州晚年定論”說,稱王世貞后悔年輕時追隨復古派,此處“俗學”即復古派無疑。第三、四則材料,錢氏直接撻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這正是復古派所舉的大旗。而“時人沉湎俗學”是說當時的一些詩人文士仍奉復古派為圭臬,錢謙益對此十分不滿,因此扛起“大雅”之旗以反對復古派的余波。
因而,錢謙益論詩詩中還包含對杜甫“別裁偽體”精神的發揚。他解釋“別裁偽體親風雅”云:“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偽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1在他看來,復古派正是“偽體”的鼓吹者。錢氏《徐元嘆詩序》說:“自古論詩者,莫精于少陵別裁偽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偽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為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說,嚴羽卿辭而辟之,而以盛唐為宗,信羽卿之有功于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為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涂鼓之毒藥。甚矣!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2可以說,錢謙益在杜甫那里找到了“別裁偽體”的共鳴。錢氏《列朝詩集小傳》云:“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后有能別裁偽體如少陵者,殆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獲罪于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3這段話正表明了錢謙益不惜被人詬病,也要以“別裁偽體”振作詩風的信念。他繼承杜甫的詩學精神,希冀可以去偽存真,以矯正詩壇的弊病。
二、“戲作”之題的意蘊
錢謙益論詩詩題名曰“戲作絕句十六首”,明顯祖述杜甫“戲為六絕句”之題,但“戲作”便是游戲之作、隨意之作嗎?郭紹虞說:“杜甫《戲為六絕句》,開論詩絕句之端,亦后世詩話所宗。論其體則創,語其義則精。蓋其一生詩學所詣,與論詩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爾游戲視之也。”4點明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莊重性,決非游戲之作。錢謙益論詩詩與其某些序跋的文學主張可以相互發明,足見非一時隨意之作,而是錢氏文學思想的一次系統表達。并且,從對杜甫論詩詩主旨的多方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戲作”之題的復雜性,以及在錢謙益那里的某種延續。
歷來關于杜甫《戲為六絕句》中“戲為”的討論有以下幾種觀點:或認為此組詩乃杜甫自況之作,因嫌于自許,故曰“戲”,許寶善《杜詩注釋》云:“蓋杜公當日,時輩必多譏誚之者,故慨然而作此詩。”5或認為此組詩為告誡后生之作,因語多諷刺,故曰“戲”,仇兆鰲《杜詩詳注》云:“此為后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6或認為此組詩為自述論詩宗旨之作,因詩忌議論,故曰“戲”,朱彝尊《曝書亭杜詩評本》云:“詩最忌議論。議論雖卓,猶戲也。”7或認為此輩不足論文,故曰“戲”,吳見思《杜詩論文》云:“《六絕》為今人論文之作。然此輩豈足論文者哉!故曰‘戲也。”8或有綜合以上幾種觀念者,不一而足。這為我們討論錢謙益論詩詩的“戲作”動機提供了廣闊的視角。
我們先看錢謙益在《錢注杜詩》中是如何看待杜甫《戲為六絕句》的。錢氏云:“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為六絕句,蓋寓言以自況也。韓退之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群兒之謗傷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題之曰‘戲,亦見其通懷商榷,不欲自以為是,后人知此意者鮮矣。”9錢謙益認為杜甫《戲為六絕句》是其自況之作,其實這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反對謗傷,二是嫌于自許。錢氏的此種態度亦可轉嫁到其論詩詩之中,而這在元好問的論詩詩中是見不到的。郭紹虞評價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云:“杜甫《戲為六絕句》猶有寓言自況之意,此則就詩論詩,非由憤激,更無寄托。”1
錢謙益論詩詩第二首云:“一代詞章孰建鑣,近從萬歷數今朝。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裴世俊說:“此詩可看作是錢謙益的詩學理論綱領,亦可當作自我寫照。”2正是說明此組論詩詩“自況”的意味。雖然這首詩表面意思是贊美前賢的功績,后輩不可隨意批評,但是錢謙益明顯將自己置于一個“挽回大雅是己事”的位置,可見其隱約的文壇盟主意識。又,第一首有“溪南詩老今程老,莫怪低頭元裕之”句,《列朝詩集小傳·松圓詩老程嘉燧》:“遺山題《中州集》后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無裕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謚之曰松圓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陽如裕之者。”3這段話通常被解釋成錢謙益對程嘉燧的推崇,但其實還有更隱晦的意思,即“錢氏欲以元好問的繼承者自居,因而把它放在開宗明義第一首,立字當頭,高自標識”4。正因懷有這種意識,錢謙益對近代詞人評頭論足,大力撻伐復古派和竟陵派,是不折不扣“嗤點”的立場;同時,他又反對時人“嗤點”前賢的行為,而曰“嗤點前賢豈我曹”。可以說,錢謙益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而這也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后來的沈德潛《與陳恥庵書》批評道:“當鐘、譚極衰之后,錢氏之學行于天下,較前此為盛矣。然而推激有余,雅非正則,相沿既久,家務觀而戶致能,有詞華無風骨,有對仗無首尾,甚至譏誚他人,則曰‘此漢魏‘此盛唐,耳食之徒,有以老杜為戒者。”5這段話指出錢氏嘲諷復古派等所帶來的負面后果——使得時人以“漢魏”“盛唐”等作為標簽攻擊他人。反觀杜甫,并沒有面對“前賢”時的矛盾心態,因為無論是先秦之風雅,還是漢魏之庾信,乃至“初唐四杰”,他都持一種贊揚的態度,所以他反對時人“嗤點”的行為也就顯得理直氣壯。如果將杜甫和錢謙益的論詩詩都看作“自況”的寫照,那么杜甫的“戲作”帶有緩解在別人面前自以為是的意味,而錢謙益則是設法走出自我設定的“嗤點前賢”的怪圈。
錢謙益論詩詩在論及近代詞人之時,亦語多諷刺。其三云,“何事后生饒筆舌,偏將詩律議前賢”,批評后生對湯顯祖不滿的態度;其九云,“關隴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兢丹黃”,不滿人們對復古派的追隨;其十一云,“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鐘譚作后塵”,揶揄竟陵派被藝妓所輕視;其十五云,“憑君若問金條脫,解道《南華》是僻書”,諷刺時人不讀書、無學問而為詩的傾向。這些詩句均涉及對近代乃至當世詩人的批評。將諷刺寓以戲筆之中,正消解了內容背后劍拔弩張的意味。而且,錢謙益論詩詩中“我”的出現,使其詼諧意味增加,在“戲作”之題中含有了游戲筆墨的成分,這是杜甫論詩詩中所沒有的。如其十四云,“贏得老夫雙眼飽,探箱撫壁每長吟”,其十六云,“麗句清詞堪大嚼,老夫只合過屠門”,都刻畫出一個對時人大為贊賞甚至自愧不如的“老夫”形象。這個略帶詼諧的老夫形象與欲重建詩風的文壇盟主形象大相徑庭,卻意外達到了一種調節前面某些過激之詞的效果。
不容忽視的是,錢謙益論詩詩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存在一個對話者——姚士粦(字叔祥)。錢氏論詩詩題為“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其中有一重要字眼,即“共論”。像杜甫以“爾曹”為假想的議論對象,元好問也說“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6,他們不僅沒有當面的對話者,而且其高瞻遠矚的詩學思想也鮮有時人的回應。錢謙益此處“共論”“戲作”的說法消解了孤獨的意蘊,同時也減弱了自身“乾綱獨斷”的意味,仿佛是兩個人隨意談話的記錄整理。當然,因為姚士粦的在場,錢氏的言論未必完全客觀。比如,錢氏論詩詩第一首開篇便曰“姚叟論文更不疑”,以示對姚氏的夸贊,但對比他人對姚氏的評價,可見出問題。如清代沈叔埏諷刺姚士粦食古不化、作詩艱澀:“老儒乃海鹽姚士粦叔祥也。其人嘗以文字佐公,負書簏之稱,蓋食古而未化者也。公寄詩有‘百靈看豹變,千眼豁狐疑句,推許甚至,余讀之,大抵奧衍而艱澀者類叔祥所為。”1又,朱彝尊批評沈思孝晚年詩風因受姚士粦影響而變得詰屈聱牙:“(沈思孝)晚交姚叟士粦,未免間作嗷牙語。”2這些評議對比錢氏論詩詩,可以看出錢氏的夸大處,足見在這種“對談”之中含有某些“投鼠忌器”的成分。
三、三個視野的觀察
一般來說,論詩詩通常會有三個視野,即古典視野、近代視野與當世視野。所謂古典視野是指遠在本朝以前的時段,此時段的詩人作品通常已成為經典;近代視野是指本朝伊始(或去今未久的前朝)到作者當世之前的時段,此時段的詩人作品往往處于受到爭議的階段;當世視野是指作者生活的時段,此時段的詩人作品往往是被批判的對象。這一劃分不過為了論述方便,其間仍會有一些問題,比如在所論述對象之中,有些人生活在易代之際,有些人是作者的前輩但又有一定生活時段交叉等,這些應視具體情況而論。實際上,杜甫、元好問、錢謙益的論詩詩都含有三個視野的影子,但側重又有不同。
在杜甫那里,古典視野便是先秦兩漢及魏晉,近代視野便是南北朝至初唐,當世視野便是盛唐、中唐。具體到詩歌所指,古典視野便是“風騷”“漢魏”“古人”,近代視野便是“齊梁”“庾信”“王楊盧駱”“爾曹”“前賢”,當世視野便是“今人嗤點流傳賦”“才力應難夸數公”“恐與齊梁作后塵”“未及前賢更勿疑”3等詩句所論述之人。可見,杜甫論詩詩的論述對象主要集中在近代視野與當世視野,古典視野只是作為一個比較的存在。從這方面說,元好問與之大不相同。元好問所論述的詩人主要生活在漢魏至北宋這一時期,其中漢魏晉南北朝詩人主要有曹植、劉楨、劉琨、阮籍、張華、謝靈運、陶淵明、潘岳、陸機、庾信,唐代詩人主要有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李白、杜甫、孟郊、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商隱、溫庭筠、盧仝、陸龜蒙,宋代詩人主要有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秦觀、陳師道,這些詩人與元好問所生活的年代相距久遠,基本都屬于古典視野,因為北宋以后的詩人是沒有的,近代視野與當世視野也無從談起。相較之下,錢謙益論詩詩與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論述視野頗為相近,從其詩題“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便可看出,他所論述的主體屬于近代視野與當世視野。這顯示出錢謙益和杜甫為當世詩歌的書寫尋求出路的用心,他們將挽回詩壇的衰頹之風當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近代視野中,錢謙益褒揚了臺閣體、吳中派、公安派,撻伐了復古派與竟陵派。這與他在《題懷麓堂詩鈔》中的認識是一致的:“近代詩病,其征凡三變:沿宋、元之窠臼,排章儷句,支綴蹈襲,此弱病也;剽唐、《選》之余沈,生吞活剝,叫號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島之旁門,蠅聲蚓竅,晦昧結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傳染日深,膏盲之病日甚。”4所謂“狂病”“鬼病”正分指復古派與竟陵派。不過,這已是學界共識,筆者亦不打算在此方面展開論述。值得注意的是,這組詩中所透露出的一些細節頗可玩味。
論詩詩第四首云:“高楊文沈久沉埋,溢縹盈緗糞土堆。今體尚余王百谷,百年香艷未成灰。”“高楊文沈”指的是高啟、楊基、文征明、沈周四人,此四人本屬于不同的文學藝術團體——高啟、劉基、宋濂并稱“明初詩文三大家”,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并稱“吳中四杰”,文征明、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并稱“吳中四才子”,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稱“明四家”,錢謙益將“高楊文沈”四人匯集起來,是因為他們都是蘇州人氏,亦即吳中風流的代表。此詩寫吳中傳統中斷已久而不被人重視,后幸有王稺登(即王百谷)接續,因而百年之后還有傳承。《列朝詩集小傳·王較書穉登》云:“吳門自文待詔歿后,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谷振華啟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余年。”1正是闡述了王氏的功績。錢曾箋注此詩云:“高啟,字季迪,長洲人。隱居松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與楊基孟載、張羽來儀、徐賁幼文為詩友,人稱吳中四杰。……沈周,字啟南,文征明,初名壁,后以字行,更字征仲,俱長洲人。吳中自北郭十子之后,風流文翰,聲塵迢然。至成、弘時,啟南、征仲輩流,閑居樂志,區明風雅。與唐解元寅、祝京兆允明,以詩文相映發,間出其閑情逸致,點綴圖繪。百年以來,中吳人物之盛,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迨及王穉登百谷,咀華披秀,流傳香艷,復擅詞翰之席者三十余年。蓋文、沈之遺韻,至百谷而如有所歸結焉。”2錢曾這段箋注可以看作一個簡明的明代吳中文學發展史,而這正提示了錢謙益此詩所隱含的意圖。
第九首云:“關隴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競丹黃。吳中往往饒才筆,也炷婁江一瓣香。”此詩前兩句旨在批評“何李”,即何景明、李夢陽所代表的復古派,而后兩句中關于“婁江”(即王世貞)的解讀往往產生錯誤。裴世俊稱:“以本詩看,他用‘關隴英才評價‘何、李,而于本鄉前輩、又是錢家夙好世交的王世貞,則是‘也炷婁江一瓣香,還仿效王陽‘弇州晚年定論,向世人昭告王世貞晚年的‘自贖,揭示七子派在復古中的新變,為其反復古的詩學理論張目。”3此解讀說明錢謙益對復古派的差異性批評,對何、李毫不留情,對王世貞則比較同情,且還炮制了“弇州晚年定論”為王氏開脫。但這種解讀的誤區在于把“也炷婁江一瓣香”的主語當成了錢謙益,其實這句詩的主語應是“往往饒才筆”的“吳中”。嚴志雄稱“此首當以‘反諷(mockery)讀之”4,可謂正解。“關隴”指陜西甘肅一帶,而李夢陽是甘肅慶陽人,何景明曾任陜西提學副使,可見關隴地區是復古派的大本營,此地的“英才”自然多受其“蠱惑”;而吳中地區本不應與其“同流合污”,但由于他們聲勢浩蕩,也有一些人追隨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復古派。所謂“英才”“一瓣香”云云俱是反諷追隨復古派者。這表明錢謙益對吳中士人追隨復古派的行為大為不滿。
在當世視野中,杜甫對時人雖然不滿,但更多的是一種勉勵的態度,而言“轉益多師是汝師”。換言之,杜甫眼中的時人是一個泛化的群體,他并未將時人做出區分。錢謙益則有所不同,他一方面批評時人菲薄前賢、溺于俗學的行為,另一方面,又對某些時人點名表揚:其一云,“姚叟論文更不疑,孟陽詩律是吾師”,贊美姚士粦與程嘉燧;其五云,“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博雅擅青箱”,贊美董其昌與王惟儉;其七云,“當筵縱筆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贊美曹學佺與尹伸;其八云,“畫筆南翔妙入神,晚年篇翰更清新。和陶近愛歸昌世,也是風流澹蕩人”,贊美李流芳與歸昌世;其十一云,“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鐘譚作后塵”,贊揚王微和楊宛;其十二云,“草衣家住斷橋東,好句清如湖上風。近日西陵夸柳隱,桃花得氣美人中”,贊美王微與柳如是。所以,錢謙益論詩詩對當世視野的批評處于一種矛盾之中。他以自己的詩學觀點對時人做出區分,對追隨復古派、竟陵派等不符合其詩學標準的時人極為不滿,而對一些符合自己詩學標準的時人大加贊賞。從這方面來說,錢謙益論詩詩仍透露著他以文壇盟主身份自比的意氣。
四、論述的文體與群體以及文本的“節點”意義
論詩詩的經典文本源頭是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在其影響下所產生的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亦成為經典文本,二者皆引來后世無數的仿效。而錢謙益的這十六首論詩詩,后世似乎沒有相關的仿作,這一方面源于錢謙益論詩詩的題目具有“私人化”特點,后世難以在題目上標明仿效,另一方面,也因為論詩詩的體裁在元好問時已臻于成熟,后人的開拓進境襯托不顯。倘若從錢謙益論詩詩所論述的文體及群體來看,則后世仍有很多論詩絕句受其沾溉。
就論述的文體而言,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雖通常被視為論述詩歌之體,但也有學者認為其所論述的內容并不限于詩歌。黃鶴認為杜甫這組詩是論文章之體的:“公雖戲為《六絕》,而俱言作文大概,欲人以庾信為法,而以楊、王、盧、駱為戒,蓋亦默寓其祖得作文之正體也。”1宗廷輔認為杜甫這組詩第一首論賦,第二首論文:“古人鑄題,極為不茍,如是論詩,何不曰‘戲成論詩六絕乎?且第一首‘賦字,第二首‘文字,作何安頓?如引《文選》為說,《文選》亦是以文概詩,未聞可指詩為文也。讀者審之。”2這表明論詩絕句始發時,論述的內容可能不僅僅限于詩歌。
這種現象在錢謙益論詩詩中更是蔚為大觀。錢謙益論詩詩論述了詩歌、古文、戲曲等文體。其一云:“姚叟論文更不疑,孟陽詩律是吾師。溪南詩老今程老,莫怪低頭元裕之。”詩歌當然還是錢氏論述的主體內容,組詩第一首所謂“詩律”“詩老”云云,皆是論詩;但“姚叟論文更不疑”可能就暗示其所論述的是一個廣義的“文”。其八贊揚李流芳“晚年篇翰更清新”,李氏乃“嘉定四先生”之一,而嘉定老生宿儒,皆出自歸有光之門,承傳唐宋派古文家法,故此處“篇翰”不只是詩歌。其三云:“崢嶸湯義出臨川,小賦新詞許并傳。何事后生饒筆舌,偏將詩律議前賢?”此首論述湯顯祖的成就,“新詞”當指湯氏之詞曲,所謂“詩律”蓋言諸生非議湯顯祖戲曲不合格律。如王驥德《曲律》云:“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 舌。”3故此處論及的文體不僅超越了詩、文,又加以戲曲。以上所論只局限于文學文體方面,而錢謙益論詩詩所論述的廣度早已超越于此,轉向更為廣闊的藝術門類,“文體”一詞已難以概括,可使用“群體”一詞予以類分。
依職業而分,錢謙益論詩詩論述了文學家、批評家、書法家、畫家等群體。文學家群體已在前文論及,但此處文學家應特指文學創作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文學批評家受到錢謙益的贊譽,如其十六云:“梁溪欣賞似南村,甲乙丹鉛靜夜論。麗句清詞堪大嚼,老夫只合過屠門。”后有自注云:“梁溪華聞修、黃心甫評定明詩三十家。”正是贊揚批評家的眼光。其四云,“高楊文沈久沉埋”,高啟、楊基是詩人;文征明不僅是詩文大家,也是著名的書畫家;至于沈周更是以畫名世。其五云,“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博雅擅青箱”,贊揚董其昌與王維儉。董其昌乃一代書畫大師,錢氏稱其“玄宰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4;王惟儉是文物收藏家、鑒賞家,錢氏稱其“好古書畫器物,不惜典衣舉息,家藏饕餮周鼎、夔龍夏彝,皆一時名寶”5。董、王二人在天啟年間并稱“博物君子”,錢謙益將兩者并舉,顯然并非論述其詩文成就。其八云,“畫筆南翔妙入神”,直言贊美李流芳的畫作成就。這些都可看出此組詩的論述范圍包含了豐富的文學藝術體裁。
依性別而論,錢謙益論詩詩也給予女性群體重點關注。其十一云:“不服丈夫勝婦人,昭容一語是天真。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鐘譚作后塵?”王微、楊宛是明末的歌妓,此詩言二女巾幗不讓須眉,可使竟陵諸子自慚。其十二云:“草衣家住斷橋東,好句清如湖上風。近日西陵夸柳隱,桃花得氣美人中。”此詩前兩句稱贊王微,后兩句稱贊柳如是。以上兩首所言王微、楊宛、柳如是,俱是當時才妓。錢氏對她們的關注,一方面可能受到當時文人對女性才藝贊揚的社會風氣影響,另一方面,也與他本人對女性詩人的欣賞有關。在他所編的《列朝詩集》中,女性詩人被分為上、中、下三編錄入,即香奩上三十六人、香奩中五十七人、香奩下三十人1,足可為證。
錢謙益論詩詩題名為“論近代詞人”,他故意采用“詞人”說法,而不用“詩人”,可見這組論詩詩的內容已非詩體所能概括。即使在行文中,錢氏也頻頻采用“詞章”“詞客”“清詞”等字眼,意在超脫詩歌文體的局限。所謂“詞人”“詞客”,本指擅長文詞之人,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時世宗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充翹館。”2但從錢詩所論述群體而言,“擅長文詞之人”的解釋也不能概之,嚴志雄將此解釋成“人文世界”的建構,頗有道理。不過,嚴先生從此出發,提出須反思今日文學分科之狹隘,筆者有不同意見。古人的藝術修養豐富,現在的學科分類嚴苛,由此造成古今學者知識結構的不對等,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倘從錢謙益論詩詩中言此,則未免將其意義過于泛化。此詩的意義是處于一個轉換的關口,錢謙益既承傳了杜甫、元好問論詩詩的傳統,也為后世開啟了變奏的法門。張伯偉說:“錢謙益在清初詩壇地位甚高,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論詩絕句,實奠定了清人論詩詩的基調。”3
首先,錢謙益之后出現很多專門論說藝術門類的絕句。論詞體有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周之琦《論十六家詞絕句》等;論曲體有凌廷堪《論曲絕句三十二首》、舒位《論曲絕句十四首并示子荺孝廉》等;論畫有宋犖《論畫絕句二十六首》、吳修《論畫絕句》一卷等;論書法有王芑孫《論書絕句十二首》、石韞玉《論書絕句》三十首等。這些論說絕句所涉及的廣闊藝術門類在錢謙益的論詩詩中已有肇端。
其次,錢謙益之后的論詩詩對女性作品的態度發生巨大轉變。早期論詩詩對女性詩歌創作的評價并不高。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二十四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4以“女郎詩”來嘲諷秦觀作詩氣格卑弱,可見此時的“女郎詩”還處于卑下的地位。而錢謙益論詩詩對王微、楊宛、柳如是等藝妓的作品俱是贊美之詞,此后的論詩詩也大多持相似的立場。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其十七云:“芍藥薔薇笑女郎,溫柔詩教試推詳。要知品格分題目,楚霸虞姬各擅場。”5這里說明男性與女性在詩歌的風格上各有擅長,不可一味貶低“女郎詩”。又如沈德潛《挽徐媛詩》三首其二云:“南樓點筆苦沉思,一樣蒼茫獨立時。拈出詠梅超逸句,誰嫌渠是女郎詩。”6沈氏在最后直接跳出來為“女郎詩”辯護。在此種流變中可觀錢謙益論詩詩承上啟下的地位。
最后,杜甫和錢謙益的論詩詩都著重于近代視野與當世視野,但杜甫著眼的是一個更加形而上的問題,所論及的王、楊、盧、駱與他不存在任何交集;錢謙益關注的則是一個更加實際的層面,所論述的程嘉燧、董其昌、柳如是等都同他有過交往。換言之,錢謙益論詩詩還透露著“懷人詩”的傾向。這種意味在后世論詩詩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從袁枚而后論詩諸家,論述率多以時人為主,或僅論同代清朝之詩人,此亦可解釋當時懷人詩何以特多之故”7。袁枚《仿元遺山論詩》雖題目標明仿照元好問論詩,但實際所論述的大多為近代視野與當世視野,與元好問所論古典視野大不相同。袁枚這組詩的小序也有說明:“遺山論詩古多今少,余古少今多,兼懷人故也。”8也點明了這組詩的性質。而且袁枚每首詩后都注明所論之人的姓名,如第一首:“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后注“王新成”。9這種方式可以看作錢謙益論詩詩方法的延續,錢氏經常在詩中注明所論之人,如第六首“楚國三袁秀絕塵”句,后自注“公安袁中道”;“白眉誰與仲良倫”,后自注“新野馬之駿”。這種以近人為論述主體的論詩詩還有管世銘《論近人詩絕句》十六首、林昌彝《論本朝人詩一百五首》、李綺青《論國朝詩人》十五首等,皆可看到錢謙益論詩詩的影子。
結? ? 語
錢謙益的一生與杜甫有太多的關聯:他詩風學杜,晚年還有專門模仿《秋興八首》而作的《后秋興》一〇四首;他所作的《錢注杜詩》也成為杜詩箋注史上的經典。不過,他們在詩學方面的聯系學界的關注并不多。以錢謙益的論詩詩鏈接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則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樣本以考察二者的詩學關系。錢謙益的論詩詩中能看到對杜甫《戲為六絕句》承繼的眾多線索,諸如時代困惑的思考、“戲筆”的斟酌、詩歌流變的觀察、論述群體的考量等。可以發現,他們都不是將論詩詩作為一種逞才的文字游戲,而是落腳于對當代詩歌出路的探求。不過,時代仍然賦予了錢謙益論詩詩新的內涵及其在歷史長河中的“節點”意義。至于此后出現的大量論詩詩,還有巨大的研究空間,值得進一步挖掘。本文的寫作也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即對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予以深入分析,并且融合作者心緒與時代新變予以考量。這也提示我們,明清詩歌的研究須轉向精深化、精細化的方向,而不能僅僅作為框架下的材料被一筆帶過。
[責任編輯 馬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