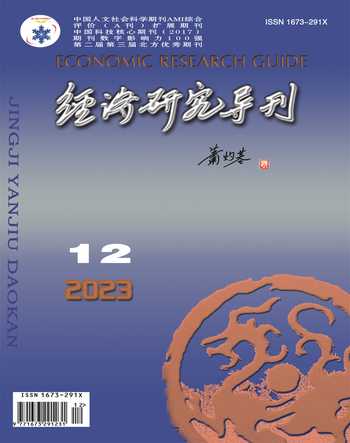報批義務的法律問題
張雨欣
摘? ?要:根據《民法典》第502條第2款的規定可知,存在著一類合同只有經辦理了相應的批準手續合同才會生效,由此,即會產生一種需要合同雙方當事人負擔的義務——報批義務。但對于該義務的性質認定以及違反該義務承擔的責任類型等方面,學界尚未達成統一的意見。因此,從報批義務的概念以及來源出發,對其性質定位問題予以探討,并進一步分析《民法典》第502條,從而肯定了報批義務的獨立性。最后整理了有關報批義務違約責任類型的幾種觀點。
關鍵詞:報批義務;獨立生效;締約過失責任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3)12-0155-03
經批準生效合同若要生效,則需經過合同當事人申請、行政機關接收申請后進行審查,符合條件的予以批準后合同方可生效。此時即存在一種義務,也就是報批義務。研究報批義務有利于正確處理對待公法與私法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有利于保障雙方當事人的合同權益。通過對其性質、違約責任的類型等進行探討,也可以使得法官審理裁判案件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從而推定司法實務的進程,進一步提高審判效率。
一、報批義務概述
(一)報批義務的概念
報批義務也被稱為“申請義務”[1]。報批義務的運作機理即締約雙方基于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準備好相關的報批材料,由其提交給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接收后需經受理、審查、決定等程序,最終決定是否批準該申請。
報批義務究竟由誰來承擔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報批事項的義務主體,此種情形下即須要根據法律規定進行。第二種情形是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并未明確規定報批義務人,但是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有具體的相關約定。第三種情形是一方當事人有證據證明合同的對方當事人手中持有履行報批手續所需要的相關一系列材料,此時報批義務即由持有資料的一方當事人主體承擔。
(二)報批義務的來源
現今學界存在一種通說觀點,即須經行政審批才生效的合同在尚未生效的情形下,并非對合同任何一方當事人均無約束力。然而,學者們對其具有的這一部分約束力能否產生積極的報批義務則存在著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只有締約合同的當事人事先約定,才會產生相應的合同約束力[2];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須經行政審批的合同在未生效之前具有合同約束力且足以產生積極的報批義務。此時若要討論何時能夠產生報批義務,則理應從不同情形分別探討。一種情形是締約雙方當事人明確約定了,此時雙方約定的該條款獨立生效。其原因為訂立該條款的目的即是為了促進合同生效,如果該條款本身并未生效,則可能會出現不利于一方合同當事人的情形,即報批義務人只有在對自己有利的情形下才會積極履行報批義務,一旦發現有不利于自身的情況發生,即怠于履行報批義務。此時,由于有關該報批義務的條款尚未生效,則可能會使合同的訂立陷入僵局。實務界存在一種觀點,即存在著兩種合同條款,他們均獨立于合同本身而生效,其中一類條款存在的意義是為促進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另一類條款的目的是在合同終止后解決基于合同產生的爭議與糾紛[3]。有關報批義務的條款屬于第一類條款。在2019年出臺的《九民紀要》中對報批義務條款的獨立性即予以了肯定,接著又在隨后出臺的《民法典》第502條內容中肯定了報批義務條款的獨立性。若根據《九民紀要》的規定,立法者似乎并不認同需經行政審批的合同在未生效狀態下,對合同各方的法律拘束力能產生積極的報批義務。但是,有關附條件生效合同的效力問題,締約當事人除了要受相關合同條款約束外,還被賦予另一項義務,即不得阻止該生效條件的成就。根據這一觀點也可以推出,未經行政審批合同的當事人也要受這一條件的約束。韓世遠教授認為,在合同還處于尚未生效的狀態時,當事人雖然沒有擁有合同約定的實質性權利,但是如果他已經擁有了相應的期待權,那么此時法律亦應當對其期待權予以保護。此時,在須經行政許可生效的合同中,倘若負有報批義務的當事人并未履行報批義務,則屬于對合同相對人期待權的一種侵害。
(三)報批義務的性質
報批義務能夠左右合同生效與否,并且其在合同成立與生效之間建立了一個重要樞紐,是須經行政審批生效合同從未生效走向生效的唯一途徑。因此,在此種情形下,只要負有報批義務的一方當事人拒不履行其負擔的義務,此時合同就將無法生效,極易陷入僵局狀態。對于其性質亦存在許多不同觀點,主要有三個學說:先合同義務說、附隨義務說、從給付義務說。前述義務均源自于債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4],現行法律對此也予以承認,即報批義務是基于誠信原則產生的。但其本質具體屬于什么尚處于爭議狀態。下面是學界有關報批義務性質的一些觀點。
首先是先合同義務說,指合同訂立但未生效時,締約雙方基于誠實信用原則負有的告知、協力、保護等義務。先合同義務是不以給付為內容的法定義務。報批義務與其相似,其同樣不具有給付內容,屬于程序性義務。先合同義務的產生階段為合同訂立階段,此時雙方當事人正在磋商以求訂立合同。其存在的時間階段與報批義務高度重合。因此,持有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無論是法定報批義務還是約定的報批義務,均屬于先合同義務。
其次是附隨義務說,此觀點也是源于報批義務的產生節點,在合同成立但并未生效的狀態下,其作用就是為了輔助合同去發力。我國實務界與理論界對附隨義務均有較大的爭議,所以對其并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但大致觀點均認為附隨義務的作用即為對合同進行補充輔助。顯然,本文所提到的報批義務內容相較于附隨義務顯得更為重要,因此若單純地將報批義務視為附隨義務顯然有失偏頗。
學界中還有一個觀點便是從給付義務說。從給付義務是一個相對概念,其是相對于主給付義務而言的。該觀點主張合同當事人通過約定可以形成報批義務,經約定后形成的義務即為約定義務。其主張,通過約定可以形成報批義務,約定之后其即為約定義務,若依據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進行報批時則為法定義務。該學說認為,報批義務存在的作用是使得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合同發生法律效力,此即為促進主給付義務實現。對該學說持肯定態度的學者認為,合同未生效但報批義務獨立于合同,屬于從給付義務[5]。據此,依前述可知,報批義務的功能在于使其通過審批促使合同生效,若未履行報批義務,則此時不能啟動主給付義務。然而,從給付義務最重要的功能是輔助主給付義務確保其順利履行,所以二者在功能上仍存在明顯差異。
二、報批義務的獨立性
(一)對報批義務與未生效合同關系的正確解讀
尚未經行政審批生效的合同,其因缺少報批環節導致其并未發生法律效力,所以,報批義務在未生效合同問題中顯得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依據前述可知,報批義務的本質雖然屬于行政許可,但因其具有另一項重要功能,即與合同的效力有關,可以促進合同生效,因此與合同密切相關,此功能也奠定了其在私法上的重要意義。因此,厘清報批義務的性質與未生效合同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厘清關系,才能正確理解適用報批義務與未生效合同之間的私法規則。合同中除了約定的義務外還會存在法定義務,它們并非是基于合同自由而出現的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前述法定義務不需要前提條件,其可以發生在合同履行的各個階段,并沒有時間段上的限制。因此,報批義務作為先合同義務,其存在于合同成立中生效前的階段,即有可能獨立于合同本身而發生效力。未生效合同中雙方當事人也可以約定輔助性給付義務。因此,即便合同未生效,也可能有生效條款的存在,堅持認為合同未生效則其全部條款均未生效的觀點是錯誤的。合同雖未生效但合同中仍存在有效的可履行的條款。
(二)報批義務具有程序價值
在一個合同中主給付義務的功能是實現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完成雙方之間的利益交換,具備實體性的性質和功能。但是,報批義務并不能進行利益交換,其僅具備促進合同生效的獨立程序價值,若不能實現程序價值,則實體價值也無從談起。否認報批義務的程序價值、否認報批義務的獨立性,則意味著他的實體價值也失去了意義。從此意義上看,報批義務類似于合同中的爭議解決條款,這些條款均有一個共性,即都是純粹的程序性條款,并不涉及任何實體權利,且獨立于合同的實體條款之外。只不過前者是在合同未生效之前,在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下解決合同能否順利生效的問題,后者則是在合同無效、被撤銷等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情況下,解決合同最終如何處理的問題,二者本質上并無差別,均是為合同不能履行創造一個解決辦法。
經約定的報批義務。經審批生效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為了履行合同而訂立,為了避免相關義務人不履行義務以使得合同不能生效,合同雙方可以約定基于一定的利益獲得賦予一方當事人以報批義務。此種情況下,義務人相當于進行了一定的利益交換。獲得了一定利益則需要遵守相應約定,即受到報批義務的掣肘。這時,報批義務的履行即遵照了雙方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報批義務當然地可以獨立生效。德國學者弗盧梅認為,一份合同如果一定要以一定的法律條件作為生效要件,則其可以通過合同雙方約定相應的協助義務,來促使合同發生法律效力。雖然報批義務是須經批準才能生效的合同的關鍵,但是因為合同當事人此時負有協助報批義務人獲得審批的義務,此種情形下與未生效合同的效力并無關系,當事人之間可以獨立地約定報批義務,當然也可以認為報批義務是須經行政審批生效合同的默示條款[6],獨立于合同效力。報批義務是默示存在的,也是當事人實現合同目的的必經程序。之所以承認報批義務條款的獨立性還有以下優勢。除了區分實體功能和程序功能之外,承認報批義務條款的獨立性更符合當事人的真實意愿和正當期待,其亦符合司法審查形式化的要求[7]。
三、報批義務的違約責任類型
我國《民法典》第502條對于違反報批義務的責任進行了相關規定,但表述得較為概括,并沒有具體指出違反報批義務所要承擔責任的性質。雖然通過過去的相關規定可知立法者將其定性為締約過失責任,但是又規定了與違約責任類似的救濟方式。由此可以看出,立法在此存在矛盾之處,學界對于此處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所以各執一詞。以下是有關違反報批義務責任性質的學說爭議。
第一種學說為締約過失責任說。該學說早在古羅馬時期即已出現,主要來源于德國學者椰林。對該學說持肯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報批義務人負有報批義務,其義務來源于誠信原則,屬于《民法典》合同編第500條所包含的違反誠信締約的行為,應當承擔的是締約過失責任。支持該學說的學者還提出,合同在未生效狀態下并不存在實體的權利義務狀態,因此并不存在違約一說,違約責任也就無從談起。
第二種學說為違約責任說。主張該學說的學者認為,須經行政審批生效的合同雖然成立未生效,但是報批義務具有獨立性,獨立于其約定的合同關系而存在,報批義務來源于合同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應屬于獨立條款,因此違反該義務應當承擔的是違約責任。還有的學者主張,合同雖然并未生效但其已經成立,合同一旦成立雙方當事人即應受到相應的拘束力,因此違反報批義務的行為應當被視為是對合同義務的違反,此時也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該學說是在合同有效的基礎上予以論述的,合同有效說的情形下,即使須經行政審批的合同尚未進行審批,但其合同的效力并不受影響。按照此觀點,其屬于違反合同義務并且應當承擔的是違約責任[8]。其中,我國現行立法關于違約責任主要規定在《民法典》第577條至594條中。司法實務中也不乏法官要求違反報批義務的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此學說與報批義務的性質為締約過失責任相悖。除此之外,合同有效說也并不能得到廣泛認可,因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該學說是否合理還有待專家學者的進一步論證。
第三種學說為效力過失責任說。該學說認為,前述兩種觀點均有失偏頗,主要在于報批義務所處的時間節點,因其處于合同成立后生效前,此時就需要創造一種新型責任類型[9]。該學說一部分與締約過失責任說相似,即二者均認為違反報批義務的性質為先合同義務。但其認為,合同成立后至生效前這一階段適用前述兩個責任承擔方式均不妥。因此新型責任承擔方式應運而生。該學說的觀點即認為,報批義務屬于合同未生效時的合同準備義務,而合同生效后的義務履行則屬于合同目的實現義務。又因為前者發生在合同成立后、生效前,而締約過失責任的時間節點則與此不同,因此該觀點認為不能將其認定為締約過失責任。這種責任承擔方式像是為報批義務量身定做的,其相較于締約過失責任時間延后了,相較于違約責任又將時間提前了,打造一個完美符合其時間節點的新型責任承擔,在合同處于僵持狀態時才能夠很好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但是筆者對此學說持質疑觀點,因為創設一種新型責任承擔方式可能不利于我國法律的穩定性,且其在損害賠償方面與締約過失責任高度相似,所以該學說是否合理尚需考證。
須經行政審批生效的合同在成立生效階段便會產生一種義務,即報批義務。該義務即須經行政審批的合同雙方基于法律規定商議由任意一方負擔,向行政機關發出申請,待行政機關審查批準后該合同方可生效,報批義務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價值。隨著《民法典》的出臺,報批義務的作用愈發凸顯,作為連接行政審批與合同效力之間的重要紐帶,其在平衡相關行政權力與個人的意思自治之間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湯文平.批準(登記)生效合同、“申請義務”與“締約過失”《合同法解釋(二)》第8條批注[J].中外法學,2011(2):23.
[2]? ?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經濟理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60.
[3]? ?崔建遠.合同效力規則之完善[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1):149.
[4]? ?晉松.審視與重塑:待審批生效合同生效之障礙及克服[J].法律適用,2011(11):73.
[5]? ?劉貴祥.合同效力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91-193.
[6]? ?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M].遲穎,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862.
[7]? ?馮時.行政審批與礦業權轉讓合同效力關系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8.
[8]? ?許中緣.未生效合同作為一種獨立的效力類型[J].蘇州大學學報,2015(1):26.
[9]? ?王利明.民法典: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保障[J].中外法學,2020(4):136.
[責任編輯? ?興?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