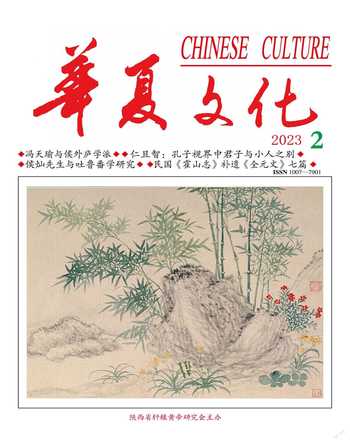《莊子》中髑髏意象
吳曉陽(yáng)
髑髏,作為人死之后所遺留的尸骨,一直被當(dāng)作死亡的象征。按《說(shuō)文解字》:“髑,髑髏,頂也。從骨蜀聲。”髑髏應(yīng)指死人的頭骨。髑髏這一意象在先秦典籍中只出現(xiàn)在《莊子》以及《列子·天瑞》中。在《莊子》中出現(xiàn)了兩次,均在《至樂(lè)》中。而《列子》中的內(nèi)容與《莊子》中第二段大致相似。自《莊子》以降,髑髏所衍生的文學(xué)作品不勝枚舉,著名的有漢代張衡的《髑髏賦》、魏曹植的《髑髏說(shuō)》、元代的道情《莊子嘆骷髏》、明代王應(yīng)麟雜劇《逍遙游》、清末梨園京劇《敲骨求金》以及魯迅先生收錄在《故事新編》中的《起死》一文。其中,魯迅的《起死》相較于其余作品形式特殊、內(nèi)容深邃,借用古代的故事并加入現(xiàn)代的元素,對(duì)《莊子》中的故事情節(jié)做了巧妙的改編,用現(xiàn)代主義荒誕的手法諷刺和批判了莊子以及道教思想的弊端和內(nèi)在矛盾,具有重要的文學(xué)價(jià)值和思想意義。《起死》雖脫胎于《莊子·至樂(lè)》,但二者的主旨卻大相徑庭。前者是用戲劇化的手法表達(dá)對(duì)文人“唯無(wú)是非觀”的批判,而后者的重心則是探討生死問(wèn)題,讓人看淡生死,安時(shí)順化。
一、魯迅《起死》一文的內(nèi)容和創(chuàng)作目的
《起死》被收錄在魯迅創(chuàng)作的歷史小說(shuō)集《故事新編》中。該書(shū)以神話(huà)、傳說(shuō)、歷史故事為基本內(nèi)容,結(jié)合新的創(chuàng)作形式,融入現(xiàn)代社會(huì)和生活的元素,對(duì)人們耳熟能詳?shù)墓适逻M(jìn)行改編,借以表達(dá)自己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取舍和對(duì)國(guó)民性改造的努力。其中不乏有對(duì)勤勞、智慧、勇敢、正義等中華民族流傳下來(lái)的優(yōu)良品質(zhì)的歌頌,如《補(bǔ)天》、《鑄劍》、《理水》等;也有對(duì)避世、消極、虛偽、圓滑等導(dǎo)致中國(guó)人劣根性的糟粕的批判。對(duì)于后者,《出關(guān)》和《起死》是其中的典型。《出關(guān)》諷刺了道家和道教的始祖老子避世、“無(wú)為而無(wú)不為”的消極思想,而《起死》則展開(kāi)了對(duì)道教尊奉為南華真人的莊子的批判。
魯迅曾說(shuō)“中國(guó)的根柢全在道教”。(魯迅:《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65頁(yè))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高潮消退之后,社會(huì)上封建復(fù)古的浪潮囂張一時(shí),國(guó)民黨政府對(duì)外采取投降政策,對(duì)內(nèi)實(shí)行殘酷壓迫,大搞白色恐怖,發(fā)動(dòng)文化“圍剿”。當(dāng)時(shí)的文藝界極為混亂,逃避現(xiàn)實(shí)的作品不斷出現(xiàn):有專(zhuān)門(mén)描寫(xiě)三角戀愛(ài)的小說(shuō),有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詩(shī),還有的專(zhuān)門(mén)向青年推薦《老子》和《莊子》。在這國(guó)難當(dāng)頭、民族危亡時(shí)刻,他們企圖用老子、莊子的清靜無(wú)為、無(wú)是無(wú)非的思想來(lái)麻痹群眾,混淆是非曲直。這是魯迅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創(chuàng)作了《出關(guān)》和《起死》,對(duì)道家和道教思想中的糟粕展開(kāi)了批判,激發(fā)人民的抗?fàn)幰庾R(shí),從精神上改造國(guó)民。
魯迅對(duì)《莊子》中的情節(jié)做了改造:莊子在前往楚國(guó)的路上碰到一個(gè)髑髏,莊子用道教的起死方術(shù)請(qǐng)司命大天尊將其復(fù)活。髑髏是死于五百年前紂王時(shí)期的漢子,名叫楊必恭。漢子復(fù)活之后不相信莊子會(huì)起死回生的巫術(shù),不僅不知感激,反而認(rèn)為莊子偷了他的衣服和財(cái)物。莊子對(duì)漢子講了一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大道理,無(wú)奈糾纏不過(guò),就請(qǐng)司命大天尊將其性命收回,但這次法術(shù)不再靈驗(yàn)。漢子大罵莊子為“賊骨頭”“強(qiáng)盜軍師”,并要扒莊子的衣服。莊子別無(wú)他法,拿出警笛喚來(lái)巡士。巡士聽(tīng)說(shuō)過(guò)“漆園吏莊周”的大名,知道自己的局長(zhǎng)喜歡莊子的《齊物論》,因此執(zhí)法中偏向莊子,莊子穿戴整齊安然離去。小說(shuō)在赤身裸體的漢子與巡士的爭(zhēng)吵與糾纏中戲劇性結(jié)尾。
莊子復(fù)活髑髏時(shí)與鬼魂的對(duì)話(huà)很有趣味,“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我是達(dá)性命之源的,可不受你們小鬼的運(yùn)動(dòng)。”(《起死》)這樣一種泯滅生死差異、階級(jí)差異,無(wú)是非、無(wú)彼此對(duì)待的觀點(diǎn)失去了其本來(lái)的面貌,完全淪落為上層統(tǒng)治者壓榨和欺騙百姓的工具。百姓的生死都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jí)的手中,而御用文人可以編出諸多高尚的哲理來(lái)為百姓是死是活提供理論依據(jù)。莊子在此借楚王的圣旨復(fù)活了髑髏,后面又想用同樣的方法讓漢子死去。普通人的生死儼然變成了上層階級(jí)玩弄的工具。不僅如此,莊子復(fù)活髑髏所念的咒語(yǔ)是《千字文》的頭四句和《百家姓》的頭四句,再加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起死》)。這樣的咒語(yǔ)即使是剛?cè)雽W(xué)的孩童也會(huì)念。魯迅在此深刻揭露了道教法術(shù)的欺騙性本質(zhì),同時(shí)也隱含對(duì)所謂儒家經(jīng)典的至上性的消解。此外,魯迅也辛辣地諷刺了莊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泯滅是非彼此差異的“齊物論”思想的內(nèi)在矛盾和欺騙性。漢子赤身露體向衣冠整齊的莊子要衣服遮蓋時(shí),遭到莊子拒絕,并對(duì)他大講:“衣服是可有可無(wú)的……”(《起死》)。但當(dāng)漢子扭住他不放,他就摸出警笛吹響喚來(lái)巡士驅(qū)趕漢子。莊子出場(chǎng)的形象是“黑瘦面皮,花白的絡(luò)腮胡子,道冠、布袍”(《起死》),言談舉止看似莊重嚴(yán)肅,實(shí)則世故圓滑、自私虛偽。當(dāng)他的學(xué)說(shuō)和人格的虛偽全盤(pán)暴露時(shí),便惱羞成怒,摸出警笛,喚來(lái)巡士進(jìn)行鎮(zhèn)壓,露出其反動(dòng)派豢養(yǎng)的御用文人的本相。
文中漢子的執(zhí)拗樸實(shí),莊子的虛偽圓滑,巡士的見(jiàn)風(fēng)使舵無(wú)不栩栩如生,深刻地揭露了國(guó)民的劣根性、道家思想的局限性、道教方術(shù)的欺騙性。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無(wú)疑具有振聾發(fā)聵的教育和引導(dǎo)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魯迅筆下的莊子并不是真實(shí)的莊子形象,魯迅筆下的莊子哲學(xué)也過(guò)于片面,有失偏頗。
二、《莊子·至樂(lè)》中的骷髏情節(jié)與形象
骷髏意象在《莊子·至樂(lè)》中出現(xiàn)在兩個(gè)段落和故事情節(jié)中,分別是“莊子之楚見(jiàn)一空髑髏”,“列子行食于道見(jiàn)百歲髑髏”。魯迅對(duì)《莊子》的改編主要選取了前者。
《莊子·寓言》有云:“寓言十九,藉外論之”,寓言在《莊子》一書(shū)中所占的篇幅為十分之九。所謂寓言,就是借助一些比喻性的故事來(lái)說(shuō)明意味深長(zhǎng)的道理。此處髑髏意象的使用其目的不在于敘述一個(gè)客觀事實(shí),而在于借髑髏來(lái)探討生死問(wèn)題。因此,故事的真假無(wú)須費(fèi)心考究,重要的是“得魚(yú)而忘荃”“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
“莊子”(此處加引號(hào)指寓言故事中的莊子,并非真實(shí)的莊子形象)首先質(zhì)問(wèn)髑髏為何失去生命:“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guó)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丑,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至樂(lè)》)“莊子”所列五者除了春秋故是自然死亡,其余均是死于非命:獲刑、亡國(guó)、自盡、餓斃。同時(shí),只見(jiàn)頭骨而不見(jiàn)尸骨,也暗含髑髏生前身首異處的下場(chǎng)。
“莊子”說(shuō)畢,就拿起髑髏當(dāng)作枕頭睡覺(jué)。夜半,髑髏托夢(mèng)于“莊子”,并對(duì)“莊子”的質(zhì)問(wèn)作出了回應(yīng)。“子之談?wù)咚妻q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wú)此矣。”(《至樂(lè)》)髑髏認(rèn)為“莊子”只知死之苦痛,卻不知生之勞累。髑髏意在消解生死對(duì)待以及樂(lè)生惡死的世俗之見(jiàn)。“死,無(wú)君于上,無(wú)臣于下,亦無(wú)四時(shí)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lè),不能過(guò)也。”“從”當(dāng)通“縱”,“縱然”為從容縱逸之意。在髑髏看來(lái),死亡反而是一種解脫,不用被生時(shí)的君臣大義、四季的冷熱凍曬所擾,可以達(dá)到從容自得與天地遨游的快樂(lè),這種快樂(lè)即使是王侯也無(wú)法比擬。有了這種快樂(lè),即使有司命復(fù)生其形,重返閭里,與父母親朋見(jiàn)面,髑髏也不愿意。“吾安能棄南面王樂(lè)而復(fù)為人間之勞乎?”(《至樂(lè)》)
可以說(shuō),髑髏所言才是《莊子》此段所要表達(dá)的主題。《至樂(lè)》所探討的問(wèn)題就是至極的快樂(lè)。《至樂(lè)》的開(kāi)篇就批判世俗所沉湎的“官能之樂(lè)”而提出“至樂(lè)無(wú)樂(lè)”。最高的快樂(lè)不在于外在感官的滿(mǎn)足,而在于內(nèi)心的恬淡、安適與解脫。而解脫的關(guān)鍵在于對(duì)生死的看淡。“死生亦大矣”(《莊子·德充符》),常人總想著求長(zhǎng)生,一方面追求現(xiàn)世的種種感官享樂(lè),極力滿(mǎn)足聲色口腹之欲;另一方面又刻意追求著長(zhǎng)生不死。“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莊子·齊物論》)世俗之人從一出生就與外物打交道,一直到死亡也不知道停止,整日沉溺于物質(zhì)世界的名利爭(zhēng)奪享樂(lè)之中,卻讓自己的心靈得不到絲毫的寧?kù)o與舒適,實(shí)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因此,《至樂(lè)》借髑髏想要表達(dá)的是一種對(duì)外物、對(duì)生死的超脫。此則寓言的主旨并非是好死而惡生,而是向死而生,借思考死亡來(lái)讓人更好地生。這里也并非完全否定親情友情君臣之義,而是教人們?nèi)绾翁幚砗猛獠渴澜绾妥约簝?nèi)心的平衡,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莊子·山木》)。
在髑髏段之上,有“莊子妻死”一則寓言。“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至樂(lè)》)。“莊子”的妻子去世,按照常理“莊子”自然要痛苦流涕,或者至少要流露出哀戚之情。但“莊子”卻蹲坐著敲著盆子唱歌。“莊子”并非不悲傷,“是其始死也,我獨(dú)何能無(wú)概然!”(《至樂(lè)》)但是“莊子”深究生死之理,人的生死不過(guò)是氣聚氣散的大化流行,“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shí)行也。”(《至樂(lè)》)人之生,是氣之聚,聚而有形,形而有生。人之死,是氣之散,散而為死,復(fù)歸于自然。因此,從天地自然運(yùn)化的角度,生死太正常不過(guò)了,根本不需要悲傷。
“列子見(jiàn)髑髏”一則更加證明了此點(diǎn)。列子在道旁遇見(jiàn)一個(gè)百歲髑髏,撥開(kāi)蓬草指著它說(shuō):“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yǎng)乎?予果歡乎?”(《至樂(lè)》)這里“養(yǎng)”,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憂(yōu)也。”(陳鼓應(yīng):《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shū)局2020年,第470頁(yè))“養(yǎng)”為憂(yōu)愁之意。髑髏既沒(méi)有死也沒(méi)有生,髑髏不會(huì)因死而憂(yōu)愁,而列子也不會(huì)因生而快樂(lè)。髑髏無(wú)死無(wú)生的原因就在于“萬(wàn)物皆出于機(jī),皆入于機(jī)”(《至樂(lè)》),此處的“幾”,《說(shuō)文解字》曰:“幾者,微也。”《莊子·寓言》:“萬(wàn)物皆種也。”“幾”正是指物種最初時(shí)代的種子,一種極微小的生物。萬(wàn)物都是從這個(gè)本源種子出生,死后又復(fù)歸于它。髑髏也是如此,生時(shí)由“幾”而生,死后又復(fù)歸于“幾”。因此,生命并非完全消亡,只是變換了一種形態(tài)生存。萬(wàn)物永恒存在,不生不滅。所以沒(méi)有必要為人身軀的消亡而感到悲傷,也沒(méi)有必要為身軀的存在而感到高興。人明白了大自然的運(yùn)轉(zhuǎn),也就通達(dá)了生命,看淡了死生。
三、總結(jié)
髑髏這一意象自《莊子》肇端,目的是借人死后所化的髑髏來(lái)探討生死大事,從而獲得對(duì)死亡恐懼的消解以及超越生死的解脫。人作為有死的存在必定會(huì)思考死亡問(wèn)題,人的現(xiàn)世生活有諸多舍不得,有諸多外物的牽引,因此在面臨死亡之時(shí)就難以讓心靈復(fù)歸于寧?kù)o與安祥。《莊子》中所講的正是一種看淡死亡的態(tài)度。世人總好生惡死,《莊子》中就反過(guò)來(lái)講生之勞累與苦痛,死之解脫與安樂(lè)。但這絕非教人輕視生命,“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莊子·大宗師》)生死都是自然的運(yùn)化,生就好好活著,不為外物所累;死就安然死去,也不必有多么悲傷。
而魯迅《起死》所批判的正是后人對(duì)《莊子》的誤解。《莊子》經(jīng)過(guò)道教以及民間方術(shù)的改造,其中的齊是非、一生死的思想成為了欺騙人民、麻木人民的工具。而其中對(duì)入世的消解以及所謂的“無(wú)為”與“逍遙”也成為了部分知識(shí)分子和貴族逃避現(xiàn)實(shí),只管自身享樂(lè)不管百姓死活的借口。魯迅所著眼的正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社會(huì)不相適應(yīng)的糟粕部分,究出其根源,并對(duì)其展開(kāi)批判。《莊子》中的思想的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莊子》關(guān)注的重心在于個(gè)體心靈的安頓,因此非常重視精神層面的逍遙與安適,但是并不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改造與治道的建構(gòu)。對(duì)于后者,荀子、墨家、法家、黃老家、縱橫家等則討論得更加深入,秦掃六國(guó)、一統(tǒng)天下、結(jié)束亂世所依靠的正是這些思想資源。
(作者:北京市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郵編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