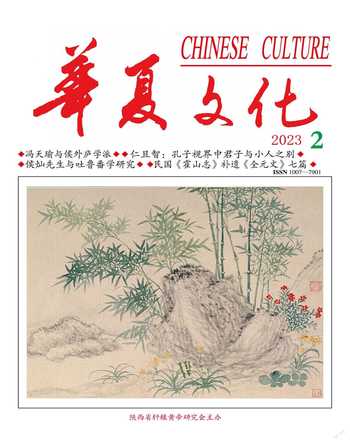紹興非遺研究:紹興目連戲的源流、特色及代表出目
一、???? 紹興目連戲的源流
紹興目連戲,是目連戲系統中的一個分支。目連戲,是指以佛教《佛說盂蘭盆經》“目連救母”故事為核心發展、演變而來的一類戲劇的總稱。目連戲脫胎于佛經故事,成型于北宋雜劇,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演變歷史。
東漢初年,隨著佛教初入漢地,佛教典籍也被陸續翻譯成漢文。西晉時期,有西域三藏法師竺法護(約3-4世紀)者,精通多國語言,翻譯了包括《佛說盂蘭盆經》在內的佛經七十四部一百三十七卷。《佛說盂蘭盆經》,便是目連故事的最早出處。
據《佛說盂蘭盆經》記載,目連(即大目犍連、摩訶目犍連)在修得神通之后,欲度父母以報養育之恩,便以道眼觀察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于是“以缽盛飯,往餉其母。母得缽飯,便以左手障缽,右手揣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王東惠:《紹興目連戲》,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年,第15頁)
目連見此,大叫悲泣,往陳于佛前。佛告訴目連,其母生前罪根深重,不論是個人,還是天神地祇、邪魔外道、四天王神,都無可奈何,唯有“十方眾僧于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現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種親屬、六親眷屬,得出三涂之若,應時解脫,衣食自然。”(《紹興目連戲》,第15頁)
《佛說盂蘭盆經》對于以忠孝立國的傳統農業社會影響甚大。隨著該經的流傳,目連故事也就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每年七月十五中元節,“天堂啟戶,地獄門開,十善增長”,佛門弟子及諸善男信女,都會舉辦禮佛齋僧的“盂蘭盆會”,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解救其“倒懸之苦”。“盂蘭盆會”及相關佛事活動,在南朝梁武帝倡辦后更為盛行。
到了唐朝,“目連救母”故事以說唱形式參與娛神、驅鬼、祈福、祭祀活動。中唐以后,在寺廟俗講中形成了《目連變文》。每年中元,寺院宣講《目連變文》,闡明因果,超度亡靈,并向聽眾傳布佛法。在今敦煌寫經中,尚存《目連變文》《大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幾種變文,故事情節已經比較完備。
入宋以后,都市經濟繁華,瓦舍勾欄興起,遂在寺廟俗講的基礎上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目連戲——《目連救母》雜劇。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中元節“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6頁)
《東京夢華錄》中的這段記載,是以戲曲形式表演的目連故事的最早記載。此時,目連故事已經和戲曲緊密結合,發展成為一個有相當長度的連臺本戲,可以連演數日,并且吸引了不少觀眾。可見,目連戲最早成型于東京(開封)一帶,是宋雜劇中的一個劇目。
紹興目連戲的起源,便與北宋《目連救母》雜劇相關。據專家考證,紹興目連戲起源于北宋開封的《目連救母》雜劇,宋以后,經元雜劇、明傳奇,至明末衍變為高腔后日趨旺盛。
清代以降,浙江的目連戲演出呈現諸腔并奏的局面,有紹興目連戲、開化高腔目連戲、永康醒感目連戲、磐安念經調目連戲等等。紹興舊時分會稽、山陰兩縣,由于地處寧紹平原,土地肥沃,鬼神迷信盛行,祭祀隆重,一直是目連戲演出的重鎮。例如康熙中后期至乾隆間形成的紹劇,往往流動于水鄉農村進行演出。每至中元節,到處盛演“祭鬼戲”,即“平安大戲”。“大戲”一般不演全本,而是移植了《起殤》《施食》《男吊》《女吊》《調無常》《游十殿》等段子,穿插在亂彈戲的長本劇目中。
晚近以來,紹興目連戲在民間曲藝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作為社戲演出而盛極一時。從現存的一塊民國六年(1917)的“目連戲場目匾”來看,共有包括《勸葷》《訓父》《嫖院》《白神》《挑經母》等在內的劇目一百三十二出,可以連演七天七夜。1926年出版的《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編記載了“紹縣做平安戲之風俗”。八十年代出版的《浙江風俗簡志·紹興篇》“中元節”條也介紹了紹興目連戲演出的盛況。
王守仁曾說,“詞華不似西廂艷,更比西廂孝義全”,魯迅曾說,“這是真的農民和手工人的作品”。接下來,我們便從紹興目連戲的舊抄本、演出特色及代表出目,具體看看紹興目連戲的藝術特色。
二、???? 紹興目連戲的舊抄本及演出特色
紹興目連戲的特色,非常典型地體現在其諸多的舊抄本和獨特的演技兩個方面。首先是抄本。抄本,劇本,是戲劇演出的依據,也是研究戲曲傳承、演變的關鍵。目連戲的劇本,在各地因語言、風俗以及戲班演出需要,往往有所差異。
在目連戲劇本中,明代鄭之珍(1518-1595)整理的《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情節連貫,文字通暢,曲牌規范,便于演出,是最重要的一個版本。《鄭本》是鄭之珍在以往目連變文、寶卷、傳說的基礎上,于萬歷十年(1582)整理、編匯而成的,共三卷,一百零四出。
紹興目連戲在《鄭本》之前就已經存在,而紹興舊抄本雖然受過《鄭本》影響,但是又保留著一些差異。例如,從《放星宿》到《回府》為《鄭本》所無,《男吊》《女吊》《白神》《訓父》等為《鄭本》所無。這些差異或衍生之處,為研究、校勘不同的版本,比較不同的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
紹興舊抄本至今保存完好的共有七種,其中三種是清抄本,三種是民國抄本。現將各版本情況綜述如下:
1.《紹興舊抄救母記》,上下兩卷,三十九出,敬義堂本,光緒九年(1883)抄。2.《紹興救母記》,八本,一百零八出,齋堂本,民國九年(1920)抄。3.《前良咸豐庚申年抄本》,分仁義禮智信五冊,一百六十四出,1860年抄。4.《前良丙寅年新老義和抄本》(《總綱》本),存義禮智信四冊,民國十五年(1926)抄。5.《前良呂順銓抄本》(《平安救母記》),分仁義禮智信五冊,一百六十七出,民國三十六年(1947)抄。6.《新昌胡卜村民國初年本》,分齋僧布施四冊,一百六十七出。7.《新昌1956年演出本》,分齋僧布施四冊,一百一十二出。
此外,還有上虞“啞目連”,二十二出;后溪口述目連戲,六十八出。啞目連,亦稱“啞鬼戲”,演劉氏獲罪被“無常”捉去在地獄受苦,戲中沒有臺詞,全憑演員的身段、手勢、表情、舞蹈、武打來體現,流布在上虞的崧廈、瀝海、南湖等地。
除了舊抄本眾多,紹興目連戲的特色還體現在精湛的演技上。張岱《陶庵夢憶》就有過精彩的記載:“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剎、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為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余人齊聲吶喊。”(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4頁)
時至今日,紹興目連戲的演出在某些方面依然保留當時之遺風,并形成了自己獨特演出風格。我們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看:
第一,紹興目連戲有專業的戲班——目連班。目連班,是專門演出“目連救母”故事的戲班,有的地方也叫“太平會”,為民間自發組織。目連班藝人一般多為農民、漁夫或手工藝人,平時都有自己的活兒。目連班和孟姜班一樣,因超度亡靈、驅鬼除疫而與其它戲班有別。由于是業余戲班,其服裝道具較差,有“目連行頭”之稱。目連班的砌末、臉譜、服飾、面具、紙扎等自成一體,異彩紛呈。
第二,紹興目連戲有古老的聲腔——調腔。目連戲的聲腔屬于越中“調腔”一系,據專家考證為南戲“余姚腔”之遺音。“目連調”有高腔、亂彈腔、懺卷調、念佛調、蓮花落、秧歌調等,念白多為方言土語,雜白混唱,一唱眾和,鑼鼓助節。后臺伴奏有鑼、鼓、鈸等樂器,不用絲弦樂器。樂器中,以“目連嗐”“目連嗐頭”最為獨特。它不同于一般嗩吶,音色凄厲、急促,至高潮伴以大鑼大鼓,氣氛更顯肅殺、恐怖。魯迅說:“這樂器好像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Nhatu,nhatu,nhatututuu地響,所以我們叫它‘目連嗐頭。”(魯迅:《朝花夕拾》,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42頁)
第三,紹興目連戲中與主線不相關的插劇多。紹興目連戲圍繞著傅相、劉氏、羅卜等人的人生經歷,穿插了不少精彩、詼諧的表演。這些小穿插肆意敷演世態,自由靈活,嬉笑怒罵,妙趣橫生,深受廣大民眾歡迎。許多人看戲,就是奔著這些小節目去的。《無常》《男吊》《女吊》《王婆罵雞》《泥水作打墻》《王阿仙嫖院》等,都是紹興目連戲特有的插段。周作人在《關于目連戲》中說:“占據目連全劇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個個劇化的笑話,社會家庭的諷刺畫。”(《紹興目連戲》,第260頁)
第四,紹興目連戲演員演技精湛。張岱曾說,當時旌陽戲子“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壇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4頁)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些精彩技藝。例如,紹劇中有打短手、九竄灘、調傀儡、疊羅漢、竄刀、甩桌等。如演《男吊》《女吊》時,“男吊”有七十二種吊法,“女吊”主要靠神態、動作、唱腔和水袖功夫來表現。再如,戲中鬼神(“無常”)上場,伴著鑼鼓聲和“目連嗐頭”,值臺師傅噴出一團團火焰,“無常”以扇掩面,曲背而上,迅速穿場而過,從“落臺口”下場。又再上場。如此三次,稱“三冒頭”,營造了一種飄忽不定的效果。
第五,紹興目連戲演出時與觀眾的互動性強。例如,紹興目連戲中有“起殤”“趕吊”“掃臺”的節目。“起殤”是邀請鬼神來看戲,以消怨超度。“趕吊”“掃臺”是將“五殤惡鬼”驅逐出去,保障五谷豐登,人畜平安。演出時以人扮鬼,臺上臺下都保持著互動,不受場地、技法、禮數等限制,互動性極強。魯迅兒時就參加過這種活動。這種場景,就像張岱所說,“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余人齊聲吶喊。”(《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第94頁)
以上我們介紹了紹興目連戲的抄本情況,以及有專業的戲班——目連班、有古老的聲腔——調腔、與主線不相關的插劇多、演員演技精湛、演出時與觀眾的互動性強五大特色。下面,我們擬選取《啞背瘋》《女吊》《跳無常》三個代表性出目,從戲劇文本的角度,進一步感受其思想特征和表現形式。
三、???? 紹興目連戲的代表出目
在上文的論述中,我們提到紹興目連戲中與主線不相關的插劇非常多。
按照《鄭本》的分卷,紹興目連戲的故事情節可以概括為:“傅長者樂善齋僧布施,感上帝寶幡接引登天;劉安人開葷遣兒出去,傅羅卜歸家諫母團圓。”“劉氏開葷結業冤,陰司譴責受諸愆;觀音點化傅羅卜,挑經挑母往西天。”“劉青提陰司受苦,釋迦佛法力無邊,曹氏女未婚守節,目犍連救母升天。”
紹興目連戲除了這一主要的故事情節,還圍繞著傅相、劉氏、羅卜等人的人生經歷,穿插了不少精彩、詼諧的表演。例如,《男吊》《女吊》《訓父》《白神》等。這些小插段肆意敷演生活情態,嬉笑怒罵,性格鮮明,曲白通俗,充分展現了紹興底層民眾的命運、心態和追求,深受民眾喜愛,具有濃厚的紹興地方特色,恰恰體現了紹興目連戲的精華。
下面,我們就以《啞背瘋》《女吊》《跳無常》這三個插段為例,從戲劇文本的角度,來感受一下其思想特征和演出特色。
第一,我們來看《啞背瘋》。《啞背瘋》在《鄭本》中名為《背瘋》,講一個“瘋婦”聽說傅相在會緣橋上賑濟孤貧,于是讓她的啞巴丈夫背她前去接受賑濟。《啞背瘋》中有一段“瘋婦”所唱的《孝順歌》,主題是弘揚孝親敬長、夫妻融洽、家庭和睦的精神的。
“瘋婦”唱道:
“小曲唱給諸位聽,子女須要孝雙親。十月懷胎在娘肚,三年哺乳靠娘身。養男育女千般苦,一世苦辛說不盡。烏鴉也知報娘恩。可憐天下父母心。//小曲唱給諸位聽,兄弟和睦娘歡心。兄弟連胞共母生,莫因瑣事便相爭。兄弟擰成一股繩,門口黃土變成金。鴻雁也有手足情,兄弟和睦家道興。//小曲唱給諸位聽,一夜夫妻百日恩。七世修來共枕眠,夫妻情誼海樣深。夫愛妻,妻敬夫,夫妻白頭心連心。鴛鴦戲水人人愛,鴛鴦到老不分離。”(《紹興目連戲》,第211-212頁)
我們知道,在紹興位于浙北的寧紹平原,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家庭、家族、村落相結合,形成了一種重現實、貴中和、厚人倫的文化形態。儒家的孝悌文化和善惡觀念深刻地影響了紹興目連戲,并借戲曲的“高臺教化”功能得以鞏固。《啞背瘋》所弘揚的孝道精神,就是民間以血緣為紐帶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模式的反映,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第二,我們來看看《女吊》。“女吊”,也名“女吊煞鬼”,即女性的吊死鬼。它和下面的《跳無常》可謂是最出名的兩出戲了。“女吊”原是一個貧苦的良家女,十三歲被賣進妓院,取名“玉芙蓉”,生前受盡老鴇、嫖客的折磨,自縊而死。死后成為吊死鬼,陰魂不散,悲憤交加,夜晚出來“討替代”。
“玉芙蓉”唱道:
“奴奴本是良家女,被人賣在勾欄里。生前受不過萬般氣,將身吊死在橫梁里!(哭)//奴奴本是一枝花,貌如西施色艷麗。年紀不過十三四,就被鴇婆梳籠髻!(哭)//梳籠髻,接客人,鴇婆將奴當搖錢樹。若還接著一個有錢的,鴇婆心中多歡喜。若還接著一個無錢的,老王八張嘴罵不息!(哭)//若還接著一個有情的,銷金帳里也歡喜。若還接著一個醉狂徒,那一夜如何受得起!(哭)//若還身體不適不遵依,鴇婆趕入奴房里。大棍子打小鞭兒抽,抽得奴渾身上下血水滴!(哭)//若還身病爬不起,叫天不應地不理。哪個是我親丈夫,哪個是我好兄弟!生前做了萬人妻,死后做了無夫鬼(讀‘ju)!(哭)”(《紹興目連戲》,第214-215頁)
“玉芙蓉”的唱詞,反映了紹興地區底層婦女的不幸和命運。“女吊”在舞臺上演出時身著紅色長衫,垂頭垂手,長發蓬松,左右甩發,呈一個“心”字形。唱詞中帶著“啊呀苦啊天哪!”的哭腔,突出了悲苦、哀怨和復仇的決心。同《跳無常》中的“嘆炎涼”一樣,既是苦難現實的反映,又是對這種現實的控訴。正如周作人所說,“我相信看的、聽的人這時無不覺得心里一抽,在這一聲里差不多把千百年來婦人女子所受的冤苦都迸叫出來了。”(《紹興目連戲》,第257頁)
第三,我們來看看最有名的《跳無常》。
“跳無常”,也稱“調無常”,可謂是紹興目連戲中最有特色的一出戲了。無常,也稱“白神”,是舊時閻君、城隍、東岳大帝等的鬼卒,渾身雪白,拿著破扇,戴著高紙帽,做著勾攝生魂的差使。紹興目連戲里的“跳無常”經魯迅、周作人、柯靈等人的介紹,遠近聞名。它為紹興目連戲所特有,若在迎神賽會的表演中,則隨著隊伍邊游邊走,隨時與觀眾互動,十分活潑,生動。
我們選擇《跳無常》中的幾處唱詞,略作分析。“無常”登場之后,就自述他的履歷,說起有一次心存私念,使堂房的阿侄“還陽半刻”,犯了瀆職之過,受到閻君懲罰,于是唱道:
“我本想用個人情,看起來實在用情不得。所以今后顧不得爹親娘眷,顧不得弟囡子侄,顧不得知己相好,顧不得朋友親戚。//哪怕你拜相封侯,哪怕你皇親國戚,哪怕你高樓大廈,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三頭六臂,我就一索吊了就走,抽筋骨,抽筋骨。”(《紹興目連戲》,第229頁)
這段唱詞魯迅在《朝花夕拾》里曾引用過。魯迅喜歡這個人而鬼、鬼而情的角色,“我和許多人——所最愿意看的卻在活無常”,因為“一切鬼眾中,就是他有點人情。”“無常”無疑具有普通人的心性,看阿嫂哭得悲傷,不免放他“還陽半刻”,然而自身卻因此受罰,于是他決定從此恪守正直公平之操守,不為人情所動。“無常”的唱詞“話粗理不粗”,告訴人們在大限將臨之時,妻財子祿、權勢名利之類終歸無有,自己難免被“一索吊了就走。”
《跳無常》中的“嘆無常”一段唱道:
“堪嘆你官迷心竅得高望高,喜得個沐猴冠帽鄉里夸耀。媚上司脅肩諂笑,縱下屬搜刮民膏。無錢的有冤官難告,有錢的法外行霸道。一心兒只把貪囊填飽,全不念冰山難久靠。……//堪嘆你財迷心竅見財忙撈,數不盡房地錢鈔金銀財寶。終日里把本利盤剝,死不放一絲半毫。你不顧親和眷,更不顧知己相交。為錢財良心全不要,獲錢財殺人不用刀。……//堪嘆你自稱高才不務正道,說什么我有筆如刀訟詞包攬。舞弄文墨作奸藏刀,拆人家骨肉分拋。裝斯文談禮教,喪廉恥行貪饕。為虎作倀是爾曹,還說什么唯有讀書高。……//堪嘆你自負風騷紈绔年少,仗父母造孽財寶遍訪窈窕。夸什么金屋藏嬌,一味地始亂終拋。見多姣,愛多姣,舊人哭,新人笑,三妻四妾還嫌少,斷子絕孫是爾曹。……”(《紹興目連戲》,第229-231頁)
“嘆無常”中每段唱詞后面還有“一旦無常到,看你再逍遙,人死難把臭名消”,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人間的種種不平等現象,痛斥了勢利之徒、奸滑之輩。在“罵狗”一段中,則以“狗”來比喻種種奸邪小人。“罵狗”唱道:
“你今朝進了財主府,翻轉狗臉勿認賬。啊嗚一口咬在我格腳跟上,你勢利狗兒太猖狂,只認衣衫不認人,就是倷批狗畜生。……”//癩皮狗,討厭狗,狗臉三寸厚,上街賣風流……壘灰狗,懶惰狗,財主狗,矮腳狗,長腳狗,下作狗,騙人狗,吃素念佛狗,黑心狗……//“黑狗、花狗、白狗、黃狗,大大小小一班狗婆娘,老狗勿管賬,小狗亂橫行。雄狗勿要臉,雌狗淚汪汪。癩狗害眾人,惡狗咬無常。……//我聲聲罵你狗畜生,狗眼勿識我活無常。我本來殺過三年狗。看透畜生壞心腸。野狗咬人容易打,家狗咬人最難防。”//恨不得明朝買來幾個藥丸子,“我看你慌不慌來忙不忙,作惡哪有好下場!”(《紹興目連戲》,第234-237頁)
“嘆無常”和“罵狗”,無情地揭示了當時的紹興社會貪官污吏橫行、人與人互相欺壓、互不信任的狀況,對人情世故的刻畫可謂繪聲繪色、入木三分。借“無常”之口,底層民眾苦難、壓抑、不滿、仇恨的情緒都宣泄出來了。
“嘆無常”“罵狗”“女吊”等蘊含的批判精神、抗爭精神,曾給予兒時的魯迅以重大影響。魯迅從小就受民間文藝的啟迪,十余歲就上臺演過目連戲中的“義勇鬼”。成年后,魯迅對目連戲演出記憶猶新,寫下了《無常》《女吊》《社戲》《五猖會》等優秀作品。正如劉佳思先生指出,目連戲中的人生思考、鬼神情結和批判精神,已經內化為魯迅內心中一種主體意識、受難情節和抗爭精神。
以上我們對紹興目連戲中三個著名的插段——《啞背瘋》《女吊》《跳無常》的情節、唱詞、角色等略作了分析,感受了戲曲藝術和地方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最后,筆者想從繼承、弘揚傳統文化的角度,總結、探討一下紹興目連戲的現代價值和意義。
四、余論:保護和研究紹興目連戲的當代意義
在本文的論述中,我們看到紹興目連戲歷史悠久,脫胎于佛經故事,與北宋雜劇一脈相承;紹興目連戲形態獨特,它具有諸多舊抄本和與眾不同的演出風格。此外,我們以《啞背瘋》《女吊》《跳無常》三個插段為代表,從戲劇文本的角度感受了戲曲藝術和地方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特色。
我國元代劇作家胡祗遹曾說過,戲曲“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厚薄,以至醫藥、卜籠、釋道、商賈之人情物理,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陳抱成:《中國的戲曲文化》,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第16頁)
紹興目連戲,正是這樣一部記錄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大百科和活化石,是展現普通民眾心理狀況、信仰狀況和生活狀況最直接的藝術樣式。在紹興目連戲中,普通民眾的思維方式、道德原則、苦樂心態和審美方式,都奇幻無比、萬態紛陳地得到了展現。紹興目連戲對于當代的戲曲研究、民俗文化研究和道德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那么,紹興目連戲中蘊含著哪些有可以借鑒的元素呢?例如我們看到,歷史上紹興地方宗族和鄉賢每每假手目連戲以凝宗聚族、明辨善惡、安撫人心等,可見紹興目連戲對維持人際關系、鄉村秩序,調節人們的生產生活具有紐帶作用。再如我們看到,紹興目連戲中的傅相行善登天乃是在教人為善去惡,目連救母歷經劫難乃是體現了母慈子孝的人間情懷,曹水英為夫守節乃是對愛情的忠貞不屈,這些對當今的美德教育、家庭關系、家風建設等,也是有一定的借鑒、啟迪之處的。
另一方面,和所有傳統戲曲一樣,紹興目連戲作為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也免不了帶有歷史局限性。例如,戲中包含的忠君思想、等級觀念、封建迷信和綱常倫理等。這也是要特別注意的。這就要求我們當前的戲曲工作者和研究者在整理、保護和研究時,要以一種辯證分析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繼承,充分發掘其中的正能量,為現代社會和現代藝術服務。
近幾十年來,在浙江省、市文化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幫助下,紹興目連戲已經得到了卓有成效的保護、開發和傳承:紹興目連戲的排演日益頻繁,紹興目連戲的舊抄本得到整理,紹興目連戲的相關研究得到展開,影響逐漸擴大。其中,有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即,它于2007年入選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于2014年入選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綜上所述,紹興目連戲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和地道的目連戲劇種,不僅在戲劇史、宗教史、藝術史、地方志、民俗學等方面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調節、維系當今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系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們有必要繼續樹立、強化傳統文化保護意識,加強對紹興目連戲的整理、保護和研究,深入挖掘越地文化,扶持民間劇團,培養年輕演員,使紹興目連戲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
(作者: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山門鎮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平陽分校講師,郵編325406)
【作者簡介】
姓名:俞正來
職務:講師
聯系方式:15101573205
Email:yuzhla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