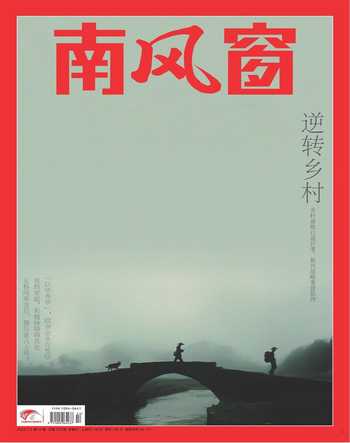“以華養(yǎng)華”,歐洲企業(yè)在想啥
辜學(xué)武

隨著俄烏戰(zhàn)爭陷入僵局,中美地緣政治沖突持續(xù)不斷,全球合作機(jī)制日益萎縮,歐洲越來越擔(dān)憂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與話語權(quán),也越來越擔(dān)憂自己財(cái)富的縮水和安全的削弱。
然而,一切跡象表明,這個古老的大陸正在奮力克服迷惑與彷徨,在中美交惡的連軋中求生,力圖找到自己未來發(fā)展的指南針。
搶奪人工智能全球標(biāo)準(zhǔn)制定權(quán)
從技術(shù)上來講,歐洲企業(yè)并不是人工智能的大玩家,真正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的企業(yè)大部分來自美國和中國。面對人工智能突飛猛進(jìn)的發(fā)展,尤其是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的不斷深入,手上毫無技術(shù)優(yōu)勢的歐洲人坐不住了。
通過制定游戲規(guī)則來奪取人工智能的話語權(quán),影響這門新型技術(shù)的發(fā)展方向,規(guī)范它的應(yīng)用場景,圈定它的使用界限,明確人工智能研究者和投資者的界限和義務(wù),成為了歐洲人試圖與美國人和中國人平起平坐,乃至超越他們,為他們“定規(guī)矩”的法寶。
歐洲人,尤其是歐盟還真有這個底氣。他們的底氣來自歐盟4.5億人口的大市場。可能有人會說,4.5億人口的市場算大嗎?大中華地區(qū)有近15億人口,印度14億人口也幾乎是歐盟市場的3倍。
然而,歐盟的單一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國統(tǒng)一市場,它不僅包含歐盟27個成員國,還和瑞士、冰島、挪威以及列支敦士登通過協(xié)議構(gòu)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完全由工業(yè)國家組成的統(tǒng)一的內(nèi)部經(jīng)濟(jì)圈。
自1993年正式建立以來,3600多條共同的工業(yè)、服務(wù)和消費(fèi)者保護(hù)標(biāo)準(zhǔn)不斷問世,將這個統(tǒng)一市場打造成了世界上“最高標(biāo)準(zhǔn)”的研發(fā)空間,生產(chǎn)基地和消費(fèi)市場。
歐洲的定力在于,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對它情有獨(dú)鐘,把進(jìn)入這個“高標(biāo)準(zhǔn)、嚴(yán)要求”的市場看作是它們在世界上成功的標(biāo)志,即使忍氣吞聲,強(qiáng)行“合規(guī)”,美國人和中國人似乎也心甘情愿。他們不愿意放棄這個市場,不僅是因?yàn)檫@里豐厚的利益回報(bào),更是因?yàn)槭艿綒W洲標(biāo)準(zhǔn)認(rèn)可后產(chǎn)生的全球競爭力: 對于中國和美國的企業(yè)來講,達(dá)到了歐洲的標(biāo)準(zhǔn),就是拿到了世界市場的通行證。
ChatGPT的橫空出世加速了歐洲人對人工智能這個“潛力無限”但又“風(fēng)險(xiǎn)巨大”的新技術(shù)加以規(guī)范的緊迫感。要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轟動效應(yīng)和與此相連的“恐懼感”,歐洲人是不會在入夏以來突然發(fā)力,極力搶奪人工智能規(guī)范制定權(quán)的。
歐洲人先是在五月底歐盟和美國貿(mào)易與技術(shù)委員會(TTC)上說服美國人同意在雙方正式完成人工智能立法程序之前,共同推出一個人工智能“行為準(zhǔn)則”(Code of Conduct),并“邀請”正在進(jìn)行人工智能開發(fā)的企業(yè)和研究機(jī)構(gòu)“自愿簽署”。
接著是6月14日歐洲議會的議員們一反常態(tài),迅速調(diào)整步伐,對歐盟委員會早在2021年提出的,被他們拖了近兩年之久的《人工智能法》草案進(jìn)行表態(tài),同意就全面開啟立法程序進(jìn)行談判。
與一些中文媒體誤解性的報(bào)道不一樣,歐洲議會6月14日通過的文字并不是所謂《人工智能法》草案,而是歐洲議會對歐盟委員會提出的 《人工智能法》草案的立場性文件。
這個文件的通過,標(biāo)志著歐洲議會同意開始啟動歐盟立法程序的“三邊談判程序”(三邊是指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 這一步固然重要,但它通過的立場文件并不是法律草案,草案只有在三方完成談判達(dá)成妥協(xié)之后才能正式提出。
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將人工智能系統(tǒng)應(yīng)用場景分為4個風(fēng)險(xiǎn)級別(微型風(fēng)險(xiǎn)、有限風(fēng)險(xiǎn)、高度風(fēng)險(xiǎn)和嚴(yán)禁型風(fēng)險(xiǎn))的主張也可能會成為世界標(biāo)準(zhǔn)。
無論如何,歐洲人趕在其它國家前面系統(tǒng)全面地完成對人工智能的規(guī)范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將人工智能系統(tǒng)應(yīng)用場景分為4個風(fēng)險(xiǎn)級別(微型風(fēng)險(xiǎn)、有限風(fēng)險(xiǎn)、高度風(fēng)險(xiǎn)和嚴(yán)禁型風(fēng)險(xiǎn))的主張也可能會成為世界標(biāo)準(zhǔn)。
至少被定義為屬于“嚴(yán)禁型風(fēng)險(xiǎn)”的人工智能應(yīng)用將被排斥在歐洲市場之外,目前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廣泛使用的生物識別技術(shù)(如臉部識別)等都被打入了“嚴(yán)禁型風(fēng)險(xiǎn)”的冷宮,這無疑將對目前正在從事這方面研究和應(yīng)用的個人與實(shí)體產(chǎn)生重大的沖擊。
以“去風(fēng)險(xiǎn)”戰(zhàn)略平衡中美壓力
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今年3月提出采用“去風(fēng)險(xiǎn)”這個概念作為歐美處理對華關(guān)系的基本思想; 4月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wù)助理沙利文正式確認(rèn)美國將放棄“脫鉤論”,將美國對華的重點(diǎn)轉(zhuǎn)向建筑所謂的“小院高墻”,降低對華交往的“戰(zhàn)略風(fēng)險(xiǎn)”。
“去風(fēng)險(xiǎn)論”在得到了美國的認(rèn)可后,迅速在歐洲政界形成共識,即使是一向反對“脫鉤”,只提“分散風(fēng)險(xiǎn)”的德國總理朔爾茨也公開對馮德萊恩的提法表示贊同和認(rèn)可。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兼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wù)高級代表博雷利5月底告訴記者,他和歐盟27成員國的外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就如何處理對華關(guān)系進(jìn)行了4個多小時的磋商,達(dá)成一致共識,接受 “去風(fēng)險(xiǎn)”這個思路,作為未來指導(dǎo)對華關(guān)系的基本準(zhǔn)則。
德國6月14日正式推出的所謂“國家安全戰(zhàn)略”基本采用了“去風(fēng)險(xiǎn)”的基調(diào)對與中國關(guān)系作了“安排”。雖然對北京的外交、內(nèi)政頗有微詞,而且在人權(quán)和國際秩序問題上用詞嚴(yán)厲,但對中國的定位還是“機(jī)遇”大于“威脅”,“伙伴”大于“對手”,“風(fēng)險(xiǎn)可控”。
預(yù)計(jì)6月下旬即將舉行的歐盟27國首腦峰會將出臺一個新的對華戰(zhàn)略文件,以取代2019年版的歐盟對華戰(zhàn)略。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去風(fēng)險(xiǎn)”這個概念將會寫在文件中,成為未來歐盟同中國打交道的指導(dǎo)思想。
雖然北京不愿意接受“去風(fēng)險(xiǎn)”這個概念,認(rèn)為“去風(fēng)險(xiǎn)”是“半脫鉤”的代名詞,用中國國務(wù)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的話來講,“去風(fēng)險(xiǎn)“就是“去機(jī)遇、去合作、去穩(wěn)定、去發(fā)展”。
然而對于歐洲人來講,這是他們頂住美國壓力的一大勝利,是平衡中美壓力的最佳選擇。他們認(rèn)為自己成功地迫使美國放棄了與中國“脫鉤”的遐想,回到了“理性思維”的軌道。
美國是否真正會回到“理性思維”的軌道,放棄同中國脫鉤,這并不是歐洲人能左右的,但歐洲認(rèn)為自己是理性的,在“去風(fēng)險(xiǎn)”思想的指導(dǎo)下,歐洲在不尋求同中國全面脫鉤的同時,會進(jìn)一步具體定義在哪些領(lǐng)域里“過度依賴”中國。
按照馮德萊恩和博雷利的說法,歐洲至少在如下幾個領(lǐng)域應(yīng)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數(shù)字轉(zhuǎn)型,光伏,稀土,通信技術(shù),電池。為了“去風(fēng)險(xiǎn)”,歐洲可能會在這些領(lǐng)域加大對中國企業(yè)的投資審核,歐洲企業(yè)的出口管控和鼓勵歐洲企業(yè)重組對歐洲更加安全,不依賴中國的全球供應(yīng)鏈。
對于華為來講,未來的壓力可能會持續(xù)加大。“去風(fēng)險(xiǎn)”這個概念將會被歐盟委員會用來作為進(jìn)一步削弱華為在歐洲市場地位的“殺手锏”,迫使“不聽話”的成員國接受歐盟的旨意。
歐盟內(nèi)部市場專員蒂埃里·布雷頓(Thierry Breton)在6月16日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就宣布,將全面禁止在歐盟機(jī)構(gòu)的場所使用華為設(shè)備。他要求所有27個成員國都切實(shí)落實(shí)2020年達(dá)成的“歐盟5G安全工具箱”的標(biāo)準(zhǔn),把“不安全的”通信設(shè)備全面移出歐洲的通信基礎(chǔ)設(shè)施,以確保整個歐盟的“共同安全”。
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布雷頓也展示了歐盟5G安全專家委員會撰寫的第二次報(bào)告,呼吁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使用“5G安全工具箱”授權(quán)的17個成員國采取積極措施,限制在網(wǎng)絡(luò)中使用“高風(fēng)險(xiǎn)”的5G設(shè)備或?qū)W(wǎng)絡(luò)供應(yīng)商加嚴(yán)安全風(fēng)險(xiǎn)管理。
當(dāng)下的歐盟委員會是一個對華態(tài)度極為強(qiáng)硬的政治集團(tuán),估計(jì)這個強(qiáng)硬態(tài)度一直會持續(xù)到它明年任期的結(jié)束。華為應(yīng)當(dāng)感到欣慰的是,并不是每一個成員國都愿意圍著布魯塞爾的指揮棒轉(zhuǎn)。
如果分頭出擊,各個擊破,分別耐心做好各個成員國政府和供應(yīng)商的工作,華為守住在歐洲的市場還是有希望的。現(xiàn)在中國在歐洲的企業(yè)最需要的就是“苦撐待變”。
烏克蘭戰(zhàn)事必將會在明年美國大選之前有一個終結(jié)。現(xiàn)在拜登的民主黨智庫重量級人士也公開發(fā)表觀點(diǎn),認(rèn)為美國不應(yīng)該繼續(xù)支持戰(zhàn)爭接著打下去,因?yàn)椤拔覀兿霂椭鸀蹩颂m取勝,但正是我們的援助可能毀滅烏克蘭”。
北京不愿意接受“去風(fēng)險(xiǎn)”這個概念,認(rèn)為“去風(fēng)險(xiǎn)”是“半脫鉤”的代名詞,用中國國務(wù)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的話來講,“去風(fēng)險(xiǎn)“就是“去機(jī)遇、去合作、去穩(wěn)定、去發(fā)展”。
一旦烏克蘭戰(zhàn)爭結(jié)束,以中國目前的對歐外交攻勢,華為的營商環(huán)境將會獲得極大的緩解。隨著對美國安全依賴的緩解,歐洲對中國“去風(fēng)險(xiǎn)”的壓力也會降低,反映在對華為的態(tài)度上不會像現(xiàn)在馮德萊恩和布雷頓那樣歇斯底里。
企業(yè)界思維轉(zhuǎn)變與“雙重戰(zhàn)略”
歐洲的企業(yè)界和商界,尤其是大型跨國企業(yè)的投資決策者一直是堅(jiān)定的“脫鉤論”反對者,然而,隨著地緣政治壓力的增長,他們的思想也開始發(fā)生微妙的變化。
一個典型的現(xiàn)象就是China+1戰(zhàn)略開始在企業(yè)界盛行。這是一個雙重戰(zhàn)略,一方面,企業(yè)堅(jiān)定地頂住來自政界和輿論界的“脫鉤”壓力,守住甚至繼續(xù)擴(kuò)大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和投資。
另一方面,在中國本土之外,尤其在中國周邊地區(qū)和國家極力尋求新的投資機(jī)會,建立新的生產(chǎn)基地,平行建立可與在華生產(chǎn)能力媲美的新產(chǎn)能,并利用這些新產(chǎn)能為中國以外的市場服務(wù),提供類似于在中國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以西門子為例,這個一向堅(jiān)定地反對與中國“脫鉤”的德國跨國企業(yè)正在推進(jìn)她的雄心勃勃的“馬可波羅計(jì)劃”(Marco Polo Project)。 按照這個計(jì)劃,西門子準(zhǔn)備追加在中國的投資,將它在成都工廠的自動化生產(chǎn)能力提升40%,以滿足中國市場急劇上升的需求。
然而,與此同時,西門子將在新加坡投資建立一個與成都自動化生產(chǎn)能力類似的新工廠,盡快開工,以滿足印度、 越南、泰國和其它亞洲國家和地區(qū)強(qiáng)勁的市場需求。
這是一個典型的China+1戰(zhàn)略: 在不放棄中國,甚至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的同時,在中國之外建立平行的生產(chǎn)基地,以規(guī)避地緣政治可能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
這個“雙重戰(zhàn)略”背后的邏輯是,一旦中國與歐洲的地緣政治沖突、利益沖突或價(jià)值沖突白熱化,西門子被迫關(guān)閉在中國的生產(chǎn)基地或退出中國,那些在中國以外的平行的生產(chǎn)基地可繼續(xù)毫無中斷地滿足亞太地區(qū)以及世界市場對西門子產(chǎn)品的需求。
從本質(zhì)上來講,這是一個“分散風(fēng)險(xiǎn)”的戰(zhàn)略,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東方不亮西方亮,一旦“中國出事”,西門子還有“備胎”,不至于束手無策,無貨可供,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供應(yīng)能力被政治沖突切斷。
然而,這個“雙重戰(zhàn)略”所帶來的長遠(yuǎn)效應(yīng)對中國開放戰(zhàn)略來講則不見得有利。西門子在中國成都的生產(chǎn)基地和在新加坡的生產(chǎn)基地有一個明確的分工:成都未來只為中國市場生產(chǎn),新加坡為中國以外的地區(qū)和全球市場生產(chǎn)。

這樣一來,西門子成都的產(chǎn)品將不再出口海外,只供給中國客戶。 如果所有的外資企業(yè)都像西門子一樣實(shí)施這個“雙重戰(zhàn)略”,中國的外貿(mào)出口將會大幅萎縮,畢竟外資企業(yè)的出口一直是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
現(xiàn)在還沒有準(zhǔn)確的數(shù)據(jù)表明,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外貿(mào)出口的下滑是否與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yè)實(shí)施China+1有關(guān),但雙重戰(zhàn)略所產(chǎn)生的效應(yīng)是另外一種“脫鉤”,即一部分世界市場的高端產(chǎn)品需求與中國領(lǐng)土上的外資生產(chǎn)能力“脫鉤”。
這種雙重戰(zhàn)略產(chǎn)生的另外一種效應(yīng)可能對中國更為不利。繼續(xù)以德國企業(yè)在中國的投資為例,德國聯(lián)邦銀行(德國央行)的數(shù)據(jù)表明,2022年德國企業(yè)在華的總投資達(dá)到115億歐元,創(chuàng)歷史新高。
但在這個“歷史新高”的后面,隱藏著一個“以華養(yǎng)華”的現(xiàn)象,這投下的115億歐元基本都來自德國在中國經(jīng)營的企業(yè)利潤收入,屬于在華利潤再投資,即把在中國掙的一部分錢不匯回母國,而是就地再投資。
利潤就地再投資折射出德國企業(yè)不愿再拿出中國利潤以外的“新鮮資金”投資中國,而是把這些真正意義上的“外資”投到了中國以外的地方。
利潤就地再投資本身沒有什么不好,但它折射出德國企業(yè)不愿再拿出中國利潤以外的“新鮮資金”投資中國,而是把這些真正意義上的“外資”投到了中國以外的地方。
西門子計(jì)劃今年內(nèi)在全球投資20億歐元,僅在新加坡就投入3個億。這些真正意義上的外資都與中國擦肩而過。如果所有的外資企業(yè)都采用這種“以華養(yǎng)華”的戰(zhàn)略,從國外流入中國的外資將會減少。
這個“以華養(yǎng)華”現(xiàn)象對中國更大的挑戰(zhàn)是,外資企業(yè)在中國經(jīng)營越順利,利潤越高,中國引進(jìn)真正意義上的外資的難度就越大,流向中國競爭對手日本和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就越多。
西門子、寶馬、巴斯夫在中國去年顯赫的投資實(shí)際上都是“內(nèi)資”,是中國人自己的錢,只不過是被這些外資企業(yè)賺了,“洗”成了外資,這讓他們有了足夠的財(cái)力進(jìn)一步開發(fā)中國以外的市場。
現(xiàn)在美國的新工廠一個接一個地蓋了起來,這些都是“真金白銀”的外資,西門子的CEO前不久在新加坡的戰(zhàn)略發(fā)布會上也高調(diào)宣布,他今年的20億歐元投資將有相當(dāng)?shù)囊徊糠滞断蛎绹?/p>
日本似乎也是歐洲在華企業(yè)“以華養(yǎng)華”戰(zhàn)略的直接受益者,近期日本股市高漲,直接受益于西方國際資本“避險(xiǎn)中國”的思潮。日本的制造產(chǎn)業(yè)、研發(fā)公司和基礎(chǔ)設(shè)施都成了外國直接投資的“香餑餑”。
當(dāng)然,這一所謂“以華養(yǎng)華”戰(zhàn)略要總體顯現(xiàn)出效果,還依賴許多假設(shè),正如前面提到多次的“如果歐洲所有在華企業(yè)都如何如何”一樣,其實(shí)現(xiàn)的條件比較極端,中國也不必過于憂慮。況且事在人為,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機(jī)會總是不斷出現(xiàn),抓住時機(jī)撬動局勢,也可能逆風(fēng)翻盤。
“以華養(yǎng)華”表明的是歐洲在搖擺,在猶豫,但也在平衡和突圍。這是歐洲的困局,也是對中國的挑戰(zhàn)。李強(qiáng)總理的歐洲行,可以被視為是向歐洲的兩大領(lǐng)頭羊伸出了橄欖枝。柏林和巴黎應(yīng)該收到了北京發(fā)出的清晰的信息:“去風(fēng)險(xiǎn)”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風(fēng)險(xiǎn)”,唯有加深合作方能真正克服困難,恢復(fù)互信,續(xù)寫中歐互利互贏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