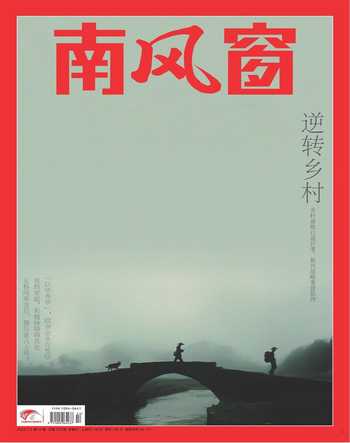海霞與孩子,普通話與石榴籽
姚遠
“推廣普通話,這有啥可做的?”
當海霞找到李搏的時候,李搏“懵”了。
那是2016年,海霞正致力于在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做一個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公益項目,并第一次找到李搏商量。
在山東人李搏的認知中,普通話應該不是什么大事兒,“頂多是有些地方口音,說得不標準,怎么著都能交流吧”。
但隨著逐步了解,李搏才明白其中的復雜、艱難與重要性。
據教育部調查,截至2020年底,全國范圍內普通話普及率達到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個百分點。
然而,基于我國14億人口基數,80.72%的普及率意味著,還有約2.7億中國人無法使用普通話交流。這些無法使用普通話交流的人,主要就是生活在海霞口中的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和欠發達地區。
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曾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指出,深度貧困的主要成因之一,就是社會發育滯后、社會文明程度低,其根子就在“很多人不學漢語、不識漢字、不懂普通話,大孩子輟學帶小孩”。
在中央電視臺工作30年,海霞說,自己“這輩子最擅長的就是說普通話”。理所當然地,她希望普通話能成為橋、成為眼,成為走出沙漠和大山的一把鑰匙。
“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海霞說,她牢記著這句話。
2016年,海霞發起“石榴籽計劃”,一個致力于普通話推廣的公益項目。
吃過普通話的虧
古露鎮,位于西藏自治區那曲市色尼區境西南部,海拔近4600米。
藏語中,“古露”的意思是“黃羊聚居的山溝”,鎮上生活著的,絕大多數是牧羊的牧民。
美朵老師在古露小學工作了20年,她告訴南風窗,鎮上牧民能聽懂普通話的大概50%;但會說的,“不超過百分之二三十”。
按照美朵的說法,有的家長比較年輕,上過學,但更多的家長,在小學畢業后就輟學了—這是他們普通話水平不高的原因,也是結果。
在邊疆、民族地區,普遍存在一種“成績倒掛”現象,即學生年級愈高、成績愈差的現象。
“原因就在于普通話不好,課程跟不上。類似我們還沒學會英語,就直接開始英語上課了。”作為北京語澤公益基金會的理事長,李搏解釋。
據統計,2017年,新疆和西藏是全國跨省務工人員比例最低的地區,新疆為6%,而西藏幾乎為0。到了2022年,新疆跨省務工人員46萬人,西藏雖有提升,但也僅為6萬人。語言是他們向省外流動的主要障礙之一。
“久而久之,一些孩子就會厭學,甚至輟學。大人干個事總是干不成還會煩惱,何況孩子?一考就20分、30分,還學什么?不想學了。”李搏對南風窗補充道。
美朵自己上學時,就吃過普通話的虧。
在班上,美朵的成績名列前茅,但普通話卻不那么好。
小學四年級,她才開始學習拼音和漢字,只會簡單造句;后來上了初中,一些課程,比如代數,開始使用普通話教學,她的理解“就很受限了”。
這導致美朵認為,她后來沒讀上更好的學校、去省外上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普通話表達能力的缺乏。說起來,美朵總覺得遺憾。
美朵老師在學生時期的遺憾,仍然困擾著今天古露鎮的孩子們。
古露小學的孩子數學成績不好,“平均只有二三十分”。美朵覺得,很可能是與她讀書時一樣:普通話不行,對抽象知識的理解就不夠好。
“被限制住了。”她對南風窗再次強調了一遍。
被限制的,不僅僅是求學之路。
外出務工,是貧困人口增加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2020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一組數據顯示,貧困家庭中,“2/3左右的直接收入都來自務工”。其中,跨省務工的收入又是最高的。
但據統計,2017年,新疆和西藏是全國跨省務工人員比例最低的地區,新疆為6%,而西藏幾乎為0。到了2022年,新疆跨省務工人員46萬人,西藏雖有提升,但也僅為6萬人。
語言是他們向省外流動的主要障礙之一。
海霞記得,她曾在《新聞聯播》播報過這么一則令她印象深刻的新聞:
新疆小伙阿卜杜拉去江西南昌謀生,賣羊肉串兒,會說的普通話只有“兩塊錢一串兒”。
后來,一位好心的大姐教他學會了一口河南味兒普通話,再有當地政府的支持,阿卜杜拉漸漸在南昌經營起11家店面、10個攤點,管理著幾十名員工。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海霞多次跟隨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在祖國邊疆民族地區調研。海霞發現一個問題:“很多民族群眾聽不懂、不會說普通話,在老鄉家里調研,雙方要借助肢體動作和當地干部的翻譯,才能勉強溝通交流,這嚴重影響了他們和外界的交往,也影響了脫貧致富發展。”

語言不僅阻礙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更羈絆住民族群眾走出家鄉、打工創業、過上好日子的步伐。
在邊疆、民族地區,如果不會普通話,基本上意味著以后的人生只能一直待在這里。
“普通話其實是一座橋。”李搏說。
教師,是重中之重
推廣普通話,推給誰?
“石榴籽計劃”將目標錨定為當地的幼兒園教師。因為,教幼兒教師說普通話,就是在教幼兒說普通話。
幼兒園階段是語言學習的黃金期,資深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員、石榴籽計劃志愿者徐博文對南風窗說,3至6歲年齡階段的孩子,對語言的吸收和掌握能力的確是最高效的。再有,幼兒園孩子“受母語發音習慣的影響還不是很深”,同樣是學習普通話發音,相較于成人,他們學得更標準、更規范。
語言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載體。
但要做這件事,就有一種與時間賽跑的緊迫感。李搏說:“必須在學前學會,等到小學,課本已經開始用普通話教課,孩子就跟不上了。”
2016年以來,“石榴籽計劃”在新疆麥蓋提、葉城,甘肅靜寧、會寧,西藏那曲,云南怒江等地,開展幼兒園教師能力提升培訓項目,累計開展線下培訓6200余人次,超過400課時;線上培訓直播,超10萬名教師在線參與。
借幼教教師群體的力量,“石榴籽計劃”希望輻射和影響一片地區。
而且,他們希望給當地帶去的,不僅僅是普通話。
作為“石榴籽計劃”幼兒園教師能力提升培訓項目的負責人,葉紅梅說,語言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載體。“老師們的目標不是學普通話,而是使用普通話去進行更優質的教學。”
張潤玲是天津市河北區教師發展中心的小學學前教研部副主任。今年的4月和6月,她作為志愿者、培訓講師,分別參與了兩期“石榴籽計劃”在新疆葉城縣開展的幼兒園教師能力提升培訓項目。
每期200位學員,有園長,有骨干教師,四期項目下來,一個縣的參培人次達到了800人。
作為幼教工作者,張潤玲堅信,自己的這份工作不僅僅是“教小朋友”。在孩子的背后,是一個家庭。
“假使一名教師帶30個孩子,這又是多少孩子、多少家庭?”張潤玲追問著。
在她參與過的不少志愿項目中,“石榴籽計劃”是特別的。
其特別之處在于:忙、累,“行程非常緊湊”。
每一期的項目,張潤玲在葉城待五天,每天上一節四小時的大課,余下半天就去下鄉,去當地幼兒園現場視導。
走進幼兒園的教室,張潤玲發現不少問題。
張潤玲舉了一個例子—學詞。
只有三歲的小朋友,剛入園時,對普通話一竅不通,“本來理解大人講話的意思就很費勁,還要學一門語言”。而這時,張潤玲看得出老師們態度上的認真、執著,但教學方法卻是枯燥和單一的。
比如,教“杯子”這個詞,就指著物體把“杯子”重復三次,讓孩子記憶,不僅無法調動起孩子的興趣和好奇心,效率也不高。
其他學科也是一樣。
張潤玲又舉了一個例子—數學。
發達地區的幼兒園已經開始普遍應用“游戲化教學”—這種教學方法旨在讓孩子在充滿樂趣的游戲活動中學習知識、發展各種能力—這是因為“數學活動需要孩子獲得直接經驗,再上升為認知結構。就像數數,大人可以眼睛看著心里默數,但小朋友必須拿著幾張紙片、幾個水果,有親身的感官體驗,才能真正地認識什么是數量”。
但在邊疆、民族地區,“老師們還比較缺乏這方面的指導”。
走訪下來,張潤玲發現,教育扶貧不再單純是硬件設施的捐贈,更應該是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的分享。
論硬件,西部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小,西部個別教學園區的配備甚至比東部更優渥,但教育質量還是有差距。為什么?就差在了“軟件”上。
論硬件,西部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小,西部個別教學園區的配備甚至比東部更優渥,但教育質量還是有差距。為什么?就差在了“軟件”上。
“游戲材料是買了,但不會玩,樂器是捐了,但不認識,怎么利用起來?往后的教育扶貧,對當地教師團隊的專業化培訓指導,是重中之重。”張潤玲說,“這一點上,‘石榴籽計劃是有遠見的。”
“做公益是會上癮的”
在新疆葉城,推廣學習普通話的力度是極大的。
面向教師,當地專門組織了普通話集訓班。但對于一些老師來說,學習仍然充斥著困難。
聲調,是一頭攔路虎。
葉紅梅向南風窗介紹,從學理上看,維吾爾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普通話的字調詞調,在維吾爾語的記憶習慣中是沒有的”。
平時的普通話培訓,基本就是臺上帶讀一句、臺下跟讀一句,通過灌耳音去學習。但這始終是個“笨方法”,“就像是我們生了病,讓你去喝白開水一樣,沒找到癥結”。
于是,去葉城之前,葉紅梅組織專家學者開教研會,基于當地的語言特點,摸索出一套更科學、精準的普通話教學方法論。
比如,講舌尖在口腔中的位置。比如,講聲調的不同音高。
這套方法,果真在課堂上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下了課,學員們會擁上來對她說,只要記住這個方法就能找到調,“真的太好了,從來沒有人和我們說過”。
令人驚訝的是,五天課程下來,沒有學員遲到,也沒有學員請假。
有一位皮膚黝黑的女老師,從中印邊境附近最偏僻的幼兒園趕來,走過危險的懸崖,走過覆蓋在山上的厚厚冰層,車程顛簸了6個小時,最終竟堅持參與培訓。
還有一位懷孕了九個月的孕媽媽,坐得久了,就挺著肚子在教室后方一邊踱步、一邊聽課。
他們踴躍、專注,他們安靜、認真,讓葉紅梅也獲得了力量。
“做公益是會上癮的。”幾位“石榴籽計劃”的工作人員不約而同地對南風窗記者說。
海霞也表示:“在公益推普路上,我決心從‘海霞姐姐做到‘海霞阿姨,再做到‘海霞奶奶。”
一部分人的知識與資源,原來真的被另一部分人熱切地需要著,原來真的可以讓一些人的生活面貌就此不一樣。
第四期課程結束,即將離開葉城的前一天,葉城縣負責教研工作的郭主任拉住了張潤玲的手,閃爍著一雙真誠、懇切的眼睛。
郭主任聲音輕輕地對張潤玲說“:張主任,我有個請求。您能帶帶我嗎?”

“我怎么帶你?”張潤玲心頭一軟。
“您回了天津也別落下我,可以帶著我么?”
張潤玲答應下來。“我一定帶著你。”
她們彼此添加了微信。
回到天津,張潤玲只要去參加各種幼教方向的講座、活動,就會建個線上會議房間,發給遠在邊疆的好友。“真的就像是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結成學習發展進步的共同體。”
在遙遠的青藏高原上,古露鎮的天氣變幻莫測。幾個小時之內,一會下雪、一會狂風,一會晴空萬里。
青藏公路、青藏鐵路橫貫境內,讓這座小鎮,成為拉薩周邊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但也正是因為交通相對便利,過往,古露鎮上條件比較好的家庭,會不遠萬里地把孩子送去拉薩或那曲讀書。
海霞也表示:“在公益推普路上,我決心從‘海霞姐姐做到‘海霞阿姨,再做到‘海霞奶奶。”
這兩年,古露幼兒園和古露小學的學生,慢慢多了起來。
2021年的夏天,“石榴籽計劃”向古露小學捐贈了一間智慧教室,包括納米智慧黑板、多媒體教學設備、音響系統和LED大屏。
通過智慧黑板,古露小學與一些內地學校建立起聯系,給孩子們上云端的數學課、音樂課、美術課。
漸漸地,特意去外地上學的孩子少了,從附近鄉鎮轉來的孩子多了。
美朵說,自己在古露工作了23年,小鎮上的人們大部分從未走出過大山,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就是這兩年,在古露小學,老師和孩子們算是真正開闊了眼界。
令她最感嘆的是一次智慧教室組織的天宮課堂之后,一個來自牧民家庭的孩子畫了張手抄報,畫50年以后的夢想。他在紙張上寫道,50年以后,“我要去月球上踢足球”。
這夢想真的太不可思議了,美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