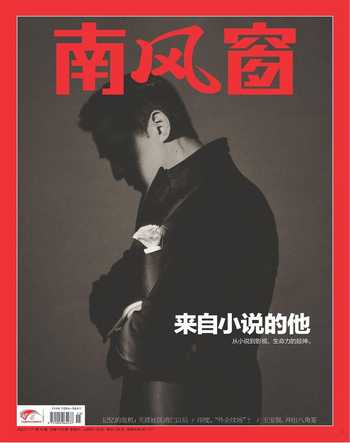印度,“外企墳場”?
龐海塵

對于跨國企業來說,赴印度投資是探險之旅還是捕捉機遇,一直是個謎。
6月下旬,對美國進行了訪問的印度總理莫迪,可謂“收獲滿滿”。蘋果、亞馬遜、微軟、谷歌等美國科技巨頭,不少都做了投資印度的承諾。其中,亞馬遜承諾將在2030年把在印度的投資增加到260億美元。承諾能兌現到何種程度不得而知,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不少跨國企業,近年來都在加大對印度的投資。
但另一方面,印度的現實又不斷在給外國企業做“風險提示”。6月9日,印度執法局發布公告,以涉嫌違反印度《外匯管理法》為由,扣押了小米公司印度分公司555.1億盧比(約合人民幣50億元)的資金。扣押資金、巨額罰款,此前不少外企都領教過。
很難否認,這種“政策風險”或多或少會受政治因素影響,但像2020年蘋果公司印度工廠遭遇打砸搶燒這樣的事件,以及印度營商環境中的“頑瘴痼疾”,不會在莫迪政府政治偏好掌控之內。而對于外企來說,這是更為根本的風險提示。有媒體把印度稱為“外企墳場”,情緒化有點重,但也絕非空穴來風。
數據“打架”
不可否認,正抓緊時機在印積極布局的中資企業開始面臨更多阻力。據《印度時報》報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在2022年,印度公司事務部就已開始審查500多家中國公司的賬簿。
當地時間6月9日,印度政府向小米在印分公司和花旗、匯豐、德意志三家銀家發出通知,宣稱“小米違反印度《外匯管理法》”,向外國實體“非法轉移資金”,以此為由向小米開出了凍結資金的處罰。據悉,小米集團2022年經調整凈利潤為人民幣85億元,這筆凍結資金相當于小米去年凈利潤的57%。
不到一周,印度又有新動作。根據印度《經濟時報》6月13日報道,印度政府要求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擔任CEO等高層職位。據報道,印政府官員特意指示中國公司要遵守當地法律,不得在印度逃稅。
考慮到在印外企頻遭調查、處罰的前車之鑒,這一“提醒”所有在印外企都無法忽視。2008年,印度稅務部門以稅款交付數額不足為由要求微軟繳納70億盧比稅款;2013年,印度監管部門以IBM謊報2009財年營收為由,要求IBM補交535.7億盧比稅款;2014年被印度罰稅2億美元的三星,在今年1月又面臨著印度稅收情報局的新一輪指控,認為三星試圖通過對遠程無線電頭進行錯誤分類來規避172.8億盧比的進口關稅,約合2.12億美元。
但事實的另一面是,印度當局不斷開出的“罰單”,也沒有拽慢外資進入印度的步伐。6月20日,特斯拉CEO馬斯克與當時在美國進行訪問的莫迪進行會面。馬斯克在會后表示,將盡快赴印投資,讓特斯拉進入印度市場。
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也在加速進軍印度。在今年1月舉行的印度汽車博覽會上,比亞迪印度子公司高級副總裁戈帕拉克里希南宣布,比亞迪計劃在2030年占領印度電動汽車市場40%的份額。
根據商業數據平臺Statista的數據,盡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2022財年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仍達到了近84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聯合國2022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則顯示,印度已躋身世界前20大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之列。
如今,持續的外國直接投資,已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說,“外企墳場”這四個字,顯然離現實比較遠。
政策搖擺
對外企來說,赴印度投資到底意味著機遇還是風險,不能只看“媒體頭條”,還取決于某些關鍵指標。
無論是外資企業,還是本土產業,能否實現蓬勃發展都繞不開營商環境這一關鍵議題。根據相關定義,營商環境可以被理解為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涉及的有關外部環境與條件的總和,它深刻影響著企業的生存成本與發展空間。
由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是目前這一領域認可度最高的評價標準。它包含10個一級指標、46個二級指標,從開辦企業成本、監管質量與效率以及公共服務質量等方面對經濟體的營商便利度進行打分。
對外企來說,赴印度投資到底意味著機遇還是風險,不能只看“媒體頭條”,還取決于某些關鍵指標。
根據截至目前最新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印度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63名。雖然距離2014年莫迪上臺時宣稱要進入前50名的雄心仍有距離,但不能否認印度的營商環境確實在改善。報告顯示,印度是進步最大的10個經濟體之一。而在2016年,印度僅位列第130名。
根據上述報告給出的數據,印度在營商便利性方面的表現,遠高于南亞國家的平均水平。與其他主要處于發展中的新興大國相比,印度的表現僅次于中國。中國的營商便利指數位列第32名,同樣也是進步最大的10個經濟體之一。
1991年經濟改革是印度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關鍵節點,也是外資大量涌入的開始。當時印度的經濟發展幾乎停滯,外匯儲備急劇縮水,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面對這一困境,當時的拉奧政府啟動了經濟自由化改革。這一改革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政府壟斷,形成了以私營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與以市場調節為主的經濟運行機制,并通過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增加了外國直接投資對運輸、技術和電力部門的參與。
在2014年,莫迪高舉發展的旗幟就任印度總理,在最初任期內大張旗鼓地進行了以吸引外商投資與改善營商環境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改革。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銷了已有65年歷史的印度全國計劃委員會,并舍棄國大黨已執行多年的“五年計劃”規劃體系,轉而成立“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專司改革的印度國家機構)。有學者表示,這意味著印度經濟政策的決策權被進一步收歸到總理辦公室,體現了莫迪政府的改革決心。
在第一任期內,莫迪確實不遺余力地推出了諸多有利于營商環境改善的舉措,包括大幅降低外資進入印度的制度門檻。但受多重因素影響,莫迪政府的經濟改革呈現出搖擺的態勢。
在某些學者看來,出現這一現象主要源于“莫迪經濟學”的內在局限性。當政策改革進入攻堅期,莫迪亟需經濟反饋爭取民心,但莫迪親商和親資本的舉措卻使貧富分化問題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
面對日益積聚的社會不滿情緒,以及政治上反對勢力的施壓,開啟第二輪經濟改革的莫迪轉而選擇以“印度制造”為中心,試圖以進口替代路線扶持本土制造業。印度的對外經濟政策開始回擺,呈現出明顯的保護主義傾向。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藍建學表示,莫迪政府于2020年3月推出的“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看似是對外企利好的政策,但實際上“有很多變數和先決條件,如強制技術轉移、企業利潤不能轉出印度等。此外,財政補貼與獎勵等優惠措施能不能真兌現,也得畫個大大的問號”。
根據聯合國今年4月的數據,印度目前擁有14.286億人口,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印度的年齡結構還相對年輕化,40%的人口在25歲以下。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21年數據,印度勞動力人口已超過9億。
豐富且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意味著較低的生產成本,巨大的人口基數則指向潛在的強大購買力。在藍建學看來,外資進入印度并非沒有風險,但為了“放長線釣大魚”,還是會選擇盡早入局。
然而,產業發展不僅有與勞動力多少相關,還與勞動力素質緊密相連。印度的勞動力長期存在管理混亂、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此外,印度本土工人鬧事,甚至焚燒外企廠房的新聞時有發生。這也是在印度已深耕15年的ODM大廠緯創資通(Wistron)在今年5月宣布將解散在印業務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印度復雜的法律體系也可能使外資面臨挑戰。印度法律體系遵循英國普通法,理論上為社會提供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制度保障。然而,這一超前的頂層設計脫離印度實際情況,客觀上嚴重抑制了投資需求,也不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
印度《勞工法》被普遍視為經合組織國家中最為嚴苛的勞動法規。以與員工雇傭相關的法律為例,企業員工一旦超過90人,就必須組建工會。如若要進行解聘或裁員,員工多于100人的企業需要先獲得地方政府的審批。
為釋放投資潛力,莫迪上臺后推出勞工改革計劃,但因觸動到工人權益而變得舉步維艱。同樣具有較大政治風險性的舉措還有《土地法案》的修訂。在印度,如果企業需要征地,應當獲得80%相關家庭的許可。為降低征地難度,莫迪政府在2015年初試圖對征地法案進行修改,但這一修正案在國大黨和利益集團的影響下被擱置。
“近期因小米事件形成的寒蟬效應將使外國企業對在印度市場的投資和業務發展更為謹慎,甚至逐漸遠離印度市場。”
除上述因素之外,印度嚴重的政治分裂問題,則是影響印度營商環境穩定性的長期風險。根據安聯保險發布的《印度國家風險報告》,印度種族、宗教情況復雜,與貧富分化問題相互交織,容易滋生暴力行徑和恐怖主義。咨詢公司“惠譽解決方案”(Fitch Solutions)指出,印度持續的恐怖主義威脅,將是長期投資者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寒蟬效應
在莫迪訪美期間,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于6月23日發表題為《不要相信莫迪的經濟成功故事》的文章,認為莫迪將“古吉拉特邦模式”拓展到全國是一種失敗嘗試。“莫迪既沒有成功創造就業,還加劇了裙帶資本主義,‘印度制造前景黯淡。”
在某些學者看來,決心提升印度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莫迪,仍未能將外國直接投資“內化”成國內制造業實力。目前這個階段,跨國企業在印設廠更主要的目的,還是搶奪消費市場,而非基于全球的戰略性布局。
盡管莫迪還未放棄最初上臺時做出的承諾,但由于難以交上滿意答卷,他在優先政策議程上也變得趨向保守。有學者表示,現在還很難確定莫迪的執政重心是否會發生根本性轉移,這也可能只是一種用來掃清前進障礙的政治手段。
只是,國家政策不只受國內環境影響,國際形勢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在藍建學看來,當前國際環境的“泛安全化”傾向開始擠壓國家間的合作空間。“這一轉變尤其體現在中印關系中。考慮到中印之間長期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兩國關系還多了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這個因素,中資企業在印發展也將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2020年4月18日,印度工業和內貿促進局(DPIIT)修改外資政策,規定“任何來自與印度接壤的國家的投資者”都只能在印度政府準入路徑下進行投資。毫無疑問,這一政策主要針對中國,因為與印度接壤的國家中,中國是最主要的投資國。
在這一新政出臺后,中國企業在印投資急劇減少。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藍建學表示,印度的諸多舉措已對印度的國際聲譽和吸引外資的能力造成損害。“近期因小米事件形成的寒蟬效應將使外國企業對在印度市場的投資和業務發展更為謹慎,甚至逐漸遠離印度市場。”“這將使赴印投資的潛在獲益,逐漸被現實中可見或隱形的風險及成本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