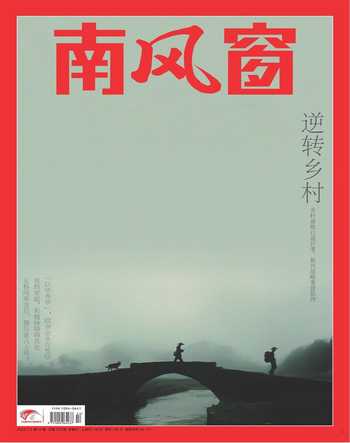戰術核武器是什么?
榮智慧

6月中旬,普京首次證實,俄羅斯已經將第一部分核裝置運抵白俄羅斯境內,在那里部署戰術核武器的工作將于年內全部完成。
此前一個月里,美國允許歐洲盟友向烏克蘭出口F-16戰斗機,德國再移交110輛“豹1”坦克,英國已經為烏克蘭輸送了幾千枚炮彈,其中包含貧鈾彈。
持續一年多的俄烏戰爭就像巨大的泥潭,軍備加碼,雙方都試圖率先打破僵局。
在冷戰結束后,使用核力量更像是“口號”,受到的關注相對有限。相比于受國際戰略核軍控條約限制的戰略核武器,爆炸當量較小、射程更近的戰術核武器,雖然不能在沖突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足以進行威懾、打擊敵人、減少進一步的軍事沖突。
戰術核武更實用
俄烏戰爭中,俄羅斯“伊斯坎德爾”導彈多次打擊烏克蘭的彈藥庫、機場跑道等高價值和加固型目標。一旦升級,“伊斯坎德爾”導彈還可以攜帶核戰斗部,成為戰術核武器。
我們以前熟知的戰略核武器,一般由威力較高的核彈、射程或航程較遠的運載工具,以及投擲發射系統和通信指揮系統組成。美、俄的陸海空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都屬于“戰略核武器”范疇。
而對戰術核武器的爆炸當量、射程,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美國有“戰區核武器”“非戰略核武器”概念,俄羅斯曾使用“戰役戰術核武器”概念,這些都可以叫“戰術核武器”。它大致涉及:射程5500公里以下的地基中程、中短程、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射程600公里以下的潛射彈道導彈;空投炸彈和射程600公里以下的火箭;用于反艦和反潛的核導彈、核魚雷和核水雷;陸軍核炮彈和核地雷。
按爆炸當量來說,戰術核武器的美國標準是1000噸至5000噸之間,按俄羅斯標準可達1.5萬噸—與美國“二戰”時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的當量相同。也可以說,如今俄羅斯戰術核武器的破壞力,相當于二戰時的“戰略核武器”。
在現有條約體系下,戰略核武器受嚴格管控。美俄均保證,對方可以通過衛星,監測己方的“戰略核武庫”,并可隨時現場檢查。除常規檢查外,還可以不定期飛檢。2021年,美俄將《新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延長了5年,同時公開了“家底”:美國有1357枚,俄羅斯有1456枚。
因此,戰略核武器“實戰”用途不大。而戰術核武器進可攻、退可守:進,可以將核戰爭“常規化”,既給對方造成巨大損失,又能推卸發動核戰爭的責任,避免全面核戰爭;退,可以發送“威懾”信號,給對方造成戰術壓力。
不過,戰術核武器什么時候使用,怎么使用,取決于使用者的戰略思想。
冷戰結束前,美國庫存的戰術核武器大概有9000枚。1987年《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簡稱“中導條約”),禁止雙方試驗、生產和部署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陸基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截至2018年,據《核態勢評估》報告,美國的陸基戰術核武器一度只有300多枚,同時俄羅斯擁有2000枚。
由此,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堅決退出《中導條約》,促進開發了W76-2—爆炸當量5000噸,相當于上一代W76-1核彈頭當量的1/20,列裝于8艘“俄亥俄”級彈道導彈核潛艇,裝備在“三叉戟-2”D5型潛射彈道導彈上。任何時候,7艘“俄亥俄級”都必須在太平洋游弋,只能有1艘入港加油。
低當量戰術核武器“對抗”,是當下大國的戰略思路。對美國而言,“戰略穩定”常與威懾相關,自身威懾力不足時,就會缺乏安全感;對俄羅斯而言,“戰略穩定”和地緣環境密切相連,地緣政治的變動會使其產生不安全感。這也造成了二者對戰術核武器不同的定義、開發和使用。
戰術核武器進可攻、退可守:進,可以將核戰爭“常規化”,既給對方造成巨大損失,又能推卸發動核戰爭的責任,避免全面核戰爭;退,可以發送“威懾”信號,給對方造成戰術壓力。
未來戰術核武器的發展方向,可能是低當量核彈頭配高超音速導彈。低當量核彈頭重量輕、體積小、破壞范圍可控,而高超音速導彈速度快、突防能力強、對載體要求低。二者相加,將大大增強低當量核武器的威懾力。
古巴導彈危機,有驚有險
戰術核武器最驚險的一次“遭遇”,莫過于“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因不滿美國在意大利、土耳其部署中程導彈,致使蘇聯多座重要城市受威脅,赫魯曉夫下令運送核武器到古巴。從古巴發射導彈,可覆蓋70%以上的美國領土,相當于在“美國的后院”安上定時炸彈。
美國軍機例行偵查時,意外發現了導彈發射架—蘇聯人將它們塞在貨船上,繞道地中海,經土耳其海峽、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紅軍水兵躲在艙底,避過多座關卡。
當時,美國緊盯蘇聯具有戰略打擊能力的SS-4和SS-5中程彈道導彈,卻不知蘇聯有百余枚短程戰術核武器也蟄伏在古巴及周邊海域。
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起名“阿納德爾行動”。戰略火箭軍第43導彈師裝備SS-4和SS-5中程彈道導彈,共60枚核彈頭。SS-4和SS-5的射程分別約為2000公里和3700公里,假如按美、蘇(俄)后來簽署的一系列限制與削減戰略進攻武器條約標準,并不屬于戰略核導彈范疇,但這兩款導彈一旦被部署到古巴西部,射程足以覆蓋美國東部數十個城市。
10月27日是最嚇人的一天。加勒比海上的蘇聯潛艇差一點使用戰術核武器。
當時,美國兩艘驅逐艦為迫使蘇聯編號為B-59的“狐步”級潛艇上浮,投放了深水炸彈。蘇聯艇長在無法與莫斯科取得聯系的情況下,以為戰爭已經爆發,準備啟動核魚雷發射系統。根據戰爭授權,發射核魚雷需要艇上三名最高階軍官一致同意,副艇長瓦西里·阿爾希波夫中校投了反對票。
而且,事件發生時,古巴上空一架美國U-2偵察機被蘇聯導彈擊落,美國總統肯尼迪正威脅要對古巴動武。
整個危機期間,肯尼迪、美國軍方和中央情報局,都知道蘇聯向古巴派駐了中程彈道導彈,但不清楚蘇方也部署了大量短程戰術核武器。直到1992年,在哈瓦那召開的“古巴導彈危機”30周年研討會上,俄方知情人士才披露了相關情況。
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戰術核武器已經充分暴露了優勢和風險。
首先是體積相對較小,便于隱匿。美國通過高空偵察發現中程彈道導彈,但一直沒察覺短程戰術核武器的存在。肯尼迪與赫魯曉夫達成的協議也沒有涵蓋這些武器,它們在古巴待了一陣子才被蘇聯撤回。
其次是運載工具核常兩用,具有迷惑性。像SS-4和SS-5中程彈道導彈被發現,就坐實了蘇聯“運送核武器”;但如果是發現“月球”火箭營,可能就會被美國忽略。其實,蘇聯派往古巴的3個“月球”火箭營配備了60枚導彈,其中就有12枚核彈頭。美國情報界也發現了FKR-1巡航導彈,但將其誤認為是常規海防導彈。
最后是使用授權下放,控制相對寬松。戰術核武器用于戰場作戰,使用權會預授給戰地指揮官,以便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態勢,而不像戰略核武器,只能由最高指揮機構下達使用命令。
反過來看,戰術核武器的三大優勢,也構成了它的核心缺陷:悄然抵近,暗暗部署,出其不意地使用。然而,一旦跨越這道“核門檻”,危機是否可控?萬一對方回應一枚“戰略核武器”呢?
死亡之手,知向誰邊
這幾年,美俄兩國均對核威懾政策進行調整,重視發展戰術核武器,從而強化本國的“實戰威懾”能力。
特別是精確制導技術的發展,也讓戰術核武器重新進入實戰討論。根據2019年3月美政府向國會提交的2020財年國防預算案,用于研制低當量核導彈的費用上調了8.3%。
B61核航彈是美軍戰術核力量的主要裝備,擁有300噸至40000噸可選當量,目前已經發展到B61-Mod12,增加了自旋火箭和安全與保險裝置,配備全新的精確制導尾翼組件和新型制導系統,圓概率誤差不超過30米。實戰中,B61的主要任務將是摧毀敵方的堅固地下工事,其鉆地版本對花崗巖和混凝土的作用深度可達35米左右。B61-Mod12重700千克,長4米,可搭載于四代戰機,目前已與五代機F-35A集成。
戰術核武器的三大優勢,也構成了它的核心缺陷:悄然抵近,暗暗部署,出其不意地使用。然而,一旦跨越這道“核門檻”,危機是否可控?
上文提到的W76-2,實際是將W76-1的次級拆除,保留初級得到的低當量戰斗部,爆炸威力在5000噸至7000噸,可以摧毀一個小城鎮。W76-2核彈頭不僅裝備“俄亥俄”級核潛艇,還會裝備“朱姆沃爾特”級隱形驅逐艦、“弗吉尼亞”級攻擊核潛艇,使美國海軍成為一支可實施靈活核戰術打擊的“核海軍”。
與美國相比,俄羅斯的戰術核武器不僅數量更多,而且種類、型號更齊備。“波塞冬”無人潛航器既能攜帶2萬噸爆炸當量的戰術核彈頭,也可以攜帶常規彈頭。該潛航器采取核動力推進,作戰航行深度在水下1000米以下。搭載“波塞冬”的09852型特種核潛艇的首艇“別爾哥羅德”號和2號艇“哈巴羅夫斯克”號,目前已經下水。
空軍方面,俄列裝“匕首”高超音速導彈,該導彈可搭載戰術核彈頭,最大飛行速度超10馬赫,射程達2000公里,由米格-31發射,用于打擊陸地和海洋目標,在俄烏戰場首次亮相。陸軍處于短程彈道導彈部隊現代化的最后階段,包括用SS-26代替SS-21。2S7M“馬爾卡”自行榴彈炮已完成現代化改裝,具備發射戰術核炮彈的能力。“伊斯坎德爾”導彈可攜帶戰術核彈頭,其反導系統也配備了核攔截彈。
低當量核武器的研制,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初。
美國有最早的戰術原子彈和核戰斗部戰術導彈。1953年5月25日,內華達州試驗場首次進行280毫米核加農炮的試射。根據評估,炮彈的威力相當于1萬噸至1.5萬噸爆炸當量。蘇聯于1953年試驗了第一枚戰術核炸彈,次年將戰術核炸彈部署在“伊爾-28”轟炸機上。1957年,蘇聯開始在東歐部署戰術核武器,以應對美國將戰術核武器引入北約。
如今,美國在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土耳其這五國的6個空軍基地,部署了約200枚B61戰術核炸彈。它們可由F-16戰斗機或“旋風”攻擊機攜帶,攻擊俄羅斯境內目標。俄烏戰爭膠著,也促使俄羅斯再度于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
核威懾由能力可信度和承諾可信度兩部分組成。“確保摧毀”過分強調能力可信度,但不能忽略前者對承諾可信度的反向影響。在“相互確保摧毀”態勢下,由于己方也一定會被摧毀,威懾方執行核打擊的決心會被對方懷疑,削弱承諾可信度。科幻小說《三體》就運用過這一思路。
戰術核武器避開了這一陷阱,也因此顯得更加“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