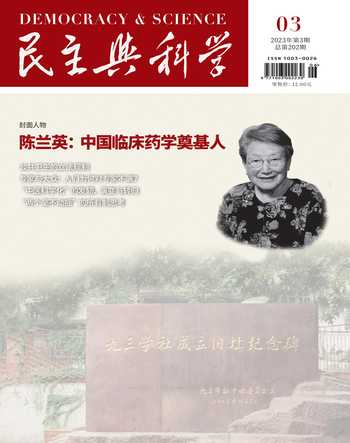為什么德國不同
吳晨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默克爾35歲。她沒有像其他民主德國人那樣,興沖沖地第一天就穿過柏林墻去聯邦德國。當天是周四,是默克爾的 “桑拿日”,她選擇像往常一樣,約了朋友一起去蒸桑拿:既然墻塌了,去西柏林的機會要多得多,不急在一時。她很能沉住氣。
在柏林墻倒塌之前,身為科學家的默克爾早就盤算好了去聯邦德國的計劃,準備像很多民主德國的科學家一樣,等60歲一退休,就辦好手續去西柏林:到時候,帶上積蓄,在西柏林找個警察局換一本聯邦德國護照,然后就到美國自駕游,從東海岸一直開到西海岸。
第二天,默克爾隨著人潮到了西柏林,從陌生人手中接過一罐啤酒。聯邦德國政府給民主德國人每人100聯邦德國馬克的 “見面禮”,默克爾沒有像其他人那樣亂花。冬天的柏林,許多開銷都免不了,在黑市上,聯邦德國馬克與民主德國馬克的比價已經到了一比十。她當時沒有想到,為了推動兩德統一,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會把兩德馬克的匯率定成一比一。
相信無論是默克爾還是當時的全球觀察家都很難想象,民主德國人默克爾在統一后的德國政壇能如此快速躍升。因為沒有歷史的包袱,1990年,默克爾作為民主德國屈指可數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代表,被選入統一后德國的新一屆國會。科爾一下子就看中了默克爾,把她收入自己羽翼之下悉心栽培。
在喧囂而民粹盛行的世界中,自2005年起就擔任總理的默克爾幾乎成為西方各國的壓艙石。
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凸顯了德國與英美治理水平的差異。與特朗普和約翰遜政府不同,默克爾在新冠疫情的處理中表現出沉著、穩健、果斷,備受稱贊。她相信科學,和民眾講清楚形勢,也制訂了詳盡的計劃,把疫情給德國帶來的沖擊減到最小。
約翰·肯普夫納在《為什么是德國:德國社會經濟的韌性》中提出,默克爾的低調與務實恰恰凸顯了戰后德國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大國,有不少地方值得英美學習。雖然默克爾在2021年辭任,但她對冷戰結束之后德國的影響深遠。
1871年1月18日,鐵血首相俾斯麥統一德國,距今只有150多年。而在短短150多年的歷史中,德國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發起了兩次世界大戰,納粹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戰)之后一片廢墟的德國又分裂了44年,真正統一的德國也才只是一代人30年的光景。為什么相對其他西方大國,德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能做得更好?這的確值得我們仔細琢磨。
直面歷史,積極向前
因為1945年前的歷史不堪回首,過去70多年,德國一直努力向前看,也一直力圖成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持重的優等生。二戰后德國直面歷史的態度,體現在三個重要的時間點。
1968年,距離二戰結束已經23個年頭,聯邦德國在這一年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但這一年更重要的事件是戰后一代年輕人的覺醒和反抗。他們把父輩在納粹統治期間的罪惡——要么服從,要么默許——暴露在陽光下,對納粹歷史展開了徹底的清算。
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英雄紀念碑前為死難的猶太人下跪,為戰爭給他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真誠地道歉。我們千萬不要小看勃蘭特的這一跪。這一真誠悔過的姿態幫助聯邦德國獲得鄰國的諒解,不僅為聯邦德國經濟崛起成為歐洲經濟的發動機奠定了基礎,也為19年后冷戰結束時兩德成功統一創造了契機。
1985年5月8日,德國戰敗40周年,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在紀念發言上提出“5月8日是解放日”。這句話很震撼,他認為5月8日不是戰敗日,而是將德國從納粹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日子,這再次表明了德國的態度。和其他大國不同,戰后的德國人很清楚,在現代,它沒有煊赫的歷史可以炫耀,歷史上背負著的都是負資產:兩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包袱、納粹上臺的包袱、屠殺幾百萬猶太人的包袱。德國必須輕裝前行,積極向前。對歷史的清算讓德國人更強調制度建設。
對歷史的反思,讓戰后的德國不僅在廢墟上重建了經濟,也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德國人變得更善于反思。而這種反思,讓德國人一方面更執著于恢復文化層面和社群層面維系人與社會健康發展的紐帶,另一方面對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快速變化有更多質疑。這種反思也讓德國人并不像英美社會那樣盲目崇拜成功,德國人會花更多時間去討論事情背后的意義。甚至在文藝創作領域,德國也有更多棱角,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沉溺于懷舊。
相反,許多英國人對德國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945年之前的刻板印象,并因為電影《敦刻爾克》和《至暗時刻》而被一代又一代地加深。作為旅居德國的英國人,肯普夫納在書中自嘲:1945年,英國丟掉了帝國,卻還沒有找到自己在全球的位置。70多年過去了,英國光是一個脫歐就瞎折騰了四年之久,脫離歐盟的英國將淪為二流國家。相反,德國人選擇只向前看,不回頭。英國脫歐之后,德國將成為歐盟27國名副其實的領頭羊。
戰后德國之所以成功,一個很大原因是它真正吸取了歷史教訓,但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夠理解這一點。《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在新作《劇變》中強調,無論是曾經的大英帝國還是如今的美國,都期望掌握主動權,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國,究其實質,還是因為它們缺少對歷史的反思。
二戰的全面失敗和戰后分裂的痛苦與重建的艱辛,讓德國人更清楚俾斯麥在150多年前就提出的觀點:德國需要清晰地理解大趨勢,必須選擇因時而動,抓住對自己有利的機會。
社會市場經濟
德國與英美到底有哪些不同?
兩德統一之后,德國境內各區域的經濟能夠相對均衡發展(當然兩德經濟還是存在差距)。德國不像英國或法國,倫敦和巴黎占據太多資源,頭重腳輕;也不像美國,東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大都市與內陸之間不僅存在經濟發展的鴻溝,政治上也日益撕裂。雖然德國老牌政黨在走下坡路,極右翼勢力抬頭,但默克爾構建的以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為主的黨派同盟執政超過15年,為德國帶來了穩定。后默克爾時代,朔爾茨率領德國社會民主黨組織新執政聯盟,沒有其他歐洲國家黨派聯盟不穩固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與20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所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不同,雖然同樣面臨全球化的沖擊和科技迭代的顛覆,德式的“社會市場經濟”仍顯示出穩健的發展步調,努力去平衡資本與勞工、大城市與鄉村、短期與長期的關系。而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這一系列關系的失衡,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就不斷產生日益嚴峻的問題。
德國經濟學家阿爾馬克提出了“社會市場經濟”這一概念。德國戰后經濟的發展也順應這一邏輯:一方面,讓市場來配置資源,發展經濟,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在經濟成果的分配上兼顧資本和勞工,體現社會的公平。
德國人特點鮮明。他們守規則,有社群精神,強調秩序。整個德國社會都構建在一種相互肩負責任的基礎上,而這一責任也代表了一種保持平衡的社會態度:國家就是為了幫助弱者挑戰強者,平衡富貴與貧窮。
在企業組織上,社會市場經濟強調勞工與資本的平衡,工會代表進入董事會,工會加入企業的管理。在面臨經濟周期下行或經濟危機的時候,企業盡可能減少裁員,用提前休假、無薪休假、減少工作時長等辦法,共度時艱。德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意識到,強有力的工會和資方與勞方共同遵守的規則是更好的制度安排。勞工的穩定讓它可以避免英美企業在經濟下行時大量裁員給勞工帶來的痛苦,也不用擔心在經濟上揚時需要花大量時間培訓新員工。強大的工會參與董事會管理,也可以確保勞資雙方大多數時候都會選擇協商而不是對抗罷工的方式解決糾紛。
持續投資人力資源,使得德國企業工人的生產率能夠持續提升。這也是2019年就有德國企業率先嘗試“做四休三”的工作制度,減少工作時長,讓員工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享受生活的原因。
資本和勞工有制度保障去謀求共識,也有助于德國企業擁抱“長期主義”。德國企業的中堅是家族連續幾代人管理的中小企業。恰恰是因為資本與勞工的利益的深度捆綁,這些中小企業的發展目標更長遠,它們也能確保自己持續在細分市場保持領頭羊的地位。
德國大企業分布在全國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幾個大城市,也確保了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平衡,以及大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柏林幾乎成為西歐所有大國中唯一對國民經濟不具備主導地位的首都,自然有其歷史原因(當然,柏林也因此成為德國的創意與創業之都)。相比之下,英美等國過去30年越來越多的工商業向主要大城市集中,加劇了社會的失衡。
面臨三大挑戰
2004年11月,在默克爾當選總理之前,有人問她,德國最能喚起她什么情感?她用一貫平實的語言回答:“我會聯想起密閉很好的窗子,沒有哪個國家能制造出密閉性又好又漂亮的窗子。”2021年底,默克爾辭任總理,德國制造的可靠性或許是默克爾管理這個國家留下的最大遺產。
在總理任上,默克爾的低調作風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她行事穩重小心,好像深思熟慮的棋手。隨著在位時間的增加,她越來越謹慎,做事強調邁小步,盡量考慮周全。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德國沒有挑戰。相反,無論是全球化的沖擊,還是技術迭代帶來的創新窘境,抑或是發達國家面臨的人口老齡化難題,都是復雜的難題。
簡單梳理一下,德國面臨著三大挑戰。
首先,在高科技不斷顛覆在位企業的時代,德國企業被普遍認為創新不足。為數不多的德國移動支付企業Wirecard爆出的造假丑聞,讓很多人擔心德國人沒有學到硅谷創新的精髓,卻沾染上熱錢吹捧出的泡沫。英國脫歐帶來的機遇,讓法蘭克福躍躍欲試,并希望取代倫敦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可是,以德意志銀行為代表的德國大銀行還沒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挫敗,依然一蹶不振。在云存儲、云計算和云服務勃興的數字經濟時代,德國軟件巨頭思愛普也和當年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美國的甲骨文那樣,缺乏競爭力。最令人擔心的是德國企業的脊梁——汽車制造業,它會不會在應對電動汽車新勢力時一再貽誤時機。
這一系列質疑都在挑戰德國企業所信奉的“緩慢但踏實”的做法。努力在資本和勞工之間謀求共識的做法,能否適應全球化帶來的更大的競爭壓力,以及科技迭代帶來的更快的變化?換句話說,德國能否適應快速數字化轉型的時代,能否在數字經濟領域推動創新?
其次,全球化的競爭顯然對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帶來了沖擊,德國該如何應對?德國一貫秉持財政保守主義,強調“黑色的零”(對赤字說不),直接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現有的基礎設施缺乏維護,數字基礎設施更是乏善可陳,比如德國的網速在發達的經合組織 (OECD)國家排名靠后。
兩德統一之后,德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基本沒有增長。收入停滯,儲蓄率高,導致德國整體消費沒有大的增長,德國巨大的產能過剩需要其他國家的消費來支撐。
歐盟一體化,短期給德國制造帶來紅利,德國國內過剩的產能可以向歐洲他國出口。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也享受到了發展帶來的紅利,可以以更低廉的價格發債刺激經濟發展。但歐元區的南北差異也帶來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暴露無遺。歐元區第一個十年的繁榮,建立在南歐過度舉債的基礎上。比如,西班牙通過債務激增來消化德國的產能過剩,但在這一過程中帶來了浪費性的消費,以及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的暴漲。金融危機過后,南歐各國至今仍然沒有從債務危機中完全走出,資產泡沫的破滅對德國和南歐國家都有所打擊。
歐盟東擴,讓兩德統一的紅利影響到更廣泛的中東歐。冷戰雙方的工資和生產率都相差甚遠。離德國和奧地利咫尺之遙的斯洛伐克,2000年的工人工資只有德國工人工資的九分之一。因此,過去30年,德國汽車企業在歐洲增加的產能幾乎全部投資在東歐。尋求更便宜的工資水平,在跨國公司眼中無可厚非,但顯然也給德國本身的經濟帶來了壓力。
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德國人也在思考一系列問題:是否過度依賴出口中國?中美未來的貿易摩擦又會對中德經貿關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中國并購德國中小企業中的行業龍頭是否會對德國經濟未來的競爭力帶來負面影響?(美的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之后,德國已經加強了對這類并購的審批。)2020年歲末,歷經七年談判長跑,中歐投資協定終于達成。默克爾一直希望中歐能就市場準入、公平競爭與可持續發展等重要問題達成協議。協議達成,不僅了卻她的夙愿,也為中德未來的經貿發展提供了制度性的規則與保障框架。
最后,統一之后的德國并沒有完全融為一體。柏林墻倒塌30年之后,不少民主德國人再度燃起懷舊情緒,倒不是對民主德國有多少懷念——很多年輕的民主德國人出生在統一之后,而是對全球化帶來的劇變感到恐慌。有人把民主德國人的這種心結比喻為 “心中的墻”。
這種隔閡感也體現在于聯邦德國人不大相同的身份認同。在不少民主德國人印象中,典型的聯邦德國人常常把類似的話掛在嘴邊:我已經厭倦了馬爾代夫的海灘,正在想要不要把自己的奧迪賣掉,換輛新車。
不知道默克爾對這樣的“凡爾賽”體,作何感想?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總編輯)
責任編輯: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