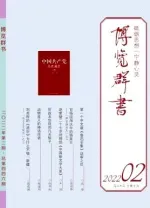隨廢名的《橋》去探尋“自由”
舒翔
現代小說中,論晦澀難讀,廢名當屬佼佼者;論情真辭巧,廢名又得勝一籌。這兩相矛盾的說法集中在一個作家的身上,并不奇怪,也不是首例。因此,廢名的小說,在田園牧歌的流派里往往廣受稱贊,另一邊又被現實主義的主流文學所排擠,被判為狹隘的、主觀主義的個人創作。像我這樣的后來者,初讀廢名時,總有一些閱讀小說形成的“先見”:作者寫的什么?就拿小說《橋》而言,哪個地方的哪座橋?發生了什么故事?人物是什么性格和命運?小說總得交代這些問題吧,反而困住了我們對鄉土小說的閱讀。周作人曾說自己是“坐在樹蔭下”讀廢名的書,溫和清雅,宛如隱逸出世。我們在閱讀廢名的時候,怎么就有些不知所云,甚至還泛起瞌睡呢?
廢名晚期做過一番自我反省,倒讓這個問題變得容易多了:
道理很簡單,里面反映了生活的就容易懂,個人腦海深處的就不容易懂。我笑著對自己說,主觀是渺小的,客觀現實是藝術的源泉。這么簡單的道理當初我為什么不懂得呀!
但容易不一定可靠,也時常削弱了廢名作為文人對時代矛盾探查的敏銳目光。晦澀與真摯之間的矛盾并沒有解決,兩者的聯系若只是囿于作者的主觀狹隘,那么,遺世至今的一大半文學作品都會蒙塵。如今便以小說《橋》為例,我們大抵是要來一場文學的探險,進入廢名的“腦海深處”,尋到那一片樹蔭,才能見識另一處鄉土的風景,挖出這兩者之間的一些必然聯系。
《橋》的創作時期是廢名小說創作的興盛期,在此之后,他也鮮有寫過小說了。小說《橋》在鄉土小說中稱得上與眾不同。《橋》始作于1925年,最后一章大概是在1937年完成,所有章節陸續發表在《語絲》《新月》等雜志報紙。最早出版的時間又是1932年,分為上下篇,共有43章。在首版《橋》的自序里,廢名說這43章“大概占全部的一半……上篇在原來的計劃還有三分之一沒有寫”,他后來又間斷地寫了幾篇,偶爾發表出來,但種種原因之下,《橋》最后成了一部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
《橋》主要講述了小林、琴子和細竹三個人物在史家莊發生的鄉土故事,每個章節就像篇散文,諸如“瞳人”“萬壽宮”“沙灘”“茶鋪”等,有單獨的小故事,自成意境,講述了獨立的生活片段。三個主人公又將這些片段串聯起來,他們的經歷與故事,都發生在史家莊及其周邊的時空中,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故鄉世界。如今看來,《橋》的形式多少有點像情景連續劇,多一篇少一篇也不影響讀者的閱讀,這也是廢名在創作之初想達成的形式——長篇小說兼有短篇的“方便”:每章都要自成一篇文章,連續看下去想增加讀者的印象,打開一章看看也不至于完全摸不著頭腦。職是之故,廢名大膽地在上篇尚未完成的時候,直接開啟了下篇,上篇與下篇之間,毫無鋪墊地跨過了十年的敘事時間,更讓人把不住線索。《橋》不僅沒有一個整體的故事結構,也沒有連續的故事支撐,即便是每個小章節里的故事也沒有個起承轉合,所謂的情節的矛盾沖突、人物的復雜命運和時代的風云變幻,都被廢名所拋棄。可能正是圖這個“方便”,廢名的這篇長篇小說不被一般讀者青睞。與其說是小說,又沒有小說的形,倒不如是散文的集子;與其說是作散文,其文言詞句又不像周作人的樸素清爽,常常跑出來一些詩詞典故,讀起來又不夠順暢和閑適,又倒不如說廢名在寫詩。
因此,廢名的這種寫法讓諸多批評家覺得他“不食人間煙火”“顧影自憐”,大抵都說他沉浸在個人的小世界而缺乏揭示社會現實的作用。比如朱光潛說:“廢名先生不能成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小說家,因為他在心理原型上是一個極端的內傾者。”按照他的解釋,這種創作形式雖是一番獨創,卻又無所依傍,《橋》的風景變成了單調的畫冊,《橋》的人物也成了作者主觀情緒的沉沒載體。后來,廢名的這番獨創被稱為散文化小說或者詩化小說,分別抓著散文的篇幅特征和詩意的文字形式,形成了新的概念。不得不說,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概念困住了《橋》,也困住了廢名。1930年廢名為《橋》作附記時寫道:“(《橋》)教了我怎樣認識道理,學會作文。我對于他也真是一個有情人了。”
我認為,《橋》的特殊性不是其散文化或詩化的表面形式,而是逸散在其內在的斷裂中。廢名每每用如詩如畫的文字勾勒出自然的一片和諧時,一股寂寞也隨之幽然升起。我們也輕易地感受到這股寂寞的與眾不同,也感受到其熱愛與寂寞之間的編織纏繞,越是和諧,越是寂寞。廢名常用夢和幻想來指稱其創造的文學世界,但在做夢與幻想時,仍然能感受到作者、人物與夢境的疏異,與幻想所不能合一的狀態,這一痛苦和寂寞不能被任何東西所和解,因其存在而熱愛,因疏異于此而痛苦,正是斷裂所在。《橋》不僅創造出了一個世外桃源的故鄉,也創造了一個寂寞沉寂的故鄉。
只是從這一簡單的寂寞感覺來說,并不有什么說服力,可能也容易變成廢名“顧影自憐”的最佳罪證。當然,如果從廢名的個人遭遇或者社會背景來進入這部小說,并不能說明其內在的斷裂,反而會讓外部的因素搖身一變,裝成內在于這部小說的因素,最適宜的方式,就是進入小說內部的語言文字,從其文字的巧思里覺察到作者的關切。
廢名擅長錘煉文字。如果讀過他的詩,大概能體會到這種巧思;如果讀過廢名的《新詩講稿》,更能見得他詩詞字句的真功夫。小說《橋》同樣也屬于這一類的作品,大可用同樣的一句話來出顯廢名的創作原則:“他是整個的想象,大凡自由的表現。”
廢名雖然不側重故事,但作者的想象往往擺脫了傳統的敘事邏輯,處處表現出他的自由。比如上篇里《萬壽宮》一章的一處描寫:
冬天,萬壽宮連草也沒有了,風是特別起的,小林放了學一個人進來看鈴。他立在殿前的石臺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著它響。他并沒有出聲的,但他仿佛是對著全世界講話,不知道自己是在傾聽了。
小林一個人來到萬壽宮看鈴,所有的細節都緊緊地貼著這一活動建構起來:風是為了看鈴特別起的;本來荒涼廢棄的萬壽宮,應該野草滿地,風一吹也會有些干擾,冬天就沒了草的干擾;經常三五同行的小林,也是一個人來的,沒有了同伴的吵鬧……看鈴對小林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作者必須鋪設好天時地利人和的完美條件,要風有風,要靜有靜,甚至連小林自己都不能發出聲音,要聚精會神、小心翼翼地“用”眼睛來“望”著,而不是左顧右盼、三心二意地去“看”,“望”仿佛將小林與鈴隔開了一段距離,這鈴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當這鈴已經顯得無比崇高神圣時,轉而回到了小林身上,不是他聽鈴,而是整個世界在安靜地等著聽他。廢名肯定不是旨在寫鈴的神圣,而是要寫人的虔敬態度;這種虔敬態度不是以刻意對人物的直接描寫或敘述來達成的,而是小林的虔敬浸滿了外物,以至于外物的神圣外溢出來,自發地、自覺地體現了小林的虔敬。鈴的神圣與小林的虔敬,合而為一。昔有莊周夢蝶,不知蝶與我;此處便是小林聽鈴,不分鈴與林。虔敬對佛還是對道并不重要,這番手法就已讓短短幾行字充滿了想象力和生命力。
再來看另一處的《茶鋪》:
琴子心里納罕茶鋪門口一棵大柳樹,樹下池塘生春草。
……?……
走進柳蔭,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唯有涼意了。——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畫影為地,日頭爭不入。
茶鋪的女人滿臉就是日頭。
琴子與細竹烈日之下路過茶鋪的所見頗有想象。不管是“池塘生春草”,還是“四海八荒同一云”,皆來自古詩中的句子,在此處都被化為了一棵柳樹和它的影子。本來茶鋪門口普普通通的一棵柳,被描繪成生春草的一口池塘,籠罩四海八荒的一片云,還是一把傘,又是會畫影子的筆……這棵柳樹如何不會讓人“納罕”,尤其那句“日頭爭不入”,廢名頗為自信,自稱為神來一筆,在北大課堂上便以此為例來講究作文如何錘詞煉句。古來多的是“群芳爭艷日”,日頭竟也有“爭”的時刻;雖有“爭”的意思,“不入”又寫出了幾分俏皮與高傲,還寫出這柳蔭與日頭之間的分明,日頭愈是“爭不入”,柳蔭愈是生涼意。日頭若是不爭這塊蔭涼,又爬上了茶鋪女人的臉,此處的日頭又指代滿臉的汗水,用得又巧妙而順暢。同時,“爭”不僅指日頭,還指的是人物的熱燥的狀態和急切的心情,甚至延伸一點,何嘗不是作者自己有一些“爭不入”的處世心態呢?爭則不入,不爭則入?
此處的“爭”與上文的“望”都能看出廢名的詞句功夫。這樣的文辭在《橋》中俯拾皆是,整部小說的種種意象都洋溢著生命力,它們生長在史家莊這片山水之間,某種磅礴的意志驅動著它們化身為人,時而鈴能言語,時而樹能繪畫,時而日頭能爭上一爭,不囿于形體,自由地輾轉在諸多不同的意象中。這種磅礴的意志,可以說是人物的情感,也可以說是廢名的想象力,甚至是作者的生命力。自由的想象力和鮮活的生命力,浸滿了《橋》的整個故鄉世界,從諸多意象中自然而然地溢出,構建起一片世外桃源,奏響一番田園牧歌。
僅此而已,大概還不夠出色,只能說是抒情文學的陳詞濫調。廢名恰恰沒有如其所愿地讓人物也停留在美滿的烏托邦,“望”與“爭”都表達出人物的一種距離感,望而不得,爭而不入,都對應著全文處處所要表達的寂寞。主人公小林在下篇有一句:“我好像風景就是我的家,不過我也最有我的鄉愁。”美麗的風景,豐滿的意象,都處于遙遙的一端,可望而不可即的寂寞都潛藏在每一處對故鄉的回憶中。因此,故鄉的風景不僅只有生動的廣度,也有了情感的深度,熱愛與寂寞共同成了文字的顏色,互為襯托。這種文字所能抵達的強度是簡單地直抒胸臆所不能實現的,一定是作者反復錘煉的結果。這也說明廢名作品的文章之美不只是來自文辭的典雅,其文字的復雜晦澀也是其情感真摯的表現,也構成了更深刻的文章之美。
廢名對《橋》的期望遠不止是一部記錄故鄉、懷念故鄉的小說。他曾經說到小說取名由來,本來想取為《塔》,為了不和郭沫若的《塔》重合,又改為了《橋》,后來聽說日本有本《橋與塔》的書也是講橋與塔,覺得非常有緣分。他還清楚說道:
寫至此,我又深深的有一段心事,只有我自己明白,我的故鄉的確也有一個橋與塔,過了橋就是塔……與諸君的世界自然無緣也。若問我為什么花了這么多時光來寫這么一個東西,則此刻我還不想說。辛苦于人總有好處。
這個故事廣為人知,但也說明小說《橋》中的橋與塔與其故鄉并沒有特別的關系,讀者與后者無緣,于是,讀這本小說應該先要去除掉傳統懷鄉小說的刻板眼光,才能進入小說的“故鄉”,體會廢名的作者“辛苦”。
《橋》中典故的運用也值得一提。《茶鋪》的例子中就有兩個典故,一個出自謝靈運的《登池上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另一個出自杜甫的《秋雨嘆三首·其二》——“闌風長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云”。前者的詩表達謝靈運在官場失意后萌生退隱之心的意志,后者表達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都被廢名直接用在情景描寫中。結合上下文,廢名豈不是典型的“斷章取義”?的確,廢名直接使用了詩句的字面意思,但他并不是隨意挪用來彰顯文采,而是變成了修辭化的表達處理。“池塘生春草”指的是柳蔭就像池塘一樣,是烈日當中難得的一股清涼,“四海八荒同一云”也是指的這片柳蔭仿佛就是烈日中唯一一朵云彩,遮蔽著整個世界。兩句詩不僅使用了比喻,同時也用了夸張,都為了突出意象的特點。作者多次刻意使用這種手法,削弱了典故原本的歷史含義,顯露出自己的創作意圖,也將舊的典故變成了新的現實意義。同時,廢名頻繁地、出其不意地用典,導致文章的字句不僅具有古典的意味,又削弱了其故事的敘事節奏和可讀性,顯得過于破碎殘缺。
廢名講新詩與舊詩時曾討論過如何用典:
詩不能不用典,真能自由用典故的人正是情生文文生情。因為是典故,明明是實物我們也還是紙上的感覺,所以是平面的,溫庭筠的詞則用不著用什么典故了。說到這里我們就要說到李商隱。
也就是說,廢名認為,溫庭筠的詞是解放自由的詩體,本就是立體的想象,不需要用典;李商隱的詩是用典故來馳騁幻想,所以是平面的,需要詩人用靈感或情感來遣詞造句,賦予典故和辭藻的新的意義;后面,廢名還補充說,蘇黃辛陸等詩人用典只是寫韻文的感覺,符合文從字順,只是一種才氣而非詩的感覺。在廢名看來,新詩便是自由的詩,就像溫詞的自由想象,或者像李商隱一樣用新的、自由的感覺去改造舊詞。按照這種說法,廢名在《橋》中如此使用典故的意義就明白了,正是作者以“情生文文生情”的方式,見到或感覺到這些意象的實物時,內心的情感油然而生,不可抑制,樸實的白話無法完全表達這樣復雜而充沛的情感,他必須用典故或其他修辭手法來表達這份情感,由此也生出新的文學表達。
因此,這兩句詩的晦澀難讀所產生的停頓恰恰成了小說的氣口。廢名善于錘煉文字,卻故意“斷章取義”,兩句詩的古典意味并不是其重點,它們所出現的位置也正是敘述將要進到故事或表達將要進入高潮的時刻,用典不僅打斷了敘事,也完成了情感的升華,個人的主觀情感與古人之意產生了對抗,甚至獲得了勝利。熟讀詩詞的讀者能知道典故的古人之意,對小說的表達可能會產生不解,甚至覺得廢名亂用典故,斷章取義;不知道典故的讀者也不難理解其字面意義,可能也感覺到閱讀過程時有一些陡峭的體驗,也感受到作者情感的不平靜。相比而言,前者反而不如后者更容易與作者的情感產生共鳴,而后者又不如前者能夠對新舊文學的差異產生反思。只是在語言文字的中介下,廢名完成了新文學的一次運動,這也是諸多運動口號所無法替代的一種真實的讀者閱讀體驗。在我看來,《橋》的晦澀難讀恰是不容易把握的自由表達,作者澎湃的情感,無法以平鋪直敘的手法來講故事,而是選擇用特殊的手法來表達情感,這一自由是古文白話所不能限制的,是詩詞格律無法束縛的。作為一般的讀者,即便無法分清新舊文學的界限,卻能感受到作者的自由,感覺到作者與文字的合一,作者與讀者的情感共鳴,這一獨特的文學體驗是舊文學所沒有的。
所以,《橋》并不只是用來記錄或懷念故鄉,還有對新文學自由的嘗試和追求。創作《橋》時,廢名當時身在北京西山,遠在他鄉的游子抒發一下思鄉之情,廢名情真辭巧地表達出對故鄉的熱愛和思鄉的愁緒,當然合理,也非常順暢。無法解釋的恰是《橋》的特殊性——非故事而是手法、有短篇的方便而又有長篇的連續、晦澀古典和情真辭巧的矛盾——這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形式斷裂,廢名以高超的文字技巧統籌平衡了古典詩意與現代白話文之間的有限性,從而達到新文學表達自由的無限可能之處。《橋》所體現的熱愛與寂寞的糾纏何嘗不是廢名在新舊文學變革之下的“辛苦”?再想想《橋》是在以散文見長的《語絲》上和讀者面世,周作人把它當散文看,廢名卻還是把它作為小說,又何嘗不是一種表達的自由?小說《橋》的語言文字并不只是一篇自我沉湎的個人小說,在其自由的表達中,顯現出廢名創作動機背后的社會驅動力,也揭示出這一歷史時期對文學重建的經驗特征。
若再延展一點,在《橋》的故鄉中,廢名所流露出來的熱愛與寂寞,也未嘗不是面對新舊文學變革潮流的一種真實情感,他希望通過文學的矛盾形式保留住人的本真性,而不是以現實內容的逼真來偽裝人的本真性。廢名曾翻譯了波德萊爾的《窗》,曾以這首詩來說明自己的文學創作,譯文如下:
一個人穿過開著的窗而看,決不如那對著閉著的窗的看出來的東西那么多。世間上更無物為深邃,為神秘,為豐富,為明暗,為眩動,較之一支燭光所照的窗了。我們在日光下所能見到的一切,永不及那窗玻璃后見到的有趣。在那幽或明的洞隙中,生命活著,夢著,折難著。
橫穿屋頂之波,我能見一個中年婦人,臉打皺,窮,她長有所倚,她從不外出。從她的面貌。從她的衣裝,從她的姿態,從幾乎沒有什么,我造出了這婦人的歷史,或者不如說是她的故事,有時我就念給我自己聽,帶著眼淚。
倘若那是一個老漢,我也一樣容易造出他的來罷。
于是我睡,自足于在他人的身上生活過,擔受過了。
你將問我,“你相信這故事是真的嗎?”那有什么關系呢?——我以外的真實有什么關系呢,只要他幫助我過活,覺到有我,和我是什么?
今天的讀者,同樣面對著各種潮流,有的來勢洶洶,有的悄無聲息,閱讀文學不是一場容易的事情,更像是冒險,需要往那晦澀的深處去探尋,偶爾才能獲得一些情感的真摯和靈魂的自由。閱讀《橋》時,大概也不能只穿過開著的窗看它的內容,也需要閉著它。打開它,我們能體驗文學里的世外桃源;閉著它,覺到里面有我,試著思考我是什么,我應是什么。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22級文藝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