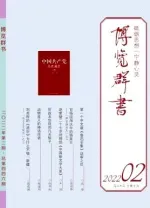輪椅上盛開的沈從文研究之花
唐秀蕓 周景峰
鳳凰因為他,從一座湘西邊城走向了世界,他是沈從文;“沈從文研究”在國內從起步到逐漸走向“顯學”,他的譯著《沈從文傳》作為“他山之石”備受關注,他是符家欽。
1990年4月,時事出版社出版了符家欽先生的譯著《沈從文傳》,它譯自美國漢學家金介甫的《沈從文傳》(1987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印行);從那時起到現在,《沈從文傳》的譯本已經由不同的出版社刊印了六版之多,雖然每個版本都有不同,但翻譯者始終只有一位,那就是符家欽。在《沈從文傳》的基礎上,符家欽又整理出版了《沈從文傳全譯本》《沈從文故事》《沈從文史詩》《沈從文小說評注本》等。而這些都是他在18年的輪椅生活中筆耕不輟的碩果,是“符家欽奇跡”中開出的花。
符家欽(1919—2002)出生于四川省合江縣一個貧苦的匠人家庭,父親是一個木匠,“肩挑負販、走鄉串鎮”,收入微薄。他是家中長子,上有一個姐姐下有4個弟弟,子女眾多之家,常以菜粥糊口。4歲時,他被送進私塾,前后接受舊式教育達8年之久,這也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傳統文化的基礎。1933年初,當沈從文在國立山東大學任教之時,15歲的符家欽考入合江縣立初中,后來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在這里,他開始讀魯迅、郭沫若、柳亞子;也是在這里,他讀到了《新聞學報》,又從《大公報》上讀到范長江所撰“西北采訪紀行”(后來被輯為《中國的西北角》),大為所動,遂立志將來投身新聞事業。
然而,初中畢業后的符家欽卻因家貧無力升學,被迫從業,留校做了書記員,擺寫公文表報,又在一小學兼任語文教員,糊口兼濟家用。1937年,符家欽于師友處籌得學費數十元,考入重慶南開中學高中部,靠為學校繪制教學用圖等半工半讀繼續學業。在這里,《列寧主義概論》成為他讀馬列書刊之始,他還組織怒潮劇社、編輯《怒潮季刊》,宣傳抗日;在合江旅渝同學會會刊事務中一人身兼多職,從撰稿、集稿到印刷所校印,“日夜操勞,亦屬不易”。1939年,符家欽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因抗戰西遷至重慶,今南京大學)地質系,第二年改讀中國文學系,因志在報業,所選課程頗為廣泛,僅外語就有英、法、日三種。他“于每周之末赴童家溪25兵工廠做抄寫工”,“繪制用表、抄寫稿件,以所得酬金,供上學之費”。1943年臨近畢業時,為維持父母、幼弟生計,每日奔走于重慶兩家報館之間,兩地奔波,晝夜伏案,從無休息。即便如此,也是捉襟見肘,難于支應。畢業之后歷任《新民報》《時事新報》《人民中國》《人民畫報》編輯、編輯主任。1958-1978年,40-60歲的符家欽,黃金的二十年在京郊農場和新疆“勞動”“支邊”。1978年復出后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英文組組長、知識出版社副主任。1987年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長期從業有積極貢獻榮譽獎狀。1989年離休。1994年1月任《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條目》責編,獲第一屆國家圖書提名獎。后以主編兩套漢英對照讀物即《名著名譯叢書》(40種)、《名著選讀叢刊》(10種),向新中國成立50周年獻禮。
結識金介甫??“解說”沈從文
1984年符家欽先生66歲,這一年他因病導致腰部以下癱瘓,生活不能自理,被困于九層樓上。痛擊之下,符先生給自己的承諾是“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鍥而不舍,日產一篇;每年一卷,伴我流年”。由于長期受褥瘡的困擾,符先生不能在書桌前久坐,必須每天“四上四下”:早上六點半起床寫作,八點半即需上床休息一次;九點半再次起床寫作,下午一時再次臥床休息,午后兩點又起床寫作,四點又臥床休息;晚六點再次起床,直到最后一次臥床入睡。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高居九層樓上,足不出戶,他感受最深的是每天月亮的變化,“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他給自己的書齋起了個動聽的名字——望月樓。十幾年中他就這樣在望月樓中迎日送月,在輪椅上朝夕耕耘,在書桌前忙得不亦樂乎,“以一天一文、一年一書”的速度創造了四百萬字的創作成果。這是怎樣的一個伏櫪老驥啊。蕭乾說:
我敬佩坐在輪椅上著譯的家欽兄筆耕之勤。他不開會,不旅行,從早到晚都務正業,多大困難也不怨天尤人,只想埋頭做得多,做得好,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界的一大奇跡。
1987年冬天,詩人荒蕪在給符家欽的信中說到他去看望沈從文時,見到了美國學者金介甫剛寄來的《沈從文傳》(原名《沈從文史詩》),幾位學者看過后都認為寫得很有特色,建議符家欽把它譯出來,并很快把原書寄給了他。
符先生“從小就是沈老作品的愛讀者”,在他的眼中,“他(沈從文)的作品風格獨特,寫湘西風物一往情深,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而金介甫則認為沈從文“永遠是全世界所欣賞的文學大師”。作為中外“沈迷”,符家欽和金介甫都喜歡沈從文和沈從文創造的文學世界。而金介甫“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一些來自西方的獨特資料,完整呈現了傳主當時的生活環境和時代氛圍”,也正因為如此,他“在評論傳主的文學成就時,又能放諸世界文學發展和傳播的大環境里,彰顯出沈從文的文學價值和地位”。符家欽在讀過金介甫的原著后也認為它史料翔實、持論平允,既實事求是,又不為賢者諱,遂產生了譯書、向國內讀者介紹的想法。但因為關于沈從文的原始資料掌握不足,老先生遲遲未敢動筆。
1988年沈從文先生謝世,這一噩耗成為符家欽排除困難將傳記快速譯出的突發因由。在蕭乾、荒蕪先生的引薦和幫助下,兩位“沈迷”建立了聯系,并很快確認了翻譯事宜。雙方書來信往,其間符先生從金介甫那里獲取了很多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他們“推心置腹,切磋字句”,進行了許多細致入微的探討,他們在沈從文身上傾注著“如此美麗的、如此令人感動”的熱情。這從金介甫致符家欽的書信中可見一斑。就這樣,符先生潛心鉆研,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翻譯完成了這部30萬字的傳記,并得到了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女士的首肯。
“信達雅”,是嚴復在其《天演論》中提出的譯事三難,所謂“信達之外還要求雅”,“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難,符家欽卻以職業翻譯家的操守欣賞并踐行著。在與金介甫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的基礎上,他細心揣摩原作的形象和意境,不斷地進行著“再創作”,終成譯著,且譯筆精準流暢,情感和溫度并存,不僅得到金介甫的認可,就連沈從文的知交、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施哲存讀后也覺得“不像在讀譯文”,透徹融洽,酣暢淋漓。而646條注文的補譯,“言必有據,無證不信”,更彰顯了原作的風格。正是因為“配上這些文壇逸事,這部文學傳記才能從多側面反映傳主的生平、性格和心路歷程”。
如果說“沈從文是他所處時代的解說員”,金介甫、符家欽是不是也可以說是沈從文的“解說員”呢?
所不同的是,金介甫教授把原著呈現給他的雙親,而符家欽則把這部譯著呈現給他的妻子趙國璋,因為她“是一位平凡而又卓越的女性。在風雨如磐的坎坷歲月中,她頂住社會歧視壓力,忍辱負重,支撐起這個小家,使之免于破巢玉碎”,“她是維系我生命的了不起的支柱”,“特別是病殘以來,她求醫訪藥百般造福,舍棄一切生的歡欣,沒有絲毫怨言。一句話,沒有她的支持,一個殘疾人想完成這部30萬字的書是無法想象的事”。濡沫之情流淌在字里行間。
2002年1月7日,符家欽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于昏迷中去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他太累了,他完成了他那份沉重的生命答卷,永遠地休息了。
坎坷一生終不改仁者襟懷蒼天有淚
身殘半世竟未泯書生意氣翰墨留香
這是兒女們為父親所寫的挽聯,是對逝者的追思緬懷,又何嘗沒有對生者的鞭策與勉勵呢。
兒女們在整理老人的遺稿時,發現了零散不全的《譯林百家》,想到父親為它付出的數年精力,想到被他打擾過的許多翻譯家,他們決心將其整理出版,給逝者和生者一個交代,為此他們還從國家圖書館等處查到部分文章資料,這就是擺在我面前的《譯林百家》。
符家欽羸弱的身軀“躺平”了,他生命和文字里的力量卻挺立著,也傳承著。他曾經那么投入、那么頑強地活著、戰斗著、耕耘著,“雖然一生歷經坎坷,但他從不說假話,對待朋友,他又是一個始終寬容的人,一次又一次的勞教流放,都沒能摧毀他的意志,沒有撲滅他的理想,沒能使他喪失智慧,沒能讓他放棄追求,已年逾八旬的病殘之身,他仍然對前途充滿了信心”“他本身就是一本耐讀的書”“爸爸的品質是我永遠也學不完的”。這是女兒們心里的父親。
沈從文辭世于1988年,彼時的符家欽已經迫不得已地過了四年的輪椅生活。他有記日記的習慣,經年不斷,蠅頭小楷,一字字一行行,筆畫嚴謹,書寫流暢。連日記都記得這樣規規矩矩,怪不得汪曾祺評老先生“心細如發,一絲不茍”了。他的兒子符東義先生說老先生就是用這樣的筆跡在輪椅上耕耘了18年。18年啊,作品付梓排版時,連標點符號都很少修正。語氣中,滿是兒子對父親的敬仰,也有一份發自心底的自豪。
2018年9月,一本120頁的史料集——《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問世。從《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中,人們可以了解《沈從文傳》中譯本成書的前后,找到此傳之所以有多個不同譯本的部分答案,還可以了解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事情。《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以紙成書、以書存史,成為國際視域下沈從文研究一項新發現的重要史料,也是一次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的實證研究。2018年是沈從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2019年是符家欽先生一百周年誕辰。而這本史料集的問世正是對一位文學巨匠和杰出翻譯家的別致而意味深長的紀念。
(作者簡介:唐秀蕓,中學教師,文史愛好者;周景峰,河北省藝術攝影家學會副秘書長,香河縣藝術攝影學會秘書長,《香河攝影》執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