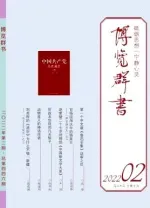王昌齡《出塞》之八面觀
許富宏
王昌齡極擅邊塞詩,他的《出塞》是其邊塞詩的代表作。《出塞》詩曰: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是一首人們耳熟能詳的七言絕句,明人推此篇為唐代七絕的壓卷之作。明代著名文學家王世貞評價說: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藝苑卮言》卷四)
李于鱗,即李攀龍,于鱗是李攀龍的字。李攀龍將此篇推為唐詩七絕的壓卷之作,在當時引起了轟動,王世貞經仔細品味揣摩,也贊同這個說法。可見,此篇確實有深刻的意蘊與動人的魅力。
我認為,此詩有以下意蘊值得人們認真品味。
第一,體現了唐詩的宇宙意識。首句“秦時明月漢時關”,突出了時間的無限延長,詩人身處唐代,下筆卻從秦漢時起,從秦漢時至詩人生活的年代,時間將近千年。同時此句也暗示了空間的遼遠,明月當空,茫茫群山之中有一關隘。為了加強空間的遼闊,次句“萬里長征人未還”,更加坐實了空間的無限遙遠。這種時間上的無限綿長與空間上的無限遼遠,就是唐詩中的宇宙意識的體現。
上下左右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唐詩中普遍存在宇宙意識。所謂唐詩中的宇宙意識就是唐代詩人在描寫的景象中,往往善于寫出時間上的無限綿長,與空間上的無限廣闊,往往超出了人們的視線之外。通過無限廣闊的時空,寫出了大自然的壯美風景,起到動人心魄的藝術效果。宇宙意識在初唐時就有表現,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其中有“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寫出長江水匯入海水交界處的壯闊景象。詩中又說“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也是寫夜晚明凈的天空的遼遠廣闊,并以一輪孤月襯托出空間的無限廣大。盛唐時期,宇宙意識得到全面的展示,如李白在早期寫的《渡荊門送別》中就有“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山在視覺之外了,到了平野的盡頭,江水流入大荒,舉目望去,一望無際,寫出空間的無限廣大。宇宙意識體現在用語上,往往用“一”“孤”與“千”“萬”對照,凸顯空間的遼闊與廣遠,通過造成巨大的反差來產生美的效果。如李白的《渡荊門送別》中的“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故鄉與萬里對比,突出路途的遙遠。《送孟浩然之廣陵》“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以孤帆對比長江,孤帆走出了視野之外,長江流向了天際,空間無限闊大,給人無限的想象。杜甫《江漢》中“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月夜天空中,廣闊無垠,其中一片云在廣袤的天上,描繪了宇宙空間的無限廣闊。盛唐邊塞詩中多有宇宙意識,如王維的《使至塞上》,其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即是宇宙意識的代表句,大漠茫茫,長河流向日落的地方,一縷孤煙升起,更加襯托出空間的廣闊。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遠上至天邊,孤城存于萬仞山,也是寫出了空間的無限遼闊,一下子打開人們的視野,顯示出唐人不同于前人的開闊氣象。因此,宇宙意識可以說是唐詩中的精髓之一,是盛唐氣象的一個重要表現,成為衡量有無宇宙意識是唐詩好壞的重要標尺之一。王昌齡的這首《出塞》體現了唐詩的宇宙意識,上述所列諸多宇宙意識的詩句大都只寫到空間的廣闊,而沒有同時寫時間的遙遠,但這首《出塞》既寫了時間的遙遠,又寫了空間的廣闊,并且將時間放在空間之前,超出了常人,是對唐詩宇宙意識的貢獻,體現了詩人高度的藝術概括能力與表達技巧。
第二,從大處著眼,不做細節刻畫,體現出壯美風格。由于絕句的篇幅普遍短小,五絕20字,七絕28字,短短20多字之中,如果要追求宇宙意識的話,就不可能作局部的細致描摹。因此,為了追求宇宙意識,唐詩絕句雖然篇幅短小,但是普遍表現出來的卻是壯美的風格。時間的無限延長與空間的無限遼闊,營造的是廣闊的畫面,加上邊塞詩風景具有的雄渾、蒼涼、孤寂,帶來的美感是壯美。此詩的前兩句,抓住“月”與“關”,萬里長征,人未能還,寫出邊疆的寥廓和景物的蕭條,渲染出孤寂、蒼涼的氣氛,寫出了戰士悲壯獻身的精神,景象宏偉,境界闊大。
第三,立意高遠,具有現代性。《樂府解題》:“關山月,傷離別也。”樂府中原有《關山月》,漢魏樂府寫關山月,注意表達底層民眾的愛恨情仇,但往往限于戰士戍邊離家的不舍與離別的感傷。《出塞》此首超過普通人的離別傷感,而轉為寫長期的戰爭使得廣大人民不堪重負。這樣,詩人站在關愛人民的立場,同情戍邊戰士為國護邊的犧牲精神。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立場是現在社會的普遍共識。詩人在唐代就能想到人民,可以說具有了跨越千年的現代意識。正因為如此,才能贏得歷代人們的喜愛。
第四,批判現實,將主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詩中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一句,使用了衛青與李廣的典故。《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這次出擊匈奴的結果是“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籠城,顏師古注即龍城。龍城是匈奴大會祭天之所。漢武帝時期出擊匈奴,衛青直搗龍城。元光六年的這次出擊匈奴,號稱漢之飛將軍的李廣也參與了此次軍事行動。龍城飛將,使用了兩個典故,指衛青與李廣那樣的名將。“但使”二字,揭示了唐代沒有這樣的將軍,暗示士兵戰死沙場的原因,乃是朝廷無人可用。朝廷為什么沒有衛青、李廣那樣的人可用?促使人們做進一步的思考,意在批判唐代長期以來不注重軍事人才的培養,有批判唐代現實政治的意圖在內。對此,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評價王昌齡的詩曰:
王江寧詩,其美收之不盡,“奸雄乃得志”一篇,尤是集中之冠。“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每一讀之,覺皇甫酈之論董卓,張九齡之議祿山,李湘之策龐勛,千載恨事,歷歷在目,真天地間有數語言。
賀裳所列舉的詩句中雖然沒有此詩中之句,但是“皇甫酈之論董卓,張九齡之議祿山,李湘之策龐勛”這種意思,即朝廷不辨忠臣良將,最終導致傾覆,“但使龍城飛將在”一句是有此意在內的。
第五,揭示中華民族面對外敵永不屈服的精神。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五千多年,從來沒有中斷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首句“漢時關”,詩人王昌齡這里是借用漢代的精神。漢武帝時驃騎大將軍霍去病出擊匈奴,最終大獲全勝。武帝賞賜霍去病豪宅,但卻被他拒絕了,霍去病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這種強敵未掃,誓不成家,反映了中國人抵御外侮的不屈的精神。漢元帝時,郅支單于禍亂邊疆,征西大將軍陳湯上書,說:“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陳湯獲準帶兵討伐匈奴,斬郅支單于。所以漢時的關隘有名將把守,邊疆穩定,國內安全。“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詩人雖然是指責唐時無名將,但暗中蘊含詩人期盼名將能夠在當時。如有名將把守關隘,就能阻擋胡人南下,抒發了詩人內心希望阻擋古人的意愿,這種意愿也折射出詩人面對外敵永不屈服的精神。王昌齡《從軍行》有云: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金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不破樓蘭誓不還,實際上是漢代“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在唐代的回響,是中國民族永不屈服精神的時代強音。漢代的霍去病與陳湯是軍人,而唐代繼承這種精神的卻是文人,雖然有譴責唐時軍人的意蘊,但更多的是詩人對漢代精神的繼承,可以說是唐人直追漢代氣質。陸時雍《詩境總論》評價說:
龍標七言絕妙在全不說出,讀未畢,而言外自前,可思可見矣,然亦終說不出。
這是蘊藏在字句背后的深沉意蘊。
第六,揭示中國古代國際關系中胡漢沖突是永恒的主題。由于特殊的地形,中國古代大致以黃河為界,黃河以南為農耕文明,黃河以北為游牧文明。隨著一年四季氣候的變遷,到了春夏季節,北方草原長草,游牧民族飲奶食肉相對從容,戰爭也就相對較少。但是一旦到了秋冬之際,草原枯黃,游牧民族要過冬,往往就會南下搶掠,南方奮起抵抗,造成胡漢沖突。這種局面,西周春秋時期即已經開始,歷經秦漢至唐。漢代是中原與匈奴之間的沖突,魏晉時期,烏桓與黃河流域曹操的沖突,南北朝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胡亂華,到了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東西突厥。所以詩人將時空延伸至秦漢之時,也有訴說自秦漢以來,胡漢沖突,導致征人萬里不還。雖然如此,漢代對胡漢問題解決得最為成功,這也是詩人托漢的原因之一。詩人寄望唐代統治者,在解決北方游牧民族問題時要拿出學習漢代的態度,從漢人的身上汲取經驗與教訓。詩歌的這層意蘊藏的很深,不細心加以體會,難以發覺。正因為如此,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寫道:
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
這可堪為確論。
第七,揭示了中國古代“防御性”為主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說:“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意思是,在戰爭中先做好防御,讓自己先不被打敗,然后才能打敗對方。中國是傳統的農耕文明,中華大地擁有黃河、長江這樣的大江大河,尤其是黃河河套地區水草豐美,歷來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的必爭之地。由于北方地區寒冷,或處沙漠地帶,不適合農耕,所以中原的人對掠奪北方游牧地區的土地不感興趣。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因為進入冬季,氣候寒冷,馬羊缺草料,人缺糧食,就南下到中原地區進行搶奪。地理環境決定了,游牧民族往往是侵略者,農耕文明的華夏人往往是防御者。這種客觀形勢決定了“防御性”作為軍事理論的主題。中國人歷來不主張侵略,但一貫重視防御,利用陰山、燕山等這種天然的山脈是一種防御,修筑萬里長城是另一種防御。就連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也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而重修長城。長城的主要作用是為了防御。“不教胡馬度陰山”,詩人在詩中并沒有表達出擊陰山之外、侵凌外族的意思,而是不讓胡馬南下,實際上也是防御性軍事思想的體現。但是詩人指出,如果僅僅依靠陰山、萬里長城是沒有辦法起到防御作用的,真正能起到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還是要依靠將軍,也就是需要像直搗龍城的衛青,或是像“飛將軍”李廣那樣的善于打仗的杰出的軍事指揮人才。這是王昌齡超出常人的地方,顯示出他與眾不同的眼光。
第八,寫景、抒情、議論多種表達手段融為一體。首句為寫景,詩人描繪了一幅月臨邊關的鮮明圖景,邊地雄關,矗立在曠野,既是阻擋胡馬南侵的屏障,也是戍邊將士保家衛國的堅定意志的象征;次句為抒情,抒發了詩人關心守關將士的生命安全的愛民之情;三、四兩句為議論,借漢諷唐,希望唐統治者重視軍事人才的培養,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重大邊防問題。此詩表現了“批判現實政治”,也反映出“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陸時雍《詩境總論》評價說:
王龍標七言絕句,自是唐人騷語。深情苦恨,襞積重重,使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惜后人不善讀耳。
范大士《歷代詩發》評價王昌齡說:
龍標七絕,如高翼矯風,半空落響,危峰墮月,哀壑承泉,首章同調,一見一新,非唯獨秀當時,抑已擅場千古。
這篇《出塞》做到了言之有盡而余味不絕,作為盛唐邊塞詩的代表作,而得到了歷代評論家的稱賞,不是沒有道理的。
(作者系文學博士,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