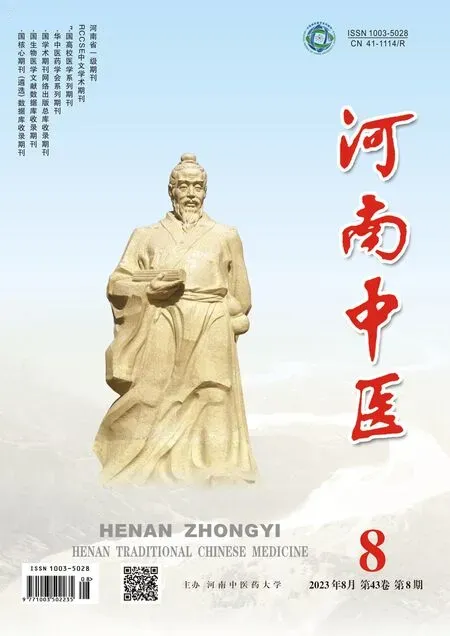《金匱要略》杏子湯所治當為脾脹*
王明炯,匡仁青,姚盛元,宋易寒,歐陽峰松
1.湖南航天醫院,湖南 長沙 410205; 2.長沙醫學院,湖南 長沙 410219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1]第26條云:“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水,發其汗即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歷代醫家對杏子湯主治及藥物組成爭論頗多,筆者認為,杏子湯所治當屬“脾脹”,試析如下。
1 后世醫家對杏子湯的認識
《金匱要略淺注》[2]言:“杏子湯方,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陳修園認為此處杏子湯為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所治為風水。《醫宗金鑒》[3]言:“沈明宗曰……麻黃四兩,杏仁五十個,甘草(炙)二兩。右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得汗止服。” 認為杏子湯為麻黃甘草湯加杏仁。《醫門法律》[4]言:“若脈浮者,其外證必自喘,當仿傷寒太陽例,用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發散其邪以救肺,此治金水二臟之大法也”。
《胡希恕金匱要略講座》[5]言:“‘浮者宜杏子湯’,這個杏子湯,這本書上這個杏子湯沒有、不見,那么各家的說法就不一樣了。有的書上說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那么在這個《醫宗金鑒》他們說就是麻黃甘草湯加杏仁,我認為這些都不對的。這個在《傷寒論》上有,根據這個說明應該是大青龍湯”。
2 水病病機
2.1 衛氣不足,少陰有寒《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言:“師曰:寸口脈遲而澀,遲則為寒,澀為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痹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沖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后,榮衛相干”。
張仲景稱氣分水病為水飲,其代表方為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和枳術湯,一方偏于溫散營衛寒氣,一方偏于溫散脾胃水飲。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言:“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于腸間。”“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以上兩條說明下焦陽氣不足,不能溫化水液,導致小便不通,此為水病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如原文所云:“寸口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19條言:“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男女在水病初期的癥狀是不同的,女性以月經不通為主,男性以小便短少為主。
2.2 水病的發生與胃密切相關《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于皮膚,故為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張仲景秉承《黃帝內經》思想,認為水病發生與胃氣虧損有關。
2.2.1 胃熱是水病發生的病理基礎《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言:“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谷,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趺陽脈侯胃氣,趺陽脈數為胃中有熱,筆者在《從“渴”漫談“風水”與“皮水”》[6]一文中已證明:越婢湯證患者起病之初當有胃熱口渴之證,可見胃熱是水病發生的病理基礎。
2.2.2 胃氣不足是水病發生的關鍵《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言:“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谷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后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腫”。 可見胃氣的虧損和不足與水病的發生密切相關。
2.3 水氣病風氣水三者的關系《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言:“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隱疹,身體為癢,癢為泄風,久為痂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水。”此條所描述水氣病風、氣、水三者的關系,見圖1。

圖1 水氣病風、氣、水三者的關系
3 條文分析
3.1 水氣病筆者認為,“風水”這一名稱所言為病因而非病名,是風邪內侵導致的水液代謝失常,可以有多組癥狀。而張仲景的寫作習慣是,每一個方劑必定有與之匹配的疾病,而每一種疾病也必定有與之匹配的方劑,杏子湯所匹配的疾病是什么呢?
3.2 杏子湯主治必有浮腫《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記載:“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這里用了“諸”字,表示這是一條總治則。而第26條言:“水,發其汗即已。”這一句常常被錯誤地理解為“水氣病宜發汗。”筆者認為其意為:水氣病,通過發汗已經將水氣去除。26條又說:“無水虛脹者,為氣。”此時,水已去,腫仍在。《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第39條云:“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金匱要略》中不少篇章均云:“其形如腫”“其人形腫”,即“無水虛脹”,此時既可以使用麻黃附子湯溫陽,又可以使用杏子湯祛風,按照這個邏輯,麻黃附子湯和杏子湯所治均為非典型水病。由原文第26條可知,不典型水病有以下特點:(1)脈沉與少陰有關;(2)脈浮與風有關。“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由上可知,杏子湯主治為浮腫且脈浮之癥。
3.3 杏子湯主治必有喘癥《神農本草經》云杏仁:“主咳逆上氣雷鳴,喉痹,下氣,產乳金瘡,寒心奔豚。”《名醫別錄》言杏仁:“主驚癎,心下煩熱,風氣去來,時行頭痛,解肌,消心下急,殺狗毒。”筆者總結了《金匱要略》與《傷寒論》中使用杏子治療疾病的條文,擇要列舉如下,《傷寒論》第43條言:“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樸杏子湯主之。”第18條言:“厚樸杏子佳。”第35條言:“太陽病,頭痛發熱……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第38條大青龍湯證,為傷寒表實證,應有喘癥。《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治》第19條云:“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16條言:“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風氣百疾”提示可能會有喘癥。由上可知,杏子所治病癥有:(1)欲發喘癥;(2)喘癥;(3)大便難。有喘癥仲景未必用杏子,但用杏子時若沒有大便難的癥狀,則必定有喘癥或欲發喘癥。以藥測癥,杏子湯主治必有喘癥[7]。
4 杏子湯主治當屬脾脹
由上文可知,杏子湯主治癥狀必定有:浮腫,脈浮,喘,而《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全篇只有一條此類記載,即原文第4條:“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為風水……咳而喘,不渴者,此為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現將此條文分析如下。
4.1 太陽風寒之變證劉維政[8]認為,對變證的討論是辨證論治的精髓所在,現將該條文所言的太陽風寒之變證敘述如下,見表1。

表1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4條所言的太陽風寒之變證
“太陽病”“脈浮緊”“骨節疼痛”為麻黃湯證的表現,但此處的“反”字,說明此證雖為感受風寒所致,但卻不是麻黃湯證,可能為“風水”或“脾脹”,而風水與脾脹的最大鑒別點為是否有咳喘。
4.2 脾脹可以出現咳喘《靈樞·脹論》言:“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文中并無“咳而喘”之癥。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言:“病苦脾脹腹堅,搶脅下痛,胃氣不轉,大便難,時反泄利,腹中痛,上沖肺肝,動五臟,立喘鳴,多驚,身熱汗不出,喉痹精少。”可見脾脹引起咳喘的病機為“上沖肝肺”,導致肺失宣降,出現“喘鳴”。《靈樞·脹論》[9]曰:“衛氣之在身也,常并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然后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2條言:“風氣相擊,身體洪腫。”該篇第21條言:“……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沖,喉咽塞噎,脅下急痛……”可見脾脹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結寒所致的氣上沖,病機為外感風寒,觸動體內結寒,引發氣上沖。鄭翠婷等[10]認為,脾脹的發生,多以實證居多,以寒濕之邪為主。
4.3 仲景治療肺脹不用杏仁《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13條言:“咳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第14條言:“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越婢加半夏湯與小青龍加石膏湯中均不含杏仁,因為肺脹的主要病機為水飲內伏,治應以化水飲為主。《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4條言:“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可知肺脹可轉化為風水,而仲景治療風水的方劑如越婢湯、防己黃芪湯中也無杏仁。
綜上可知,杏子湯主治當屬脾脹,其藥物組成為麻黃、杏仁、甘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