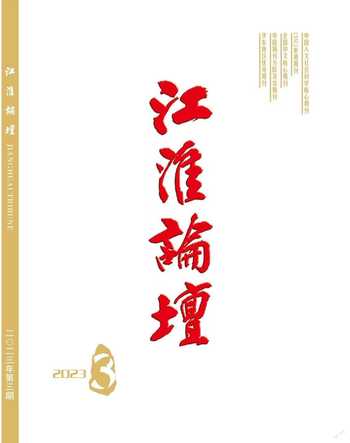鄉村旅游的空間生產與本質歸元
江立華 陳暉月
摘要:鄉村旅游是助力鄉村振興的新興生產力。文章以湖南省Y縣L村鄉村旅游發展為例,基于資本與村民的互動關系,從村莊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角度探討鄉村旅游與村民生產生活的互嵌關系,以期找尋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之路。鄉村旅游要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重回村民日常生產實踐,將資本驅動的鄉村旅游與村民生產生活互嵌,建構以村民為中心的生產空間、營造獨具鄉土文化的生活空間和塑造可持續的生態空間。
關鍵詞:空間生產;空間;鄉村旅游;生活方式
中圖分類號:F590-05?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3)03-0084-007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鄉村振興進入新時代,鄉村旅游成為助力鄉村振興的“新引擎”。《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合理規劃建設特色旅游村鎮,因地制宜推動鄉村旅游差異化、特色化發展,推進多元功能聚合,營造宜居宜業宜游的休閑新空間”[1]。當前,許多農村依托豐富的鄉土文化資源、保護較為完好的生態環境發展鄉村旅游,促進了鄉村整體面貌的改善。但是作為一種新興產業,鄉村旅游在發展中面臨諸多困境。一是雖然在制度設計上要求鄉村旅游因地制宜、特色化發展,但實際運作中卻往往忽視村莊公共空間和生態空間的建設,破壞了鄉村原有的自然、和諧,旅游開發同質化現象突出。二是資本主導著旅游發展的方向,市場與村民主次顛倒,本應發揮主體作用的“原在地者”村民成為鄉村旅游發展的邊緣角色,市場成為主導鄉村旅游空間生產的主體。
針對鄉村旅游發展的困境,已有研究一是從制度層面,提出通過“政策嵌入”和社區內外主體互動生成地方制度等客觀機制[2],圍繞具體的鄉村環境制定出系統化的旅游產品開發體系,從而糾正當前存在的執行偏差;[3-4]二是從發展模式層面,提出將“生產—生活—生態”相結合,推動景區走向鮮活的日常互動體驗,建構起多主體共同治理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5-6]三是從參與主體層面,提出應該明晰政府與市場對于旅游開發的邊界,在政府主導之下引導資本下鄉,同時結合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推動企業與社區達成一致的資源開發目標和立場,將經濟事務轉化成公共層面的治理事務,實現資本的責任投資;[7]四是從村莊空間層面,提出進行空間賦能,以村民傳統生活空間為基礎,在農文旅結合中重塑鄉村性。[8-9]
總體上看,已有研究揭示的鄉村旅游發展的邏輯與路徑,主要立足經濟思維,將鄉村旅游看作是以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為目標的新業態,將政策作為一種服務工具,而沒有將鄉土文明作為發展鄉村旅游的內生要素,也忽視了村民的主體地位與能動性。鄉村旅游作為新業態,其必然重塑村莊的生產生活空間。當前研究還存在僅從政策、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角度分析鄉村旅游,脫離鄉土底色的空間系統,無法找到農村農民現代化的路徑。本文案例村L村鄉村旅游的發展,經歷了從資本驅動的空間生產到“村民在場”的空間生產的轉變。第一階段,資本的介入造成生產空間的純粹生計化、生活空間的疏離化和生態空間的非持續性,給村民的正常生產生活帶來困擾,進而引起村民的反對。第二階段,政府引導構建鄉村旅游讓位于以村民日常生產生活實踐為中心的“三生”空間生產,真正使得鄉村旅游成為村民的生活方式。這一變化過程為回答鄉村旅游為誰發展、如何發展問題提供了有效的經驗素材。
二、村莊空間生產中的資本與村民
(一)外來資本與村委會“合作”
各地發展鄉村旅游,外來資本大多通過與基層政府“合作”的方式進入,與村委會建立“委托—代理”關系,形成兼具行政合法性和市場合理性的資本。具體地說,外來資本將與村民的合約關系委托給村委會,通過村委會的行政代管對鄉村旅游的經營主體進行統籌,而“村委會則將生產要素交給外來資本進行統一開發利用,對村莊空間進行鄉村旅游發展的包裝及市場化運作”[10]。
外來資本之所以選擇與村委會“合作”,主要是考慮村委會作為基層政府的末梢組織,不僅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身份,而且具有利用地緣關系獲取村民認同的優勢。村委會承擔著發展鄉村產業、帶領村民致富的重任,在“國家—村民”之間起橋梁作用,使得他們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能輕易將制度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本,并依托政治合法性以集體經濟的名義將村莊內部的資金、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整合利用,為外來資本的進入提供了有利條件,外來資本則通過對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整合利用,以迎合市場的“景觀化”手段吸引客流,促進村莊的旅游開發。
(二)資本的空間生產邏輯
資本空間化是指外來資本借由發展鄉村旅游,依附于商品、土地、勞動力等多種要素進入村莊空間,實現農民與土地空間所有權的分離,將村民和土地全面納入資本生產空間結構。空間資本化是指村莊空間從自在空間向資本空間轉變,一方面是對于空間這一生產要素的商品屬性的發掘,促使空間生產方式重組,另一方面改變空間的社會屬性,資本化傾向的社會關系導致“原在地者”村民逐漸失去對村莊要素的主導和支配。
鄉村旅游的發展,資本在運作中會從單純的市場邏輯擴展到“社會—市場”邏輯,對村莊空間的控制會從單純的經濟層面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領域,重塑村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也就是說,資本驅動下的空間生產,包括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三個層面。生產空間是生產者借由生產工具與勞動對象互動,進行日常生產實踐,并由此建構出特定生產關系的空間,它不僅是單純的地理空間,也是技藝與記憶借以傳承與再現的空間;生活空間是人們生活與交往的空間,包含了家庭生活空間與公共生活空間,內含真實的、富有人文性的共同價值。正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中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所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并被社會關系所生產”[11];生態空間不僅指為人類生存發展的生態服務或生態產品的自然空間,也是人與環境進行直接對話,進而獲得精神依托的場所。人們通過對于物的直接感知、構想與再現,實現對生活世界的親歷與意義建構。“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作為一個整體性的三元空間,構成具有方向性、關系性和環境性的生命系統。
資本空間化與空間資本化在促進鄉村旅游發展、讓村民得到要素分紅或者成為雇傭勞動者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生活空間疏離化、陌生化,并最終危及鄉村旅游的可持續性。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讓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與鄉村旅游共生,構建出資本與村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讓“原在地者”—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實踐嵌入鄉村旅游發展,享有村莊空間生產的主動權與話語權,進而實現鄉村旅游的發展與村民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同步。
(三)案例村概況
田野點L村位于Y水河畔,地形以丘陵和盆地為主,全村面積7.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4040畝,林地面積3800畝,魚塘水面245畝,截至2021年,L村共有44個村民小組,1291戶,4541人。歷史上長期以種植業為主,漁林、手工業為輔。村內的楊家洲漢墓群在201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留存有500年前的“一元第”古牌坊及恢復重建的孔廟。
自2008年開始,L村充分利用山水林田河湖等自然資源以及文物古建等歷史文化資源發展鄉村旅游。2009年,L村成立Y縣第一家學生社會實踐基地,由此開始走上鄉村旅游發展之路。由于鄉村旅游發展前景不確定,前期參與這一項目的村民寥寥無幾,僅由幾個村“兩委”成員家庭進行試水。隨著研學旅游的逐漸風靡,一大批外來資本通過市場和政府進入L村,2018年,L村以農田重金屬治理為契機,運用種植結構調整補貼政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流轉村民耕地2000余畝,同時組建資產股份合作社、旅游股份合作社、勞務股份合作社及置業股份合作社等5個合作社,集中利用土地種植花海、西瓜等經濟作物,為外來資本的進入打開市場,隨后LZ種植專業合作社、G成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進入村莊。2021年,S休閑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進入L村,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和便利的基礎設施發展旅游農業與休閑觀光農業。與此同時,部分農戶作為研學旅游的接待戶承擔游客的食宿,由此形成了“村委+基地+合作社+公司+農戶”的旅游業發展模式。在伴隨著“資本下鄉”的鄉村旅游發展中,村民是資本鏈條上的服從者,不斷讓渡著生產生活空間的話語權,村莊社會從一個具有人文性的生產生活空間逐漸轉變為逐利性的消費空間。2022年后,政府、村委會和部分村民意識到資本對村民和鄉村空間的排擠,開始認識到讓鄉村旅游回歸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實踐的重要性,并探索出了一條以村民為核心的鄉村旅游新路。
三、鄉村旅游的空間生產:從“資本驅動”到
“找回村民”
外來資本在基層政府的支持下進入村莊發展鄉村旅游,不僅影響了鄉村的經濟發展,也關系到村莊社會秩序和村民生活方式。
(一)資本驅動的空間生產
1.生產空間生計化
外來資本進入村莊更多是從資本增殖角度對空間進行開發利用。2021年S休閑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入駐L村后,以文旅結合、團建度假為主要內容,先后開發建成愛情大道、彩虹橋、漂流等旅游項目,并且逐漸將村民所經營的種植業、養殖業等個體產業納入資本的生產鏈條之中,以統一的標準對產業進行包裝和宣傳,形成農旅結合、文旅結合的產業發展模式。學生社會實踐基地則牽頭進行農業文化長廊建設,在田間地頭呈現活態化、情境化的農業文化遺產。同時村委會組織村民出售自家農副產品,如此便將旅游業、農業與手工業結合在一起,形成“村委+基地+合作社+公司+農戶”的旅游業發展模式。
與此同時,“原在地者”村民產生分化,村委會作為村級集體經濟代言人成為外來資本的合作方,部分村莊精英在以旅游業為主導的產業鏈中居于上端,而普通村民中一部分人“離土不離鄉”,成為鄉村旅游的服務人員;另有一部分“不離土不離鄉”,但是其生產性質從自由經營轉變為資本化經營鏈條上的一環,其生產資料及產品均受資本的統一調配。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原有的主客體親和性的喪失,意味著村民的生產空間轉變為資本驅動下的純粹生計空間。截至2021年,L村僅有13%左右的勞動力從事種植業,這一部分人多在60歲以上。他們憑借著多年的種植業經驗,成為水稻、油菜、西瓜種植大戶的雇傭勞動力,同時成為農耕文明展示的活標本。
隨著資本對村莊空間的全面滲透,村莊空間本身變成了可增殖的資本。生產活動被置于資本及其背后權力關系的介導下。該村“村委+基地+合作社+公司+村民”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表面上看似乎使得村莊空間在結構和功能上實現了村莊空間秩序的再生產,但實際上這是由資本及其代表設定的空間秩序。外來資本和村莊精英利用旅游業發展生產出等級化的生產關系。發展鄉村旅游帶動了包括農業、工業、手工業、服務業在內的一系列上下游產業的發展,普通村民通過種植、養殖、務工等生產活動參與到鄉村旅游中,全村50個作為接待戶的農家每接待一個游客,其食宿費由村委會抽成50%,村集體及基地從中分紅達100萬元左右。除接待戶外,旅游業提供了約150個就業崗位,分布在保潔崗、旅游設施維護崗、農耕文明展示崗等崗位,而產品開發崗、技術支撐崗則大多由村委會成員及外來資本代理人承擔。普通村民的主體地位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并沒有隨著旅游業發展凸顯出來,他們居于產業鏈下端,然而產業鏈等級化帶來的普通村民表面化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是鄉村振興中生活富裕的本義所在。
2.生活空間疏離化
生活空間包括公共生活空間和家庭生活空間。公共生活空間承載著社會活動和地方文化精神,是村民通過社會互動和情感共享而建構“自致性強關系”的理想場所。外來資本進入村莊,通常憑借著內外部的公共資源優勢,意圖掌握公共生活的話語權,而村民作為公共資源的劣勢方,在公共生活空間建構中通常只是追隨者。一方面,公共生活空間在資本的驅動下,逐漸凸顯出由身份等級所決定的排他性與競爭性,導致村民喪失空間實在感,缺乏庭院、田間地頭的交流。村莊空間文化活動通常由以外來資本為代表的村莊精英主導,如在鄉村旅游文化節中,普通村民在策劃到舉辦的整個過程中僅僅是作為“活標本”“移動工具”存在;另一方面,資本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加速對村莊空間景區化、商業化、市場化的改造,村民原有的地緣親和性被資本切割,社會交往和公共事務參與大多在諸如黨群服務中心、公司辦公場所等正式的公共空間中進行,缺乏高質量的集體活動和公共性的社會參與,公共性式微,在精神上逐漸缺乏共同體意識,并進一步導致村民之間社會交往質量的下降,村民之間的互惠關系逐漸從“今天你給我家一把菜,明天我幫你家包粽子”轉變為付費機制。村民間的人情味被物化、商品化,人際關系走向疏離與陌生。
隨著公共生活空間與家庭生活空間的分離,居住空間的使用價值讓位于價值,村民生活發生異化。一方面,在旅游接待上,旅游接待戶的家庭布局由基地進行統一規劃與驗收,游客床鋪設計成清一色的大通鋪,游客菜單也由基地統一制定。另一方面,資本引導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在村莊中變質為盲目的“物以新為貴”“物以‘西為貴”,而忽視了與家庭傳統文化和整體格局的匹配。村民逐漸喪失對自我生活方式的建構能力,傳統的特有家庭文化逐漸趨于同一化。
3.生態空間非自然化
在資本的驅動下,L村的生態空間,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自然性逐漸讓位于資本的逐利性。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外來資本以打造“Y縣小桂林”為目標,大力開發村里的河道池塘等自然資源拓展旅游項目。為了擴大湖泊觀賞和游玩面積,資本方還將耕地開掘成湖泊池塘,并進行人為筑堤,從而破壞了耕地的水利灌溉系統。另外,許多旅游設施建筑于農田之上,對農田的肥力等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為了給游客提供“山居”的旅游體驗,外來資本在林地投資建造民宿及一系列配套設施,人為地破壞了林地的生態平衡。
(二)“找回村民”的空間生產
2020年9月以后,國務院辦公廳陸續發布了《關于堅決制止耕地“非農化”行為的通知》《關于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等文件,為L村鄉村旅游的整治和轉型提供了政策契機。2022年,Y縣根據中央要求出臺了《土地非糧化和非農化整治方案》,鎮政府要求S公司拆除原建于耕地上的旅游設施。S公司面臨800余萬元投資沉沒的處境,L村面臨大量土地和勞動力何去何從的困境。政策這一外部性因素的介入宣告了資本驅動的鄉村旅游空間生產模式的不可持續,也說明了鄉村旅游的發展不能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因此,如何將外來資本從村莊空間“人—地”關系的解構性因素轉變為服務于村民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工具,成為L村必須直面的課題。L村的做法主要從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生產中逐漸找回“失蹤的村民”。
1.生產空間人文化
以土地非糧化和非農化整治為契機,基層政府發揮行政力量的優勢參與空間治理,同時L村村委會轉變旅游發展的主體定位,讓村莊空間的生產重回村民日常生產實踐。通過評選各類生產活動的杰出代表,凸顯“土專家”“田秀才”在鄉村旅游中的作用。非遺的跨文化傳播將受到關注[12],“土專家”“田秀才”以他們對農業文化遺產的知行合一為資本,服務于生產活動的精細化、藝術化創造,從而不斷在鄉土文化和鄉村旅游的結合中增殖出價值。如“田秀才”將作物的生長歷程搬上研學課堂、“豆腐專家”將磨豆腐的工序打造為團建體驗項目。通過這一類日常生產實踐的實景展示,針對游客中的不同年齡群體,喚起年長游客對于傳統生產實踐的記憶感或激發年輕游客的新鮮感和探索欲,以此滿足游客的差異化需求。
2.生活空間人情化
L村在旅游經營中,挑選了50戶村民作為接待戶承擔研學學生或游客的食宿服務。學生或游客入住農家之后,房主會帶領他們到菜地里采摘新鮮的艾草和蔬菜,隨即教他們制作艾葉粑粑、燈盞糕、南瓜餅等特色小吃。除去基地組織的集體活動,學生們還以小組為單位在村民家中度過三天兩夜。村民的家庭生活被真實、全方位地展示。研學學生或游客通過“進入現場”與村民同吃同住以及持續性的交談,切身地感受村民衣食住行的具體形態,從而對農村生活從固有印象和表面化認知上升到自我感知和自我體驗。
作為公共生活的具體表現之一,儀式性活動在L村鄉村旅游中凸顯出重要性和獨特性。如在游客的一項體驗活動“唱章”中,村民通過儀式性活動傳承著他們對生活空間的認同與歸屬。資本的介入方式是組織游客進入到儀式性活動中。如此,游客雖然是通過“付費”機制進入到村莊的公共空間之中,但卻能夠與村民共享信仰與儀式,從而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找到心靈的歸處。在活動中,村民及游客匯聚一堂,在村口處架起以楓樹木為主體,雜以檀、柏等木的寶塔狀天架,擇吉日寫有祝禱類話語的條幅于其上,鞭炮聲響,架香燃起,人們在架香前祈愿,隨后在各家各戶門前張貼“平安”符,最后村民和游客共進“唱章”宴席,在這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詮釋。
3.生態空間本真化
在“找回村民”的生態空間生產中,L村以鄉村土地資源的整合利用和生態環境的提檔升級實現鄉村自身價值的提升,將保護生態有機融入到旅游發展之中。L村村委會根據上級政府要求,嚴格落實“河長制”“林長制”和“田長制”。在實際運行中,山水林田湖草保護制度在村莊落地過程中被日常生活實踐重新解讀,政策語言轉化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語言,通過墻畫、環境整潔評比等方式轉化為村莊生態空間再生產的一部分。村委會在完善村莊基礎設施,凈化、亮化和綠化人居環境的同時,提倡村民在自家院落栽花種果,由此營造出“春賞菜花夏嘗瓜,秋賞桂花冬品果”的景觀。村民在將生態要素轉化為生態資本的過程中嘗到了甜頭,從而自發地打造庭院式院落。村莊生態空間的本真性回歸,既提升了村民生活的品質,也促進了旅游業自身的可持續性發展。
四、本質歸元:重塑“村民在場”的鄉村旅游空間
鄉村旅游作為一種新興業態,其興盛一方面是由于現代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社會矛盾和生活壓力,引發的居民新需求。鄉村承載著人們的情感寄托與傳統的文化價值觀。生活在城市的人們對鄉村景致、節慶民俗的向往,也有對家國情懷、家訓家風、鄰里守望、誠信重禮等風尚的推崇。發展鄉村旅游其實質是在追求生活富裕的基礎上啟迪民智,從人的內心、自我進行探尋,找尋到本真的人性,達到人與自然空間和合共生的精神境界,從而實現空間再生產與人的再生產的“歸元”。鄉村旅游在村民生產生活的村莊空間進行,應當真正成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村民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生計方式。當前,許多地區的鄉村旅游僅僅被作為一種服務經濟發展的工具。資本驅動的旅游業短期給村民帶來了收益,但是從長遠看資本空間化和空間資本化定會對鄉村社會造成危害,無法帶來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要把鄉村旅游作為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手段,關鍵在于堅持以村民為主體,讓村莊空間本身以其自生的生產關系及其社會網絡吸納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資源。而資本則應成為村莊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構成要素,以市場優勢嵌入到村莊社會之中,促進鄉村旅游發展本土化與市場化的統一、村莊本身人文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的統一。也就是說,鄉村旅游的發展不僅要給村莊帶來經濟效益,更要實現村民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只有讓村民日常生產生活嵌入旅游發展,鄉村旅游才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從精神上改造村民,讓他們以一種新的視角去看待他們身處其中的世界和他們自身,才能讓游客從傳統與現代交織的鄉村文明中探尋到“家”的社會文化根源,彌補其在個體化社會中的孤獨感與“無家感”。
(一)生產活動嵌入旅游,重塑以村民為中心的生產空間
生產活動嵌入鄉村旅游,就是將村民生產實踐重新引入到空間生產的中心,以生產實踐引導鄉村旅游的發展,讓鄉村旅游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和人文底色。
城市的快節奏生活驅使人們回頭尋找具有傳統意味的農村圖景。然而,城市生活方式的擴散讓鄉村也難以保留具有原真性的生產實踐。這就使得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重塑成為鄉村旅游的發展取向。作為農耕文明的活的載體,村民是生產空間的核心。在將生產實踐嵌入旅游中時,村民首先應該從意識層面自覺地對生產活動進行美學闡釋,以主人翁的精神促進生產空間的現代化轉型;其次是在實踐層面上對包括土地在內的農業生產體系及景觀進行審美再發現與再創造,促進有本土特色的生產活動藝術化、人文化,讓旅游真正成為一種能夠展現時代價值的鄉土文化,而非短期的生計來源。與此同時,政府、資本等外部力量則充分發揮自身行政力量、社會網絡和市場手段的優勢,從村民本身生活方式變革與滿足受眾需求兩方面幫助村民將日常生產實踐藝術化、市場化,但同時保留鄉土性。首先,外部力量應以村莊本身的人文、生態等為底色,為創造性地使用、轉化農業生產活動中的文化遺產和生態資源,因地制宜地發展特色旅游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規劃建議。其次,通過在田間地頭打造農業文化展示坊等專業機構,將物質遺產和農民主體性相結合,集中展現村民的日常生產實踐。游客在歷史與現實的轉換中更真實地體會到農業生產實踐中人與土地的關系,從而重新找尋到內心的歸屬與逝去的價值。在村民賦權的生產實踐話語體系之中,村民與外部力量及游客形成良性互動,實現空間生產的正義性和價值重塑。
(二)日常生活嵌入旅游,營造獨具鄉土人情的生活空間
村民的日常生活嵌入鄉村旅游本質上就是將村民的真實生活情境放置于鄉村旅游的核心位置。對于游客來說,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碗一瓢都是旅游場景的展現。這些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作為情感的載體和象征符號為游客提供了一個全景式的生活化旅游空間。游客進入這一空間,整體性、深入性地自我體驗、自我感受、自我探尋村民生活及其內容,體悟村民在現代化與鄉土文化雙重影響之下的特有行為方式與心態。在與村民的生活空間對話的同時,游客自身也形成對于空間的想象和認知,從而在回憶與認同中促進文化意義的傳承與再創造。這不僅提高了游客的旅游滿意度,也促進了村民生活空間的適應性生產。
當前,鄉村旅游的生活空間營造普遍存在表面化、片段性的問題,鄉村旅游成為沒有人文精神的符號化、形式化的商品,活生生的人從生活空間中消失,存在的只是角色。而通過“在地者”與游客的直接互動,村莊空間得以形成一種兼具機制化建構與意義化表達的生產模式。鄉村旅游的發展就是找回了村民的主體地位,村民和游客雙方在村莊生活空間中建構起互動的關系網絡,而非通過資本建立游客與鄉村的表象化、片段化聯系。首先,讓家庭生活嵌入鄉村旅游,就是要讓村民與游客直接互動,讓村民的真實家庭生活成為游客體驗的對象。如一些村莊的研學基地建設,可以讓村民作為接待戶參與,村委會制定標準,村民以“競標”的方式獲得接待資格。在獲得資格后,村民的家庭生活被有機融入到鄉村旅游中,形成集生產與生活為一體的現代化家庭產業綜合體。其次,堅持讓村民以自我的形象而非表演式的形象出現在鄉村旅游空間中。通過全方位地展現村民社會生活原始形象,擺脫表演式的關系建構。在此情境中,村民與游客在進行溝通和共同行動的過程中不經意地建立了超出于買賣雙方的關系,也正是這種語言的建構與解讀、行動的連續性形成讓空間從抽象上升到實體,變成了活態的生命承載體。最后,資本要轉變自己的空間生產角色定位,以激發村民的主體性為導向,通過“智庫式”及“保姆式”服務有機融入到村莊空間生產中。這樣,村莊空間中的各參與主體不僅讓身體存在于此空間中,而且進入到現場的關系之中,在構建關系的過程中進行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三)自然教育融入旅游,塑造可持續的生態空間
當前,各地的鄉村旅游發展中,生態系統通常被當作生態資本或生態產品。人們僅僅著眼于它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從而在“人—地”關系上走向對立。在此境況下,生態正義的提出具有全局性的意義。不同于環境正義,生態正義從自然倫理的角度對“人—自然—社會”的關系進行了價值上的規定。從可持續的生態空間塑造來看,生態正義最終指向的就是人與自然和合共生。在鄉村振興戰略下,樹立人與自然和合共生的理念,重構以人為核心,回歸本真性的生態空間是走向鄉村現代化、獲得人的自我解放的必然選擇。
重塑“村民在場”的鄉村旅游空間,首先要防止利益相關者對生態空間進行權力切割,而應該建立起共識性的道德自覺,站在生態系統的立場上思考共生路徑,以生態系統自身的發展為人們創造外部正效應;其次是通過村民與游客在生態空間構建中的直接互動,激發出村民對于生態環境的重視,讓村民用自己的方式、語言將生態保護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從而自覺地促使生態空間由符號化生產轉向精神性生產,從被動地接受制度層面上的生態保護政策條例的約束走向主動地在生產生活中解讀生態文明的內涵;最后要通過展示原生態的自然風光,“美化”游客的游玩體驗,從而激發出游客對于生態環境的情感。[13]在這一過程中培養出游客的共生思維,達到自然教育的目的。這樣,各主體在與自然互動中實現了意義的相互建構與表達,實現了村莊生態空間的再生產及其可持續發展。
鄉村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歸根結底要落到作為空間生產主體的村民的現代化。生活方式作為一個群體性的文化現象,是過去、現在、未來這一時間性和“整體—區域”這一空間性的融匯。當前,我國鄉村旅游尚屬探索階段,無論是制度設計還是實際運行都在逐漸成熟的過程中,通過村民的生產活動、日常生活與旅游發展“互嵌”,最終要實現的是鄉村旅游真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與旅游發展在空間自我生產與主體自覺活動中實現“互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鄉村旅游才能夠喚醒村民的集體記憶與認同感,找回自我以及生活的價值,從而實現鄉村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2022-4-20).
[2]岳曉文旭,王曉飛,韓旭東,等.賦權實踐如何促進鄉村新內源發展——基于賦權理論的多案例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22,(5):36-54.
[3]龐清云,保繼剛.涓滴策略對鄉村社區旅游收益分配的影響[J].旅游學刊,2022,(8):13-25.
[4]豐曉旭.共同富裕目標下的鄉村旅游資源開發邏輯及關鍵問題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2023,(2):305-317.
[5]傅才武,李俊辰.旅游場域中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生產邏輯與價值回歸[J].江漢論壇,2022,(10):131-137.
[6]彭華,何瑞翔,翁時秀.鄉村地區旅游城鎮化的多主體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寧水際村為例[J].地理研究,2018,(12):2383-2398.
[7]孫九霞,張凌媛,羅意林.共同富裕目標下中國鄉村旅游資源開發:現狀、問題與發展路徑[J].自然資源學報,2023,(2):318-334.
[8]林繼富.“空間賦能”: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J].西北民族研究,2021,(4):97-109.
[9]姚尚建.鄉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間”的權利視角[J].理論與改革,2023,(2):48-60.
[10]趙曉峰.從合約治理到行政統合——資本下鄉過程中治理策略轉換的案例研究[J].社會學評論,2022,(4):222-239.
[11][法]亨利·列斐伏爾.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包亞明,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12]謝梅,趙森,臧雨琪.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熱點與趨勢——基于知網資源的知識圖譜分析[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22,(4):75-83.
[13]張愛紅.短視頻嵌入文旅融合的產業傳播路徑探究——基于格蘭諾維特嵌入性理論的分析[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6):60-70.
(責任編輯 蔡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