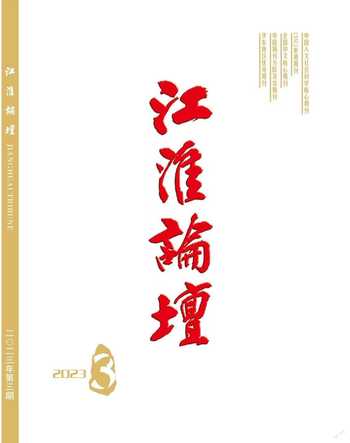儒家文論與曹植頌文的創新
丁靜
摘要:漢魏之際,曹植融匯儒家經典,吸收儒家文論,并將其運用在頌文創作中,在本質論、功能論、形式論等維度使該文體呈現出系列新變:其一,他在儒家文論“詩言志”“詩緣情”等基礎上,突破了頌只能歌頌的文體規范束縛,明確了頌“吟情述志”的本質,在頌文創作中注重作家主體情感的抒發。其二,依據儒家詩教“美刺”論,強調辭賦等文學介入社會的價值,拓展了頌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潤色鴻業”“宣上德”的頌還具備了“諷諫譏評”的價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論“主文譎諫”的思想下,打破頌體樸實厚重的語言風格與單調的形式節奏,追求頌的形式美,講究頌的語言技巧,提倡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使頌呈現出辭采華麗、文情并茂、音律諧和的藝術特色。曹植對頌文的創新,不僅體現出鮮明的儒家文論思想和美學趨向,彰顯了儒家文論的價值與意蘊,而且促進了晉代頌文的發展繁盛,在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曹植;頌文;儒家文論;主體情感;創新
中圖分類號:I207.2?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3)03-0168-008
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也是頌體文學的衍變期。以曹植為代表的頌體作家,在創作中力求新變,有意識地追求美、改造文體,對頌體進行了大膽的變革與創新,使頌脫離了原本“義必純美”、莊重典雅的頌美之風與創作體式,呈現出內容題材豐富、情感濃郁、文采飛揚,且具備諷諫統治者、譏評時事等功用的特點,故劉勰在《文心雕龍·頌贊》篇稱魏晉的頌為“雜頌”[1]96。長久以來,學者們大都將曹植文學創新的動因歸結于魏晉文學的自覺,認為曹植是在審美意識的覺醒下進行美的追求。然而,通過對曹植頌文的文本細讀,結合他的文學思想和相關史料,筆者認為除了時代環境的影響外,儒家文論對曹植的頌文創新及理論建構影響較大。
近年來,學者們已開始關注曹植文學與儒家思想的關聯問題,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代表性論著有李煥有的《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辭賦中的彰顯》[2]、陳麗妍的《從對儒家詩教之依違看〈洛神賦〉主題》[3]以及張家國、何新文的《曹植的經典意識與辭賦創作》[4]等,分別從儒家詩教、儒家文化和儒家經典等方面,對曹植辭賦進行深入研究。但是,學界對最能體現曹植儒家文論思想的頌文卻少有關注。曹植幼讀儒書,深受儒家經典浸潤,踐行儒志,一生追求經邦濟世、建功立業的政治理想。[4]他謹守儒家思想,亦深受儒家文論的影響,并將其運用于文學創作。從創作主體角度來看,他明確了頌“吟情述志”的本質,在頌文里抒發了多種情感志趣;在內容功用上,他創作了具有諷諫政治作用的頌,拓寬了頌的政治功能和價值范圍;在語言藝術上,他追求頌的語言形式美,提倡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使頌具有了辭采華麗、文情并茂、音律和諧的風格特點。
一、吟情述志:頌文創作主體情感的注重
頌起源于原始宗教儀式,最初只是施于宗廟郊祀或舉行重大典禮時的贊美詩。降及西漢,頌才成了一種專門用于頌揚的實用文體。《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5]271不管是頌王德以告神明,還是后來發展為頌一般的人和事物,頌只限于贊美歌頌。例如,漢代董仲舒《山川頌》歌頌山水之德,揚雄《趙充國頌》歌頌功臣良將,王褒《甘泉宮頌》和《碧雞頌》分別歌頌了宮殿和祥瑞之物等。在這種文體規范的制約下,作者不可任意抒發個人情感。
“詩言志”是儒家文論對詩歌本質提出的最早命題。漢代班固繼承并發揮了“詩言志”的傳統詩論,認為詩是“哀樂之心感”的產物,即情的產物。[6]1701《詩大序》以情志論詩,提出了情志統一的詩歌本質論。曹植吸取儒家文論“詩言志”“詩緣情”等思想,也認為文學乃吟詠性情的產物。如其《愍志賦序》曰“予心感焉,乃作賦”[7]32;其《離友序》言“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7]54;其《神龜賦序》又曰“余感而賦之”[7]96,均強調創作動機源于個體情感的生發。不僅如此,他還在《學宮頌序》提出“歌以詠言,文以騁志”的觀點,突破頌的文體慣例,視頌與其他文學體裁一樣,都是作者用于抒發情懷、表達志向的載體。他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并創作出蘊含作者多種創作意圖和復雜情感的頌作。
(一)尊儒興學的熱情謳歌
曹植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8]557。在儒家正統思想的濡染下,他將儒家經典融匯于頌文之中,并依經立義,傳承了儒家思想文化。例如,曹植在《學宮頌》序文中將孟子、子貢對孔子的評價與贊美融入頌文里,不僅增強了孔子的人格魅力,而且還有著深厚的文化意蘊。他熱情洋溢地歌頌了孔子,其序文曰:
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7]115
序文敘述了漢末長期戰亂,社會動蕩不安,造成了“五帝典絕”“三王禮廢”的情境,學術文化遭到空前破壞與沖擊。在古代所有圣賢之中,作者首推孔子,認為“齊賢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并引孟子所言“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來評價孔子的超卓杰出。在曹植看來,孔子講授的儒學,尤其是人性與天道,是超越其他學說的高深理論,僅僅依靠耳聞是不能夠學到其精髓的。正如南朝梁皇侃在《論語義疏》中所說:“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9]可見,頌文抒發了作者對孔子及儒學“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敬仰之情。
黃初二年,曹丕下詔修復孔廟,奉孔子之祀,曹植便作《孔子廟頌》,由衷地贊賞曹丕尊儒興學之舉。作者在序文鋪敘了孔廟遭毀、祭祀墮壞的情景:
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后,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曹植集校注》卷二)[7]228
天下戰亂,儒學衰微,孔廟傾廢,儒學遭遇衰敗廢棄的境況,作者慷慨陳詞,直抒胸臆,發出“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的呼聲,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的悲慟、痛惜之情。當朝廷“紹繼微絕”“興修廢宮”、尊儒興學以教化天下時,他道出了作頌的緣由:
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于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圣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圣,隆化如此,能無頌乎?(《曹植集校注》卷二)[7]228
路寢,名始見于《詩·魯頌·閟宮》之“路寢孔碩”,《毛傳》曰:“路寢,正寢也。”[5]614《禮記·玉藻》說祭祀曰:“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以清聽政。”(卷二十九)[10]可見,路寢是帝王正殿所在,意指古代天子﹑諸侯的正廳。泮宮,乃西周諸侯所設大學。《漢書·郊祀志上》記載:“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卷二十五上)[6]1193泮宮后泛指學宮。這里引用殷商路寢、西周泮宮以及商王武丁、魯僖公之典故,意在以殷商帝王有路寢以清聽政之義、西周諸侯有開設學堂之舉、商高宗武丁和魯僖公有修德立頌之功,來襯托贊美魏帝在“創業垂統”之始便“褒崇大圣”,尊孔尚儒,使社會風氣隆化淳厚。頌文引入大量的儒家經典,彰顯了作者對孔子及其儒學的無比仰慕與推崇。
(二)人生境遇的哀怨與欣喜
曹植一生遭遇很多波折,尤其在魏文帝黃初年間,其處境窘迫,運命艱危。曹丕親情涼薄,利用各種手段迫害曹植,甚至欲除之以泄其憤。曹植曾多次被改徙臨淄、鄄城、雍丘、浚儀、東阿等封地。這些封地大都貧瘠,因此曹植所處的境遇非常困窘。他在《轉封東阿王謝表》中提到在雍丘時的情況:“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財糊口,形有裸露。”[7]390后來改封比較肥沃的東阿,曹植對此封地比較滿意。為此,他專門創作了《社頌》,其序文言:
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繕宮室,務園圃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饑寒備嘗,圣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曹植集校注》卷三)[7]427
從序中“塊然守空,饑寒備嘗”可知,曹植昔日所在封國的貧瘠與清苦,而今被封“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的東阿,作者是怎樣的一種既哀怨又欣喜的情緒。于是作者由衷贊頌道: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具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修敘。(《曹植集校注》卷三)[7]427
在貧瘠之封地,飽受生活艱窘之苦,經歷了太多辛酸與困苦之后,能夠保全生命,得到朝廷的恩賜,作者感慨之余,更多是祈禱神靈福佑,希冀所在封國農桑繁興,豐年有余。
(三)政治失意的悲愴與落寞
儒學要求士人志存天下,積極入世。孔子為了“用世”,曾大聲疾呼:“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11]144孟子提倡“濟天下”,其名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11]351,更成為中國歷代士大夫的座右銘和行為準則。曹植也有著宏大的政治志向和積極的從政心理,期望自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三國志·魏書》)[8]565。但是,他空有一腔政治熱情,卻沒有突出的政治表現和軍事功績。曹丕當政期間,曹植于黃初初年兩次獲罪,處境險惡,一度有性命之虞,更無從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負。太和時期,曹叡放松了對他的猜忌和限制,曹植重燃起建功立業、揚名后世的希望,但始終不被朝廷重用。據《魏書》載:“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8]576雖滿懷希望,卻不能把握機遇、施展才華;雖屢遭坎坷,卻依舊堅持理想、不愿放棄。曹植的人生始終充溢著苦悶和哀愁,因此,他在頌文中更多是抒發這種悲愴與落寞之情。
《酈生頌》正文已佚,只留存序文。其序言:“余道經酈生之墓,聊駐馬,書此文于其碑側。”[7]257酈食其為秦漢之際著名謀士,游說齊國歸順,為劉邦“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作者途經酈食其之墓,特意下馬,寫下此頌文,顯然是有感于酈食其的不朽功業。與酈食其相比,曹植終究是“無錐刀之用”。《魏書》記載黃初二年,曹植再次轉回雍丘,“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掛風人‘彼其之譏。”曹植熱切盼望著“逞千里之任”“驗搏噬之用”,而終究是“無伯樂、韓國之舉”,徒有“竊自痛者”的傷悲[8]566。
二、刺過譏失:頌文社會政治功用的強化
儒家文論的一個顯著特色是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功用。從孔子提出以詩“事父”“事君”到《詩大序》論詩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5]271,都認為詩歌具有強大的社會政治功用。文學創作“發乎情,止乎禮義”,既承認作者抒發宣泄內在情感的需求,同時又強調要用儒家道德禮義為內容規范,目的在于發揮其政治教化作用。
漢代作家囿于“漢頌”思想和“潤色鴻業”的社會定位,頌文創作基本上沿襲《詩經》“三頌”歌功頌德的題旨內容,如西漢揚雄的《趙充國頌》、劉向的《高祖頌》《列女傳頌》等,都是通過歌頌贊美人物的功德,樹立封建倫理道德標準,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教化作用。東漢光武中興、明帝修禮后,班固、傅毅、崔骃等人的征巡頌更是為了“宣上德”而“盡忠孝”,如《后漢書》載漢章帝“每行巡狩”,班固“輒獻上賦頌”[12]1373;傅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12]2613;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以稱漢德,辭甚典美”[12]1718-1719等,這些頌文均以“頌漢”為旨歸,歌頌贊美帝王功德,有著彰顯漢德、賦頌當世的社會政治意義。漢魏之際,曹植出于積極投身政治、建功立業的理想情懷,并將其投諸頌文創作,有意識地改造頌體,使內容題旨“純美”的頌文還具備了諷諫、譏評等政治作用,使頌文的社會政治功能得以強化。
(一)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
摯虞《文章流別論》指出“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他認為“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13]1905。頌一開始就與帝王功德相關,依附于國家政治而產生。曹植在《學宮頌序》曰“予今不述,后賢曷識”,強調作頌是為了記敘傳述先賢事跡,以便后學者能夠明白辨識。他在《與楊德祖書》中,還表明自己志向不成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而一家之言”[7]154,有著深厚的儒家注重史實、經世致用的思想。曹植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價值,其觀點主要見于他與楊修之間往來的書信及一些作品的序文中。
在《與楊德祖書》中,曹植對文學創作評價如下:
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7]154
曹植在信中論文言志,言辭慷慨,用意曲折。他本人的詩文做得很好,這里卻稱之為“小道”,亦自謙之辭,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學。對于好友的虛懷請益、懇切謙和,楊修在回函《答臨淄侯箋》中說:“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子,風雅無別耳。”“若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文選·卷四十》)[14]楊修追本溯源,認為賦頌乃“古詩之流”,其創作與追求功名并不沖突,對曹植及文學創作給予了肯定。
對于曹植“辭賦小道”的這番話,看似在貶低文學價值,其實是將文學創作活動同他畢生以求的政治理想相比較,文學便顯得不足為道,因而他反問道:“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曾指出,曹植說文章小道大概是違心之論。何新文先生在《中國賦論史稿》中引用魯迅的觀點,并指出曹植“少好詞賦”,一直寫作不輟,和揚雄悔其少作、輟不復為的創作情況是不相同的。[15]聯系上下文來看,曹植稱辭賦文學為“小道”,不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以及引揚雄“壯夫不為”的事例,說明其在文學的價值評判標準上是比較認同揚雄的觀點的。
揚雄非常重視辭賦的政治諷諫意義,他在《甘泉》《長楊》等四賦的序文中,反復強調了創作辭賦應以諷諫為目的。他還在《法言·吾子》中強調賦的“諷諫”作用,一旦賦未起到應有的諷諫作用,就加以否定,得出“童子雕蟲篆刻”乃至“壯夫不為”的結論。[16]但是,揚雄的賦作也有例外。因漢成帝好酒,揚雄曾作《酒賦》以諷之。曹植《酒賦序》對其評價曰:“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7]125揚雄的《酒賦》今殘,作者以游戲的筆調敘寫。因缺少諷諫作用,即便“辭甚瑰瑋”,曹植仍稱其“不雅”。顯然,曹植強調文學創作應追求雅正,他認為徒有華藻會陷入膚淺,甚至陷入虛詞濫說。
綜上所述,曹植稱辭賦為“小道”,并非是貶低文學,除了自謙之外,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與政治功業相比,他更重視在政治上施展抱負,不愿僅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二是與揚雄的儒家文藝觀相似,曹植是以作品是否具備相應的政治功用、是否起到一定的社會效益為標準,來評判文學的價值。而這種文學的功利價值觀也與曹植積極入世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追求相合。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他實際的頌文創作中得到印證。
(二)拓寬頌文的政治功用
孔子以“興觀群怨”來論文學的社會作用,其中“怨”是指“怨刺上政”,開啟了干預社會現實、批評政治過失的儒家文論傳統。《詩大序》指出詩歌的社會政治功用體現在“上以風化下”和“下以風刺上”[5]271兩方面。鄭玄在《詩譜序》中則明確了“美刺”的含義:“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5]262漢人論賦深受儒家政教文論思想的影響,認為文學要具有“美刺”功能,表現出一定的諷喻或揄揚內容,實即諷、頌兩端,如王充《須頌》篇云:“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17]此論與班固“潤色鴻業”的思想一致[18],體現了“美”和“頌”之端;揚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漢書·揚雄傳》)[6]3557,他提倡辭賦創作應以諷諫教化為目的,則是“刺”和“諷”之端。
單從頌的政治功用來講,其歌功頌德僅體現了“美刺”論之“美”的一面。但是,由于漢代賦頌兩體自身的發展衍化,存在交叉、互滲的關系[19],其內容、功用及理論建構等也存在很多趨同性,因此漢代也出現了含“諷”意味的頌文,如東方朔的《旱頌》、馬融的《廣成頌》等,但為數并不多,內容上也多為戲說、規勸等,并非典型的諷諫之作。直到三國時期,曹植在頌文創作中,不僅繼承了頌“潤色鴻業”“宣上德”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還使頌具備了“諷諫”的作用。
曹植的《皇太子生頌》乃諷諫之作,明為歌頌皇太子的誕生,其實是奉勸明帝曹叡要安撫百姓、以天下為重。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輯錄此篇題名為《皇子生頌》,且所錄頌文與嚴可均輯本在個別字詞上稍有出入。其文曰:
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祗肅郊廟,明德敬惠。潛和積吉,鐘天之厘。嘉月令辰,篤生圣嗣。天地降祥,儲君應祉(嚴本作“社”)。慶由一人,萬國作喜。
喁喁萬國,岌岌群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職(嚴本作“妾”),終天之經。仁圣奕代(嚴本作“世”),永載(嚴本作“戴”)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祗承予聽。(《曹植集校注》卷三)[7]454
皇太子誕生在“嘉月令辰”,舉國慶賀呈現出一片喜氣祥和的氛圍。頌的后半部分由歌頌轉而進行勸諫:“慶由一人,萬國作喜”有著明顯的諷刺意味,與“喁喁萬國,岌岌群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中點評曰:“太和時代,曹叡對吳蜀接連用兵,又大修宮殿,賦役繁重,勞民傷財,百姓極為困苦。”[7]454作者指出百姓的生存危機,提出“稟命我后,綏之則榮”,實則借歌頌皇子誕生之機,諷諫曹叡要以天下蒼生為重。此頌并不是一味歌頌贊美,還摻雜作者對統治階層的諷諫以及對下層人民疾苦的同情,因此,劉勰稱之為“雜頌”,并認為“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1]96。
《宜男花頌》是曹植的另一篇諷諫之佳作,其文頌曰: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曜晃,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濟太姒,永世克昌。(《曹植集校注》卷三)[7]395
宜男花,萱草別稱,舊時祝頌婦人多子之辭。《齊民要術·鹿蔥》引晉周處《風土記》曰:“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蓮。懷姙人帶佩,必生男。”[20]可見,宜男花本來就有多生子的寓意。頌文敷寫了宜男花之美,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引發聯想,借太姒多子、螽斯繁殖力強來祝福曹叡多子多福、永世克昌。據《魏志·高柔傳》卷二十四載:“(明帝)后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后宮。后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8]686因而此頌也有諷諫統治者的意蘊。
《柳頌》的正文已佚,其序文曰:
余以閑暇,駕言出游,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枝葉。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譏當世之士。(《曹植集校注》卷一)[7]197
作者在序中稱“表之遺翰”,譏評“當世之士”,點明了此頌的寫作意圖。邢培順推測此頌應該是“通過述說柳樹的狀貌品質,觀物比德,以批評俗士的隨風而動、操守不固之類”[21]290。晉代蘇彥在《女貞頌序》曰:“昔東阿王作楊柳頌,辭義慷慨,旨在其中。余今為女貞頌,雖事異于往作,蓋亦以厲冶容之風也。”(《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八)[13]2255蘇彥認為曹植的《柳頌》“辭義慷慨,旨在其中”,因而效法創作《女貞頌》,目的也是“以厲冶容之風”。據此可知,《柳頌》應該為借物敘志、勸勉譏評世人“浮夸不正”之風的作品。
三、主文譎諫:頌文語言形式美的追求
《論語·雍也篇》云:“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11]89孔子論文,內容與形式并重。在具體創作中,孔子強調用精巧的藝術形式來表達內容。《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孔子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5]1985文采能使言辭得以充分表達,且對內容有著重要的意義。《詩大序》從統治者接受“刺上”的心理角度,認為“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5]271,對詩歌形式提出了“主文譎諫”的要求,即通過詩歌的形式,用譬喻的手法進行諷諫。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影響了后世文學創作注重文采、講究形式、追求含蓄委婉的特點。
漢代的頌文基本上是沿襲《詩經》“三頌”的創作體式,以四言句式為主,風格莊重典雅。雖然漢末蔡邕對頌文的寫作體例進行了一些創新,比如注重頌的序文寫作,融入一些敘事技巧,但其頌的正文依舊很簡潔,語言古樸厚重,形式節奏單調。直到漢魏之際,曹植不僅受到“藝術自覺”社會風尚的影響,創作開始注意藝術形式技巧及作家才情品性等問題,而且在頌文創作中,他始終與儒家“主文譎諫”的文論要求相一致,打破頌體樸實厚重的語言風格與單調的形式節奏。他在提倡頌文應具有社會教化、政治諷諫內容功用的同時,有意識地追求頌文語言的形式美,以精巧允當的句法、文義相扶的情采以及自然諧暢的聲律,使頌文的內容與形式、感情與文辭達到了和諧統一。
(一)精巧允當的句法技巧
對偶修辭手法古已有之,在《易經》《尚書》等文獻中屢見不鮮。漢代作家作頌時也常使用對偶手法。如王褒在《圣主得賢臣頌》中用“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與“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漢書》卷六十四)[6]2823作對舉,隔句相對,用詞講究,體現了作者嚴密的邏輯推理性。蔡邕在《祖德頌》序文中言“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絕非自己的功勞,而是因“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全后漢文》卷七十四)[13]874。其文句對仗工整,意象鮮明,流露出古樸莊重的韻味。
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文學自身的發展,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越發精密和深刻,對偶修辭手法也就日趨增多。到了魏晉時期,曹植的頌文較多地運用對偶手法,并利用對偶句來增強表達效果,呈現出明顯的駢偶化特征。如《孔子廟頌》序文曰:
皇上懷仁圣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于無方,淵恩淪于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煙煴。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發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曹植集校注》卷二)[7]228
這些對偶句形式不同,自然成對。在詞語意象上,更為精密成熟,如“殊俗解編發而慕義”與“遐夷越險阻而來賓”,“嘉瑞踵武”與“休徵屢臻”,生動恰切,形象鮮明。作者將形式與內容完美結合,渾融一體,純熟精湛的句法技巧一目了然。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篇謂:“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厘。”[1]384他認為魏晉作家造句講究精密,聯字配合情趣,對仗辨析毫厘,他還將“精巧”“允當”作為衡量對偶修辭手法及技巧高低的標準[1]385。曹植頌文的對偶句法正具備了精巧允當的特征。學者李蹊從駢文的特征和產生時代考察,提出“晚漢和魏代文章是正式駢文的過渡形式”,認為曹植在作品中較多使用偶句,通脫華美,自然流暢,是典型的駢偶化古文句式。[22]
(二)文義相扶的情采特征
曹植認為,文學作品不僅要充分表達內容、融入個人才情,還要辭采華美。如他在《七啟序》中評價枚乘等人的“七體”作品“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7]6;在《王仲宣誄》中贊揚王粲“文若春華,思若涌泉”[7]164等,足見其對文章辭采的重視。在創作中,曹植的頌文有著“文義相扶”的情采特征。
首先,曹植的頌文有著“辭采華茂”的特點。如在《宜男花頌》里,他細致描摹了宜男花的楨干和花葉,用“綠葉丹花”“光采晃曜”將宜男花鮮艷奪目、明艷光彩的形象展現出來;他在《皇太子生頌》中夸贊皇后曰“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祗肅郊廟,明德敬惠。潛和積吉,鍾天之厘”,刻畫出一位尊禮仁德、恭謹慈祥的皇后形象;在《學宮頌》中,他以“玄鏡作鑒,神明昭晰”來稱贊孔子之功績,稱其光輝“仁塞宇宙,志陵云霓”,等等。邢培順在《曹植文學研究》中也指出,曹植在頌、贊、誄等文章中,將“原來的說明性和評價性的語言改造為敘述性和描寫性語言,增強文章的形象性和生動性,使傳統的禮儀性的文體變為具有較強文學審美特征的作品”[21]382。可見作者遣詞之講究,辭采之精美,意境之深遠。
其次,曹植的頌文講究情文并茂。例如,曹植在《答明帝詔表》中稱贊曹叡所作的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哀動神明,痛貫天地”[7]498;在《與陳琳書》中,他反對徒逞辭藻而不顧內容情感,如他譏評陳琳模仿司馬相如辭賦文采而“志絕于心”[7]176。在曹植看來,好的作品應該兼顧辭采和感情。因此,曹植的頌文追求語言技巧和思想情感的和諧統一。如在《孔子廟頌》序文中,作者引用典故,運用排比,對大魏朝廷統一天下、教化四方的歷史功績予以熱情謳歌,在華美文辭里洋溢著濃郁的感情色彩。當敘述孔廟遭遇亂世時,則是“寢廟斯傾,闕里蕭條”,朝野上下乃“靡歆靡馨”的頹廢之局面;在經過朝廷“修復舊堂,豐其甍宇”后,則又是“莘莘學徒,爰居爰處”,四海升平、煥然一新的情景。
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提出文章應以“述志為本”,《詩經》以來“為情造文”的優良傳統是為了“吟詠性情,以諷其上”的緣故,因此作者要體現出真實的感情和精煉的文辭[1]347。曹植的頌文抒懷言志,吟詠性情,塑造出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其用詞精美雅致,又融入作者真切的情感。作者信筆寫來,自然暢達,在情采方面達到了文義相扶的藝術效果。
(三)自然諧暢的聲律節奏
曹植的頌文頗為講究聲韻。他精通音律,頌文節奏明快,音調諧美,讀來別有一種順暢流美的愉悅感。如《社頌》曰: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具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修敘。(《曹植集校注》卷三)[7]427
頌文隔句押韻,前六句押“土、古、主”韻,后八句押“舉、與、宇、敘”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頌文并非一韻到底,而是根據實際需要和情感變化隨時變韻,節奏非常明快,音韻流暢。
再如《孔子廟頌》的正文,前十六句隔句押韻,分別押“將、商、光、綱”韻和“靈、榮、傾、馨”韻,接下來又隔三句押韻,分別押“武、宇、沮”韻,最后十句又隔句押韻,押“譯、期、茲、之、基”韻。還有《玄俗頌》共八句,也是隔句押韻。這些聲韻構成了語言文字的音樂美,使頌文語言流暢,節奏明快,韻調諧和。曹植對自然音律進行了靈活運用,其頌文的韻律“得乎自然,有若天成”[21]181。
四、曹植頌文創新的文學史意義
縱觀頌的發展歷程,從最初依附于宗教的祭祀儀式,到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再到歌頌贊美普通人事物品,它經歷了由神圣性話語向政治性話語,再向標志著身份、尊嚴與智慧的修辭性話語的演變過程,其實用功能也越來越趨向于文學藝術和審美趣味的追求。誠如劉師培所言“東漢以來,贊頌銘誄之文,漸事虛辭,頗背立誠之旨”,而“文章各體,由質趨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23]。漢末魏晉,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24],也正是頌文由質樸趨向華麗衍變的重要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曹植深受儒家文論的浸潤,將儒家文論思想植于頌文創作實踐中,并有意識地改造頌體,對頌文的創新以及后世頌文的影響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第一,從儒家“情志”論出發,曹植明確了頌“吟情述志”的本質,注重頌文創作主體的情感表達,在頌文里抒發了多種情感志趣,從而影響了晉代頌文的創作理論。例如,陸機在《文賦》里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著名論點,還指出了頌“優游以彬蔚”的創作特征。[25]陸云在《與兄平原書》中提出“深情至言”的文學思想,以一個“情”字作為衡量文章優劣的標準,視有深情至言的詩、賦、頌等為文學正宗。[26]陸機的“詩緣情”與陸云的“深情至言”觀念,不僅加速了儒家“情志”論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對頌文創作的抒情意識起到了理論上的推動作用。
第二,在儒家“美刺”論的基礎上,曹植拓寬了頌的政治功能和價值范圍,使“義必純美”的頌還具備“美刺諷喻”的功能,進一步強化了頌的社會政治功用。他創作的頌不單可以歌功頌德、潤飾鴻業,還可以刺過譏失、諷諫政治,有著匡扶社稷、勸勉譏評世人的社會價值。晉代頌文受此影響,其社會功能價值明顯擴大,還出現了并非一味地歌頌贊美人物的作品。如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體式宏大,辭采紛呈,作者分別列舉了輔佐漢高祖安邦定國、建功立業的三十一位功臣,其中褒功貶過,客觀公正,展現了作者精確允當的論析判斷能力。在作者“頌”功德之余,還摻雜了對人物過錯的批判,凸顯了頌體“論”與“評”的價值功能。因而,劉勰在《文心雕龍·頌贊》中稱其曰:“褒貶雜居,頌之訛體。”[1]96
第三,在儒家“主文譎諫”形式論的影響下,曹植追求頌的語言形式美,使原本語言古樸厚重、形式節奏單調的頌具有了辭采華麗、文情并茂的風格特點。他的頌文不僅講究句法、辭藻、音律等藝術形式,而且還能夠有機融合情感內容,達到文義相扶、音情頓挫的藝術境界。受其影響,曹植以后,晉代頌文在體式、章法、辭藻、音律等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越來越講究辭采、韻律,呈現出自覺的審美追求。如陸云創作頌文特別注重語言的形式美,非常講究韻律,其《盛德頌》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華麗繁縟。
綰而言之,曹植對頌文的開拓與創新彰顯了儒家文論的價值與意蘊。正是在儒家文論的影響下,曹植打破了頌的書寫體例藩籬,延伸了頌的文體內涵,拓展了頌的創作空間,使頌文呈現出情感濃郁、功能多樣化、情采并茂等特征。曹植創作的頌較之前代,更加注重主體情感抒發和藝術形式追求,實現了頌文“由質趨華”的文體發展與轉變。經過曹植的開拓創新,頌在內容題材上不斷豐富擴展,在藝術手法上也臻于成熟完善,從而迎來了晉代頌文百花齊放、爭相斗艷的繁盛景象。
參考文獻:
[1][梁]劉勰.文心雕龍注釋[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李煥有.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辭賦中的彰顯[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122-124.
[3]陳麗妍.從對儒家詩教之依違看《洛神賦》主題[J].長春師范大學學報,2018,(9):96-98.
[4]張家國,何新文.曹植的經典意識與辭賦創作[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157-165.
[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
[6][西漢]班固.漢書[M].[唐]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7][三國魏]曹植.曹植集校注[M].趙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8][晉]陳壽.三國志[M].[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9][梁]皇侃.論語義疏(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151.
[10][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43.
[11][宋]朱熹.四書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南朝宋]范曄.后漢書[M].[唐]李賢,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13][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G].北京:中華書局,1958.
[14][梁]蕭統.文選(下)[G].[唐]李善,注.長沙:岳麓書社,2002:1247.
[15]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M].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58.
[16][西漢]揚雄.揚子法言譯注[M].李守奎,洪玉琴,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6.
[17][東漢]王充.論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07.
[18]何新文,王慧.班固的“賦頌”理論及其《兩都賦》“頌漢”的賦史意義[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2):136-142.
[19]彭安湘.漢代頌體風貌以及頌與賦的關系[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67.
[20][北朝]賈思勰.齊民要術譯注[M].繆啟愉,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13.
[21]邢培順.曹植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22]李蹊.駢文的發生學研究[M].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230.
[23]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
[24]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5][晉]陸機.陸機集[M].金濤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2.
[26][晉]陸云.陸云集[M].黃葵,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137.
(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