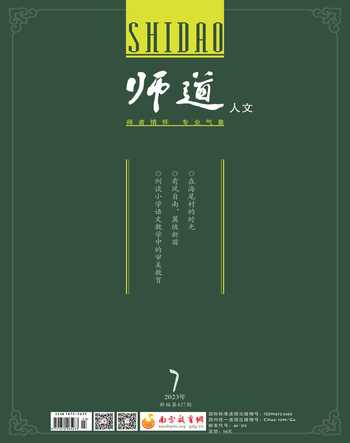向上閱讀,在永恒沖突中實現安寧
成旭梅
人人向往自由,將自我表達于世間;但這亦將帶來多聲部的混亂,使人走向“他者即地獄”的境況。個體終究單薄而孤獨,我們期待對世界有更深的理解,所以需要秩序將自我與他者連接,形成對話共同體,在此共同體中將異質多元的“自我”交織,以普遍秩序將思維共鳴于他人,從而構筑人類共同時間。
秩序的建構過程以“永恒沖突”為基本特征。面向永恒沖突時的不安,是人擺脫“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的原始沖動。現代性下的時代迷失里,時間里的經驗對解除當下之困具有非常的意義,因此,向上的閱讀是必要的。以面向人類共同經驗為基本方式的文化閱讀,建構思維秩序之集群狀態。
思維之文化秩序模型呈現為一動態過程:自我原初秩序(即自我秩序)與他者秩序在共時空里形成沖突,產生解困的心理需求。解困可能發生的路徑是兩個:一是向共時空下的另一向度求取解困之路;一是向歷時空(前人經驗)發起質疑與求證。歷時空(前人經驗)之所以高于共時空,乃在于對于人類共同經驗的仰望與認同。閱讀的獨特,在于以虛證實,領略智者超越于一般生物的浪漫主義特質。
文字將人類普遍秩序以美與善的樣態延迤于時間。普遍秩序融合了人的本性,使人以價值理性理解了時間與萬物。詩,正是普遍秩序渾化了人之個性的結果。詩以固著的格式,負載自由的靈魂——以一種理性-自由的方式將人對世間的探索與理解表達出來,帶給人類個體在秩序中最熱烈的生命樣態與精神價值。這種價值要比動物的狂吼來得更有力。顧城在《遺囑》中寫道:“當淚的潮涌漸漸退遠,理想的島嶼就會浮現。”當我們在文字里透過時間里的有序去面對生命、過去與現在,我們將會獲得對生命本質的體認,從而與我們的生命和解,與生命中種種的磨難與困境和解,我們終將通過人類普遍秩序,于永恒沖突中實現安寧。
但沒有個體性,秩序的存在只是生命的枷鎖。如托爾金所說:“英雄的超越是理想在現實中埋下的一點伏筆,即在人格境界上最終對物欲與平庸的超脫,一種高遠、澄明的人生風范便從黑暗混亂的擠壓中飄然而出。”秩序的力量可以支撐人類保持對探索生命的熱情與渴望,保持一直前進的力量與方向,保持始終堅守的自我與初心。另一方面,個體性不會因為秩序而受損,每個個體將會以最厚重的方式在共同生活樣態中保留下獨特的自我,從而形成既同又不同的時間,生生不息。余光中在獨白中寫道:“月光還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還是李白的霜。”這種在秩序中存在的無上美感與超越時間的人與人的對話,使個體性有了超越形式的宏大的價值,我們的精神因之永存于世間,人類綻放了人類的偉大。
向上閱讀,我們終將在永恒沖突中實現安寧。
責任編輯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