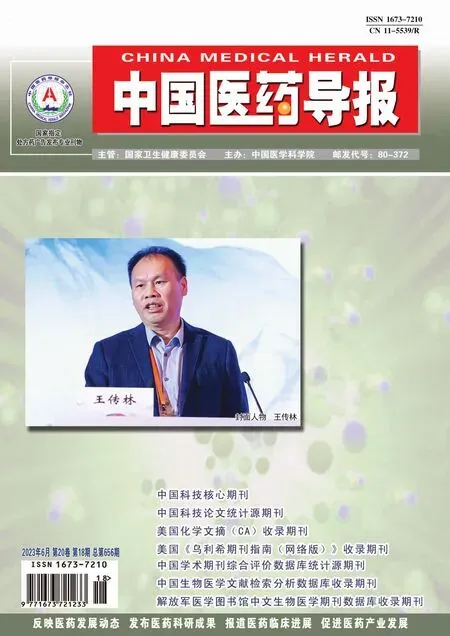基于品管圈的術后護理對下肢骨折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的預防作用
金念念
安徽省安慶市第一人民醫院脊柱外科,安徽安慶 246003
下肢深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 of lower extremity,DVT)屬下肢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是指血液在深靜脈內非正常凝固形成血栓,進而引起一系列血管血液回流障礙的臨床綜合征[1-2]。一旦發生血栓脫落,栓子可流入肺動脈而誘發肺血栓栓塞癥,對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嚴重威脅。下肢骨折患者通常需要接受手術治療,術后需要長時間臥床進行恢復,極易發生DVT[3]。目前對于術后DVT 的預防措施主要是健康知識宣教、術前評估、藥物控制、并發癥處理等,缺乏科學化、系統化的術后護理預防措施[4]。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活動是指在相同或相似工作場所的人員自動自愿組成的小團體,按照規定的活動步驟來解決工作問題[5]。本研究將基于QCC 的術后護理應用于預防下肢骨折患者術后DVT。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21 年1 月至2022 年3 月在安徽省安慶市第一人民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接受手術治療的90 例下肢骨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41 例,女49 例;年齡18~75 歲,平均(57.39±15.38)歲;骨折部位:脛骨骨折32 例、股骨骨折34 例、踝關節骨折8例、髕骨骨折7 例、其他類型骨折9 例。本研究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AQYY-YXLL-20-07)。
納入標準:①年齡18~75 周歲;②首次進行骨科手術治療,病歷資料齊全完整;③術后病情穩定、意識清晰。
排除標準:①術前合并凝血異常、血液系統疾病;②術前已伴有下肢靜脈曲張、靜脈血栓等疾病;③既往有下肢骨折史及下肢手術治療史;④合并嚴重心、肺、肝、腎功能障礙及惡性腫瘤。
按照隨機數表法將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45 例。觀察組中男22 例,女23 例;年齡18~74 歲,平均(57.16±12.53)歲;骨折類型:脛骨骨折14 例,股骨骨折19 例,踝關節骨折3 例,髕骨骨折4 例,其他類型骨折5 例。對照組中男20 例,女25 例;年齡18~75 歲,平均(55.42±14.21)歲;骨折部位:脛骨骨折18 例,股骨骨折15 例,踝關節骨折5 例,髕骨骨折3 例,其他類型骨折4 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護理方法
對照組給予常規圍手術期護理干預,具體包括健康知識宣教、術前告知、病情監測及術后飲食指導及功能鍛煉等。
觀察組采用基于QCC 的術后護理干預。具體如下:
(1)成立QCC 小組。QCC 小組成員包括主任醫師1名,住院醫師1 名,護師3 名,護士6 名,成員共計11 人。
(2)確定主題。全體小組成員根據平時的臨床工作開展頭腦風暴,將本次QCC 活動設定為無阻圈,目的為促進患者術后下肢靜脈血液循環,預防和減少術后DVT的發生。
(3)現狀調查。下肢骨折患者接受手術治療后需要較長時間的臥床休息,容易發生DVT,其原因與醫護人員、護理因素及患者自身因素有關,本次QCC 互動主要針對上述因素進行針對性的術后護理。
(4)分析原因。采用頭腦風暴法分析DVT 發生的原因,DVT 發生的高危因素包括專業知識培訓和健康宣教力度不夠,護理人員、患者及家屬對DVT 的認知和預防重視程度不夠;圍手術期的護理操作不熟練;術后的飲食計劃、功能鍛煉不規范、不合理。應對措施。①加強對護理人員的專業知識培訓,要求所有成員參與其中,經理論知識、護理操作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崗;②規范評估標準:根據Caprini 評估量表[6]評估DVT 發生的危險等級,根據評估結果給予相應的護理干預措施,詳細記錄患者臨床表現及術后恢復情況和相應的護理措施;③加強對患者及家屬的健康知識宣教,通過現場講解、演示圖冊、視頻等形式進行健康知識宣教,詳細告知DVT 的發病原因、危險因素、主要癥狀等,為患者講解術前、術后功能鍛煉的方法等;④圍手術期做好患者的保溫工作,術后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給予個性化飲食指導,排除禁忌后給予高蛋白、高維生素食物,叮囑患者多飲水以降低靜脈血液黏稠度;⑤進一步規范術后功能鍛煉,指導、協助患者規范完成術后功能鍛煉的所有項目。
1.3 觀察指標
①定期觀察患者的雙下肢血液循環情況,記錄術后DVT 發生情況,術后DVT 的診斷參照《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第三版)》[7],對所有患者進行Homan 征、Neuhof 征檢查,記錄陽性患者;②術后第1、7、14 天采用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股靜脈、腘靜脈的血液流速情況;③護理干預結束后采用自制調查問卷由患者及家屬對護理人員進行綜合素質評估,包括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積極性、團隊意識及責任心等,每項總分10 分,分值越高代表素質越高。測量問卷的總Cronbach’s α 系數為0.857,各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14、0.893、0.872、0.803、0.904。該調查問卷的各個條目的內容效度指數為0.82~1.00,平均效度為0.93。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統計學對所得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比較采用t 檢驗;多個時間點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進行。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術后下肢DVT 及Homan 征、Neuhof 征發生情況比較
觀察組術后下肢DVT 及Homan 征、Neuhof 征發生率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術后下肢DVT 及Homan 征、Neuhof 征發生情況比較[例(%)]
2.2 兩組術后不同時間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比較
整體分析發現:兩組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組間、時間點和交互作用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內比較:兩組術后1、7、14 d 的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兩組術后1 d 的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術后7、14 d的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術后不同時間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比較(cm/s,)

表2 兩組術后不同時間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比較(cm/s,)
注 與本組術后1 d 比較,aP<0.05;與本組術后7 d 比較,bP<0.05;與對照組同期比較,cP<0.05
2.3 兩組護理后患者對護理人員的綜合素質評估比較
護理后,觀察組護理人員的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積極性、團隊意識及責任心評分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護理后患者對護理人員的綜合素質評估比較(分,)

表3 兩組護理后患者對護理人員的綜合素質評估比較(分,)
3 討論
手術是治療下肢骨折的有效手段,能夠有效恢復患者的下肢生理結構,促進運動功能的恢復[8]。由于下肢骨折患者術后需要較長的臥床休息,加之手術創傷等多種因素,導致下肢血流緩慢[9-12],血液瘀滯而引發DVT,DVT 發生后極易引發肺血栓栓塞癥,后者的致死率可達70%以上[13-14]。對于DVT 的臨床治療及預防,目前仍存在一定爭議,準確評估DVT 風險,進一步完善圍手術期DVT 的預防護理干預策略十分必要[15-17]。
QCC 是一種持續質量改進的護理措施,目前已廣泛應用于臨床治療及護理工作中[18-20]。本研究在下肢骨折患者圍手術期的護理干預中引入QCC 的術后護理策略,按照QCC 的活動要求和步驟,首先成立了11人的QCC 小組,全體成員運用頭腦風暴,發動群策群力,確定了本研究中QCC 活動的目的是為促進下肢骨折患者術后下肢靜脈血液循環,預防和減少術后DVT 的發生,通過對當下下肢骨折患者的現狀進行調查,發現導致術后DVT 發生的原因與醫護人員、護理因素及患者自身因素有關,具體原因包括:專業知識培訓和健康宣教力度不夠,護理人員、患者及家屬對DVT 的認知和預防重視程度不夠;護理人員在圍手術期的護理操作不熟練;術后的飲食計劃、功能鍛煉不規范、不合理。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本研究制訂了相應的術后護理策略:首先以Caprini 評估量表為基礎建立了下肢骨折患者DVT 風險的分級評價體系,根據DVT 風險分級評估結果對患者進行分級管理和動態追蹤;其次,本研究還對健康知識宣教、個性化飲食指導、術后功能鍛煉等一系列圍手術期的護理流程進行進一步強化和細化,進而實現了DVT 預防護理的具體化、流程化、規范化與系統化[21-23]。本研究結果中,觀察組術后的DVT 及Homan 征、Neuhof 征發生率均明顯低于對照組,術后7、14 d 的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均明顯高于對照組。肌肉泵作用缺失、局部靜脈回流動力減弱、全身性心功能減退(Virchow 三聯征)是導致靜脈血流速度緩慢的主要原因[24-25],術后功能鍛煉加速了血液流動速度,關節、肌肉的運動加速了靜脈回流;而術后飲食、飲水方面的護理策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增加血液黏稠食物的攝入,適量增加飲水可稀釋血液,增快靜脈血液循環速度[26]。基于QCC 的術后護理策略更有利于恢復下肢深靜脈血流速度,可有效降低術后DVT 的發生[27]。
基于QCC 的術后護理策略的實行,QCC 小組成員能夠及時發現臨床護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溝通,護理模式由既往的被動護理轉變為主動護理,溝通協調能力和參與積極性得到顯著提升[28-29]。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的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積極性、團隊意識及責任心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實行基于QCC 的術后護理策略后,護理人員的各項綜合素質得到顯著提高。
綜上所述,基于QCC 的術后護理策略能夠使下肢骨折患者的術后護理干預更加合理、科學,同時還能積極調動全體QCC 小組成員的工作積極性,護理人員的各項綜合能力得到顯著提升,進而達到有效預防下肢骨折患者術后DVT 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