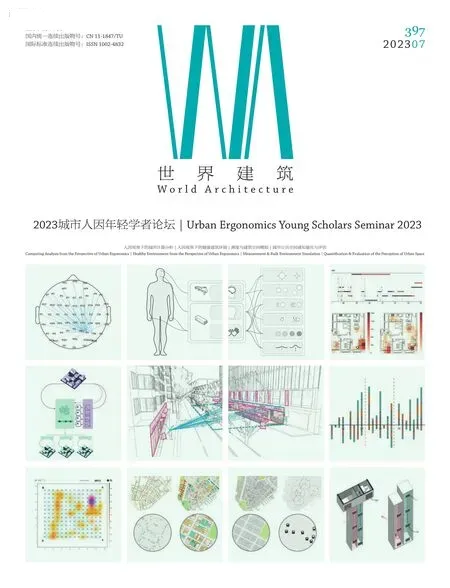基于人居活動數據的城市分析
——紐約市實踐經驗及其城市人因工程學啟示
來源,胡安妮
0 前言
21 世紀以來,城市人居在數字與智慧技術的影響下,不斷呈現出虛實結合的空間演變與人機交互的智慧場景。大量涌現的城市數據為使用機器學習與信息可視化等技術開展科學量化分析提供了豐富的數字資源,通過對多源大數據與多模態信息分析解讀,可促使我們更全面地了解人與多尺度、多維度空間中多種元素的相互作用。然而,在數字化、智慧化技術嵌入人居活動的過程中亦會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隨著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不斷滲透人居空間與城市生活,當代城市物理—賽博—社會三元空間中多種智慧化技術應用與人不斷交互影響,演化出眾多新的用戶體驗、生活場景和交互方式,為城市分析帶來了新問題、復雜性與新風險。與此同時,城市人因工程從人體與空間的體驗、互動與感受出發,關注物理空間規劃設計與人交互所帶來的生理、心理影響與作用,成為探討未來城市空間的重要研究視角。

1 智慧城市環境下的人居活動信息構架
本文首先闡述了21 世紀以來智慧人居的關鍵技術、科研進展與人居場景演變。結合美國紐約市的多項實踐案例經驗,梳理了城市分析的內涵及其在場所、社區、城市等多種尺度和多種智慧場景建設等方面的應用。基于以上關于城市分析的初步發現,進一步總結了城市分析當前所面臨的難題,并對城市人因工程視角如何啟發智慧人居建設背景下的城市分析展開探討。總結而言,基于人居活動數據的城市分析為未來城市智慧人居建設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撐,而城市人因工程在完善城市分析的“人本性”“交互性”“社會性”方面提供了獨特視角,這不僅對支撐未來智慧城市人居規劃、建設、治理具有實際意義,更為面向未來的數字化、智慧化人居環境科學和信息賦能設計科學提供重要的理論探討。
1 城市智慧人居的演進趨勢
1.1 智慧技術創新推動城市科學
在過去的20 年中,智慧城市伴隨著城市基礎設施老舊和城市治理挑戰等難題經歷了新興技術驅動的4 次創新浪潮[1]。對其內容與特征可進行如下概括:(1)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即在城市范圍與空間尺度上的通訊信息(ICT)基礎設施更新建設,通過無線網絡、傳感器等結合,以實現城市建成環境與公共通訊網絡互聯互通,形成一個將信息與物理系統連接起來的“數字城市”[2];(2)信息化社會網絡形成階段,即新興科技產業模式關注個人用戶體驗的信息媒體,以市場化的個人智能設備、物聯網、社交媒體平臺等形成一系列新型的商業模式;(3)城市大數據增長階段,伴隨數字基礎設施、感知設備與社交網絡的成熟帶來了多樣化的城市大數據資源和以服務市民為核心的城市數據平臺建設,城市開放數據、城市數據分析、城市數據科學成為新興技術議題;(4)城市科學與城市信息學興起階段,當城市數據資源快速增長,伴隨城鎮化進入新的階段,引發了包括城市分析、城市預測、數字孿生城市等學術話題,并促成城市實驗室、新城市科學、未來城市、智聯社區等多種人居科學探索與技術開發途徑[3];(5)自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城市信息技術在疫情監測防控、公共衛生管理、社區健康服務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體現了智慧城市應用于公共健康領域的重要作用[4]。
美國紐約市作為全球科技創新領先城市,自21 世紀以來亦經歷了上述5 個演進階段,尤其在2010-2020 這10 年間,無論是城市政府部門的職能建設,還是當地高校與科研機構對城市科學與智慧城市技術的研發應用,抑或科技企業與商業機構對智慧城市人居的參與,該市均作出了諸多前沿科學探索與設計應用示范。因此以下將以紐約市為例,具體展開說明該市在城市分析及其相關的智慧人居建設方面的實踐經驗。
1.2 智慧城市多層信息構架
關于智慧城市的信息構架,Habibzadel 等將其概括為包括數據層、通訊層、傳感層、應用層、安全層的多層級、多系統的城市信息構架[5](圖1)。以紐約市為例,該市自2012 年提出了城市開放數據平臺(OpenNYC)作為城市數據層的管理機制,通過地方性立法和城市條例為其提供了政策保障、實施路徑、技術支持與人力資源。在通訊與傳感層面,紐約市開展了多個城市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與傳感監測項目,包括基于公共空間智能設備的LinkNYC 項目[6]、基于聲學監測的SONYC 項目[7]、基于遠紅外遙感觀測的Urban Observatory 項目[8]等;在應用層面,紐約市不僅對該市的公眾服務熱線(NYC 311)進行信息系統改造與數據管理優化[9],還依托OpenNYC 推出一系列基于城市開放數據資源的智能應用[10];在信息安全層面,紐約市成立了科技與創新辦公室(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OTI)并于2017 年借助谷歌云(Google Cloud)的技術合作支持建立了紐約市賽博控制部(New York City Cyber Command),以對全城的公共數據安全及其相關信息系統安全性提供技術保障[11]。
1.3 虛實結合的人居場景演變
數字時代下,城市的發展不斷呈現出虛實結合的空間演變與人機交互的智慧場景。一方面,傳感設備、監測系統、云計算、分布式算法、信息交互界面等多種后端、中端、前端技術將城市空間及其空間中的各種人居活動數據化、虛擬化成為了可能。美國城市規劃設計學者Mitchell W.對此提出了“比特城市”(City of Bits)的概念,認為未來城市規劃設計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物理空間塑造,還包括對賽博空間的設計干預[12];另一方面,居民活動在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賽博空間中不斷拓展,人們的行為、決策、交流無不受到數據驅動與算法影響,并在多種信息交互中萌生出新的行為方式。對于這種轉變,瑞典社會心理學家Bradley G.將其形容為“網絡人”(Humans on the Net)現象,并探討了數字技術所催生的社會新現象與社區信息學新興領域[13]。在智慧城市與數字人居的背景下,荷蘭法學專家Ranchordás S.進一步探討了當代與未來信息技術對人的行為意識干預所涉及到的法律問題與倫理爭議[14]。
在實踐層面,智慧技術逐漸在多種城市規劃、設計與治理場景中得到了應用示范。早在2008 年,紐約市警察局就與微軟聯合提出了基于域感知系統(DAS)的下曼哈頓安全倡議,探索信息技術支撐城市公共安全和安保數據管理[15]。該系統將監控視頻源、車牌閱讀器、輻射探測和化學傳感器、911 警報和其他機構數據整合到一個中央信息交換中心,并于2015 年首次在城市部署了槍擊檢測系統,以增強公共安全監測和威懾犯罪的能力。在公共空間方面,紐約市公園管理局于2016 年啟動了“公園智能長椅”的試點項目,將物聯網裝置引入公園智能設施與行人活動數字化管理[16]。每個智能長椅配置有可供手機充電的太陽能裝置和用于收集公園空間使用趨勢和行人軌跡數據的WiFi 設備。這種智能長椅不僅為公園使用者帶來便利,還能為公園管理局提供實時信息和量化數據以實現由數據驅動的管理決策。2019 年,紐約市交通局(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與大都會交通管理局(The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紐約警察局(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NYPD)合作開展了“公交提升行動”計劃[17]。該計劃旨在通過公交優先政策工具包、增加攝像頭設備、公交車道執法、公交服務管理舉措和公交路線優化等措施,將全市公交車速度提高25%,從而鼓勵使用公共交通以緩解交通擁堵。綜上,城市在多種數字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呈現出虛實結合的人居場景演變與智慧化的應用場景,不僅為城市的規劃、設計、治理過程帶來了多種數字化、智慧化的技術支持,還為隨后開展的城市分析提供了大量數據資源與實證研究依據。

2 數據分析的類型分類,根據參考文獻[21]繪制
2 基于人居活動數據的城市分析
2.1 城市分析的內涵
早在1960 年代就興起了對數據以及數據分析內涵的討論,美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Tukey J.認為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是通過發掘、解讀、交流數據所揭示模式規律的研究方式[18]。對于城市分析(urban analytics)的內涵,不同專家學者提出了多種解讀和定義。例如Batty M.認為城市分析是一種快速新興的工具,用于解決大數據、城市模擬、地理人口統計等問題[19];Goodchild M.認為城市分析是通過利用來自社交媒體、眾包、感知網絡等新興數據資源進行城市研究創新[20]。數據分析的類型可根據其方法途徑、復雜程度與智能價值分為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tics)、診斷性分析(diagnostic analytics)、預測性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與規范性分析(prescriptive analytics)[21]。描述性分析旨在利用數據統計與可視化等方式對數據進行總體描述與特征總結;診斷性分析主要通過回歸模型與歸因分析等來對不同變量間的相關性與因果關系進行分析驗證;預測性分析利用統計模型、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等方法對歷史數據或抽樣數據進行分析以實現預測的能力;規范性分析亦利用多種統計模型和機器學習方法,但其目的偏向于提供建議與推薦(圖2)。
基于人居活動的城市數據分析流程可大致歸納為以下5 個步驟:(1)數字化(digitizing),即利用多種技術將多源信息轉化為機器可讀的數據格式;(2)計量化(quantifying),即將觀察結果計數和測量為數據的數量;(3)流程化(pipelining),即策劃在整個生命周期中數據存儲庫的管理與使用,包括創建、存儲、傳輸、歸檔和更新;(4)模型化(modeling),通過構建基于統計學習、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的回歸模型、預測模型或分類器,以實現由數據驅動的歸因、識別、分類、預測、推薦等多種分析算法;(5)可視化(visualizing),即將分析結果進行圖形化展示以及可實現用戶交互的信息界面。
作為城市分析的先行者,紐約市于2013 年正式成立“數據分析市長辦公室”(Mayor's Office of Data Analytics,MODA)并明確了該機構組織的3 項重點工作:(1)為本市其他機構提供數據分析支持服務;(2)促進城市機構與多方主體之間的數據共享;(3)管理和推廣多樣化的城市開放數據項目,其內容涵蓋城市的市政運營、經濟發展、環境可持續、租戶保護、應急響應等不同空間尺度與時效性的城市分析與決策支持[22]。在方法層面,對于城市原始數據的處理解讀往往需要依賴信息學(數據和信息的使用)、分析學(從數據中提取知識)和城市專業領域知識(理解知識的相關性和潛在價值)等多學科的知識技能。因此,城市分析貫穿了城市信息系統的后端(數據管理)、中端(算法與模型)、前端(信息輸入輸出與交互界面),其成果不僅包括數據分析結果(類似于傳統咨詢企業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服務),還包括作為用戶友好體驗和靈活使用接口和門戶網站(作為數據控制臺或終端)。綜上,城市分析與傳統城市量化研究不同,數據不僅可作為實證研究的依據,還能為城市信息管理設計、智慧城市系統運維、決策支持算法等方面提供信息源。
2.2 城市多源數據融合分析的多尺度發現
多源大數據與多模態信息能更全面地反映人與多尺度、多維度空間中多種元素的相互作用,為使用機器學習與信息可視化等技術開展科學量化分析提供了豐富資源。紐約市作為數據驅動城市運營和開放數據的先驅,近年來在不斷建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豐富多樣的城市數據資源環境。在地點和場所尺度,與人居活動相關的城市建成空間元素,例如土地使用情況、建筑物占地、街道網絡、公共交通設施、公共空間家具、行道樹等,均已進行了數據化記錄并實現城市公共數據開放化。通過空間提取、清理、融合等數據處理流程后,這些信息可支持對城市本地微觀區域特征進行量化,客觀定量地描述局部空間質量及其場所特征,并進一步支持解讀分析當地動態多變的人居行為活動。例如,作者先前名為“量化場所”(quantifying places)的研究項目利用紐約市多源大數據,對該市范圍內100 個地點的局部空間元素及其場所特征進行了量化、分類與回歸模型分析,相關結果闡釋了不同類型場所中行人活動的主要驅動因素,并揭示了人居活動分析中城市環境(空間因素)和社會動態(事件因素)的重要考量因素[23]。
在人居健康層面,筆者先前的一項研究利用紐約市內174 個郵政編碼區內居民的就醫活動行為記錄量化計算了城市不同局部空間中季節性呼吸疾病就醫率,并結合反映環境、社會、經濟、人口等因素的多源數據,通過構建地理加權的多元回歸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GWMR)分析了包括建筑質量、空氣質量(PM2.5 濃度)、花粉暴露、人口年齡、家庭經濟因素與過敏性哮喘就醫率間的相關性[25]。由此可見,除了建成環境及其場所特征,城市中不同空間局部的人居活動往往伴隨著經濟、社會、文化、健康等多重因素的累積疊加效應。
2.3 理解賽博空間人居活動情況
如上文所述,近20 年來的信息技術革新帶來了城市生活改變,人居系統在數字化趨勢下亦演變出其在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諸多行為,反映出了列斐伏爾(Lefebvre H.)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所提出的由“現實—精神—社會”所構成的三元空間下的人居活動行為模式[26]。數字政務平臺、社交網絡、自媒體、虛擬現實、元宇宙等多種新型信息交流與管理方式為理解更加具有動態性、時效性、多維性的城市人居活動提供了新的數據資源與實證研究依據。與此同時,新的信息源和數據格式亦需要通過新的分析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描述性解讀、歸因分析、聚類識別以及時空預測。
在2010 年以來,紐約市多個政府部門對其相關業務開展了數字政務管理、城市信息系統升級、數據融合分析等多種數字化、智能化提升,以不斷融合城市管理運維在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賽博空間中的高效融合。以紐約市建筑局(NYC Department of Buildings)為例,其對建筑活動許可、建筑安全檢查、建筑質量評估、建筑能耗能效、建筑產權信息等相關部門業務開展了信息采集、數據分析與智能化決策支持應用。例如,作者先前的一項研究對紐約市建筑局1,058,547 項建筑改造活動許可記錄進行了數據分析,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其進行了內容分析、主題趨勢和話題模型的構建,從而識別城市居民自發進行的建筑改造活動的時空動態[27]。在了解居民對物理空間的利用改造之外,也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平臺信息來了解城市人居動態,尤其是包括情緒、態度、意見等超越物理空間活動的人居信息動態。針對此,作者的研究團隊曾對紐約市274 個社區相關社交媒體數據進行時序變化和輿情態度識別分析,通過對賽博空間信息的提取來衡量城市社區鄰里變化與居民實時態度,探索了一種基于社交媒體動態的城市輿情指標構建、社區情況預警監測和公眾意見收集的綜合技術途徑[28]。
3 城市人居活動數據分析的痛點
隨著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不斷滲透人到居空間與城市生活中,當代城市“物理—賽博—社會”三元空間中多種因素與人不斷交互影響,演化出眾多新的用戶體驗和生活場景,為人與城市空間交互帶來了新問題、復雜爭議與未知風險。整體而言,較為顯著的問題主要包括由數字鴻溝帶來的數據偏差問題、由高精度觀測帶來的數據質量問題以及由多主體多系統帶來的協同問題。
3.1 數字鴻溝造成的數據偏差
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問題體現在社會不同群體對信息技術的可接入(access)和使用(use)方面體現出的差異性[29],包括了設備的可用性、技術使用主動性、技術的社會支持與信息技術使用目的等方面所呈現出的差異性。因此,城市中不同社區在數據中的表現程度通常并不相同,不同社區和群體之間存在數字資源差異,低收入人群與社區可能存在數據缺失或數字表達不完整等問題。以紐約市民投訴與公共服務熱線311 數據為例,McLafferty 等通過對全市范圍市民關于室內臭蟲(bed bug)投訴行為的分析揭示了居民自發行為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VGI)背后的地理空間與社會經濟偏見。分析比對發現,關于家居室內臭蟲的假陽性(false positive)投訴往往出現在高品質住宅和高收入社區人群,若單純以此數據作為市政服務和城市健康依據,就會導致低收入社區的實際問題遭到忽視[30]。因此,隨著智慧技術持續滲入城市規劃、治理和運維等工作環節,相關決策與智能化控制不斷依賴居民活動數據,亟需重視由于數據質量、采樣偏差、測量誤差及其相關分析算法所帶來的數字不平等(digital in equality)問題。
3.2 高精高頻數據的質量檢查
除了上文所介紹的由數字鴻溝所帶來的數據偏差之外,智慧城市背景下的諸多人居活動數據具有高精度、高頻率、多尺度的特點。這些來自于傳感器監測、物聯網運維、地理位置服務(location-basedservices)、手機信令、智慧應用、信息平臺、社交媒體等多種信息源的數據為存儲、清洗、檢查、解讀等一系列處理流程帶來了技術挑戰[31]。以傳感數據為例,Teh H.等通過對6970 篇使用傳感數據的研究論文進行分析,對傳感數據的常見錯誤進行了總結,排序前5 位最常見的數據質量問題分別是異常值(outlier)、缺失數據(missing data)、偏差(bias)、漂移(drift)和噪點(noise)[32]。需要強調的是,許多數據質量問題不僅僅源于監測設備的系統性誤差和傳感裝置調試問題,還可能是由當地人居活動影響而造成的。例如,先前一項關于紐約市社區空氣質量檢測的研究表明,局部微觀尺度的空氣質量監測極易受到當地居民夏季戶外燒烤活動的影響,從而對觀測數據采集帶來異常值的干擾[33]。因此,隨著更多的智能設備不斷走入日常生活,城市分析需要應對多源、高精度和高頻率的數據處理、檢查和解讀任務。

3 城市局部空間多種要素提取,引自參考文獻[24]
3.3 多主體多系統多場景協同
智慧人居規劃設計與管理需要應對多利益主體、多參與主體、多技術系統與多智慧場景協同的難題,這源自城市規劃設計學科和人居環境科學問題的復雜性。因此,未來城市需要能整合數據管理、計算分析、公眾科學一體化的城市信息整體框架以支持城市分析過程中所涉及的多主體、多系統和多場景協同難題[34]。具體就數據分析而言,需要整合基于各種集體現象觀測的多源異構數據,相應的數據分析框架既要應對基于傳感系統的環境客觀測量,還要考慮代表不同利益和參與主體評價的主觀反饋[35]。從模型構建的角度來看,城市現象的復雜性往往分布在多個尺度上,通常具有無標度統計特性且難以通過預測目的的簡單平均值表示。這說明了僅基于數據統計建模和模擬預測的局限性,也突出了人工解讀在城市問題實際管理應用,尤其是涉及語義和認知判斷方面的必要性。此外,城市分析模型往往還涉及到市民活動行為、城市文化、社會經濟等多個領域,這些非系統性的行為活動加上難以量化的社會文化影響,可能會造成模型結構及其參數相關性在不同情況下發生變化,從而導致不準確的解讀與誤判[36]。
4 人因工程視角對城市分析的啟示
城市人因工程學(Urban Ergonomics)是通過建立描述性模型以支持城市的空間體驗量化與設計干預的設計科學途徑[37]。城市人因工程學源于人因工程學和人居環境科學的交叉融匯,其目的是改善城市空間與基礎設施系統,使其更好地服務居民在生理、社會、心理等維度上的生活、安全與健康的質量[38]。其秉承著以人為本的原則,涵蓋人體工程學(人體生理學)、認知工效學(感知心理學)與組織工效學(社會技術系統)3 個具體領域,利用多種技術工具來改善設計學過程中的空間認知與干預,并綜合考慮個人尺度體驗與多主體利益的平衡。它基于多學科專業領域知識,關注人與環境的交互,并通過多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理解這種復雜關系[36]。圖4 概括了城市分析與城市人因工程學之間的聯系,作者認為城市人因工程學對城市分析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人本性”“交互性”“社會性”3 個方面。
4.1 城市分析的人本性
“人本性”指城市應遵循亞里士多德“城邦源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的基本理念,城市規劃學者梁鶴年曾圍繞“城市人”的概念對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開展探討[39]。時至今日,無論是智慧城市規劃設計,還是智慧人居場景運營,抑或是數據驅動的城市分析,都應秉承科技向善和以人為本的規劃價值導向[40]。在城市人因工程領域,以人為本的設計由Mike Cooley 提倡,是一種交互式系統開發方法,旨在通過關注用戶及其需求,并通過應用人為因素/人體工程學、可用性知識和技術,使系統可用和有用[41]。城市人因工程作為探討未來城市空間智慧化與人性化設計的重要途徑,在平衡“人—人、人—社會、人—環境”[42]這3 種維度間的互作互用發揮關鍵作用,因此經常與“人為因素”交替使用而統稱為HFE/EHF(Human Factor Ergonomics)。

4 城市人因工程學視角下的城市居民活動數據分析
具體在城市設計領域,人因工程從人體與空間的體驗、互動、感受出發,關注物理空間規劃設計與人交互所帶來的生理、心理影響與作用。城市人因工程關注人與城市建成空間之間的界面,將這些抽象的空間品質定義為可感知與測量的城市體驗層次,并在宏(群體)、遠(遠體)、中(中體)、近(近體)、微(體表)5 個不同的尺度上開展科學研究與設計干預,以創造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空間與智慧人居體驗[43]。總結而言,作者認為城市人因工程體現了從現代城市主義延伸出的新型人文主義理念,是未來設計科學探索的重要價值導向。
4.2 城市分析的交互性
“交互性”是指人因工程強調的“人—機器—環境”之間的多重交互及其在設計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以參與式城市設計為例,其設計過程中既將用戶參與作為研究手段或分析工具,也將用戶數據作為推進設計研究的主要客觀依據和考量因素[44]。這兩種方式代表了參與式城市設計的不同階段:前者側重于將人的視角融入鄰里評估,默認參與者和此項目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而是為了解城市局部情況與空間活動提供中立的客觀依據;后者則將參與者視為規劃設計的參與主體,通過將公眾參與引入場所營造和社區更新等多種設計情境中,通過將多方利益主體帶入決策情境以期達成更加完善的解決方案。以上兩種交互方式雖有不同的側重,但都依賴城市數據平臺對目標受眾、研究人員或普通用戶的信息開放。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數字化智慧化技術為參與式設計提供了數智賦能的機遇,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信息技術介入于參與式設計中,信息源和數據量的增加也提高了數據的篩選、分析、管理和解讀流程的復雜性。此外,參與式設計往往需要高質量和高準確性的數據支撐,例如民意調查問卷的問題需要更加精準的把控和引導。總結而言,參與式設計雖然能有效解決當地局部問題,但是城市規劃仍需要總體宏觀指引。因此,未來城市設計可借鑒人因工程手段來實現在數據信息的廣泛度和精準度之間的平衡關系,并進一步構建基于人機交互的參與式規劃設計模式,以便于更加全面精確地了解多元參與主體的特征與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
4.3 城市分析的社會性
“社會性”是指城市分析過程中的社會因素以及城市人因中所體現的社會屬性,這是分析個人活動擴展至集群活動過程中的重要考量。早在1990 年代,Cohen 和Smith 就曾以人因工程學視角審視當代城市病與社區問題,并提出“社區人因工程學”(community ergonomics)的設想[45]。Lane N.等進一步提出可將基于人本尺度傳感的量化監測串聯擴大至社區尺度,從而得以分析“網絡社區行為”(networked community behavior)所反映的集群特征、社會連接與活動規律[46]。從社會性視角來看,社區人因工程學由社會子系統(社區居民)、技術子系統(機構、服務、政策等)和社區人因程序(連接社會和技術子系統與環境的因素,例如經濟)組成,旨在通過社區居民對其生活環境的把控以及對其行為對他人和環境后果的認識,來彌合社區居民與環境之間的差距。社區人因工程學的核心是通過個體的生理過程、外部社會和文化環境以及組織機構的自我調節來實現人類重要功能(如發展、感知、動機和學習)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在社區人因工程學中,個人被視為一個有組織的系統,其行為的指導和過程取決于個人對社區環境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發展相互反饋控制的能力。
社區人因工程學包含7 項原則,分別為:(1)以行動為導向的方法注重對選定目的和目標的關注,旨在實現集體目的和觀點對所關注問題的影響,并通過具體行動來達成具體目標和愿望;(2)通過個人參與、行動小組、委員會等機制促進公眾參與,為居民提供思想源泉、激勵手段、教育新思想與新行為方式;(3)通過加強多樣性管理和沖突處理,城市社區能夠更好地應對不穩定因素,提升自身的環境跟蹤和互動能力;(4)鼓勵式學習在控制權轉移、知識轉移和技能轉移等技術向社區轉移的過程中發揮作用;(5)通過創建具體任務、行動和學習機會來建立自律,以提高個人或團體對環境施加影響的能力;(6)整合反應性反饋、工具性反饋和操作性反饋機制,使閉環控制、社會跟蹤和自我調節原則在社區環境改善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發揮作用;(7)通過評估實施操作要求、衡量有效性并利用信息反饋來持續改進和創新原有規劃[47]。
作者認為,城市分析的社會性既體現在其結果所揭示的社會問題,也體現在其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以紐約市為例,該市政府與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理工學院等多所當地教育科研機構開展合作,通過建立“社區實驗室”的方式將公眾科學與社區參與和城市分析相結合,開展聚焦人群健康、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智慧人居探索[48]。這說明,在城市智慧人居的實踐過程中,城市分析的社會性、人本性、交互性往往呈現出相互交融的形式。
5 結語
隨著城市信息技術創新與大數據不斷涌現,基于人居活動數據的城市分析將在未來城市規劃、設計、建設、治理過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在新數據、新方法和新技術持續應用于城市智慧人居發展的同時,未來的城市數據分析仍需更好地應對信息偏差、數據質量和多元主體需求等復雜挑戰。作者認為,城市人因工程作為前沿新興的設計科學途徑,能夠有效地結合城市體驗量化研究與空間設計干預,并從“人本性”“交互性”和“社會性”3 個方面對城市數據分析進行支撐。總而言之,基于人居活動數據的城市分析在智慧化城市規劃治理中承擔核心角色,而城市人因工程學的理論與方法對城市分析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科學啟示,將是探索智慧人居設計科學的關鍵路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