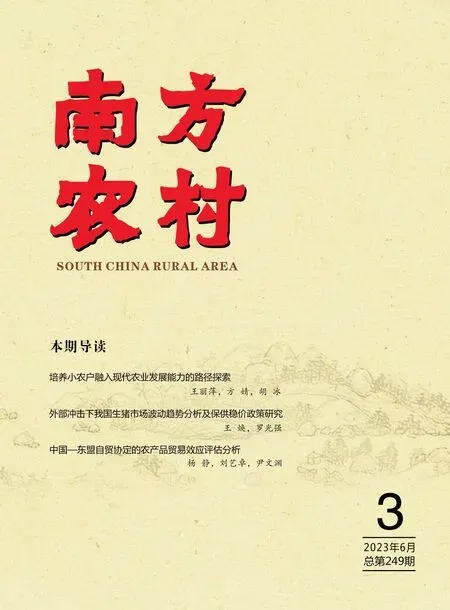外部沖擊下我國生豬市場波動趨勢分析及保供穩價政策研究
王 煥,羅光強
(湖南農業大學 經濟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一、引言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豬肉生產和銷售國,豬肉市場供求關系變動與市場價格波動既是歷史事實,又是客觀現象,更是當下問題[1]。生豬市場的保供穩價不僅關系到相關產業的健康發展,也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經濟利益[2]。生鮮市場產品價格不僅受到環境、飼養成本等因素的影響,更易受到社會突發事件的沖擊。如2013年爆發的H7N9禽流感,造成大量瘟雞被捕殺,人們對雞肉安全信任度下降,雞肉及其互補品價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表現低迷。2014年爆發的豬藍耳病,造成公豬精子品質下降,母豬早產,仔豬免疫下降,從而使市場豬肉供給減少。2018年爆發的非洲豬瘟疫情,造成國內市場生豬出欄量下降,仔豬成活率降低,雖然現在已經得到有效的控制,但由于徹底根除的防治疫苗尚未研發成功,因而引致著我國當前生豬市場產能持續下滑,豬肉市場供給偏緊,加之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沖擊”影響的疊加,當前生豬市場供給缺口偏大、生豬市場均衡價格偏高。
一般地,將經濟系統和金融市場之外的事件或者力量引起的對經濟體的影響稱之為“外部沖擊”。大量研究表明:在沖擊事件發生時,產品價格在需求和供給共同作用下發生劇烈波動[3]。在沖擊事件結束后,雖然消費者對于產品的需求可以快速恢復到原有水平,但由于生產時滯的存在,產品價格將會受到沖擊事件的慣性影響[4]。因此,經濟學者提出為促進我國生豬市場穩定運行,今后的相關研究可以從供給角度著手,尋求減緩外部沖擊影響穩定市場價格的途徑[5]。然而,關于非洲豬瘟產生的外部沖擊雖然已成為近期研究的熱點話題,但從規律視角所進行的響應政策研究有待進一步的深化。基于此,本文試圖利用外部沖擊概念與模型分析非洲豬瘟疫情對我國生豬市場波動的影響,以便為“保供穩價”政策提供參考。
本文首先定性分析豬瘟疫情對我國豬肉市場的影響,并以此為基礎分析外部沖擊下我國豬肉市場價格波動特征以及受影響強度;然后利用ARMA模型預測如果不進行人為干預,外部沖擊下我國生豬市場波動的未來趨勢特征;最后根據外部沖擊的效應特征與趨勢特征探尋促進生豬市場保供穩價的相關政策。
二、非洲豬瘟對我國豬肉市場的影響
(一)生豬出欄量下降,豬肉市場價格大幅度上升
從2019年4月份開始,隨著豬瘟疫情在廣東、四川等地的大范圍蔓延,我國生豬存欄量、生豬出欄量以及豬肉產量開始巨幅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止到2019年年末,我國全年生豬存欄量為31041萬頭,出欄量為54419萬頭,市場豬肉供給量為4255萬噸,相比2018年同期分別下降27.5%、21.6%和21.3%。本文選取2013年1月—2021年2月的全國生豬價格月度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整個樣本期間,豬肉價格從2013年4月的22.03元/kg上漲至2013年5月的31.3元/kg,隨后下跌至2014年4月的19.7元/kg后觸底反彈,呈現波動中上升的態勢,于2016年6月達到31.29元/kg。之后震蕩跌至2018年5月19.52元/kg,與2014年4月基本持平。2018年5月之后生豬價格整體上升趨勢凸顯,陡坡上升至2020年2月的58.89元/kg,每千克生豬平均上漲40.37元,上漲幅度達到201.69%。之后隨著政府對豬肉市場的干預和對豬瘟疫情的防控,2020年3月—2021年2月期間,全國生豬價格有所下降,但整體仍處于40元/kg—45元/kg范圍。
(二)價格季節性波動更加顯著,周期性震動幅度增加
受到居民消費習慣以及節日等的影響,我國豬肉市場價格一直呈現季節性波動,呈現“雙峰值”結構。一般來講,每年的6月—9月豬肉市場價格逐漸上升,11月之后有所下降。之后隨著冬季到來,春節、元旦等節日也進一步提高了豬肉需求,使豬肉消費逐漸進入下一個小旺季,因此12月到次年的1月期間豬肉價格將再次回升,但是回升幅度不會超過9月,2月—5月再次下降。在受到豬瘟疫情沖擊之后,豬肉價格波動的季節性特征更加明顯,除較疫情發生之前,在疫情發生之后首次價格峰值更大之外,還存在著雙峰之間時間間隔變短,震動幅度減緩等特征。
豬肉價格呈現周期性波動主要受到以下原因的影響。一方面,從仔豬到生豬發育成熟可以出欄需要一段時間,而生豬養殖戶往往會根據前期豬肉價格確定當期仔豬養殖數量,若前期價格上漲,養殖戶的養殖積極性有所提高,養殖規模將會擴大從而增加當期生豬供給,降低豬肉市場價格。受當期豬肉價格下降的影響,養殖戶將會縮小下期養殖規模,減少生豬供給,市場供不應求使豬肉價格再次上漲,形成豬肉價格呈現周期性波動。另一方面,豬飼料成本是影響生豬出欄成本從而影響豬肉市場價格的主要因素,豆粕、玉米等谷物作為豬飼料的主要組成成分,其生長將會受到環境氣候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生長周期,這也將造成豬肉價格的周期性波動。在此次疫情的影響下,2018年生豬出欄量下降,從而造成2019年豬肉市場供給的嚴重不足,豬肉價格出現更加激烈的周期性波動。
(三)國際貿易市場結構發生改變
據統計,2017年全國豬肉總產量為5451.8萬噸,進口量為121.7萬噸,其中從美國進口豬肉占比13.72%。2018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中國開展“232措施”和“301調查”,即對從中國進口的包括鋼材以及知識產權類產品加征關稅,中美貿易戰由此展開。在此期間,受中美貿易摩擦事件的影響,我國豬肉國際市場進口貿易結構逐漸發生改變,從美國進口的冷凍豬肉以及豬肉制品總量大幅度減少,而德國、巴西、西班牙等歐盟國家開始成為我國主要的豬肉供應國[6]。2018年我國豬肉進口總量為119.2萬噸,美國出口量為8.6萬噸,占比7.2%。2019年我國受到豬瘟疫情的影響,國內豬肉市場供需嚴重失衡,為滿足消費者對豬肉的日常需求,緩解豬肉供需矛盾,政府擴大了冷凍豬肉及其制品進口規模,全年進口總量為210.8萬噸,相比2018年增加75%。其中得益于2019年9月中旬的“豁免美國出口的部分豬肉及大豆的關稅”政策的實行,2019年中國從美國進口冷凍豬肉及其制品總量增加至17.2萬噸,占總進口量的8.16%。
(四)替代品價格上漲
在豬瘟疫情的影響下,我國豬肉市場供給偏緊,豬肉價格上漲。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除商品本身的價格、人的主觀心理因素之外,相關商品的價格也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豬肉價格大幅度上漲時:一方面,平常購買豬肉的消費者,如果在價格上漲時仍選擇購買豬肉將會增加日常生活開支,對一些人來說經濟壓力過大,因此購買豬肉的消費者的數量將會下降;另一方面,消費者在豬肉價格上漲時會減少單次購買量,兩方面共同作用使豬肉市場需求有所下降。但由于肉類包含了消費者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營養需求,因此消費者在減少對豬肉購買的同時,將會增加雞肉、牛羊肉、魚肉等與豬肉功能相近的替代品的需求。而動物生長周期的存在,使替代品的供給無法迅速增加以滿足所有消費者的需要,因此市場將會出現短期雞肉等替代品供不應求、價格上漲的現象。
三、疫情對豬肉價格沖擊的波動特征分析
“外部沖擊”可以大致概括為匯率、自然災害、突發疫情等因素,非洲豬瘟作為一種典型的外部沖擊事件,對我國生豬市場的穩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此,以下運用周期分析技術探尋豬瘟疫情下的豬肉價格波動特征。
一般認為,經濟變量主要是由趨勢、周期、季節以及隨機四種成分組成,并且通過對組成成分的分析可以對經濟變量的長期趨勢作出預測。因此本文將做如下分析:首先采用Census X12季節調整法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調整,分解出季節成分、隨機成分和趨勢循環成分;再利用H-P濾波法將趨勢循環成分進行分解,得到趨勢成分和周期成分。由此得到豬肉市場價格的趨勢成分、周期成分、季節成分以及隨機成分,并著重對趨勢成分進行分析。
(一)疫情沖擊下我國豬肉價格波動的一般特征分析
本研究共計98個樣本,樣本數據來自于中國農業農村部網站。首先通過Eviews軟件建立經濟模型進行分析,數據命名為PRICE。根據豬肉價格波動趨勢分析結果(圖1),可以了解到全國豬肉市場價格在2013年1月—2021年2月整體呈現上漲趨勢。對整個研究期間經濟事件分析可知,造成豬肉價格波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是一些重大的外部沖擊事件,如2013年爆發的禽流感、2014年產生較大危害的豬藍耳病、2015年的禽流感、2018年的豬瘟疫情等,市場價格波動的拐點與這些事件的出現有著密切的聯系。

圖1 2013年—2021年生豬月度價格變化總趨勢
(二)疫情沖擊下我國豬肉價格波動的不同特征分析
豬肉市場價格總體趨勢在季節等因素的影響下圍繞著均衡價格上下波動。豬肉價格趨勢成分在2013—2018年雖略有波動但整體平穩,呈現緩慢增長狀態;而從2018年8月左右豬肉價格開始呈線性上升,由2018年8月的21.96元/kg上漲到2021年2月的39元/kg,整體上漲幅度為77.6%(圖2a)。價格最低值出現在2014年4月和2018年5月為19.52元/kg,最高值出現在2020年8月為58.89元/kg,波動幅度高達201.69%。豬肉價格季節成分圖顯示,受到人們消費習慣以及節假日等因素的影響,豬肉價格表現出較明顯的季節性波動(圖2b)。如果按照從一個谷底到另一個谷底為一個完整周期的劃分方法,可將整個研究樣本劃分成兩個半大周期,周期時間分別為2013年1月—2015年3月、2015年4月—2019年2月和2019年3月—2021年2月。其中,第2個周期的持續時間最長為46個月,第3個周期的波動幅度最大為26(圖2c)。

圖2 2013年1月—2021年2月全國豬肉價格不同成分的變化趨勢
隨機成分由社會偶發性事件引起,是價格波動的白噪聲,外部沖擊會造成隨機成分的劇烈波動。從豬肉價格隨機成分圖可以看出,隨機成分在2013年、2018—2020年發生了劇烈的波動。實際情況表明,2013年爆發的禽流感疫情、2018年爆發的豬瘟疫情等社會突發事件均對豬肉價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四、外部沖擊下我國豬肉市場價格的沖擊效應分析
在經濟學中,“沖擊效應”被定義為宏觀經濟中的總供給或者總需求在短期內受到突然而劇烈的影響,導致迅速提高或者降低,主要是指經濟學中的“供給沖擊”效果。本文主要利用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法考察外部沖擊下我國豬肉市場價格波動的方向及力度。VAR模型通過把每個內生變量看作所有內生變量若干滯后項的函數進行回歸,來解釋變量本身以及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它經常被用于分析時間序列序列中隨機成分對于系統的沖擊,從而用來解釋社會中各種偶發性事件對經濟系統的影響。
數學表達式為:Yt=A1Yt-1+A2Yt-2+…+ApYt-p+BXt+Et,t=1,2,….,T。
為了進一步分析疫情對豬肉價格的隨機沖擊,以豬肉價格為因變量,價格滯后項以及價格隨機成分為自變量,建立VAR模型。在建立模型前,利用單位根法檢驗各經濟變量的穩定性,檢驗結果如下(表1):變量price的ADF統計值大于1%的臨界值,不能拒絕原假設即序列price本身不平穩,一階差分后得到的Dprice為平穩序列;隨機成分price_ir本身即為平穩序列。因此以Dprice為因變量,以Dprice滯后項和price_ir為自變量進行回歸。

表1 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2 VAR模型滯后期的確定

表3 生豬價格方差分解結果
滯后階的選擇對于VAR模型的建立也十分重要,在選擇模型滯后階時要綜合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較大的滯后階才能比較貼切的反應經濟變量長期動態變化特征;另一方面,滯后階越大說明需要估計的參數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相對就較少。本文利用LR統計量、AIC準則、SC準則等來判斷模型的最佳滯后階,帶*的表示軟件根據以上準則選擇的最佳滯后階,分析結果確定當滯后5期時模型擬合最好。
VAR模型作為一種非理論性模型,很難對其系數進行具體解釋,研究更多的是依靠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法進行分析。模型穩定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特征值的倒數都落在單位圓內(圖3),即以Dprice為因變量,以Dprice的滯后項和price_ir為自變量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穩定的,滿足后續分析的條件。

圖4 生豬價格的脈沖響應程度
脈沖響應函數主要用來分析當模型受到某種沖擊后,隨著時間的推移系統受到的動態影響。采用Eviews生成的脈沖響應軌跡圖顯示,豬肉價格從第1個月就開始響應,說明豬瘟疫情對價格的沖擊不存在時滯。在前4個月價格對沖擊的響應為負,最大響應程度出現在沖擊發生的第二個月為-2.12,隨后出現正向響應。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首先,隨著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豬肉形成剛性需求,疫情發生后,市場可以即時反應。其次,消費者對生鮮食品安全問題越發的關注,豬瘟疫情的出現引起消費者心理的恐慌導致需求量下降,對豬肉價格呈現負向沖擊。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府對疫情的控制,消費者恢復對豬肉的信任使需求量增加,但由于“豬周期”的存在導致市場供給難以快速恢復,從而造成價格上漲。
方差分解主要是分析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的改變對VAR模型的影響程度。生豬價格本身以及價格隨即成分的雙重作用導致生豬價格的變化,引起價格波動。分解結果表明,疫情事件是豬肉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從10個月的時間來看,疫情對價格的影響先上升后下降,在初期價格波動的61%來自疫情的擾動,隨后逐漸下降,最終穩定至56%。究其原因在于,我國生豬養殖主要是以家庭散養、小規模養殖為主,疫情初期由于養殖戶認識不足,往往出現就地掩埋、隨意宰殺販賣的現象,造成疫情的擴散。在疫情大規模爆發之后,國家進行市場干預,養殖戶防控水平的提高,都將逐漸降低疫情對價格的影響。
五、外部沖擊下我國生豬市場波動趨勢分析
ARMA(p,q)模型是由Box和Jenkins提出的一種較為完善的統計預測方法,其原理在于利用數學模型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描述,確定模型系數之后,便可以利用序列的過去值和當期值對未來值進行預測,從而揭示經濟變量的波動趨勢。因此,本文利用研究樣本建立ARMA模型對我國生豬市場波動趨勢進行預測分析。
上述對時間序列數據波動特征分析結果顯示,將時間序列price一階差分可以消除其趨勢性,使序列平穩,因此選擇ARMA(p,q)模型。如圖5所示,序列price的一階差分Dprice的AC值和PAC值都很快地落入到隨機區間,PAC值在滯后一階時不為0,在k>1時都落在95%的置信區間內,說明序列Dprice的偏自相關函數具有截尾性,所以p=1;從自相關系數圖分析可知,序列Dprice的自相關系數在1階截尾。綜合考慮,建立模型為ARMA(1,1)。圖6中ARMA(1,1)模型檢驗結果顯示,AR(1)和MA(1)所對應的P值都趨于0,但是常數項C對應的P值為0.7578,并不趨于0。因此將模型常數項去除之后,重新進行估計和殘差檢驗,結果如圖7所示:不含常數項的ARMA(1,1)模型的系數更加顯著,且赤池信息準則值變小,說明去除常數項之后模型預測結果更加精確。其中ARMA(1,1)模型對應的數學表達式為:Dpricet=-0.7868Dpricet-1+εt+0.9625εt-1,其中εt為殘差序列。

圖5 Dprice自相關-偏自相關分析圖

圖6 ARMA(1,1)模型檢驗結果

圖7 ARMA(1,1)模型去常數項C檢驗結果
對模型進行檢驗之后,對ARMA(1,1)模型的εt序列進行白噪聲檢驗,檢驗結果(圖8)顯示εt序列為白噪聲序列,即該殘差序列中的所有有用信息已被完全提取,模型擬合程度較好。

圖8 ARMA(1,1)模型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利用以上建立的模型ARMA(1,1)對2021年3月至2026年2月的全國豬肉月度市場價格進行預測,結果如下所示(表4)。

表4 生豬月度價格預測
圖9是預測數據經過Census X12季節調整法處理之后得到的季節成分。分析結果顯示,未來五年季節性因素將會對豬肉價格產生顯著影響,季節性波動凸顯,且季節性影響具有較強的重復性。

圖9 未來價格季節成分
利用Census X12季節調整法可以將預測數據分解出趨勢循環成分,再使用H-P濾波法可以將其分解成趨勢成分(Trend)和循環成分(Cycle),如圖10所示。與本文研究的樣本數據進行對比發現,2021年3月至2026年2月期間全國豬肉市場價格呈現線性平穩下降趨勢。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是由于:第一,消費者的飲食習慣可以長期發生轉變,形成替代性消費。由于各種肉制品之間功能相近,在豬肉供給出現短缺時,消費者可以轉向購買功能相似但價格更為低廉的其他肉制品,減少了對豬肉的需求造成價格的下降。第二,產業鏈安全管理初顯成效。通過對生豬養殖、加工、流通等環節的安全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仔豬成活率穩定生豬供給,減緩突發事件對價格的影響。第三,政府對市場進行管理調控。豬肉消費具有季節性特征,政府通過跨時間調配也可以降低市場價格。

圖10 未來價格趨勢成分和循環成分
周期成分分析結果顯示,未來價格周期性波動衰減,按照具有明顯上升或者下降為一個完整的周期劃分原則,可以將預測數據波動大致劃分為5個周期,如下所示,周期開始于2021年9月,截止于2025年12月。從表5分析可知,未來價格的周期不具有對稱性特征;第1、2周期振幅相對較大,3、4周期居中,第5周期振幅最小為0.009。

表5 2021年3月—2026年2月生豬月度價格周期劃分
六、促進我國生豬市場的保供穩價政策選擇
本文分析結果顯示,在外部事件的沖擊下新時期我國豬肉價格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季節性和周期性波動顯著,受隨機成分影響較大。未來五年預測結果顯示:豬肉價格整體上呈下降趨勢,周期性波動衰減,季節性波動凸顯。因此,經濟新時期下為促進我國生豬市場的保供穩價,政府可以從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促進生豬消費的“替代響應”。相比生豬養殖,其他禽類具有成長發育周期短、成活率高、運輸方便等優點。因此,政府可以從需求角度出發,通過豐富消費者的“菜籃子”,引導消費者消費功能相近的其他肉制品,減少市場對豬肉的需求,彌補豬肉市場供需缺口,抑制豬肉價格的短期劇烈波動。
第二,加大國家公共財政支出和養殖行業保險投入力度。很多養殖戶在疫情發生時往往無法抵擋疫情沖擊,不得不縮小養殖規模甚至退出生豬養殖市場。生豬養殖保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穩定農戶收入,同時研究也表明政府財政補貼以及優惠政策的落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養殖戶的保費支出,增加養殖戶的投保積極性,減少市場豬肉供給的大幅度波動[7]。
第三,統籌布局做好冷凍豬肉的進口、儲存和投放。此次豬瘟疫情造成我國豬肉供應的短缺,為彌補供需缺口,滿足消費者的日常需求,政府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采購冷凍豬肉及其制品,并根據我國豬肉波動特點,實現跨區域、跨時空調配,穩定市場價格。冷凍豬肉的存儲與投放需要更加安全高效的生鮮倉儲系統和冷鏈物流體系作為支撐,因此在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政府應該將科研財政支出向該類研究傾斜。
第四,促進生豬產業鏈整合,建立豬肉可追溯體系。我國生豬行業主要是以散養戶為主,且養殖規模化水平低,豬肉可追溯體系并不完善,這就造成了近幾年來我國豬肉市場價格波動頻繁,生豬行業發展不確定性較大[8]。政府通過政策導向可以降低散養戶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生豬養殖的規模化;通過加強市場監管,建立豬肉可追溯體系,可以增強消費者消費的信心,轉“危”為“機”,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第五,加強生豬市場監管,建立疫病輿情指數。政府通過加強對生豬市場的監管,監測價格波動,建立應急防控機制,可以及時發現價格異常波動,有效控制疫病傳播,穩定生豬市場,提升應急保供效能。
第六,加強生豬養殖合作組織建立和創新。通過建立生豬養殖合作組織,可以構建開放透明的信息交流平臺,及時向養殖戶傳遞國家政策的同時,也將促進養殖戶之間的信息交換和技術合作。
第七,加大政策宣傳力度,提升生豬養殖戶有關病死豬無害化處理政策的認知。相比于其他養殖業,生豬養殖戶政策認知缺失,對病死豬處理不當也是導致疫病發生頻率高、傳播范圍廣、豬肉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的重要因素之一[9]。提高養殖戶對疫病防控以等知識的認知,可以從源頭上確保豬肉供給的穩定性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