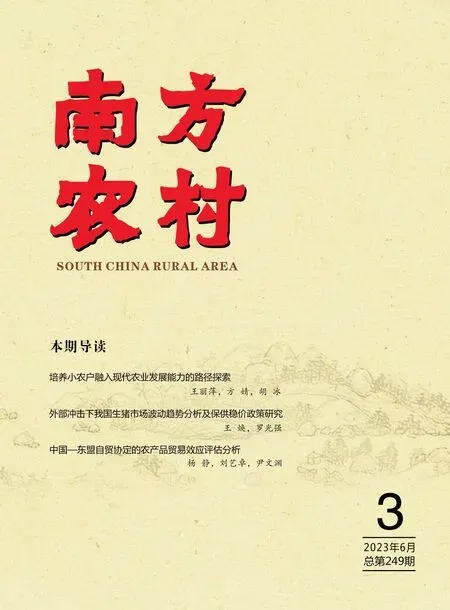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的農產品貿易效應評估分析
楊 靜,劉藝卓,尹文淵
(1.農業農村部 農業貿易促進中心,北京 100125;2.商務部 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北京 100710)
一、引言
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將深化同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東盟歷來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也是中國第一大農產品貿易伙伴。自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實施以來,雙邊農產品貿易快速發展,為促進雙邊農業經貿全面合作奠定了扎實基礎。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已共同決定,2023年為“中國—東盟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合作年”,將為進一步深化雙邊農業合作創造新機遇。作為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協定,研判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實施對中國宏觀經濟和農業發展的效應,對中國農業政策和自貿協定農業談判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始于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分別于2004年、2007年和2009年簽署《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和《投資協議》,并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為進一步促進雙邊經貿合作,雙方于2015年11月22日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關于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書》,并于2019年10月22日對所有協定成員全面生效。
目前,多位學者對自貿協定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分析,以宏觀層面[1-3]和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4-6]的研究為主。針對農業視角下自貿協定的影響,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對自貿協定的農業經濟效應進行了預判和評估。劉藝卓等[7]預判了中韓自貿協定實施對中國農業的影響。王艷枝[8]采用引力模型測算了中澳自貿協定對中國乳制品進口的影響。劉芳菲[9]分析了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對日本農業的影響。蔡海龍等[10]通過GTAP模型測算了TPP對中國農業的影響。王妍霏[11]分析了中國自新西蘭農產品進口格局與自貿協定升級的關系。總體來看,現有研究為中國自貿協定農業談判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建議,但目前對自貿協定的研究對象多以全行業為主,且以定性研究為主,在農業領域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將根據中國—東盟自貿協定農產品降稅進程,梳理雙方農產品降稅模式和自由化水平,對比分析自貿協定實施后雙邊農產品貿易變化情況,采用引力模型,從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檢驗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對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并提出相關建議。
二、協定實施前后農產品降稅及貿易情況
(一)農產品降稅情況
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是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協定,雙方在農業領域均做出了較大的開放承諾。
一是貨物貿易分階段進行降稅,所有農產品減讓已于2020年全部完成。2003年中國—東盟完成早期收獲計劃談判,所涉產品自2004年起開始降稅,范圍主要包括稅則第1—8章的農產品,如畜產品、水產品、乳品、果蔬等。從東盟內部看,泰國等6個老成員國早期收獲產品截至2006年全部降為零,越南等4個新成員國享受更長過渡期,最遲于2010年全部降為零。2005年起正式實施《中國—東盟貨物貿易協定》,將產品分成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大類,正常產品最終降為零,敏感產品最終不需要實現零關稅,目前貨物降稅安排所有已于2020年執行完畢。
二是農產品降稅是雙方農業領域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東盟協定項下,中方做出巨大農產品關稅減讓承諾,其中小麥、大米和玉米部分稅號2015年降至50%以下;黑麥、大麥、燕麥等谷物2009年降為零;麥芽、玉米淀粉、面筋等谷物制品2010年降為零;未梳棉花2018年降至5%;大豆、油菜籽、葵花油等2009年降為零;花生、葵花籽、芝麻、花生油、橄欖油等2010年降為零。這也是中國首次在自貿協定中涉及關稅配額產品的關稅削減。東盟成員同樣對其敏感產品做出減讓承諾,如泰國對其稻谷、大米、煙草、咖啡等高度敏感產品的關稅2015年降至50%以下,印度尼西亞等其煙草等一般敏感產品2018年降至5%以下,菲律賓對其食糖等高度敏感產品2015年降至50%以下,越南對其糙米等一般敏感產品2020年降至5%以下。
三是總體上雙方農產品減讓較為平衡,基本實現互利互惠。根據協定安排,中方94.5%的農產品稅目針對東盟實現零關稅,包括東盟有極大出口利益的榴蓮、香蕉、荔枝等熱作農產品;東盟成員中,新加坡100%取消農產品關稅,印尼、馬來西亞等成員95%的農產品稅目對華取消關稅,其余成員80%以上的農產品稅目對華取消關稅,包括鮮蘋果、鮮葡萄、鮮梨、蘑菇、洋蔥、魷魚等我方有商業利益的產品。盡管在貨物降稅方面,中國給予東盟較多照顧,多降、快降,東盟國家少降、晚降,但從農產品貿易發展實際效應看,基本實現了雙向平衡和互惠互利。

表1 中國—東盟國家敏感產品數目及主要產品
(二)農產品貿易變化情況
東盟成員多為傳統農業經濟國家,自然資源充裕,優勢特色顯著,農產品貿易是中國與東盟雙邊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2017年,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額首次超過美國躍居第一位,雙方互為彼此最重要的農產品貿易伙伴。
一是農產品貿易規模迅速增長。2004—2022年,雙邊農產品貿易總額從58.3億美元增至610.3億美元,年均增速13.9%,高于同期中國對全球11%的平均水平。中國對東盟農產品出口從21.2億美元增至240.6億美元,進口從37.1億美元增至369.8億美元,年均增速分別達14.5%和13.6%,出口增速高于進口增速。2013年,東盟超越日本穩居中國農產品出口市場首位。2022年,東盟是中國農產品第一大出口市場,同時也是第三大進口來源地,僅次于巴西和美國。
二是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自早期收獲計劃實施以來,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快速發展,中國一般處于逆差,逆差額約為20—40億美元。近年來,在國內需求增長推動下,中國自東盟農產品進口迅猛增長,特別是木薯、大米、香蕉等進口量增長較快,逆差額迅速擴大。2021年逆差達到99.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倍。2022年逆差繼續擴大,突破百億美元大關,達到創紀錄的129.2億美元,增長29.7%。
三是雙方在農產品貿易產品結構上實現互補。中國對東盟出口主要是水產品、蔬菜和溫帶水果,進口主要是熱帶水果、木薯等,產品間的互補性對豐富雙方市場供給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東盟出口以水產品(墨魚及魷魚、鯖魚、金槍魚等)、蔬菜(蘑菇、大蒜、木耳等)、溫帶水果(葡萄、蘋果、柑桔、梨等)等為主,2022年出口額分別為54.9億美元、52.8億美元和33.4億美元,占對東盟出口總額的22.8%、21.9%和13.8%。自東盟進口以熱帶水果(榴蓮、山竹、香蕉等)、水產品(對蝦、鯰魚等)和棕櫚油為主,進口額分別為94.4億美元、45.2億美元和40億美元,占自東盟進口總額的25.5%、12.2%和10.8%。
四是中國與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四國貿易占比超85%。從進口看,2022年自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農產品進口額分別為125.9億美元、103.7億美元、60.9億美元、38.9億美元,占比分別為34%、28%、16%、10.5%,在中國進口來源地中分列第3、第6、第10和第15位。自泰國進口僅次于巴西和美國,主要產品為榴蓮、木薯、番石榴、芒果等。從出口看,對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出口額分別為59.1億美元、54.1億美元、48.9億美元、28.4億美元,占比分別為24.5%、22.5%、20%、11.8%,在中國出口市場中分列第5、第6、第7和第9位。
三、協定的農產品貿易效應評估
(一)模型選擇
借鑒現有文獻對貿易效應評估的相關研究,本文采用引力模型,選擇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出口金額作為因變量,農產品關稅、各國GDP、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運輸成本以及匯率等為自變量,從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檢驗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對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關系模型構建如下:
進口模型:
lnimpit=α+β1lntcct+β2lnGDPit+β3lndisit+β4lnexrit+μi+θt+εit
出口模型:
lnexpit=γ+λ1lntcit+λ2lnGDPit+λ3lndisit+λ4lnexrit+μi+θt+εit
其中,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lnimpit和lnexpit為被解釋變量,分別用以表示中國自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貿易水平和中國向東盟國家農產品出口貿易水平;lntcct和lntcit為核心解釋變量,分別表示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和中國出口東盟國家農產品關稅水平;lnGDPit表示各國經濟發展規模;lndisit為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的運輸成本;lnexrit表示各國貨幣兌美元匯率水平。此外,α、γ為常數項;μi為國家固定效應;θ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由于雙邊貿易結構反映了基于各國比較優勢的國際勞動分工,經濟規模是影響雙邊貿易的核心要素,而物理距離的遠近反映了對雙邊貿易交流阻礙作用強弱,決定著貿易過程中的成本費用。為進一步研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框架下,經濟規模、運輸成本等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創造效應的影響作用,本文在進一步研究中加入了GDP規模差異、地理距離等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農產品關稅以及各控制變量之間的交乘項對相關預期進行檢驗。
(二)變量的選取
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是中國第一個簽署的多邊自貿協定,2002年啟動并開始大福下調關稅,綜合考慮數據樣本的充分性,本文選取1995-2021年中國和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緬甸、老撾、柬埔寨、文萊等10個東盟國家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其中,lnimpit和lnexpit分別在進口模型和出口模型中表示t年中國自東盟國家i進口的農產品貿易額的對數和t年中國向東盟國家i出口的農產品貿易額的對數,為容納進出口額為零的狀態,根據學界普遍采用的做法,在原始進出口基礎數據的基礎上加1再取對數;lntcct表示t年中國農產品的平均進口關稅稅率的對數,lntcit表示t年中國農產品出口東盟國家i的平均關稅稅率的對數,同樣為容納進口關稅稅率為零的狀態,在原始關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加1再取對數;lnGDPit表示t年國家i的GDP規模的對數;lnexrit表示t年i國貨幣兌美元匯率的對數;lndisit表示i國與中國雙邊貿易的運輸成本,在相關的研究中通常采用各國首都的直線距離來計算兩國的地理距離用以表示運輸成本,但考慮到該指標不隨時間而發生變化,為消除模型模擬中的共線性問題,在數據處理過程中采用實際地理距離與當年國際油價的乘積表示兩國的地理距離,更好的反應兩國間的貿易運輸成本。
(三)數據來源及樣本描述性統計
在本文采用的數據中,中國自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額和中國對東盟國家農產品出口額來自中國海關統計數據;中國和東盟國家農產品關稅相關數據根據WTO《世界關稅概況》及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文本測算;各國GDP規模、各國貨幣對美元匯率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此外,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運輸成本采用實際地理距離和當年石油價格測算,其中,地理距離采用CEPII數據庫中兩國主要城市人口與距離的加權距離,石油價格采用WTI原油期貨歷年數據。表3列示了本文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中國與東盟各國農產品進出口額、各國GDP規模水平、關稅水平、各國貨幣對美元匯率、各國與中國的運輸成本等指標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值均較大,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情況及相關的資源稟賦并不平衡。

表2 變量的定義及說明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1.貿易創造效應
本文分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和固定效應模型來檢驗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實施帶來的分階段關稅減讓對中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流量的影響。表4列示了進口模型的回歸結果,其中(1)為POLS的回歸結果,未對國別個體效應進行控制,結果顯示,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在1%的水平下顯著,符號為負,說明在控制物流成本、GDP規模水平、匯率等因素的條件下,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與中國自東盟國家進口農產品金額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隨著關稅水平逐漸下滑,中國自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額增長明顯。(2)-(5)均為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對國別個體效應進行控制。模型(2)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的回歸結果,(3)-(5)中依次加入物流成本、GDP規模水平和匯率水平等控制變量,回歸結果顯示,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系數顯著為負,始終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多數控制變量的顯著性水平良好,除物流成本外,GDP規模、匯率水平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可以看出,中國和東盟國家簽署和實施自由貿易協定,隨著分階段的關稅減讓逐步深入,關稅水平不斷下滑,中國自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顯著增長,關稅每下降1%,中國自東盟國家的農產品進口額上漲1.022%。

表4 進口模型回歸結果
表5列示了出口模型的回歸結果,其中(1)為POLS的回歸結果,未對國別個體效應進行控制,結果顯示,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在1%的水平下顯著,符號為負,說明在控制物流成本、GDP規模水平、匯率等因素的條件下,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與中國向東盟國家出口農產品金額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隨著關稅水平逐漸下滑,中國向東盟國家出口的農產品金額增長明顯。(2)-(5)均為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對國別個體效應進行控制。模型(2)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的回歸結果,(3)-(5)中依次加入物流成本、GDP規模水平和匯率水平等控制變量,回歸結果顯示,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系數顯著為負,始終在1%的水平下顯著;控制變量中GDP規模水平在1%的水平下顯著,各國貨幣兌美元匯率水平在5%的水平下顯著,東盟各國與中國的距離在10%的水平顯著,模擬效果良好。與進口模型的趨勢相同,中國和東盟國家簽署和實施自由貿易協定,隨著分階段的關稅減讓逐步深入,關稅水平不斷下滑,促進了中國向東盟國家出口農產品,關稅每下降1%,中國自東盟國家的農產品進口額上漲0.312%。
對比進口模型和出口模型可以發現,進口模型中,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的預期系數為-1.022,而在出口模型中,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的預期系數為-0.312,說明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簽署和生效后,相比于中國農產品出口,關稅減讓對農產品進口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這與韓劍等[12]和魏景賦等[13]的研究類似,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國較為早期的政策出口導向性更強,農產品出口基數大,因此在簽訂和實施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后,關稅減讓對農產品進口產生的貿易效應大于對促進出口的相對作用;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漸深化,中國貿易政策逐漸由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轉變為進出口雙向平衡政策,既鼓勵出口,也鼓勵進口,因此對農產品進口的需求顯著增加也是農產品進口效益大于出口效應的主要原因。
2.經濟規模
經濟規模是雙邊貿易的核心要素,國內外已有研究普遍支持貿易雙方的經濟規模對于雙邊貿易由正向影響,當其他條件保持不變時,兩國的經濟規模越大,雙邊貿易也更大。例如吳丹[14]利用引力模型,對東亞幾個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數據進行檢驗,研究顯示,貿易伙伴國經濟規模及國家間的經濟水平差距是東亞雙邊貿易流量的主要影響因素。
為進一步檢驗中國東盟國家經濟規模差異對雙邊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效應,分別在進口模型和出口模型中加入中國和東盟國家GDP規模的差值的對數與關稅水平、匯率水平和運輸成本的交互項。表6列示了經濟規模差異對中國自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貿易的影響效應,回歸結果顯示,加入中國和東盟國家GDP規模的差值水平與中國農產品關稅水平的交互項以及中國和東盟國家GDP規模的差值水平與東盟各國匯率水平的交互項后,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東盟國家GDP規模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同時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中國進口農產品關稅減讓能顯著提升中國自東盟國家的農產品進出額,且當東盟國家與中國經濟規模差值相對較小時,這種促進效應有所增長。

表6 經濟規模差異對中國自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貿易的影響效應
同樣,在出口模型中,如表7所示,加入中國和東盟國家GDP規模的差值水平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的交互項后,各國關稅水平系數顯著為負,東盟國家GDP規模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同時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東盟各國農產品關稅減讓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促進作用在經濟規模與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更為顯著。

表7 經濟規模差異對中國出口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效應
3.運輸成本
物理距離成為雙邊貿易的研究范疇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Tinbergen將引力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的研究中,為進一步檢驗運輸成本對中國—東盟雙邊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效應,分別在進口模型和出口模型中加入中國和東盟國家運輸成本與關稅水平、匯率水平和運輸成本的交互項。
表8列示了運輸成本對中國進口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效應,模型(1)中加入中國和東盟國家運輸成本與中國農產品關稅水平的交互項后,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中國與東盟國家運輸成本系數顯著為負,同時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東盟國家進口農產品關稅減讓能顯著提升中國自東盟國家的農產品進出額,且當東盟國家與中國運輸成本相對較小時,這種促進效應有所增長。模型(2)中加入中國和東盟國家運輸成本與東盟經濟規模水平的交互項后,東盟國家經濟規模水平系數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運輸成本系數均顯著為負,同時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運輸成本的增加將抵消掉部分因關稅減讓而帶來的進口貿易促進作用。同樣,如表9所示,出口模型也呈現出相似的回歸結果,說明不論在中國—東盟農產品進口還是出口貿易中,關稅減讓對貿易的促進作用會隨著運輸成本的增加而減弱。

表8 運輸成本對中國進口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效應

表9 運輸成本對中國出口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效應
(五)研究結論
本文采用1995-2021年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數據,對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框架下的農產品關稅減讓帶來的貿易促進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檢驗了經濟規模差距和運輸成本對貿易促進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的簽署和實施后,農產品關稅減讓的分階段實施對促進中國和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對進口的促進作用大于出口。同時,從經濟規模來看,在東盟國家中,與中國經濟規模差距較小的國家,自貿協定對農產品的貿易促進效果更為顯著;從運輸成本來看,與中國距離較遠的國家,運輸成本將對雙邊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產生抑制作用從而降低自貿協定對農產品貿易的促進效應。
四、相關政策建議
在國際地區形勢深刻復雜演變的大國博弈背景下,東盟始終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和“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應繼續以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為抓手,促進雙邊農業經貿合作,為推進鄉村振興、建設農業強國、實現共同富裕以及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做出農業貢獻。
第一,以自貿區升級為契機,促進雙邊農業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全面積極參與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農業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談判,優化農產品原產地規則程序,提升農業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促進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深層次融合;探討參與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等涉農新規則領域以及糧食安全合作相關議題談判,加強與東盟在數字農業、綠色發展等方面的合作。同時,以廣西和云南自貿試驗區為重點,推動與東盟在農業領域的開放合作,優化農產品通關和檢驗檢疫流程,促進農產品邊境貿易發展,鼓勵打造跨境農業產業鏈。
第二,利用RCEP開放機遇,擴大雙邊農產品貿易效應。雖然在中國—東盟自貿協定項下,雙方在農產品貨物貿易降稅方面,已經實現了90%以上的自由化水平。但在RCEP項下,雙方的農產品自由化水平進一步提升。例如,中方將對東盟的未磨胡椒、菠蘿汁、椰子汁等農產品在RCEP下進一步取消關稅。雙方企業可比較RCEP和中國—東盟自貿協定項下農產品關稅稅率,選擇最優惠稅率進行貿易,這將進一步擴大自貿協定的貿易創造和轉移效應。同時,應指導企業充分利用RCEP項下的區域累積原產地規則,促進中國和東盟各國抱團將農產品出口至日韓等重要市場,構建完整和穩定的農業產業供應鏈。
第三,依托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促進與東盟農業互聯互通。距離是影響中國與東盟各國農產品貿易的重要因素。中國西部省區農業資源豐富,但由于大部分西部省區距離出海口較遠也不與東盟各國陸路接壤,制約了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發展。因此,應以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建設為契機,積極推動通道農產品跨境直通車試點工作,加大與東盟國家熱帶水果種植園、生鮮產地物流中心的冷鏈運輸銜接,支持特色生態農產品借助全程通道冷鏈運輸,降低農產品損害率,并借助數字技術提升通過效率,發揮通道對沿線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及農業對外開放的帶動作用。
第四,促進農業雙向投資,擴大雙方農產品需求空間。對外投資方面,鼓勵企業充分利用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升級版以及RCEP中的相關投資優惠條款,圍繞種植、養殖、深加工、農產品物流等領域到東盟投資,幫助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東盟國家提高農產品產量和經濟發展水平,間接擴大農產品貿易空間;建議探討建立東盟國家重點國別項目信息庫和企業庫,圍繞重點合作國家和領域,加強重點項目的收集與跟進,進行項目對接。利用外資方面,鼓勵引進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發達農業技術,借鑒其在三產融合方面的經驗做法,引導其流向中西部地區,帶動當地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村環境改善,助力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