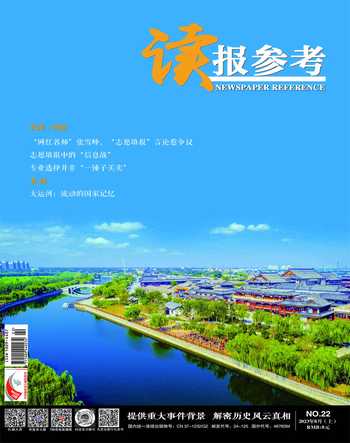志愿填報中的“信息戰”
盡管“張雪峰式”填報志愿的邏輯和方法,難以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但他的存在并非偶然。記者在張雪峰的直播間里,找到了一些考生和家長。對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來說,填志愿是一場“自己不懂,也沒人教”,但又絕對不能落后于人的另一場大考。困惑與迷茫令他們點進了直播間,希冀從中獲得一條普通人能走得好的人生之路。
火爆的直播間
網絡上流傳的一則視頻里,張雪峰舉著話筒演講,以他一貫激情的狀態號稱“志愿填好了,能夠彌補50分的差距”。隨后,他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通過選擇合適的專業,少考50分的人在畢業后能與分數高出50分到100分的同齡人獲得同樣的工作機會。 這段話基本上解釋了張雪峰火爆的原因。在他的填報邏輯里,從志愿出發,略去學習過程、性格成長、能力發展等諸多環節,直奔主題——工作,或者再直白一些,掙錢。
諸多直播間連線的片段,被剪輯成短視頻在互聯網上傳播,也因此誕生了類似“家里沒有企業要管理的別報管理”“家里沒有資源的別報金融”等諸多“名場面”。
盡管這些言論看似荒誕不經,但不乏有人對張雪峰的直播間趨之若鶩。對許多填報志愿能力近乎為零的家長來說,張雪峰的直播間是他們可觸及的信息資源極限。
38歲的刈水人在直播間評論區提問:“孩子只考了400分,怎么選才能上本科?”直播間的評論如奔涌潮水,他的留言很快沉底不見。但他并不氣餒,在輸入框重新鍵入相同的問題,再次發送,期待被選中答復。刈水人來自河南南陽,孩子所在的班級人數多,自己的孩子成績一般,“老師更多是幫好學生作志愿填報解答”。
相比之下,方向明確的陜西考生周鴻偉從容不少。與父母商量后,周鴻偉決定報考醫科。一方面工作穩定,還能照顧家人;另一方面家族中有親戚從事醫生這個職業,或許能幫忙指導。但他依舊會去張雪峰的直播間尋找更多信息。
從高一開始,周鴻偉就關注到張雪峰講的高考志愿填報。 他認為,在張雪峰的直播間一定能挖到有效信息。比如,以醫科為例,張雪峰曾在直播中建議成績只夠二本的考生,在選擇醫科時盡量避免“臨床醫學”,而是要另辟蹊徑選擇“影像學”等醫學技術學科,邏輯是二本院校的臨床醫學學生,比得過985/211等大學培養的臨床醫學學生嗎? 周鴻偉覺得此話有理,高考成績還沒出分,全家就一致決定,如果上不了一本,“影像學”會成為首選。
缺失的信源
并非所有考生都像周鴻偉這樣,在專業選擇上早有準備。
河南考生林星感覺,自己是被突然“踢”上志愿填報“戰場”的。新買的《河南招生考試之友》參考書厚厚一沓,面對海量的院校專業,她毫無頭緒。
“高中三年從來沒想過這些,書里面很多專業,我聽都沒聽說過,真的填不出。”林星說。她記得,高三課間老師偶爾會問,你以后想干什么。那時,她要先把思緒從作業本里抽出來,再飄向更遠處的“夢想”。大多數時候,沒等思緒抵達,老師就緊皺眉頭,算了別想了,還是先做作業吧。
林星聽別人提到最多的專業,是近幾年很熱門的“計算機”,但這些專業是什么、要怎么學、畢業后能干什么?高考結束至今,林星每天都在各大短視頻及咨詢App之間反復切換。
起初,這些渠道有些幫助。林星記得張雪峰在直播間講過,家庭條件普通的考生不要選擇管理類專業,她便在志愿書上將這一欄劃去。但減法無法一直做,填報志愿時間節點在即,林星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張雪峰直播間這樣的志愿填報規劃服務成了“救命稻草”。
高考放榜后,林星在張雪峰的抖音評論區留言了自己的成績跟需求,沒想到得到了幾十個網友的關注跟回復。“他們給我推薦了院校跟專業,還幫我分析了這個專業就業的前景。我覺得那些網友也很真誠,而且這些建議都是不收費的。”
作為互聯網原住民,“00后”學生們消弭信息差的能力已經比上一輩強很多。但在欠發達地區,數字鴻溝依然橫亙在城鄉之間,復雜多樣的社會環境、日益激烈的學歷競爭以及瞬息萬變的行業動向,常常難以抵達處于信息接收末端的考生們。
掙扎在信息差里的網友們互幫互助,是社交媒體評論區里的常態。有時候“張雪峰”似乎成了一個暗號,考生和家長們舉起填報志愿的求助牌,就會有千萬個“張雪峰” 們前來引路。
根據“企查查”數據顯示,2023年國內有關“高考志愿填報咨詢”的企業超2600家。自2016年起,全國填報志愿相關企業數量逐年攀升,年增量在100家以上,近3年增速尤為迅猛。其中,2021年國內相關機構增量超740家,為近10年來的高峰。
生活的不確定性
志愿填報規劃師或許能在當下給一個看似合理的最優解,但誰能超越時間,預判這個世界的未來走向呢?
來自江西的謝薇在張雪峰的直播間里為今年高考的妹妹打探消息。這是她第二次參加志愿填報,上次是5年前自己高考的時候。她稱,那場志愿填報是“不幸中的萬幸”——幸運是成功被省內的一所一本大學錄取,代價是從第一志愿醫科滑檔調劑到張雪峰口中的“天坑”專業——環境科學。
然而,畢業一年后,她覺得這個所謂的“天坑”,好像并沒有張雪峰說得那么“坑”。比如,她發現在考公時,對應的崗位并不少。同時,因為大家都對環境學避之不及,導致報考同一崗位的人數相較熱門專業崗位少了很多,競爭壓力隨之減小,“也算是一個優勢”。此外,謝薇察覺到,很多所謂熱門專業畢業生的出路,也沒有像網上說得那么好。
盡管“張雪峰式”的志愿規劃服務依舊火熱,但許多人依然會選擇相信身邊人的建議。
高考出分后,比一本線高了79分的周鴻偉決定報考省內某大學的臨床醫學五年制專業。他打電話給學校招生辦問過,知道這個專業未來要考研,學校每年的考研上線率超過50%。他還咨詢了當骨科醫生的三叔,對方表示,在西安,該院校臨床醫學專業的就業形勢挺不錯。
“雖然張雪峰講得有一定道理,但每個地區的情況不同,也不能全部照搬。還是以自身情況為主,多問問身邊前輩的意見吧。”周鴻偉說。
盡管張雪峰在直播間多次強調大學所選的專業與未來就業的強掛鉤性,但現實生活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看似清晰的志愿規劃路徑,常常遭遇“失效時刻”。
2018年,河南考生王瑩瑩報考了華東地區某所985大學的法語專業。4年后,她成了上海一家法國獵頭企業的員工。現在回看,她確信自己在填報高考志愿時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沒考慮該專業在時代大背景下的供求關系,也沒考慮未來是否要考研、出國,或是抓緊時間輔修一門其他專業。如果再給一次機會,王瑩瑩會填報會計或者法律等專業性強一些的專業。
不過,她并不后悔。“我不可能先拿到正確答案再去選擇過什么生活。時代一直在變,沒有永遠的鐵飯碗。誰也不知道這輩子會經歷什么,真正永恒的抗風險的技能又是什么。”王瑩瑩說。
(應受訪者要求,皆為化名)
(摘自《解放日報》沈思怡、李楚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