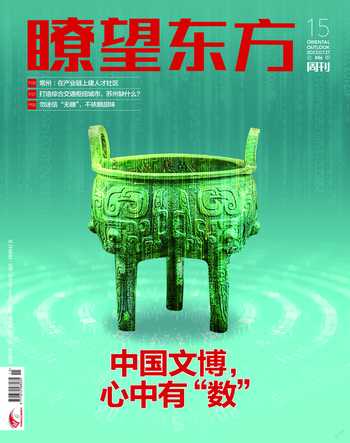烏爾善:娛樂電影也要注重文化尋根
劉佳璇 呂佳心

《封神第一部》饕餮追襲場景海報
無論是對電影導演烏爾善而言,還是對整個中國電影市場而言,《封神三部曲》的創作過程可謂“慢功出細活”。
距離上一部作品《尋龍訣》上映已過去近8年的時間,51歲的烏爾善把電影導演創作生涯中的近十年都投入在了《封神三部曲》上。
這個以《封神演義》故事為題材的系列電影項目,于2014年開始籌備,2018年開啟為期一年半的三部連拍。2023年,《封神第一部》終于在7月20日上映。
“電影化手段和當代的文化內容中有很多東西都是外來的,中國創作者的文化根源到底是什么?我們的文化傳統里有哪些具有當代價值的東西可以分享?”在與《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對談時,“傳統”成為了烏爾善提及最多的詞語,在《封神三部曲》這場前所未有的電影實踐中,他完成了一次將傳統文化基因注入神話史詩電影的表達。
美國學者約瑟夫·坎貝爾說:“夢是私人的神話,而神話是公眾的夢境。”封神故事是中華民族一個公開的夢境,它表現了中華民族最核心、最獨特的情感,那就是親情和倫理。
在文化土壤上再創造
《瞭望東方周刊》:成書于明朝的《封神演義》是《封神三部曲》的主要故事母本之一,從文學文本到電影,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烏爾善:改編《封神演義》,既要了解文本的核心價值、歷史作用,也要在改編中體現出當代價值。
首先,在項目開發階段,對原著進行明確的分析定位。2014年6月第一次開策劃會時,我們邀請了民俗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學者,挖掘《封神演義》的原著價值。這部小說講述殷商時期的故事,將中國的道教神祇和民間諸神整合,形成中華民族的神仙體系。所以說,其文化價值遠高于文學價值。
其次,改編過程中,要體現出當代價值理念。我們不可能去重復明代的一些價值觀,比如原著中的宿命論觀念。我們需要找到故事的情感核心主題,而這個主題要能引起當代共鳴。
除了《封神演義》,我們也梳理了其他重要文本,比如《列國志傳》《武王伐紂平話》,以及《史記》《尚書》對相關歷史的描寫,最終整理出兩方面的核心元素:一是商周歷史;二是神話的想象世界。
最后,把這些元素進行電影化整理,寫作劇本。原著故事基本結構分為三大段落,所以可以使用三部曲電影結構,但三部曲既要獨立成片,也要形成完整敘事,這是一個巨大挑戰。
劇本寫作耗時四五年,重點是整合元素,找到能貫穿三部曲的核心人物和戲劇沖突。武王伐紂、天下歸周,符合正義戰勝邪惡的英雄史詩主題,也是改編劇情的核心內容。
《瞭望東方周刊》:《封神三部曲》屬于幻想類電影,對這類電影來說,構建一個自成體系的美學世界至關重要,《封神三部曲》是怎么做的?
烏爾善:我大學是學油畫的,對中國藝術史中經典的幾個文化藝術巔峰時期很熟悉,我希望能把這些時期的視覺美學運用進來。
中國的文化藝術史是非常精彩的,但中國人了解得太少。在項目籌備階段,我們做了大量創作考察,去了河南、陜西、山西的博物館和研究所調研,分別對應殷商、周朝和元明道教藝術。總之,盡量讓所有東西都有依據。
最后呈現的細節要做到逼真,讓觀眾能進入并相信情境。它只屬于這個電影中的神話世界,與真實歷史是不同的。但創造要基于經典,而不是胡來,回到中國藝術的精髓里去找靈感,再把它變成電影創作結果。
人物造型參考元明道教藝術的造型體系,自然環境參照宋人青綠山水,紋樣圖形則來源于殷商青銅紋飾……將橫跨3000年的幾個歷史視覺元素重組,形成“封神世界”中視覺元素的細節,打造高度凝練、重新組合出的神話世界。
觸及中華民族情感核心
《瞭望東方周刊》:每個人對于封神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想象,是否擔心電影對于人物的再創作給觀眾帶來落差感??
烏爾善:大家腦中的傳統形象,來自于影視劇、動畫片、小人書等,都是基于后人的再創作。
比如紂王,他的故事形象長期被嚴重扁平化,是一個沉迷酒色、滿身橫肉的昏君。實際上,《荀子·非相》形容他“長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史記》說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紂王本是一個高大威猛的統帥、能言善辯的君主,這才能構成一個真正有力量、對主角有威脅的反派。
再如,元始天尊在很多影視劇里被演繹成一個“老神仙”,但在道教藝術中,其形象其實是黑須長髯、仙風道骨的中年人。
總之,我們希望《封神三部曲》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正本清源。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是有些陌生的,封神故事是一個中華民族先祖創業的經典故事,我們應該通過電影傳播一些有關自身文化傳承、文化特點的信息。
《瞭望東方周刊》:在《封神三部曲》籌備階段接受本刊采訪時,你曾說神話史詩講述的是一個民族的心理現實,你認為封神故事表達的民族心理現實是什么??
烏爾善:美國學者約瑟夫·坎貝爾說:“夢是私人的神話,而神話是公眾的夢境。”封神故事是中華民族一個公開的夢境,它表現了中華民族最核心、最獨特的情感,那就是親情和倫理。
商周之變的歷程,是把殷商時期方國部落聯盟體系破壞掉,變為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分封制,本質是以家族血脈、親情倫理為紐帶對國家制度進行重建。“天子”之稱,就是用家庭倫理關系界定人與自然的關系。
家庭倫理、血脈親情,至今都是中國社會結構、中華民族情感結構的核心。作為神話史詩,封神故事觸及了這個部分,電影改編也由此生發、提煉。
我認為,中國人已經開始從生活富足走向對精神傳統的追溯,想去了解自己文化的核心與特性,想在精神層面尋找中國人的歸屬感。這是文化尋根、確認自己、講述自己的需要。
《瞭望東方周刊》:《封神第一部》的敘事內核或情感主題是怎樣的?
烏爾善:三部曲總體的核心主題是善惡斗爭、英雄成長、時代變革,這都是電影敘事的經典主題。但是在單部中,需要找到能跟當代觀眾產生情感共鳴的部分。
寫劇本時我設想,如果沒有任何視覺包裝和大場面,最終觀眾還會關注誰。
“文王食子”讓我印象很深,姬昌為了保護次子姬發而吃掉了長子伯邑考的肉,這是正常情境下一個父親不可能做的事,給人的情感沖擊非常強烈。另外,紂王之子殷郊在母親被妲己害死后站在父親的對立面,此后他又回到父親身邊成為捍衛者,也構成很有張力的人物關系。
在第一部的故事里,父子關系、親情主題就是核心。圍繞姬昌與姬發、紂王與殷郊兩對父子展開故事。另外,我們把姬發放到紂王身邊,讓姬發從紂王的崇拜者變為反抗者,用反轉來闡述一個青年的人生道路選擇問題。這讓故事具備令人共情的可能性。
電影市場呼喚經典價值
《瞭望東方周刊》:《封神三部曲》體量宏大,你認為它能給中國電影界提供怎樣的新經驗?
烏爾善:“封神”項目的體量與積累的經驗,可以說前所未有。
一是類型拓荒。神話史詩類型觸及歷史、神話、宗教、民間傳說的想象空間等方面,是華語電影極少觸及的類型。
二是三部連拍。無論是三部曲的劇作創作,還是三部連拍的制作難度、周期長度和復雜性,都是空前的。制作周期長、工作量和劇組規模極為龐大,籌備用時兩年,拍攝共18個月、438個拍攝日,劇組管理人數最多超過8000人。我們建構了科學的生產流程和可靠的工作體系,做到有序、安全、高效地拍攝。
三是技術創新。相比場景類特效制作,雷震子、九尾白狐、墨麒麟等有生命的數字角色和數字生物視效的制作難度更高,要能夠表現動態、做出細膩的情感表演,逼真程度要達到電影級。對中國的視覺技術發展來說,這次要上一個新臺階。
《瞭望東方周刊》:從《畫皮Ⅱ》《尋龍訣》到《封神三部曲》,你一直在深耕商業娛樂電影,你認為其理想形態是什么樣的?
烏爾善:我一直想做“電影院的藝術”,因為那是大眾的藝術。我追求的是一種“娛樂電影的最好形態”:從娛樂效果上,它用巨型銀幕帶來聲音、畫面的震撼,充分釋放影院的力量,帶來觀影愉悅;美學形態上,其電影語言表達具備一定影史意義;內在主題上,有清晰的情感主題,有深層的文化表達能力,值得多層面解讀,而不是一個粗淺的娛樂快消品。
《指環王》《星球大戰》等電影,與自身歷史文化背景相連接,與神話、宗教等宏大主題有關聯,又有幻想、動作等元素,這才成為影史上的經典娛樂電影。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中國電影市場的改變和發展有哪些體會?
烏爾善:電影市場的一些變化是我們無法預判的,但我做《封神三部曲》是出于對市場心理的判斷。
我認為,中國人已經開始從生活富足走向對精神傳統的追溯,想去了解自己文化的核心與特性,想在精神層面尋找中國人的歸屬感。這是文化尋根、確認自己、講述自己的需要。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越來越感到自信和自豪,愿意多了解自身文化傳統,也希望通過當代電影重新呈現、解讀這種文化的傳承,更想在電影里看到“我”的文化、“我”的生活、“我”的情感表達。
雖然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早已脫下古裝,但是我們的精神世界仍來自于這片土地久遠的歷史。時間在變、服裝在變,而一個民族的心理和人性的本質并沒有變。中國電影人可以重新去確認那些經典的價值,把來自我們文化根源的美學展現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