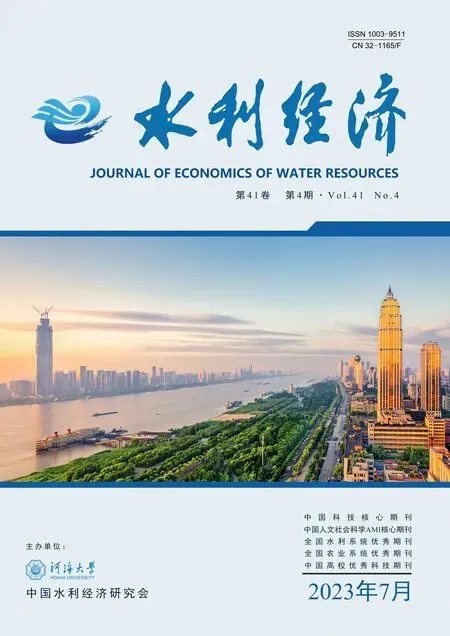河長制對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策略的影響
張 穎,沈奇嶸,劉瀟天
(1.河海大學(xué)商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1100; 2.昆士蘭大學(xué)商學(xué)院,昆士蘭 布里斯班 4702)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jīng)驗的決議》,明確指出我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仍然是一個明顯的短板,資源環(huán)境約束趨緊、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等問題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各類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呈高發(fā)態(tài)勢,成為國土之傷、民生之痛,如果不抓緊扭轉(zhuǎn)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的趨勢,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雖然中央政府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就將環(huán)境保護列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但地方政府出于晉升考核等目的,存在犧牲環(huán)境效益換取經(jīng)濟效益的環(huán)境規(guī)制非完全執(zhí)行行為[1]。2007年太湖藍(lán)藻危機暴發(fā),面對嚴(yán)峻社會壓力的無錫市政府發(fā)布了《無錫市河(湖、庫、蕩、氿)斷面水質(zhì)控制目標(biāo)及考核辦法(試行)》,任命全市各級黨政負(fù)責(zé)人為每條河道的負(fù)責(zé)人,并將治理成效作為政績考核和選拔晉升的重要依據(jù)。河長制的實行激發(fā)了地方政府官員治理水污染的動力和決心,緩解了環(huán)境規(guī)制非完全執(zhí)行的行為,同時在河長的主導(dǎo)下,流域內(nèi)多部門實現(xiàn)了協(xié)同治理,避免了九龍治水的弊端[2]。之后,無錫市的成功經(jīng)驗逐漸推廣至河北子牙河水系、云南滇池水系,并輻射至廣東、山東、浙江等地。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wù)院辦公廳頒布了《關(guān)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指出要全面建立省、市、縣、鄉(xiāng)四級河長體系,標(biāo)志著河長制成為一項國家層面的水污染治理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重工業(yè)、制造業(yè)先行發(fā)展戰(zhàn)略推動了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然而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也帶來了高能耗、高污染問題[3]。黨中央強調(diào),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是關(guān)乎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的根本大計,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保護生產(chǎn)力,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發(fā)展生產(chǎn)力,決不以犧牲環(huán)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jīng)濟增長。重污染企業(yè)作為污染排放的主體,是實現(xiàn)節(jié)能減排和健全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關(guān)鍵。河長制實施后,重污染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壓力上升,可能采取多種措施應(yīng)對外部壓力,如停工減產(chǎn)、環(huán)保投資和綠色轉(zhuǎn)型等[4],而綠色轉(zhuǎn)型可以幫助重污染企業(yè)獲得清潔能源和節(jié)能減排技術(shù),從源頭上解決高能耗、高污染問題,實現(xiàn)經(jīng)濟效益和生態(tài)效益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5]。重污染企業(yè)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xiàn)綠色轉(zhuǎn)型:一種是偏向內(nèi)部研發(fā)的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策略;另一種是偏向外部獲取的綠色并購策略。本文探究了河長制對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產(chǎn)生的影響,以期為未來國家制定和實施環(huán)保政策以促進(jìn)重污染企業(yè)發(fā)展提供參考。
1 文獻(xiàn)綜述
隨著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wù)院辦公廳頒布《關(guān)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學(xué)者們從多個角度對河長制政策的實施效果、擴散模式等進(jìn)行了研究。部分學(xué)者通過對比轄區(qū)內(nèi)水質(zhì)在實施河長制前后的變化,探究了河長制對水污染治理帶來的提升與不足:沈坤榮等[6]研究發(fā)現(xiàn),河長制的實施顯著提升了水中溶解氧的濃度,緩解了水體黑臭問題;She等[7]以長江流域地級市為研究對象,發(fā)現(xiàn)河長制降低了水域中化學(xué)需氧量和氨氮含量,改善了水質(zhì)情況,并當(dāng)城市GDP較高或環(huán)境規(guī)制更為嚴(yán)格時該現(xiàn)象更為明顯;Li等[8]發(fā)現(xiàn),河長制對于不同污染物具有異質(zhì)性影響,河長制實施后酸堿度和氨氮情況明顯改善,但化學(xué)需氧量和溶解氧沒有發(fā)生顯著變化。上述研究均發(fā)現(xiàn)河長制的實施有效改善了水質(zhì)情況,但對于水質(zhì)改善程度觀點不同:沈坤榮等[6]認(rèn)為地方政府存在粉飾性治理行為,僅解決了水體黑臭問題,但并未徹底解決水污染問題。也有學(xué)者從擴散方式、經(jīng)濟收益等方面對河長制的演進(jìn)進(jìn)行了探討。王班班等[9]將河長制擴散模式劃分為平行擴散模式和向上擴散模式,結(jié)果顯示兩種模式在經(jīng)濟效益與治污效果之間有所取舍,平行擴散模式下地區(qū)政府犧牲了較少的經(jīng)濟收益,但治污效果不佳;而向上擴散模式下治污效果良好,卻需要付出較大的經(jīng)濟代價。除擴散模式外,官員特征也被證實是河長制推行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年輕官員為更快晉升看重經(jīng)濟利益,缺乏推行河長制的動力;年長官員晉升概率下降,出于避免上級問責(zé)的目的,更傾向于推行河長制[10]。此外,李強[11]根據(jù)長江經(jīng)濟帶市級面板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河長制通過增強地區(qū)環(huán)境規(guī)制強度,促進(jìn)了城市產(chǎn)業(yè)升級。
重污染企業(yè)是污染排放的源頭,也是地方政府污染治理中的重點關(guān)注對象,政府希望通過環(huán)境規(guī)制促進(jìn)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實現(xiàn)節(jié)能減排,從根源上解決污染問題。近年來學(xué)術(shù)界已經(jīng)針對綠色轉(zhuǎn)型的兩種重要策略——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策略和綠色并購策略進(jìn)行了充分探討。根據(jù)波特假說,適當(dāng)?shù)沫h(huán)境規(guī)制可以促進(jìn)企業(yè)R&D投入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實現(xiàn)企業(yè)治污能力和產(chǎn)品科技含量雙提升,并緩解規(guī)制對企業(yè)帶來的不利影響[12]。在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下,關(guān)于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的關(guān)系,頡茂華等[13-14]認(rèn)為二者顯著正相關(guān),即環(huán)境規(guī)制有助于促進(jìn)重污染企業(yè)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也有研究證明,二者之間存在非線性的U型和門檻效應(yīng),即只有當(dāng)環(huán)境規(guī)制達(dá)到一定強度,才會對重污染企業(yè)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產(chǎn)生正面影響[15-16]。上述研究中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污染治理水平計算而來,概括了重污染企業(yè)所在區(qū)域內(nèi)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強度。
也有研究從具體環(huán)保政策入手,利用差分模型,評價了單一政策對重污染企業(yè)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造成的影響。如齊紹洲等[17]發(fā)現(xiàn),排污權(quán)交易試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誘發(fā)企業(yè)整體層面的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也有學(xué)者研究了企業(yè)社會責(zé)任強制披露[18]和低碳城市[19-20]對企業(yè)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影響,結(jié)果證明二者均會帶來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
與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相比,有關(guān)環(huán)境規(guī)制與企業(yè)綠色并購的研究相對較少。邱金龍等[21]探究了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企業(yè)綠色并購的影響,發(fā)現(xiàn)市場激勵型環(huán)境規(guī)制與企業(yè)綠色并購呈倒 U型關(guān)系,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企業(yè)綠色并購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除此之外,潘愛玲等[22]發(fā)現(xiàn)由于新上任官員面對的環(huán)境治理壓力較大,會積極開展污染治理工作,所以官員更替有助于推動企業(yè)綠色并購。
綜上所述,現(xiàn)有研究對河長制及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但當(dāng)前有關(guān)河長制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視角展開,缺乏對微觀層面的討論,無法識別河長制對于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行為的影響機理。目前有關(guān)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對于企業(yè)綠色并購的討論較少,鮮見考慮重污染企業(yè)面對多種綠色轉(zhuǎn)型策略時的選擇偏好問題。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策略和綠色并購策略二者相互補充,為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利用2008—2019年中國重污染企業(yè)數(shù)據(jù),探討河長制對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策略的影響。
2 機理分析
2.1 河長制與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
河長制將水污染治理與政績考核相掛鉤,地方政府領(lǐng)導(dǎo)干部作為污染治理的負(fù)責(zé)人將受到一定的環(huán)境監(jiān)管壓力。對于地方官員而言,提升水污染治理政績的最好方法是從源頭減少污染物的排放。而企業(yè)作為污染排放主體,排放了80%的環(huán)境污染[23]。為了更好地控制地區(qū)水污染、提升自身政績,地方官員的工作重心會偏向于控制企業(yè)污染排放。而重污染企業(yè)作為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勢必面臨更為嚴(yán)峻的外部環(huán)境壓力。根據(jù)資源依賴?yán)碚?當(dāng)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企業(yè)會采取各種策略改變自身以適應(yīng)環(huán)境變化[24]。而重污染企業(yè)面對河長制實施后日益加重的環(huán)境治理壓力,可供其選擇的應(yīng)對方式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可以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獲取清潔能源和節(jié)能減排技術(shù)以得到長期收益[25];另一方面重污染或產(chǎn)生短期應(yīng)激反應(yīng)造成停工減產(chǎn),消極避免污染產(chǎn)出[26]。與前者相比,停工減產(chǎn)會導(dǎo)致企業(yè)產(chǎn)生巨額沉沒成本,損害股東利益。除非環(huán)境治理壓力嚴(yán)重超出預(yù)期,重污染企業(yè)不會輕易做出停工減產(chǎn)的決策[27]。
a.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具體而言,重污染企業(yè)可以進(jìn)行內(nèi)部技術(shù)創(chuàng)新,通過內(nèi)部研發(fā)獲取清潔能源和節(jié)能減排技術(shù),實現(xiàn)綠色轉(zhuǎn)型。雖然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可以同時兼顧經(jīng)濟效益和環(huán)境效益,但其具有投資周期長、收益率偏低等缺陷。重污染企業(yè)在進(jìn)行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但投入產(chǎn)出之間卻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后效應(yīng),同時研發(fā)過程中還伴隨一定的沉沒成本,致使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不確定性上升[27]。隨著我國并購市場規(guī)模逐漸擴大,重污染企業(yè)愈多通過綠色并購實現(xiàn)綠色轉(zhuǎn)型。
b.綠色并購。與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不同,企業(yè)綠色并購[28]通過獲取標(biāo)的企業(yè)的清潔能源和節(jié)能減排技術(shù)實現(xiàn)轉(zhuǎn)型,而非內(nèi)部研發(fā),使得企業(yè)綠色并購具備了一定的速度優(yōu)勢[21,29]。同時,在河長制實施后,各級政府均向外界明確公布了各級河長清單與污染檢舉渠道,使得水污染治理成為一項大眾參與的活動。重污染企業(yè)面對來自政府、群眾的雙重外部監(jiān)管壓力,勢必急于向外界傳遞綠色轉(zhuǎn)型信息、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可是,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難以為外部利益相關(guān)者所知曉,即便重污染企業(yè)投入大量資源用以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也無法快速向外界傳遞信息[30]。與默默無聞的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相比,企業(yè)綠色并購可能更符合重污染企業(yè)的需求,因為并購公告可以帶來眼球效應(yīng),迅速向外界傳遞企業(yè)積極履行社會責(zé)任、保護環(huán)境的信號,以緩解外部環(huán)境壓力[27]。
根據(jù)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1受到河長制影響,重污染企業(yè)更傾向于外部獲取策略(綠色并購)而非內(nèi)部研發(fā)策略(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
2.2 河長制對綠色轉(zhuǎn)型的影響機制
河長制之所以可以對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造成影響,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受到環(huán)境績效考核和上級政府問責(zé)的雙重壓力,調(diào)整了重污染企業(yè)的相關(guān)政策,促使企業(yè)通過綠色轉(zhuǎn)型節(jié)能減排,達(dá)到既定目標(biāo)。地方政府作為政策的執(zhí)行者和制定者,具有較大的決定權(quán),可以通過制度支持和制度壓力對企業(yè)造成影響[31-32]。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環(huán)保補償正向引導(dǎo)重污染企業(yè)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由于綠色轉(zhuǎn)型過程中需要企業(yè)投入大量資源,侵占了企業(yè)部分經(jīng)營資源,導(dǎo)致資源約束、綠色轉(zhuǎn)型動力不足[33]。地方政府通過給予環(huán)保補貼沖抵一部分資金投入,緩解了綠色轉(zhuǎn)型對經(jīng)營資源的侵占,使得重污染企業(yè)得以兼顧綠色轉(zhuǎn)型與日常經(jīng)營。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收緊環(huán)境規(guī)制,通過出臺節(jié)能減排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調(diào)整環(huán)境監(jiān)測標(biāo)準(zhǔn)或?qū)ξ廴九欧懦瑯?biāo)企業(yè)進(jìn)行環(huán)保處罰等手段將環(huán)境治理目標(biāo)直接轉(zhuǎn)移至重污染企業(yè),倒逼其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5]。根據(jù)資源依賴?yán)碚?當(dāng)環(huán)境規(guī)制變得日益嚴(yán)格,重污染企業(yè)會做出戰(zhàn)略調(diào)整以應(yīng)對環(huán)境變化。而嚴(yán)格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會增強企業(yè)環(huán)境合規(guī)成本,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重污染企業(yè)會考慮通過綠色轉(zhuǎn)型從根源上減少污染排放,達(dá)到環(huán)境規(guī)制的要求,降低合規(guī)成本。邱金龍等[21]的研究證實,無論是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還是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均會對企業(yè)綠色并購產(chǎn)生影響。河長制對綠色轉(zhuǎn)型的影響機制見圖1。

圖1 河長制對綠色轉(zhuǎn)型的影響機制
根據(jù)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河長制通過環(huán)保補貼引導(dǎo)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
假設(shè)3河長制通過環(huán)境規(guī)制倒逼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
3 研究設(shè)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shù)據(jù)來源
為了更好地考察河長制對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策略的影響,同時避免新冠疫情沖擊對試驗結(jié)果造成影響,以2008—2019年中國重污染企業(yè)為研究對象,主要關(guān)注當(dāng)年發(fā)起過并購的企業(yè)。關(guān)于重污染行業(yè)的定義,參考潘愛玲等[27]的研究,根據(jù)2010年環(huán)境保護部印發(fā)的《上市公司環(huán)保核查行業(yè)分類管理名錄》和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發(fā)布的《上市公司行業(yè)分類指引(2012 年修訂)》,將以下15類行業(yè)定義為重污染行業(yè):煤炭開采和洗選業(yè)(B06),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yè)(B07),黑色金屬礦采選業(yè)(B08),有色金屬礦采選業(yè)(B09),紡織業(yè)(C17),皮革和毛皮等(C19),造紙和紙制品業(yè)(C22),石油加工和煉焦及核燃料加工(C25),化工原料和化工制品(C26),化學(xué)纖維制造業(yè)(C28),橡膠和塑料制品業(yè)(C29),非金屬礦物制品業(yè)(C30),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C31),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C32),電力、熱力生產(chǎn)和供應(yīng)業(yè)(D44)。
在此基礎(chǔ)上,對數(shù)據(jù)中的并購事件進(jìn)行二次篩選:①剔除重組類型為資產(chǎn)剝離、資產(chǎn)置換、債務(wù)重組、股份回購的樣本;②僅保留標(biāo)的類型為股權(quán)或資產(chǎn)的樣本;③剔除已經(jīng)持有標(biāo)的企業(yè)股權(quán)比例高于30%的樣本;④剔除收購金額小于100萬元、股權(quán)收購比例小于30%的樣本;⑤剔除交易失敗樣本和數(shù)據(jù)缺失樣本;⑥對同一企業(yè)同一年份發(fā)起多次并購且標(biāo)的相同的樣本進(jìn)行合并,對同一企業(yè)在同一年份進(jìn)行多次并購且并購標(biāo)的不同的樣本,僅保留其中交易金額最大、收購比例最高的樣本。經(jīng)過兩輪篩選,最終得到711個樣本。
本文數(shù)據(jù)來源為:①河長制信息主要來源于各地方政府官方文件、北大法寶和百度;②企業(yè)綠色并購數(shù)據(jù)由巨潮網(wǎng)發(fā)布的并購公告手工整理得到,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研究數(shù)據(jù)服務(wù)平臺(CNRDS)綠色專利研究數(shù)據(jù)庫;③其余企業(yè)層面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shù)據(jù)庫,地方層面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家統(tǒng)計年鑒和國家環(huán)境統(tǒng)計年鑒。
3.2 變量測度
3.2.1被解釋變量
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策略:分別使用企業(yè)綠色并購和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作為外部獲取策略和內(nèi)部研發(fā)策略的代理變量。參考潘愛玲等[28]的研究,將企業(yè)綠色并購(Mit)定義為將綠色理念引入公司并購決策,實現(xiàn)以可持續(xù)發(fā)展為目的的并購,且在并購標(biāo)的選擇、并購交易設(shè)計和并購后整合的全流程中貫穿綠色發(fā)展理念。采用內(nèi)容分析法逐一分析并購背景和目的、雙方的經(jīng)營范圍以及該次并購對主并方帶來的影響并進(jìn)行綜合分析,判斷該并購事件是否為企業(yè)綠色并購。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Tit+1)參考李青原等[5]的研究結(jié)果。
3.2.2解釋變量
河長制實施情況(Hit):參考沈坤榮等[6]的研究,整理了樣本涉及的153個地級市河長制的推行情況。首先從重污染企業(yè)所處地級市或省份政府官方網(wǎng)站檢索與河長制相關(guān)的官方文件與新聞報道,整理各市河長制實施時間,如浙江省紹興市推行河長制的時間是根據(jù)《紹興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guān)于在紹興市區(qū)主要河道實施河長制管理工作的通知》(紹政辦發(fā)[2012]135號)確定;同時為確保數(shù)據(jù)準(zhǔn)確,并解決部分河長制實施較早地區(qū)官方信息缺失、網(wǎng)頁無法加載等問題,進(jìn)一步使用北大法寶和百度進(jìn)行了交叉驗證,通過檢索關(guān)鍵詞“河長”,并設(shè)置時間限制以鎖定各地開始推行河長制的時間,并確保河長制信息有所依據(jù)。
3.2.3控制變量
參考李青原等[5]、齊紹洲等[17]、潘愛玲等[28]的研究,分別從企業(yè)層面和地方層面選擇控制變量,變量具體定義與衡量方式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3.3 模型設(shè)定
構(gòu)建基準(zhǔn)回歸模型對假設(shè)進(jìn)行檢驗:
Tit+1=β0+β1Hit+βX+γt+μi+ε
(1)
Mit=β0+β1Hit+βX+γt+μi+ε
(2)
式中:下標(biāo)i、t分別為企業(yè)和年份;X為控制變量;γt、μi分別為年份固定效應(yīng)和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β、ε分別為系數(shù)和殘差。考慮到專利產(chǎn)出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yīng),所以Tit選用t+1期的數(shù)據(jù)。考慮到Mit為0/1虛擬變量,故式(2)選用非線性概率Probit模型,式(1)使用多元回歸模型。此外,為防止極端值對回歸結(jié)果造成影響,對所有連續(xù)變量進(jìn)行了上下1%的縮尾(winsorize)處理。
4 實證結(jié)果及分析
4.1 描述性統(tǒng)計
表2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結(jié)果。由表2可見,第二產(chǎn)業(yè)GDP占比均值達(dá)43.3%,說明第二產(chǎn)業(yè)在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承擔(dān)著重要的作用,而各地區(qū)工業(yè)廢水排放量均值較大、標(biāo)準(zhǔn)差較小,說明在各地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的同時也存在著較嚴(yán)重的污染問題。但可喜的是,樣本中大多數(shù)重污染企業(yè)都進(jìn)行了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且產(chǎn)出了大量的綠色專利;同時,重污染企業(yè)開展的并購活動超過40%都是綠色并購,這些均表明我國重污染企業(yè)正積極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此外,有47.8%的樣本受到了河長制的影響,對照組、試驗組較為均衡。在正式回歸之前,對變量進(jìn)行了 VIF 檢驗,以避免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對估計結(jié)果產(chǎn)生影響。結(jié)果顯示VIF最大值小于5,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2 描述性統(tǒng)計
4.2 回歸結(jié)果分析
表3為基準(zhǔn)回歸的結(jié)果,表中(1)(3)列僅考慮了時間固定效應(yīng),(2)(4)列則在此基礎(chǔ)上加入了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結(jié)果顯示,受到河長制沖擊,重污染企業(yè)綠色并購傾向明顯上升,但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沒有受到顯著影響,假設(shè)1得到驗證。該結(jié)果說明當(dāng)?shù)胤秸趯嵭泻娱L制后,重污染企業(yè)為減少外部壓力,會通過企業(yè)綠色并購?fù)苿悠髽I(yè)綠色轉(zhuǎn)型。可能的解釋是相比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企業(yè)綠色并購具有響應(yīng)速度快、能夠向外界傳遞綠色訊息的特點,更能滿足重污染企業(yè)快速緩解來自利益相關(guān)者壓力的需求。

表3 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
4.3 穩(wěn)健性檢驗
4.3.1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事件分析法對事前平行趨勢進(jìn)行檢驗,具體做法是在保留式(2)被解釋變量的基礎(chǔ)上,將解釋變量河長制實施情況替換為河長制推行前和推行后4年的啞變量,并建立以下回歸方程
(3)
式中:Mit為企業(yè)綠色并購變量;Dt為政策推行前后的年度虛擬變量;βt為需要關(guān)心的系數(shù)。將河長制實施年份設(shè)置為基準(zhǔn)年(t=0)。由于河長制推行年份并非統(tǒng)一,故t=0實際代表了不同年份。
根據(jù)圖2結(jié)果,河長制推行前Dt的估計系數(shù)均未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試驗組與對照組滿足平行趨勢假定。因此,試驗組對對照組企業(yè)綠色并購出現(xiàn)顯著上升的情況是河長制推行的結(jié)果,而不是事前差異的結(jié)果。

圖2 平行趨勢檢驗結(jié)果
4.3.2安慰劑檢驗
盡管在基準(zhǔn)回歸模型中已經(jīng)控制了企業(yè)特征、地區(qū)特征等變量,但回歸結(jié)果仍可能受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為了排除回歸結(jié)果受到遺漏變量干擾的可能,參考Chetty等[34]和沈坤榮等[6]的研究,通過隨機生成河長制變量進(jìn)行安慰劑檢驗。基于隨機生成的河長制變量,重復(fù)500次基準(zhǔn)回歸。根據(jù)圖3的結(jié)果,隨機生成的河長制變量樣本估計值基本集中分布在0附近,且基準(zhǔn)回歸得到的系數(shù)(0.480)完全獨立于該分布之外,說明河長制對企業(yè)綠色并購的影響并未受到遺漏變量的影響。

圖3 安慰劑檢驗結(jié)果
4.3.3傾向得分匹配檢驗
為了驗證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同時處理可能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選擇傾向得分匹配法(PSM)為試驗組匹配對照組。通過比較不同模型的極大似然值選擇了較為合適的協(xié)變量Rit、Lit、Git、Eit、Pit、Fit和Vit。進(jìn)一步地,使用Logit模型估計傾向得分,并選擇最近鄰匹配法(1∶1)以共同支撐原則對樣本進(jìn)行匹配。結(jié)果顯示,匹配前后兩組樣本的均值差異并不顯著,且平衡假設(shè)檢驗結(jié)果表明,匹配后變量的標(biāo)準(zhǔn)化偏差均處于10%以內(nèi)。匹配后的回歸結(jié)果如表4所示,結(jié)果顯示河長制對企業(yè)綠色并購的系數(shù)仍顯著為正,證實了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此外,為了避免匹配方法對結(jié)果可靠性的影響,同時使用核匹配法和半徑匹配法(Caliper為 0.01)重復(fù)上述檢驗流程,結(jié)果一致。

表4 PSM檢驗結(jié)果
4.4 進(jìn)一步分析
4.4.1機制分析
為了檢驗假設(shè)2和假設(shè)3,明晰河長制與重污染企業(yè)綠色并購間的內(nèi)在機理,參考溫忠麟等[35]提出的逐步回歸法,分別將環(huán)保補助(Bit)和環(huán)境規(guī)制(Zit)兩個變量引入回歸模型。Bit使用重污染企業(yè)當(dāng)年獲得的環(huán)保補助與年末總資產(chǎn)之比衡量;Zit參考陳詩一等[36]的研究,使用地方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的環(huán)保詞頻進(jìn)行衡量,具體衡量方式為:地級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xiàn)的與環(huán)境相關(guān)的詞頻數(shù)占報告全文詞頻總數(shù)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選擇環(huán)保詞頻作為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代理變量,是為了盡可能地減少中介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問題。當(dāng)前主流環(huán)境規(guī)制是由污染物排放量計算而來,與本文的控制變量存在一定的內(nèi)生性問題,而環(huán)保詞頻很好地避免了這個問題。
由表5中的(1)(3)列可知,河長制實施前后環(huán)保補助并沒顯著變化,說明河長制的實施并沒有促使地方政府為重污染企業(yè)提供額外環(huán)保補助,誘導(dǎo)其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而(3)(4)列中,Hit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明河長制實施后地方政府更加關(guān)注環(huán)境治理,收緊了環(huán)境規(guī)制,而較為嚴(yán)格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成功倒逼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假設(shè)3得到驗證。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通過倒逼而非引導(dǎo)重污染企業(yè)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的可能解釋是:一方面政府部門給予的環(huán)保補助可能被用于直接環(huán)保投資,而非綠色轉(zhuǎn)型[5];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與企業(yè)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政府部門難以監(jiān)管環(huán)保補助的真實用途,環(huán)保補助可能淪為管理者獲取私人收益的途徑[37]。

表5 機制分析結(jié)果
4.4.2異質(zhì)性分析
a.媒體壓力。畢茜等[38]認(rèn)為地方政府受制于行政資源的局限性,往往在管理企業(yè)時處于信息劣勢,難以全面洞察重污染企業(yè)的環(huán)境違法行為。而媒體出于自身生存和謀求利益的目的,往往熱衷于曝光企業(yè)負(fù)面丑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重污染企業(yè)與社會之間信息不對稱[39]的問題。而媒體負(fù)面報道的同時會對重污染企業(yè)造成重要影響:一方面負(fù)面報道會影響投資者未來預(yù)期,往往公眾會認(rèn)為媒體曝光的問題僅是冰山一角,企業(yè)實際污染問題更為嚴(yán)重[40],導(dǎo)致投資者紛紛拋售股票,企業(yè)市值嚴(yán)重下滑[41]。另一方面,負(fù)面新聞曝光后,為避免事態(tài)升級、引發(fā)上級問責(zé),地方政府必須對此做出回應(yīng),重污染企業(yè)無可避免需要接受調(diào)查甚至受到處罰。在負(fù)面新聞被曝光后,重污染企業(y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會成為媒體、公眾和政府三方共同關(guān)注的對象,面對巨大的外部環(huán)境壓力。而企業(yè)綠色并購一大特點是具有眼球效應(yīng),能夠通過并購公告快速回應(yīng)媒體質(zhì)疑,挽救企業(yè)形象。并購公告也在資本市場釋放訊號,避免可能發(fā)生的股價下行風(fēng)險。因此,可以預(yù)期當(dāng)重污染企業(yè)媒體壓力較高時更傾向于發(fā)起企業(yè)綠色并購。
為檢驗媒體壓力存在差異情況下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策略的異質(zhì)性,根據(jù)各年度媒體壓力的中位數(shù)將樣本劃分為高媒體壓力組和低媒體壓力組。媒體壓力使用上一年度媒體負(fù)面報道與媒體報道總數(shù)之比進(jìn)行衡量,媒體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研究數(shù)據(jù)服務(wù)平臺(CNRDS)。表6中(1)(2)列顯示,在媒體壓力高的企業(yè)中,河長制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明當(dāng)重污染企業(yè)面對較高媒體壓力時更容易發(fā)起企業(yè)綠色并購策略,這與本文的推導(dǎo)是一致的。該結(jié)果同時也說色明媒體壓力有助于推動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

表6 異質(zhì)性分析結(jié)果
b.環(huán)境不確定性。盡管企業(yè)綠色并購與綠技術(shù)創(chuàng)新相比速度更快、能夠釋放眼球效應(yīng),但并購活動是一項涉及多方的復(fù)雜性系統(tǒng)工程,無論是在標(biāo)的選擇階段、并購交易階段還是并購整合階段都需要進(jìn)行合理的設(shè)計規(guī)劃,任何疏忽都可能導(dǎo)致并購失敗,反而給重污染企業(yè)帶來經(jīng)濟損失[21]。同時,企業(yè)在實施綠色并購過程中會占用其他方面的資源,增加了企業(yè)運作成本,可能造成經(jīng)營效益下滑。所以,根據(jù)上述分析,企業(yè)綠色并購背后伴隨一定的風(fēng)險,可能會對重污染企業(yè)造成負(fù)面影響。因此,重污染企業(yè)僅會在自身可以承受潛在損失時才會發(fā)起綠色并購。企業(yè)總是在特定的市場環(huán)境中開展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的,市場環(huán)境的波動會對企業(yè)經(jīng)營業(yè)績和風(fēng)險產(chǎn)生明顯的影響[42]。當(dāng)環(huán)境不確定性較高時,信息不對稱程度上升、企業(yè)盈余穩(wěn)定性持續(xù)性變差,管理者難以評估潛在風(fēng)險、制定合適的企業(yè)戰(zhàn)略[43]。在此情形下,重污染企業(yè)或?qū)ζ髽I(yè)綠色并購采取更為審慎的態(tài)度,呈現(xiàn)風(fēng)險規(guī)避偏好。而當(dāng)風(fēng)險不確定性程度較低時,企業(yè)能夠準(zhǔn)確預(yù)測環(huán)境的未來變化,做出正確的戰(zhàn)略決策,維持經(jīng)營績效穩(wěn)定。在此情形下,可以預(yù)期企業(yè)能夠承受綠色并購帶來的潛在損失,愿意發(fā)起綠色并購。
為了探究重污染企業(yè)在不同環(huán)境不確定性情況下的反應(yīng),依據(jù)各年度中位數(shù)將樣本劃分為高環(huán)境不確定性組和低環(huán)境不確定性組。參考申慧慧[43]的研究,使用重污染企業(yè)過去5年剔除穩(wěn)定增長部分銷售收入的標(biāo)準(zhǔn)差并經(jīng)行業(yè)調(diào)整后的值來衡量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根據(jù)表6中(3)(4)列顯示,河長制系數(shù)在低環(huán)境不確定性組中顯著為正,說明重污染企業(yè)在環(huán)境不確定性較低時更愿意發(fā)起綠色并購,而當(dāng)外部環(huán)境不確定性較高時或?qū)⒏鼮楸J?不愿開展綠色并購。
5 結(jié)論與建議
5.1 結(jié)論
本文利用A股上市重污染企業(yè)數(shù)據(jù),使用雙重差分識別策略,研究了河長制影響下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策略的選擇行為。實證結(jié)果表明:受到河長制的影響,重污染企業(yè)為了快速獲取清潔能源和環(huán)保技術(shù),并向外界傳遞積極履行社會責(zé)任的訊號,樹立良好的企業(yè)形象,企業(yè)綠色并購傾向顯著上升。該結(jié)果說明企業(yè)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獲取策略而非內(nèi)部研發(fā)策略應(yīng)對河長制帶來的環(huán)境監(jiān)管壓力,并且當(dāng)重污染企業(yè)面對較高的媒體壓力,或環(huán)境不確定性較低時該效應(yīng)更為明顯。機制分析表明,河長制實施后,地方政府為了應(yīng)對晉升考核和上級問責(zé),會通過收緊環(huán)境規(guī)制倒逼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
5.2 建議
a.河長制有效推動了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各地區(qū)應(yīng)當(dāng)持續(xù)推進(jìn)落實河長制,實現(xiàn)河長制有名亦有實。同時嚴(yán)格執(zhí)行環(huán)境績效考核,將環(huán)保指標(biāo)納入政績考核體系,避免唯經(jīng)濟論,充分調(diào)動地方政府和重污染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積極性。
b.重污染企業(yè)在污染防治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提前布局,循序漸進(jìn)地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將低碳節(jié)能、綠色環(huán)保作為企業(yè)長期發(fā)展目標(biāo),推動自身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同時地方政府應(yīng)給予企業(yè)適當(dāng)緩沖期,提供企業(yè)內(nèi)部綠色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研發(fā)時間,避免對企業(yè)造成過大壓力。
c.地方政府應(yīng)當(dāng)制定明確的環(huán)境治理目標(biāo),并通過制度支持和制度壓力等方式督促重污染企業(yè)節(jié)能減排,從源頭緩解污染問題。但在污染治理過程中切不可急功近利、過分冒進(jìn)。應(yīng)當(dāng)因地制宜,綜合各項條件制定適合本地的目標(biāo)計劃,平衡生態(tài)和經(jīng)濟效益。
d.地方政府以及廣大群眾應(yīng)當(dāng)重視媒體在環(huán)境治理中的作用,可以適當(dāng)借助媒體之手緩解重污染企業(yè)與外界社會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況,了解企業(yè)排污治污的真實情況,達(dá)到環(huán)境監(jiān)管的目的,促進(jìn)重污染企業(yè)綠色轉(zhuǎ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