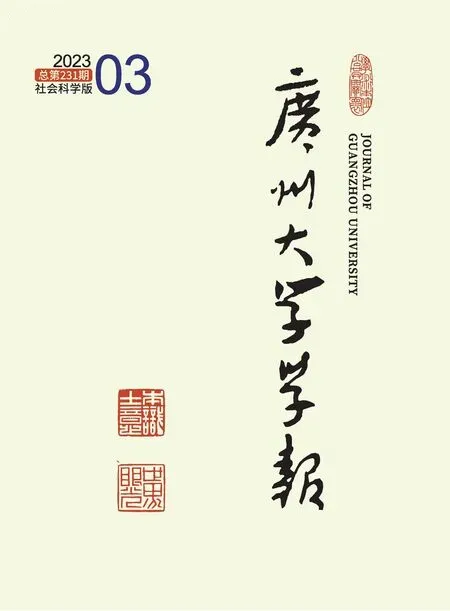時空意識與闡釋活動的文化差異
馬 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闡釋學高等研究院, 北京 102488)
闡釋作為一種通過語言所進行的社會化活動,總是在一定的時空中進行的,通過闡釋活動,闡釋主體時間性的內在精神凝練為空間化的社會人格,從而賦予個體生命以公共性。張江在《公共闡釋論》中,將公共性定義為闡釋的根本特征,闡釋活動的前提、根據、發生、過程與結果都圍繞公共性展開,“闡釋之所以公共,是因為闡釋的全部前提來源于公共,立足于公共,在闡釋過程中連續發生作用,為闡釋提供可能”[1]。從更大的視角看,闡釋不是一種抽象的個體活動,而是一種被文化所滲透的社會化活動,中西文化不同的觀念自然會折射到闡釋活動的過程中,使其不可避免地帶上文化的烙印,這決定了闡釋公共性的不同走向。相對于西方的闡釋活動偏于對闡釋主體內在時間意識的探索,中國的闡釋活動更加注重闡釋客觀效果的空間延展,這不僅體現在“闡”字本身就表征了一種空間的開放性,同時也體現在衍生所建構的意義再生產的方式、通達所展示的闡釋目標等方面;中國的闡釋活動注重開放、衍生,尋求闡釋話語在現實世界的通達,西方的闡釋活動則注重個體精神的自我尋繹,表現為面向彼岸世界的精神超越。
一、立象盡意與精神的自我開掘:闡釋活動的出發點
從闡釋一詞在中文語境中的詞源來看,據張江考證,“闡”本義為開,作為會意字的 “開 (開)”,是雙手對舉打開門閂,意在開門,與“闡”同為“開”義的,還有“辟 (闢)”等字,其中,“辟”又謂 “開”,且為 “多開”。[2]闡的本義是開門,這是一種空間上的延展,有了空間的開放,人才能耳聰目明,而不是閉目塞聽。將空間延展與人的精神活動相連接,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心理特征,這與漢語造字上的象形特征有關,也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密切相關。從闡釋活動的起點來看,李紅巖認為,《周易·系辭》蘊含闡釋行為的生成暗碼:“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3]闡釋活動植根于感性直觀活動之中,以觀看行為為起點,形成選取、合并、分類、確證等思想,進入到符號化、抽象化、范疇化、理論化階段,反映圓形思維模式。[3]闡釋活動以觀看始,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一俯一仰之間,構筑起人的視覺空間,經過思維的加工提煉,形成闡釋的語言表達空間。我們的思維正是在此空間中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從而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這種思維特征,王樹人等將其概括為“象思維”。所謂“象思維”本質上就是一種空間性的思維過程,“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和內在感知之象,[4]無論外在感知之象和內在感知之象,都是將人的主觀感受空間化,與空間性的身體感知相關。
通過象的中介,連接起了闡釋的兩個要素:言與意。不僅語言是通過象形的方式所構造,意義也可以通過形象來傳遞,象在思維和表達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言:言不盡意,則圣人立象以盡意。言—象—意的闡釋系統是中國文化所特有,它最初起源于《易經》的卦象系統,其中,“象”是連接言和意的中樞和核心,在哲學的思維方式和美學的世界觀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兩大現象與之相關:一是哲學上‘言意之辯’, 二是美學上的人物品藻以及與此關聯的, 在南朝大為發展的美學—藝術理論。前者主要關切理論言說, 從而走向語言符號系統中的言意問題,后者的理論目的乃美學言說, 走向審美符號系統的言象意問題”[5]。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論是理論思維還是審美活動,都有一個言—象—意的三元結構。其中,象是中介也是核心。我們的理論思維往往是通過立象來闡釋和傳達的,象征、比喻的修辭手法頻繁地運用于論說文中,體現了象思維的特征。而在文學作品和審美活動中,象進一步擴大化為空間化的“境”,意象與意境,代表了中國人審美闡釋的最高理想,“意境是在物我互動中成就的,是外境與主體心靈之境的統一。心物交融成就了意境。王昌齡所謂的三境說,是在物境與情境的統一中創構意境”[6]。無論是象還是境,都是一種外向的空間化的建構和表達。
可見,在中國的表達和闡釋活動中,象所體現的空間感非常重要,我們并不是通過語言的邏輯功能來把握意義,而首先是通過心物交融的意象來體悟價值。在言—象—意的闡釋系統中,言與意的關系是互相遮蔽的,言往往是不可靠的,空間化的象與境更能表達意,意境代表著主客體的圓融統一。與此相關,在闡釋活動中,我們更加注重意義的空間拓展,即闡弘使大:“凡物之大,共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闡弘使大。”[7]通過闡釋,使事物的意義得以彰顯擴大。這種拓展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意義通過闡釋得以豐厚,二是意義得以獲得更大范圍的認同。這種累積式的意義生產方式,體現在美學上就是“積淀說”。
與中國的“闡”字展示出的空間拓展特征相比照,在西方語境中,闡釋(hermeneutics)一詞起源于古希臘神話的信使赫爾墨斯(Hermes)。古希臘神話中以人格化的神表征社會活動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正義女神“忒彌斯”、智慧女神“雅典娜”、農業神“德墨忒爾”等,闡釋的詞源來自人格化的神,體現為作為信使的赫爾墨斯對于神意的猜度,不同于開門的意象所展示的空間結構,“宙斯—信使—人”之間構成了一種信息之間的時間傳遞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作為信息發出者的宙斯、作為信使的赫爾墨斯和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人都是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的,闡釋的目的并不是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圍內彰顯,而是通過闡釋開掘個體的精神世界。中西闡釋在出發點上的這一內在微妙的差異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基因,西方闡釋學更加重視闡釋者內在的時間意識,這從西方現代闡釋學的開創者施萊爾馬赫那里就可以看得出來。
施萊爾馬赫創立現代闡釋學,其本質就是將闡釋活動從文本與讀者構建的二元空間關系中解放出來,而賦予其深入主體精神的時間性,“‘理解’無非是‘思維著的精神逐漸地自我發現’”[8]。在西方經典的闡釋活動中,作為經典的《圣經》是一種絕對化的存在物,闡釋活動是圍繞《圣經》文本進行的語義考辨,而施萊爾馬赫開創的現代闡釋學則將闡釋活動的焦點轉移到了闡釋者的主體,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主要是立足于語法規則與精神表達之間的沖突:“理解只是這兩個環節的相互作用(語法的和心理學的)。(1)話語如果不被理解為一種語言的關系,那么它就不被理解為精神的事實,因為語言天賦性限制精神。(2)話語如果不被理解為一種精神事實,那么它就不被理解為語言的樣態,因為所有個人對語言的影響的根據就在于講話,而語言本身是由講話所決定的。”[9]言在這里表現為一種客觀的語法規則,意則表達為一種個體心理上的精神事實,語言的內在邏輯限制著話語的表達。同時,人的內在精神事實也需要通過話語來得到表現。之前的闡釋學更多突出話語與語言之間的聯系,忽視了話語與精神表達之間的關系,而“施萊爾馬赫看到了作者使用的語言既具有普遍性或同一性,又具有個別性或差異性”[10]。話語本身具有內在的二重性:既有言所體現的規范化含義,也有意所體現的精神化含義。闡釋活動的目的不單是要通過語言的規范性避免對文本的誤解,更是要開掘文本之下的個體精神的含義。
施萊爾馬赫對于語言的這種雙重理解,在西方哲學中有著悠久的傳統,古希臘哲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語言的規范性與個體表達的超越性之間的沖突。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會說話的動物。”這里的“說話”并非普通意義的言說,而是指規范性的理性即邏各斯,理性對于語言具有規范的一面,體現為語法和邏輯規則。與此同時,古希臘對理性的理解還有超越性的一面,即個體心靈(努斯)意義上的理性。努斯是阿那克薩戈拉提出的哲學概念:“心靈則是無限的,自主的,不與任何事物相混,而是單獨的,獨立的,自為的。”[11]70心靈(努斯)的提出標志著西方哲學將個體的精神從自然界中獨立出來。語言不僅作為一種社會交往的工具,更重要的,作為一種精神自我開掘的工具,它可以用于反映內心,這種功能使得語言擺脫了單純邏輯性的工具論,而具有了詩化和隱喻的色彩。“古代語言自然帶有這種有機生命的特色,是因為語言除了作為人與人相互交往的社會工具之外,還具有表現生存的詩化性質;或者說,正因為它具有這種表現性質,它才能成為社會交往的工具(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語言的詩化性質只有在社會交往中才能形成)。”[12]正是語言的工具論與語言的表現論之間的內在沖突催生了西方現代闡釋學的誕生,當代的許多西方哲學家往往將時間作為研究的主題,其中所暗示的就是一種個體的生命意識。
二、向外衍生與向內循環:意義的再生產方式
闡釋是意義的再生產過程,意義再生產按其時空向度可以分為向外的擴展與向內的深入。一般而言,中國的闡釋更注重意義外向的衍生,同時始終不離其生發的經典之源,從而構成中國闡釋悠久的經學傳統;而西方的闡釋更強調通過闡釋循環創造出新的內在意義,這種新的意義甚至可以顛覆文本的本來意義,造成了西方思想家不斷推陳出新。
皮錫瑞在其《經學歷史》一書中,開篇即提出了一條經學闡釋的原則:“凡學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13]考其源流、別其得失,正是中國古代經典闡釋的基本方法。中國闡釋始終在擴張與守約之間尋找一種平衡,這種闡釋的方式,張江名之為“衍生”:“衍為約束之衍。《說文》注:‘旁推曲暢,兩厓渚涘之間不辨牛馬。故曰衍。’此謂衍雖廣布,但有約束和規矩,衍為于‘兩厓渚涘之間’長流。”[14]“衍”本身代表著一種擴張和流變,但又不是漫無邊際,而是朝宗于海,始終以文本本身為約束。中國的闡釋學之所以以文本為中心展開,就在于作為闡釋對象的文本并非一般的文本,而是具有經典的含義,文本對于闡釋的主體來說始終是外在的需要學習的對象,而經典文本由于漢語的暗示性,恰恰具有豐富的可以衍生的意義。于是,對經典的闡釋就是一個經典不斷自我肯定和豐富的過程,闡釋者也藉由對經典的闡釋融入文化建構的過程中,從而達成教化。
李清良在《中國闡釋學》一書中,將中國闡釋的基本方式概括為“解喻結合”:“所謂‘解’,主要是指名物訓詁以及字詞章句之間的串通,其目的是使文本的基本意思即‘原意’或稱‘文義’得以呈現;所謂‘喻’,則指在文本的‘原意’基本明了的基礎之上,通過提供若干不同的具體語境,全面呈現作者的‘用心’。”[15]解喻體現了意義衍生的兩種方式,都是立足于文本的原意,或以訓詁方式貫通文意,或以譬喻方式貫通讀者的理解,但無論哪種方式,都是以文本本身作為約束的。從語言角度看,之所以會有“解”和“喻”兩種闡釋方式,其根源在于中國語言的多義性和豐富的暗示性,即詩化特征。詩在中國語言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我們對語言的認識,不是把它當做認識的工具,而是當成一種詩性本體的表現:“西方人談語言的性質,不管用為載體或本體,都是從其與人的邏輯思維的關聯上著眼的,言說基本上成了理性的表記;而中國傳統的語言觀,特別是從‘言不盡意’的那個方面來說,言說所要表達的是人的詩性生命體驗(形而上的哲思亦屬生命體驗,是對生命體驗的反思與感悟),它自己不過是通向生命境界的一個階梯。”[16]如果說,西方古典的語言觀是以語言的工具論遮蔽了語言的表現論,中國則是以語言的表現論遮蔽了語言的工具論,詩化的語言自身就具有意義的衍生性,這種衍生最終要達到的不是精神個體的自我確認,而是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達到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衍生并非一種邏輯關系,而是一種生命體驗的聯系。
西方現代闡釋學中,對于意義生成方式的表述為“闡釋學循環”。衍生是一種空間化的拓展,類似于河流的匯聚,文本中隱微的含義通過衍生而不斷擴大和彰顯;循環則是一種內在的時間性的開掘,更加注重闡釋者對于文本的介入甚至解構,經歷了一個從語法闡釋到心理闡釋再到歷史闡釋的過程。[17]無論是文本、心理還是更廣闊的社會歷史,闡釋學循環所看重的都是闡釋者內在的精神統一性,相較于衍生對于文本本意的重視,闡釋學循環更加重視闡釋者自身的精神世界。“海德格爾把這種情況稱作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schen zirkel):我們只能理解我們已知的東西,只能聽出我們已讀出的東西。若按自然科學的認識標準來衡量,這似乎是無法容忍的。但實際上唯其如此歷史的理解才可能。關鍵不在于避開這種循環,而是從正確的方式進入這種循環。”[18]42闡釋之所以能夠循環,就在于個體以其內在精神的主體性不斷介入文本、介入歷史,在歷時性的活動中不斷打下自己的印記,在對象中看到自身,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復自身。
西方闡釋學的這種精神的循環思想,在哲學史上也可以找到源頭,如果說,中國闡釋活動的衍生意象體現出一種水的流動性,西方闡釋活動的循環思想則表征了一種火的能動性。火被引入哲學話語源于赫拉克利特對世界本源的追溯。火不同于之前哲學家提出的水和氣,就在于火具有強烈的能動性。“火是元素,一切都由火的轉化而形成,或者是由于火的稀薄化形成,或者是由火的濃厚化形成。……宇宙是有限的,只有一個世界,是由火產生的,經過一定的時期后又復歸于火,永遠川流不息。”[11]15這里面已經有循環的思想。循環不是機械的更替,而是人內在精神的火燒向外部世界,從而在更高層次回復自身的過程。這種循環的思想,一方面造就了西方思想家們不斷向內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思想史成果;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思想,馬克思則沖破了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帷帳,提出不僅要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變世界。
三、現實的通達與超越性的視域融合:闡釋活動的指向
闡釋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總有其目的和指向。張江把闡釋活動的指向概括為“通”與“達”:“‘通’有‘開通’義,‘達’有‘明達’義,‘通達’組合,綜合了敞開、去除遮蔽的意味,體現的正是闡釋的開放性。”[19]通達體現了闡釋活動外向的空間指向,闡釋者不是向內探索個體精神的深化,而是向外求得個體表達的公共性,個體理性必須上升為公共理性才能獲得其闡釋的有效性,“闡釋的結果就是在公共理性的基礎上相互妥協、共生,而非將一己私意強加于人,此為通達的另外形式,可稱作‘圓通’或‘融通’”[19]。在語言層面,通達指向求真務實的理性精神;在實踐層面,通達體現了一種洞明練達的做事態度;在人生哲學層面,通達則彰顯了一種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通祛障礙,達及澄明;通貫歷史,達及當下;通徹各方,達及一致。”[19]可見,通與達總是在現實中得以實現的,這體現了中國闡釋求真務實的現實理性特征。
求真務實的闡釋目標,與中國文化重現實的心理指向密切相關。在語言層面,任何言說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根據。一方面,現實要符合名的規定,所謂“循名責實”“名實相符”;另一方面,名本身就是現實倫理秩序的投射。“形而上范疇的倫理化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就使中國哲學中除了道德本體之外,再無任何真正哲學意義上的本體和獨立的本體論。……本體論經認識論內化為倫理學,倫理學又經認識論外化為本體論。”[20]這種知行合一的思維方式塑造了中國闡釋學的現世追求,闡釋的目的始終是在現世的倫理秩序框架之內的,闡釋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教化。
在西方現代闡釋學中,對于闡釋的目標常常表述為視域融合。視域首先是從闡釋者的個體出發的,體現為一種個體精神的超越性。“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Gesichtskreis),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容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21]從個體精神的視域出發,最終要通過闡釋超越自我,建構“效果歷史”,正體現了闡釋主體與歷史視域相互建構的依存關系。一方面,歷史不是超越于主觀精神的客觀物,而是浸透著人的主觀理解和表達,即人的主觀“效果”;另一方面,闡釋主體也在自己的前判斷和歷史視域中活動,闡釋者與效果歷史之間相互建構、密不可分。“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把理解主體置于歷史之中意味著忘我的境界,即要求主體摒除一切自己的主觀性而進入作者的視域;但在伽達默爾,進入歷史視域的主體必不可免地攜帶著自己的前判斷,這就是說,進入歷史視域并不意味著主體自己的視域之消失,純粹以歷史的視域作為自己的視域,而是主體在歷史的視域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前判斷之作用,從而真正形成一種‘效果歷史’。”[22]從視域融合到效果歷史,西方闡釋學關注的始終是個體的精神超越,從施萊爾馬赫到海德格爾,闡釋學越來越深入闡釋者的主體自身,揭示主體內在的辯證關系。海德格爾開創了當代西方的本體論闡釋學,其本體并非大寫的本體、文化的本體,也不是文本的本體,而是小我的本體、此在的本體。本體論闡釋學就是此在的超越之途,體現了鮮明的時間意識。
四、結 語:在比較視野中建構當代中國闡釋學
語言體現了人的思維方式,任何闡釋都處在一種文化語境中,不可能有脫離語境的闡釋。伽達默爾曾言:“一般說來,語言能力只有在自己的母語中才能達到,亦即在人們生長和生活的地方所說的語言中才能達到。這就說明,我們是用母語的眼光學會看世界,反過來則可以說,我們語言能力的第一次擴展是在觀看周圍世界的時候才開始得到表現的。”[18]6沒有對中國闡釋學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我們對于西方闡釋學的理解也只是皮相的,只有借助對于中國闡釋學的理解,我們才能深入到西方闡釋學的背后,理解其概念、命題背后的文化背景,而不是進行簡單的比附,中西闡釋學之間也才能展開有效的對話。因此,我們建構當代中國闡釋學,就不能對西方闡釋學進行簡單地移植,而是需要立足于更高的層次,看到中西闡釋生發之處不同的文化心理背景。中西闡釋學從出發點、路徑和闡釋的目標來看,均存在明顯的差異:中國闡釋學注重開放、衍生,尋求與現實世界的通達,閃爍著理性務實的智慧之光;西方闡釋學則注重精神的自我尋繹,體現出一種個體的超越之途。中西闡釋學的不同概念,不只是語詞的差異,而是浸潤著深厚的文化內涵。
對闡釋活動文化背景的理解和把握,對于當代中國闡釋學的建構具有特殊意義。湯一介早在20世紀末就提出過創建中國闡釋學的構想。[23]不過,湯一介之后,人們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中國有沒有普遍性的闡釋學的討論之上,而忽視了闡釋現象是一種任何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對此進行系統的反思,必然可以構建出一門屬于自己文化體系的闡釋之學,不同文化所創構的闡釋學必然是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的。重要的不是提出一種涵蓋所有文化的闡釋學理論,而是在對本民族闡釋觀念和方法的提煉中,獲得一種自我意識,這是在與其他文化的闡釋學進行比較的過程中產生的。闡釋學本質上不是一門學問,而是流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