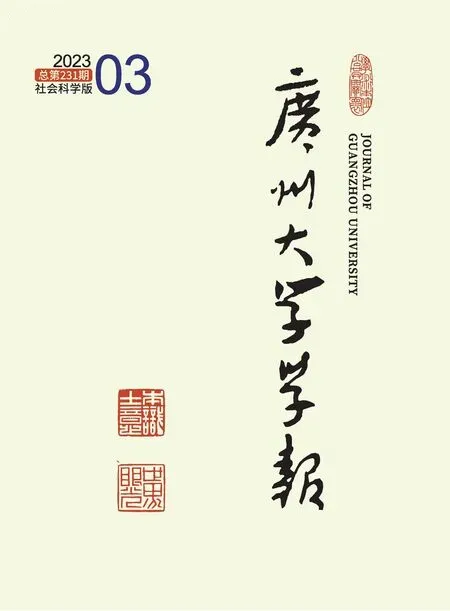期待視域之外
——疫情與集體記憶①
阿斯特莉特·埃爾著,劉 藝譯
(1.法蘭克福大學 現代語言學院,德國 法蘭克福 60323; 2.四川外國語大學 德語學院,重慶 400031)
在大流行病肆虐期間,記憶研究似乎顯得不合時宜,因為目前我們仍身處其中,然而,對過去大流行病的回憶或遺忘嚴重影響人們在新冠疫情期間的體驗。在新冠疫情期間,對歷史的回憶、歸檔、紀念等等實踐活動證明了自身作為重要社會資源的價值,并且新型冠狀病毒最終也會成為被回憶的對象,從而影響社會的未來。因此,我將在文中探討在新冠疫情之前、期間以及之后的集體記憶(kollektives Ged?chtnis)。
對集體記憶的研究始于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了“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這一概念,他強調記憶始終“處在社會框架中”②。當前記憶研究是在跨學科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范疇內進行的③,集體記憶被認為是一個囊括了生物、心理、社會、媒介、文化和物質層面的復雜過程,不斷重置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系。“個體”和“集體”不再是相對概念,而是記憶研究領域中的不同研究視角:心理學研究個體的記憶能力,而社會學更傾向于觀察其在社會及國際范圍內發生的過程。集體記憶與歷史也不是相對概念,在這里,歷史事件是記憶的對象,歷史書寫則是集體記憶的方式。④
一、疫情之前的集體記憶
讓人始料未及的是,歐洲人在全球性疫情面前毫無準備,而我們本該預料到它的到來的。過去的一百年內就發生過多次流行病:亞洲流感(Asiatische Grippe)(1957—1958年)、香港流感(Hongkong Grippe)(1968—1970年)、俄羅斯流感(Russische Grippe)(1977—1978年)、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的艾滋病毒或艾滋病(HIV/AIDS)、非典(2002—2003年,也就是SARS冠狀病毒)、禽流感(Vogelgrippe)(2004年),豬流感(Schweinegrippe)(2009—2010年)、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2015年)、寨卡病毒(Zikavirus)(2015—2016年)、埃博拉(Ebola)(2014—2016年)。
可見,大流行病總是有規律地反復出現。早在2019年,醫學歷史學家弗蘭克·M·斯諾登(Frank M. Snowden)就將埃博拉和非典病毒看作是21世紀下一場大流行病的“預演”[1]466。然而,大多數歐洲人似乎都忽視了流行病,因為他們對流行病的想象總是投射在“它者”(das Andere)身上——要么是前現代的歐洲人(黑死病),要么是文化或地理上的它者。埃博拉似乎是專屬西非的疾病,20世紀初的“亞洲流感”(正如它的名稱錯誤地暗示那樣)則是亞洲人的事情。
(一)被遺忘的西班牙流感(Spanische Grippe)
如果那些近期發生的流行病還不夠令人難忘,那么1918—1919年有著驚人死亡數量的大流感(即所謂的西班牙流感)應該在人們的記憶中占有一席之地。從1918年春季至1919年春季,西班牙流感共出現了三次高峰期。醫學史上對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數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在全世界范圍內共有5000萬至1億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2.5%至5%。
《蒼白的騎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了世界》是一部非常值得閱讀的作品,它全面地講述了西班牙流感史。據作者勞拉·斯賓尼(Laura Spinney)所言,這場流行病是“自中世紀黑死病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流行病,甚至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流行病”,死亡人數“超過了一戰(1700萬)以及二戰死亡人數(6000萬),甚至可能比兩者加起來的總死亡人數還要多”。[2]12西班牙流感是當時所有流行病的源頭,通過病毒變異,多次掀起較小的流感潮,但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歐洲,它卻完全被遺忘了。
(二)經驗空間(Erfahrungsraum)與期待視域(Erwartungshorizont)
2020年初,對于大部分歐洲人來說,流行病并不屬于萊因哈特·科賽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說的“經驗空間”[3]。在文化中所感知、體驗和記憶的東西會對未來的想象產生影響,這便是“期待視域”。2018年,西班牙流感一百周年之際,西班牙流感在歐洲獲得了很多關注,但它既不屬于紀念文化活動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學校教學計劃中的課程內容。
正因為如此,新冠疫情徹底破壞了經驗空間與期待視域之間的關系。歐洲人自認為曾經所知道的或曾經所想的(關于呼吸系統疾病的危險、在民主社會中實行封控措施和臨時立法的可能性、義務教育、經濟穩定性以及佩戴醫用口罩等問題)在短短幾周內盡數失效。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新體驗幾乎在所有方面都超出了期待視域。正如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2020年4月23日的政府聲明中所言,新型冠狀病毒很快就會變成“一種苛求”⑤,這一苛求不僅是對民主而言,而且也是對通過集體記憶承載的關于時間節奏和變化的社會想象而言。
然而,各地人們對同一時間在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事件卻并非都有相同的感知。原因便在于集體記憶的形式不同:例如韓國對新冠疫情就有所準備,這或許是因為曾經歷了嚴重的非典和中東呼吸綜合征;西非人在2020年春季對于新冠疫情的到來似乎也并不驚訝,這可能是因為他們仍記得埃博拉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此外,各地的知識秩序和習慣記憶也各不相同:亞洲大部分地區習慣使用醫用口罩,這種習慣似乎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流感;而在2020年春季的歐洲,關于醫用口罩的有用性和適用性卻帶來了長時間爭論。
(三)預媒介化(Pr?medialiserung)
我想使用“預媒介化”這一概念來描述集體記憶如何塑造未來,即群體和社會以何種方式預測、解釋和應對新事件。但為什么要使用這一聽上去有些別扭的概念呢?從手勢、口頭交流到書籍、電視和互聯網——記憶需要表達和實現社會共享的媒介。集體記憶建立在媒介化之上,因此集體期待始終是由媒介預成型的,也就是預媒介化的。
西班牙流感就是例子:在歐洲,西班牙流感沒有被充分媒介化以及再媒介化,從而也就未能使其成為新冠疫情的預媒介化動力⑥。歐洲缺少關于西班牙流感的當代著名的回憶錄、繪畫和小說,沒有具有強烈視覺沖擊的圣像畫或敘事,以及能夠由此形成的社會性集體記憶。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的《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畫像》(Selbstportr?tmitderSpanischenGrippe, 1919)或埃貢·什勒(Egon Schiele)的《蹲著的夫婦(家庭)》[KauerndesMenschenpaar(DieFamilie), 1918]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不屬于藝術家的核心作品,也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圣像畫流傳下來。而對中世紀瘟疫的深刻集體記憶恰恰基于一些經久不衰的藝術作品——比如今天還可以在教堂里找到的關于死亡之舞的繪畫或者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Dekameron,約1349—1353年)這樣的迄今都屬于歐洲社會的經典作品。
(四)回憶(Erinnerbarkeit)
各種原因導致了西班牙流感的低度可回憶性。第一,它作為歷史事件,其建構不明確。H1NI流感病毒在當時還不可見且傳播迅速,通常在短短三天內就能致人死亡。它無法被檢測到是因為當時病毒在電子顯微鏡下還不可見(20世紀30年代開始可在電子顯微鏡下觀測到病毒),所以它與當時肆虐的其他流行病病毒如結核病病毒混在一起,此外還有戰爭和饑餓奪走人的生命,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當時的人們很難將西班牙流感視作單獨事件,從而將其與其他事件區分開來。
第二,西班牙流感缺少敘事潛力,即不太可能從混亂的歷史事件中創造出完整的故事,因為要是不清楚事件的真實情況,事件發生的過程和地點、開始和結束的時間,那么故事就不能展開。
第三,西班牙流感正處在這樣一個時期,當時士兵們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戰死并被英雄化。對于當時的社會而言,流感死亡的“可敘述性”更低,也就是說新聞價值更低。
第四,記憶文化傾向于成為規范。“歷史教訓”更容易從戰爭、種族滅絕和恐怖行動等事件中被總結出來,因為從這些事件中人們更能清楚地認識到人類的罪責和責任。面對氣候變化和人類世(Anthropoz?n),人們才慢慢意識到洪水和流行病等自然災害是由人類(共同)造成的,人類應對此負責。
第五,可回憶性同時也是存檔問題。就像西班牙流感一樣,這類在當時語境下沒有被明確定義為單獨事件的歷史事件,缺少某種特定的動力,使人去分享其間的經驗并流傳至后代[在歷史學中,這被稱作“傳統”(Tradition),它是“殘余”(überrest),即無意中留下的原材料的反義詞]。
(五)什么叫作集體記憶和遺忘?
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范圍內都留下了痕跡,也就是說留下了西班牙流感的殘余,其中主要包括病毒學和在過去幾十年內增多的醫學史研究所使用的醫學和統計學數據。就病毒學而言,在20世紀期間已滅絕的H1N1流感病毒是一個典型事件,在2005年出于研究目的被用于基因改造。[2]221在科學系統中一直保留著對西班牙流感的記憶,而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是家庭記憶,它的傳承從未中斷,正如蓋·班納(Guy Beiner)等人在《大流行再覺醒》(PandemicRe-Awakenings, 2021)中寫到,在世界范圍內仍有家庭記得他們的祖先曾死于西班牙流感。[4]
集體記憶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頭腦中都有相同的表征符號,而是指在社會群體中,過去的特定事件通過話語、媒介和實踐被不斷更新并與其他主題關聯在一起。同樣,集體遺忘并不意味過去事件的所有痕跡都消失了,而僅僅指在特定的社會框架中記憶行為的缺失。這樣一來,公眾記憶中的事件才能被回避、壓抑、禁止或難以言說。但記憶(例如西班牙流感)往往會繼續在家庭或地區范圍內——再或者在科學的專業話語中——繼續存在。
二、疫情期間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在新冠大流行期間發揮了什么作用?疫情經歷觸發了哪些回憶?哪些應對策略被挖掘了出來?在疫情期間可以觀察到哪些記憶文化實踐?
(一)歷史類比(Historische Analogien)
充滿矛盾的是,這樣一種跨越國界的病毒卻導致了包括在記憶領域中的重新民族化:為了理解疫情現狀并使政治行動合法化,民族記憶中的歷史類比通通被搜羅了出來。首先是記憶文化中的“慣常嫌疑”(die üblichen Verd?chtigen)被激活了: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回憶了二戰期間英國人民的戰斗意志和社會凝聚力;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其首次就新冠問題的全國演講中曾六次重復了“我們正處在戰爭狀態”(nous sommes en guerre);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將2020年5月開始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和珍珠港事件進行類比(暗示“亞洲人”的偷襲),明確宣告病毒是一場“戰斗”。⑦將新冠疫情和二戰進行類比的方式在曾經的同盟國中有一定的集合和動員作用,這是形成集體身份認知的記憶模板(當時和現在都是“我們”對抗“他們/它們”⑧,更確切地說,在新冠疫情期間對抗的是“它”)。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88年在其論文集《艾滋病及其隱喻》(AidsundseineMetaphern)中所說的那樣,“戰爭”大多被用于隱喻緊急情況和巨大社會犧牲的合法化。⑨
對新冠疫情的體驗也導致了對歷史上的大流行病的回顧:一百年以來,西班牙流感首次受到了廣泛關注;瘟疫和艾滋病也成了公眾的焦點;出版了多部關于流行病歷史的比較研究作品,如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的《大瘟疫世紀》(DasJahrhundertderPandemien, 2021);關于流行病主題的經典文學作品——從薄伽丘的《十日談》、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紀事》(DiePestzuLondon, 1722),到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鼠疫》(DiePest, 1947)——出人意料地再次成為暢銷書籍,被重新閱讀和討論。
(二)(壞的)思維習慣(Denkgewohnheiten)
疫情重新激發了陳舊的刻板印象。用傳染、疾病和墮落等表達方式來掩飾對它者的恐懼,這一習慣由來已久。早在中世紀,猶太人和妓女就被認為是淋巴腺鼠疫的源頭。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能長達數千年的負面刻板印象和替罪羊思維突然重新出現。甚至包括那些人們認為早已被摒棄的思想,重新回歸的刻板印象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2020年春季在維基百科上發布的“2019年冠狀病毒大流行相關排外及種族主義”(Xenophobie und Rassismus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COVID-19 Pandemie)⑩列表證明了這一事實,它列出來數百項條目,從尼日利亞的恐華癥到德國的反日歧視,再到美國的反猶主義等等。刻板印象是內隱的文化模板和思維習慣,通過代際記憶和媒介文化得到傳播,但在這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
在政治領域,人們戰略性地使用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刻板印象,在疫情期間就預設了未來的集體記憶。對于流行病名稱的爭論并非是新鮮事物: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這個名字,僅僅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立國西班牙是首個公開承認受到流感襲擊的國家,而戰爭強國的審查機制掩蓋了受到流感襲擊這一事實。盡管這一名稱是不恰當的,但它仍然被保留在集體記憶中,以致形成了某種歷史假象。為了防止“前瞻性回憶策略”(prospektive Erinnerungspolitik)此類做法,自2015年起,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避免對流行病進行污名化或者誤導性命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這一名稱就是這一努力的結果。
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當前的危機是集體記憶的檢索標記。這些更新了的記憶涵蓋了對歷史類比的梳理,似乎被遺忘的刻板印象的再度出場以及刻板印象的戰略性功能化。
(三)檔案和紀念
目前可以看出,歷史類比思維是業已結束定位和應對疫情的第一階段,對特定歷史事件的搜尋暗含了一種歷史循環觀。隨著2020年秋季第二波疫情的到來,整個社會似乎已經處在了疫情的全盛期,作為歷史事件的新冠疫情的唯一性和獨特性已經顯現出來。現在,集體記憶不再以過去而是逐漸以未來為導向。
新冠疫情檔案館的成立就是證明。在德國,最著名的此類檔案館是在線新冠疫情檔案館(Onlineportal Coronarchiv),該檔案館共收錄4000多篇稿件,其中收錄了“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經歷、思考、媒體和回憶”。人們在全世界范圍內發起了數百場活動,目的在于將疫情危機下的經歷記錄下來。許多博物館已經開始創建自己的新冠疫情陳列館。所有這些活動都基于這樣一種認識:人類社會正處在歷史性的時刻,而導致其出現的源頭應該讓后代了解和銘記。
文學和藝術也試圖描寫和刻畫疫情肆虐的當下,以保存下來留給未來。由蘇格蘭詩人卡羅爾·安·達菲(Carol Ann Duffy)發起的“在我們現在的位置去書寫”(Write where are we Now)項目已經發展成為大型國際詩歌集,收錄了在疫情期間創作的詩歌。新冠疫情漫畫也屬于世界范圍內以新冠疫情為主題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朱莉·澤(Juli Zeh)的《關于人》(überMensch)和西婭·多恩(Thea Dorn)的《慰藉——給馬克斯的信》(Trost.BriefeanMax)是德國首批關于疫情的小說,這種將生活經歷加工成文學內容的速度令人驚嘆,尤其是當人們將它與一戰后的文學作比較時會發現,直到一戰結束十年后才開始出現與之相關的文學作品,又或者人們可以回憶一下,德國等待它的“轉折小說”(Wenderoman)究竟等待了多長時間。
人們在疫情期間就已經開始以各種方式開展對疫情的回憶。疫情持續至一周年時,人們舉辦了首次正式的紀念儀式:2021年3月18日(意大利新冠受難者國家紀念日),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在貝爾加莫為死難者獻上了花圈;德國聯邦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在2021年4月18日主持了新冠受難者紀念儀式。對逝者的紀念[在揚·阿斯曼(Jan Assmann)看來是文化記憶的“原初場景”(Ur-Szene)[5]],不在事件結束后才進行,而是在其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恰好是在國家層面上具有象征含義的第一年結束時)。除了這種公共的、具有傳統性質的國家紀念活動,還有草根紀念活動,其中包括在泰晤士河旁未經授權的國家新冠疫情紀念墻,人們在墻上畫下數千顆紅心并寫下了多個疫情紀念網址。
三、疫情之后的集體記憶
疫情之后,人們會記住什么?面對現狀,人們不禁想說:所有的一切!我們的記憶文化以自我反省為特征,因而我們能夠強烈意識到自己正身處歷史時刻之中,對新冠疫情的特殊的歷史化也無處不在。西班牙流感時期,人們沒有設立疫情期間真實經歷的檔案。而新冠疫情時期的每秒鐘的經歷似乎都被儲存在數字媒體中,這也正是新冠疫情的特點。這是世界上首次經歷和記載下的數字化的疫情,是新媒體時代全球記憶生產的測試性案例。但問題是,在未來將有哪些媒介化了的經驗、觀點和敘事將被儲存在主流記憶文化中?畢竟集體記憶具有高度選擇性。一方面,集體記憶的產生和維持取決于自上而下的紀念行為。問題在于:會引入(國家以及國際性的)新冠疫情紀念活動嗎?會建立疫情博物館嗎(或許會在現有檔案和資料的基礎之上)?學習流行病相關知識會成為學校教學計劃的一部分嗎?另一方面,集體記憶還有其他形式,也就是以共有的、深刻感受的經驗為基礎的、自下而上的動態記憶,代際記憶(Generationsged?chtnisse)便是其中的一例。
(一)代際和記憶
新冠疫情期間很可能會產生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說的“一代人”(Generation),即一個在形成期受特殊經歷深刻影響的(從而定義自己或被他人定義)、年齡大致相同的群體。通常認為,“形成期”(formativperiode)或“關鍵期”(kritische Jahre)介于17歲至24歲之間。社會學研究表明,在這一階段發生的事件極容易影響其政治信念。認知心理學研究以自傳體記憶中的記憶突點(reminiscence bump)為出發點:我們記得最清楚的事就發生在形成期。
尤其對于年輕一代來說,疫情是極其重大的事件。中小學和大學都暫停教學,人們不能參加大型聚會、出國或者舉行慶典儀式(例如畢業派對),而在這一地區,正是這些活動決定了青少年和成年早期階段。因此,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新冠疫情將作為代際記憶被保存下來。“疫情歲月”(Corona-Jahre)的經歷是否會跨過代際的界線,這個問題將取決于我們在回顧疫情時是否會把它視作變革性事件(它不僅僅是重大事件,而且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了家庭和社會)。
(二)大流行敘事
集體記憶的基礎是選擇——選擇要記憶的元素(由于大腦容量的關系能被記憶的東西非常少)——以及敘事結構化,即以連貫敘事的方式排列記憶要素。那么,新冠疫情在未來將被如何講述?敘事結構是集體記憶的基礎,因為每次經歷和每件歷史事件都會被追溯到它的開始、經過和結局。對歷史理論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來說,“通過敘事結構化來進行解釋(情節化)”(Erkl?rung durch narrative Struktur)是講述歷史的開始[6],因此,敘事和敘事結構都是無法避免的。但問題是,現如今反事實敘事與被肆無忌憚簡化了的、虛假的陰謀神話,在和基于事實進行的(沒有那么令人興奮的)敘事爭奪進入集體記憶的機會。為了把復雜事件和在疫情期間的不同經歷盡可能準確而有效地轉化到集體記憶中,需要哪些敘事結構呢?
與所有的流行病一樣,新冠疫情也提出了特殊敘事挑戰。流行病是自然災害,而自然災害很難被講述——至少在我們現代記憶文化框架內是這樣,因為它正是在經歷了20世紀的世界大戰、大屠殺、國家恐怖主義、專制政權以及全球恐怖組織等事件后成型的。這些敘事(有充分的理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規范性的,它們強調個人和社會的過失、罪責和責任。
但是在一場由RNA序列引起的災難中,誰是“肇事者”?該如何重新定義“英雄”?“受害者”又是誰?什么是“歷史教訓”?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未來的記憶文化必須學會以“隱含主體”(impliziertes Subjekt)的思維模式在后人類框架中更有力地運作[7-8],此時需要的不是前現代或現代的記憶方式,而是我認為的“相互關聯”(relational)的回憶方式,而這又指的是什么呢?
(三)相互關聯的回憶
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風險社會”(Weltrisikogesellschaft)中,災難在許多人的共同協作下發生,而個人卻沒意識到自己的罪責。[9]“隱含主體”[7]這一概念,指的是導致災難的系統中的能動部分。在社會的不公、種族主義、饑餓、氣候變化和物種滅絕等情況下,盡管不容易定義罪責和犯罪者,甚至他們自己也會成為受害者,但是大多數人(尤其是在西方)作為隱含主體應該對此承擔責任。
在后人類框架中接受這一思維模式意味著承認我們與非人類主體如動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共同處于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關系中[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稱之為“共生”(sympoiesis), 簡·貝內特(Jane Bennett)則稱之為“分配代理”(distributive agency)]。[10-11]在新冠疫情中,病毒的RNA出現變異和跨物種傳播的趨勢,這一現象伴隨著人類入侵野生動物棲息地,正是這種入侵使得病毒的“跳躍”——流行病的開端——成為可能。疫情大流行幾乎不能歸因于明確的原因或確定的肇事者,如斯諾登寫的那樣,它們“并不是隨機事件[……]它們隨著環境破壞、人口過剩和貧困而蔓延”[1]505。
2021年,我們同時經歷了一場全球流行病、洪災、火災以及極地冰川融化,因此人們可以認為,新冠疫情將在集體記憶中與氣候變化相關事件聯系在一起。將來,人們回憶起新冠疫情時是否會把它當作氣候歷史上的轉折點或者臨界點,這個問題只能在數年后才能得到解答。
【注釋】
① 原文出自Astrid Erll,PandemieundKollektivesGed?chtnis.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GeschichteundErinnerung. APuZ, 2021年10月4日, 本文獲得作者授權譯發。 摘要、 關鍵詞為譯者所加。——譯注
② 參見: Maurice Halbwachs,DasGed?chtnisundseinesozialenBedingungen, Frankfurt/M. 1985 (1925); ders.:DaskollektiveGed?chtnis, Frankfurt/M., 1991 (1950)。 ——原注
③ “記憶研究協會”于2016年成立。 參見: www.memorystudiesassociation.org。 ——原注
④ 參見: Astrid Erll,KollektivesGed?chtnisundErinnerungskulturen, Stuttgart, 2017。 ——原注
⑤ 參見: www.bundeskanzlerin.de/bkin-de/aktuelles/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in-merkel-1746554。 ——原注
⑥ 再媒介化作為集體記憶的動力。 參見: Astrid Erll/Ann Rigney (Hrsg.),Mediation,remediation,andthedynamicsofculturalmemory, Berlin, 2009。——原注
⑦ 2020年3月16日, 特朗普推特發文明確提到“中國病毒”。 國內外多家媒體對此進行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3月20日對此進行回應, 具體可參考網頁: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2088541.html。——譯注
⑧ 德語中的“他們”、 “她們”和“它們”都是“sie”, 此處既指法西斯聯盟又指新冠病毒。——譯注
⑨ 參見: Susan Sontag,KrankheitalsMetapher/AidsundseineMetaphern, Frankfurt/M., 2012 (1988)。 ——原注
⑩ 參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cidents_of_xenophobia_and_racism_related_to_the_COVID-19_pandemic#cite_note-dw52862599-3。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