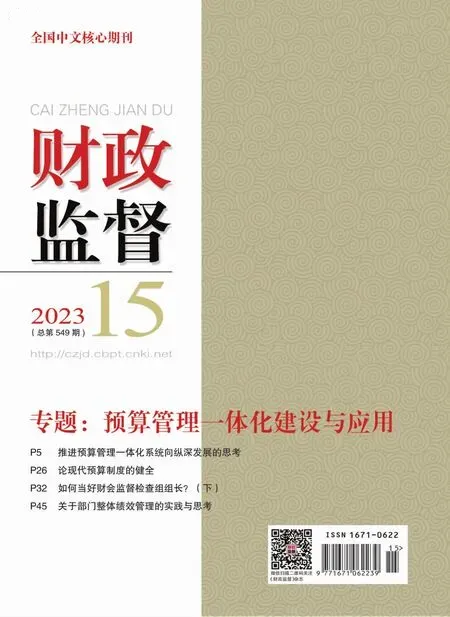后BEPS 時代國際稅收情報交換與反避稅治理研究
●王文靜 鄭皓茹
大數據的發展,不僅為商業經濟帶來廣闊的市場前景,也為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有利機遇。 具體到稅收征管領域,大數據的應用成效日益凸顯,數據信息成為政府反避稅治理的重要工具。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OECD”)和二十國集團(簡稱“G20”)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簡稱“BEPS 行動計劃”)的推動下,稅收情報交換成為打擊跨國企業激進避稅行為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聚焦于國際稅收情報交換的最新發展,并對實踐中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我國深度參與國際稅收情報交換、提升國際稅收治理水平提供相關建議。
一、BEPS 行動計劃下國際稅收情報交換的新發展
早期國際稅收情報交換的開展,主要依據避免所得和財產雙重征稅的國際稅收協定中的情報交換條款以及專項的稅收情報交換協定。 在BEPS 行動計劃的推動下, 國際稅收情報交換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交換的情報進一步聚焦到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稅收裁定信息、國別報告信息等特定主題,參與交換的國家(地區)范圍極大拓展,情報交換的數量與頻率大幅提升,情報交換在打擊跨境避稅和偷逃稅方面的功能效用日益顯著。
2014 年OECD 發布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簡稱“AEOI標準”),致力于在多邊范圍內推動實施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的自動交換。截至2023 年5 月16 日,簽訂《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多邊主管當局間協議》 的國家(地區) 已達到120個, 第一批信息交換的時間是2017年9 月, 截至2022 年10 月產生的雙邊交換關系已超過4900 項,覆蓋110多個國家(地區)①。 參與交換的國家(地區)不僅包括高收入經濟體,也包括中、低收入經濟體。 百慕大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開曼群島、馬恩島、澤西島等國際避稅地也已加入并實施信息交換。
作為BEPS 行動計劃的最低標準之一,第5 項行動計劃(考慮透明度和實質性因素,有效打擊有害稅收實踐)要求交換稅務機關簽署的特定類型稅收裁定信息,以便發現有害稅收實踐的存在,更有針對性地打擊跨國企業利用特定稅收工具或政策實施激進避稅行為。 以稅收裁定信息交換為例,在實施交換的第一年(2016 年)就已進行了6000 次交換,在2017 年上升至14000 次,截至2021 年結束已累計交換約50000 次②。
第13 項行動計劃(轉讓定價文檔和國別報告)也是BEPS 行動計劃的最低標準之一。 根據該項行動計劃,符合條件的跨國企業需要填報國別報告, 稅務機關之間自動交換國別報告信息,相關國別報告信息被稅務機關用于識別評估跨國企業的跨境避稅風險。 截至2023 年6 月8 日已有97 個國家(地區)簽訂了《國別報告交換多邊主管當局間協議》,自2018 年6 月開始第一次信息交換,截至2022 年10 月產生的雙邊交換關系已超過3300 項③。
除此之外,歐盟內部范圍也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情報交換, 不僅涵蓋前文所述三種信息類型,還進一步拓展至反洗錢信息、中介機構和納稅人所掌握的跨境安排信息、 平臺賣家信息、加密資產和電子貨幣信息等。在歐盟法律制度的強有力約束下, 歐盟內部的信息交換進展較為順利,為區域跨境稅收情報交換合作積累了有益的實踐經驗。
不難發現,當前國際稅收情報交換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呈現出以下典型特征:
(一)稅收情報交換的內容和類型更加豐富
國際稅收協定的情報交換條款所涉及的內容范圍較窄,僅限于協定相關。例如,我國和新加坡簽訂的國際稅收協定中第二十五條 “情報交換”,將內容范圍限定為與協定執行相關的事項,以及協定所涉及稅種的國內相關法律。相比較而言, 專項稅收情報交換協定的內容范圍較為廣泛,但是締約一方大多為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巴哈馬等國際避稅地,這些國際避稅地通常未開征所得稅或者所得稅率為零。
與傳統的稅收情報交換相比,新實施的稅收情報交換在內容和類型方面實現了質的轉變。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交換,將情報交換的內容延伸到了非居民的金融賬戶,不再局限于涉稅數據本身,而是收集個體(包括企業和自然人)的金融賬戶信息并交換至其居住國。稅收裁定信息交換,則是將情報交換的內容拓展到稅收征管領域的稅收裁定文件。稅收裁定制度作為一項事前審批制度,在為納稅人提供稅收確定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簽署的稅收裁定通常不對外公開,在一些實施裁定信息公開的國家(例如美國、澳大利亞等)也僅為匿名公開(吳東明,2018)。 BEPS 第5 項行動計劃要求交換稅收裁定信息,正是發現了這一稅收工具的潛在扭曲風險,致力于打擊跨國企業在一些國家(地區) 利用隱形稅收優惠大幅降低實際稅負的行為。 國別報告信息交換聚焦于跨國企業集團內部信息,BEPS 第13 項行動計劃要求上一年度合并財務報表收入達到7.5 億歐元及以上的跨國企業提交國別報告,該報告涉及跨國企業集團內部的運營布局、利潤分配、納稅情況、經濟活動與功能風險等信息,并在所涉及國家(地區)的稅務機關之間進行交換。
(二)稅收情報交換的形式由雙邊拓展為多邊
從交換形式來看,盡管上述三種新類型的情報交換仍呈現的是雙邊交換關系,但是不同于傳統稅收情報交換的雙邊形式,新型情報交換的雙邊關系進一步構筑了多邊信息交互網絡,從本質上來說屬于多邊信息交換。 基于多邊主管當局間協議,情報交換在多邊范圍內實現統一行動。 金融賬戶涉稅信息交換可以實現“多對一”的交換形式,某一納稅人的居住國稅務機關,可以接收到來自該納稅人在其他多國(地區)的金融賬戶信息。 國別報告信息交換則能夠實現圍繞單一對象的“一對多”交換形式,一家跨國企業集團的國別報告信息,可以由其最終母公司居住國稅務機關交換給集團內部其他公司所在地的稅務機關。
(三)稅收情報交換的模式由被動升級為自動與主動
傳統的稅收情報交換主要依托締約一方發送申請的模式,這種被動模式下的交換效率整體偏低。 相比較而言,稅收情報交換的自動性與自發性,能夠顯著提升信息的時效性。在BEPS 行動計劃下,情報交換不僅成為打擊跨境避稅和偷逃稅的重要工具,國際反避稅共同行動也對情報交換的效率提出全新要求。 在多邊協議的法律約束下,稅收情報交換得以更高頻、更廣泛地實施。 自2016 年以來,稅收裁定信息、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國別報告信息相繼在全球較廣范圍內進行交換,交換數量、交換頻率、交換范圍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稅收情報交換的局限性,充分體現出新型情報交換的效率優勢。
(四)稅收情報交換的參與主體拓展至非稅務部門
特別是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 進一步將信息的收集主體拓展至各類金融機構。 根據AEOI 標準下的共同申報準則 (簡稱CRS),金融機構在非居民身份識別和金融賬戶信息收集報送方面發揮關鍵性作用。 稅務機關之間交換的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均來自金融機構報送的數據, 這與傳統情報交換主要由稅務機關收集信息存在顯著區別。除此之外,國別報告信息交換也將參與主體拓展到跨國企業, 符合條件的跨國企業需要額外填報國別報告信息, 稅務機關之間交換的信息來自跨國企業自主填報的信息。
(五)稅收情報交換的信息體例更加統一
傳統的稅收情報交換并未設置固定的信息報送規范體例, 但是在多邊情報交換機制下,信息交換的數量大幅增長,涉及的國家(地區)更為廣泛,信息體例的統一性對于信息的交換效率和使用效率尤為重要。共同申報準則和國別報告均采用統一的信息采集體例和規范,不同國家(地區) 稅務機關能夠無障礙地匯集整合這些信息,為國際反避稅合作提供了有利支持。
二、 當前國際稅收情報交換合作面臨的現實問題
盡管已有研究表明BEPS 行動計劃以來的稅收情報交換在打擊跨境避稅與偷逃稅方面具有較為顯著的效果, 但是其局限性仍不容忽視。例如,Casi 等(2020)發現CRS 導致在避稅地的境外存款減少了11.5%,但是并未加入CRS 的美國成為對跨境存款頗具吸引力的選址地。 Joshi(2020) 對歐盟內部的國別報告信息交換效應進行了檢驗, 發現歐盟2016 年實施國別報告信息交換之后,相關跨國企業的實際稅率增加了1—2 個百分點,但是跨國企業受稅收因素驅動的利潤轉移行為在2018 年才有所減少。 稅收情報交換效應的有限性一方面來自這一方式本身的理論自限性,另一方面可能來自執行過程中的實踐偏誤。
本研究顯示,實驗組老年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滿意水平高于對照組,P<0.05;實驗組術后治療的依從性評分、住院時間優于對照組,P<0.05;護理前兩組血氣分析的相關指標以及焦慮情緒相似,P>0.05;護理后實驗組血氣分析的相關指標以及焦慮情緒優于對照組,P<0.05。實驗組術后肺部感染及呼吸衰竭等老年非小細胞肺癌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
(一)稅收情報交換的自身局限性
盡管稅收情報交換能夠為打擊跨境避稅和偷逃稅提供關鍵性的信息支持,但是這一方式也有其自身局限性。 第一,稅收情報交換的實際效果與交換網絡密切相關,未參與情報交換的國家(地區)往往會成為利潤或資產的新選址。不同于固定資產,隱藏和轉移金融資產通常較為便捷且更不容易被發現。在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交換方面, 如果納稅人擁有雙重或者多重稅收居民身份,很大概率可以暫時規避相關國家(地區)金融機構的信息收集環節,從而在一定時期內避免金融賬戶信息被其他國家(地區)稅務機關發現,納稅人也因此具備了實施資產轉移的時間機會。第二,在稅收情報交換變局下,納稅人通常會采取一定的應對策略,例如跨國企業可以選擇不申請或者不續簽稅收裁定,以規避裁定信息交換下的潛在稅務風險。 第三,稅收情報的使用效率存在不可忽視的現實局限性,這主要受制于國別(地區) 之間的稅制差異以及國際反避稅能力差異。例如,稅收裁定信息通常涉及一國(地區)的稅制規定和征管慣例,國別(地區)的稅收裁定實踐因此存在較大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信息接收方對稅收裁定信息的使用效率。
(二)信息采集成本視角下的第三方參與積極性與行動準確性
稅收情報交換協定明確了信息采集過程中的成本負擔問題,例如根據我國與開曼群島簽訂的稅收情報交換協定,第十條“管理費用”規定“為提供協助而產生的日常費用由被請求方負擔,提供協助的非日常費用(包括在訴訟中聘用外部顧問等的費用) 應由請求方負擔”。 在實踐中,成本因素往往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情報交換的時效性、積極性和準確性。 尤其是將信息采集的工作交由非稅務部門時,委托代理難題不容忽視。 例如,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交換已覆蓋110多個國家(地區),但是這些國家(地區)金融機構在規模、人員、管理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即便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在制度管理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這些機構自身差異可能進一步帶來參與積極性與行動準確性方面的差異。 金融機構需要配置相應的人力和物力開展非居民身份的識別和金融賬戶的信息收集和報送工作。 尤其是非居民身份識別具有較強的稅收專業性,如果僅靠客戶自行申報聲明,可能存在較多偏誤。 考慮到這些額外的成本負擔,金融機構的參與積極性和行動準確性很可能會低于政策預期。
(三)國別(地區)信息交換錯配關系
盡管多邊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稅收情報交換的共同行動效率, 但是在當前稅收情報交換實踐中,國別(地區)之間的行動不一致性問題仍不可避免。 例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并未參與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交換, 而是繼續實施其主導的海外賬戶納稅遵從法案, 使得參與AEOI 標準的國家(地區)稅務機關無法掌握其稅收居民在美國金融賬戶的信息, 而美國通過該法案仍可以獲取其稅收居民在海外的賬戶信息。 稅收裁定信息交換則較多受到各國 (地區)稅收裁定實踐差異的影響。 例如,百慕大群島、開曼群島等純避稅地并未開征所得稅,也不實施稅收裁定制度, 因此并不屬于稅收裁定信息交換的范圍。 再如,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稅收裁定實踐相對偏少,發送的裁定數量也較少; 而常被稱為導管避稅地的荷蘭、比利時則交換了數量可觀的裁定信息。 除此之外,國別報告的發送國(地區)與接收國(地區)之間的錯配現象同樣存在,這主要受到資本跨境流向的影響, 跨國集團最終母公司的聚集地很可能成為國別報告的主要發送國 (地區),但是該國(地區)不一定能從相應的國別報告接收國(地區)獲取到較為對等的信息量。 這些錯配關系的存在,將直接導致不同國家(地區)在稅收情報交換方面的受益性差異, 從而可能進一步影響相關國家(地區)后續信息交換的積極性和可持續性。
(四)稅收情報交換在不同經濟發展體之間的不對等關系
在實踐中,與發達國家(地區)之間大規模的信息交換情形相反,發展中國家(地區)參與的信息交換明顯偏少, 存在稅收情報交換的不對等關系。 例如,2020 年僅有2 個發展中國家(地區)向其他國家(地區)交換了稅收裁定信息,而這一年全球整體的交換次數達到5000 次;再如,2022 年僅有5 個發展中國家(地區)能夠接收來自境外的國別報告④。 這一不對等關系,與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實力差異有關,也與稅收治理能力差異密切相關。發展中國家(地區)在國際稅收情報交換中的參與程度有待全面提升。
三、 我國參與國際稅收情報交換的機遇與挑戰
除了根據國際稅收協定和稅收情報交換協定開展信息交換之外, 在BEPS 行動計劃背景下我國⑤也積極參與了非居民金融賬戶、 稅收裁定和國別報告的信息交換, 發送了數量可觀的涉稅信息, 在國際稅收情報交換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AEOI 標準框架下,2018—2022 年間我國發送信息的目的地國家(地區)數量由52 個增加至76 個,2021 年我國共有2627 家金融機構進行報告,覆蓋18994224 個金融賬戶⑥。 我國報告的金融賬戶數量規模不僅遠超百慕大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開曼群島、馬恩島、澤西島等國際避稅地,以及瑞士、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等歐洲避稅地,也遠超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 在稅收裁定信息交換方面,2021 年我國稅務機關簽署的屬于BEPS 第5 項行動計劃信息交換范圍的稅收裁定共有4 份;同年發送稅收裁定信息的次數為31 次, 且均為轉讓定價主題,這一數量高于英國、法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⑦。 在2016—2021 年間, 我國接收的稅收裁定信息同樣以轉讓定價主題為主,其次是稅收優惠制度,還涉及常設機構、應稅利潤調整、關聯導管公司、知識產權制度等主題,信息來源方既包括美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發達國家,也包括印度、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還包括比利時、瑞士、荷蘭、盧森堡、新加坡、庫拉索等避稅地。 表1 展示了2021 年的具體情況。

表1 2021 年我國接收的稅收裁定信息概況⑧
我國在國際稅收情報交換中呈現出不同于發達國家(地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特殊性,這與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現實情形密切相關。在當前國際稅收環境下,我國運用稅收情報交換開展國際反避稅治理既迎來機遇也面臨挑戰。
(一)大規模外資進入和對外直接投資環境下的國際反避稅治理
跨境資本流動背后可能代表真實的經濟活動,也可能隱含跨國企業的避稅行為。我國既是資本流入大國,也是資本流出大國,很多跨國企業在我國設立子公司或者分支機構, 我國也有大量企業“走出去”,加強我國的國際反避稅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傳統的雙邊稅收情報交換模式下,我國積極履行情報交換責任,但是締約另一方的積極性和時效性可能并不高, 從而會限制稅收情報交換的反避稅功能。 在BEPS 包容性框架下,多邊的、及時的情報交換為我國稅務機關有效識別跨境資本流動背后的稅基侵蝕行為帶來了全新的反避稅治理機遇。 根據所獲取的稅收裁定信息和國別報告信息, 我國稅務機關可以更好地掌握我國“走出去”企業(尤其是大型跨國企業)在境外的稅務安排與實際稅負情況。但是,與很多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偏好于在歐洲國家設立公司不同,我國企業“走出去”更多是在發展中國家(地區)設立公司,而發展中國家(地區)在信息交換方面的劣勢地位, 會進一步影響我國的信息獲取情況,這正是當下我國所面臨的特殊情報交換困境。
(二)信息技術發展背景下的大數據反避稅治理
隨著多邊信息交換的深度發展, 提升稅收情報的使用效率成為當前國際反避稅工作面臨的新挑戰。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進步尤其是數據挖掘技術的發展, 為開展大數據背景下的稅收治理提供了有利機遇。第一,大數據領域的信息技術有助于高效實現不同類型稅收情報之間的識別匹配。目前可獲取的國際稅收情報既包括內容和體例差異較大的涉稅信息(與執行國際稅收協定有關的涉稅信息、 專項稅收情報交換協定下的個案涉稅信息、稅收裁定信息),也包括主題和體例較為統一的涉稅信息(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國別報告信息)。 打通這五類信息之間的內在關聯,有助于識別出更多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風險點。第二,智能化數據挖掘分析有助于稅務機關在面對海量非本土語言數據時更及時、準確、有針對性地開展稅務稽查工作。但是,由于國際避稅和偷逃稅行為的隱蔽性和復雜性, 完全依賴計算機系統和人工智能并不可行, 仍需同步提升稅收專業人才的數字化水平,將兩者優勢相結合。
(三)國際稅收情報交換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地區)稅收利益維護
無論是傳統的雙邊稅收情報交換, 還是當前BEPS 行動計劃下的多邊稅收情報交換, 均由OECD 主導,主要代表以OECD 成員為主的發達國家(地區)稅收利益,這也是國際稅收規則的博弈格局現狀。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且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在參與國際對話時不僅需要主張自身的稅收利益,還需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地區)發聲,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爭取合理的稅收利益。 具體到稅收情報交換這一國際反避稅合作領域,加強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稅收情報交換能力、稅收情報利用效率的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地區)分擔稅收情報交換成本,提升發展中國家(地區)在稅收情報交換中的收益,才能更好地實現不同經濟發展體之間稅收情報交換的可持續性。
四、國際稅收情報交換下加強我國反避稅治理的相關建議
隨著BEPS 多項行動計劃逐漸落地,國際反避稅環境持續發生變化。在此背景下,建議我國積極把握稅收情報大數據與信息技術帶來的機遇,進一步提升國際反避稅治理能力, 持續深度參與全球稅收治理。
(一)構建境內外一體化稅收情報收集與分析體系
在當前國際稅收情報交換背景下, 建議我國進一步探索境內跨區域之間的稅收情報交換,同步實施境內信息交換與跨境信息交換。 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 將境內外稅收情報進行多維度識別匹配,構建一體化稅收情報分析體系,將境內稅收風險與跨境稅收風險進行協同識別處理。 以涉稅信息為連接點,打通境內外反避稅治理工作機制,全面提升國際稅收情報的利用效率。 與此同時,增加對境內信息收集方與提供方(例如AEOI 標準下的金融機構、 符合國別報告填報條件的跨國企業)的監管,降低相應的信息偏差風險。
(二)綜合協調稅收情報交換與其他國際反避稅措施
一方面, 針對稅收情報交換在打擊國際避稅和偷逃稅方面的局限性, 可以通過實施其他反避稅措施予以彌補。 例如, 正在全球廣泛推進中的數字經濟征稅“雙支柱”方案,盡管一些跨國企業可以通過特定方式規避涉稅信息交換以降低實際稅負,但是“支柱二”方案中的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為大型跨國企業設置了15%的最低實際稅負水平, 預期該規則能夠有效打擊大型跨國企業的激進避稅行為。 另一方面, 稅收情報交換可以進一步增強其他反避稅措施的實施效果。 在國際反避稅行動中, 我國稅務機關可以依托大數據信息分析提升涉稅信息的處理利用效率, 從而更高效地助力受控外國公司法規、 非居民間接股權轉讓管理等其他反避稅措施的實施。
(三)共建“一帶一路”稅收情報交換反避稅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旨在為“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提供便利支持, 助力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 該機制打破了傳統地理區位限制,以一種“泛區域”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推動不同經濟發展體之間的稅收交流與合作,尤其為更多發展中國家(地區)提供稅收治理支持。 建議我國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下進一步推動國際稅收情報交換的“泛區域”深度合作,并助力發展中國家(地區)全面提升稅收情報交換反避稅治理能力。
注釋:
①③資料來源于OEC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CRS[EB/OL].(2023-06-08). https://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internationalframework-for-the-crs/.
②⑦⑧資料來源于OECD.2022. Harmful Tax Practices-2021 Peer Review Reports o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Tax Rulings [R]. Paris:OECD Publishing.
④資料來源于OECD.2022. G20/OECD Roadmap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Taxation:OECD Report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R].Paris:OECD Publishing.
⑤基于稅收管轄權的考慮,本文關于“我國”的討論僅限于“我國境內”。
⑥資料來源于OECD.2022.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2[R]. Paris: OECD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