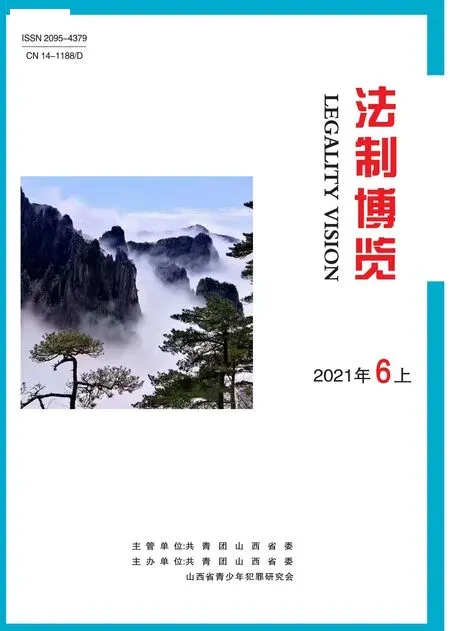對《專利審查指南》“補交實驗數據”章節修改的思考
譚 磊
(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北京 100088)
為全面貫徹國家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知識產權的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關于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第391號公告并于2021年1月15日施行[1]。此次修改,進一步明確了依據《專利法》進行專利審查的審查標準,其中關于發明專利補交實驗數據部分的修改對申請人獲得專利權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修改的背景
隨著經濟科技快速發展,我國逐漸從知識產權引進大國轉變為知識產權創造大國,對知識產權工作的要求已經從追求數量轉變為提高質量。為適應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提升以及知識產權審查規則的需要,我國正逐步修改知識產權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專利審查指南》也適應性進行了修改。
自國家知識產權局于1993年頒布實施第一版《專利審查指南》以來,在隨后的近三十年中,《專利審查指南》經歷了多次修改。國家知識產權局先后于2001年、2006年和2010年公布了三版《專利審查指南》。2010年之后,國家知識產權局本著適應性修訂為主的修訂原則,分別在2013、2014、2017、2019、2020年以國家知識產權局第67號、第68號、第74號局令及第328號、第343號、第391號局公告的形式,公布了關于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決定,對《專利審查指南》相關章節進行了修改。
在《專利審查指南》的歷年修改中,與“補交實驗數據”相關的章節部分由于對專利審查授權和確權具有重要影響,也經歷了多次修改。從申請人獲得專利權的過程來看,在專利申請階段,發明專利申請人在提交的原始申請文件中通常記載有實施例和實驗數據,其目的是證明發明技術方案能夠取得某種技術效果,而這種技術效果的確定將影響多個法律條款的適用。在專利審查過程中,面對審查員提出的專利申請說明書公開不充分或者權利要求不具備創造性等審查意見時,申請人需要提供補交實驗數據以進行針對性答復,例如通過補交實驗數據證明說明書確實具有聲稱的技術效果從而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下稱《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關于說明書應當充分公開的要求,或者通過補交實驗數據證明權利要求的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相比取得了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從而符合《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關于發明應當具備創造性的要求。由于專利申請“補交實驗數據”的規定對于申請人的專利申請行為、專利審查過程中的合理應對、申請人獲得專利授權等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對于《專利審查指南》“補交實驗數據”章節修改的研究,在知識產權領域具有豐富的理論研究價值和對實際操作的指導意義。
二、修改的內容
關于“補交實驗數據”在《專利審查指南》(1993年版)第八章中規定“補入實驗數據,以說明發明的有益效果,或補入實施方式和實施例以說明在權利要求保護范圍內發明能夠實施。但是這些補充內容可以放入申請案卷中,供審查員審查專利性時參考”。在《專利審查指南》(2001年版)中進一步將前述版本指南中所述的“專利性”明確為“新穎性、創造性或實用性”。在《專利審查指南》(2006年版)中要求“判斷說明書是否充分公開,以原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記載的內容為準,申請日之后補交的實施例和實驗數據不予考慮”[4]。在《專利審查指南》(2010年版)第二部分第十章中仍然維持了上述規定,即“申請日之后補交的實施例和實驗數據不予考慮”。2017年修改《專利審查指南》(2010年版)時在第二部分第十章新設第3.5節“關于補交的實驗數據”,將“申請日之后補交的實施例和實驗數據不予考慮”修改為“對于申請日之后補交的實驗數據,審查員應當予以審查。”[5]
2020年對《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3.5節“關于補交的實驗數據”部分做出較大修改,在第3.5節下新增第3.5.1節“審查原則”和第3.5.2節“藥品專利申請的補交實驗數據”。其中,第3.5.1節修改內容涉及“對于申請日之后申請人為滿足《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第二十六條第三款等要求補交的實驗數據,審查員應當予以審查”。第3.5.2節內容為“按照本章第3.5.1節的審查原則,給出涉及藥品專利申請的審查示例”。同時,對于示例1和示例2也進行了修改。以上為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修改中涉及發明專利補交實驗數據的章節內容,也是《專利審查指南》關于專利申請補交實驗數據的最新要求。
三、修改的影響
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中新修改的“補交實驗數據”章節,將之前版本指南中關于“補交實驗數據”的原則性規定進行具體細化并適應性修改了兩個具體案例,首次明確了適用的法律條款即《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第二十六條第三款,也首次對具體發明領域提出適用要求即涉及藥品專利申請,進一步明確了審查中對于申請日后提交的效果實驗數據的審查標準。
(一)對發明專利審查的法律層面的影響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專利法和本細則制定專利審查指南。《專利審查指南》前言部分記載:“國家知識產權局作為國務院專利行政管理部門”“依據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一百二十二條制定本專利審查指南”“作為國家知識產權局部門規章公布”。可見,《專利審查指南》屬于我國法律淵源體系中的國務院部門規章,是國家知識產權局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據和審查標準,也是有關當事人在上述的各個階段應當遵守的規定。此外,根據《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門規章,必要時可以在判決書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可見,制定和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目的就是對《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中與專利行政授權、確權等事項有關的規定進行具體化。
從權力來源上,《專利審查指南》受《專利法實施細則》明確授權而制定,屬于“有權解釋”,是行政機關針對行政法律規范的意義而制定的能夠對外產生普遍的法律效力的法律規范。從內容特點上,《專利審查指南》的內容呈現詮釋性、指導性特點,同時結合審查實踐對上位法的法律規則進行類型化的示例和說明,強調可操作性與標準執行一致性,具有鮮明的“解釋”屬性,體現了專利行政程序專業性、技術性、類型化的自身特點。
《專利審查指南》在法律層面既包括行政立法,也包括行政解釋。行政立法以對法和細則中未明確提及的行政程序性事務進行規范為代表,行政解釋以從指導審查實踐的角度對法和細則中的條款進行進一步釋義和審查示例為代表。作為部門規章,審查指南在法律屬性上的類型可定義為“立法性行政解釋”。
因此,2020年針對《專利審查指南》中涉及發明專利補交實驗數據部分章節的修改,其屬于在《專利法》及其《專利法實施細則》的條款沒有修改或沒有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對上位法作出具體解釋、補入審查實務中形成共識的內容。其與以前版本對同一法律問題如“補交實驗數據”在內容和表述上存在差別,但是在法律層面仍然遵循“實體從舊,程序、解釋從新”的原則。
(二)對發明專利審查的行政授權的影響
從專利審查行政授權的角度,補交實驗數據證實的技術效果與《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的說明書應當公開充分、《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發明應當具備創造性等專利授權要求密切相關。申請人通過補交實驗數據證實專利申請說明書的公開充分以及權利要求具備創造性,在不存在其他缺陷的情況下,專利申請通常具備了獲得專利授權的條件。
從專利審查的證據角度,補交實驗數據通常應當是在請求保護的發明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之間實驗得出的,即直接證據。但申請人有時會提交間接證據,例如與請求保護的發明或者與現有技術的技術方案之一非常接近的第三技術方案的技術效果。該技術方案證實的技術效果與原始文件記載的技術效果,以及最接近現有技術中記載的技術效果之間存在關聯,能夠起到“橋梁”作用進行效果比較。
不論在審查過程中具體適用的是哪個條款或者補充實驗數據屬于哪種證據類型,專利審查應當標準執行一致,補充實驗數據所證明的事實必須是原始申請文件公開的。或者說是所屬技術領域技術人員能夠從專利申請公開的內容中得到的,不能是一個新的事實。在判斷是否能夠“得到”時,審查員應當綜合考慮現有技術狀況、專利申請文件所記載的內容等,站位本領域技術人員進行事實認定并判斷技術效果是否公開,而不是簡單取決于該技術效果在原始申請文件中是否有文字記載。判斷申請日之后申請人為滿足《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第二十六條第三款等要求補交的實驗數據能否證實申請人主張的技術效果,在專利審查的行政授權階段,通常是按照以下原則進行審查:
1.補交實驗數據應當與請求保護的發明和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密切相關,不能證明一個新的事實。
2.補交實驗數據為直接證據時,其技術方案應當介于請求保護的發明和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兩者之間,技術效果可以直接進行比較判斷。
3.補交實驗數據為間接證據時,首先,應當考察該間接證據的技術方案是否介于要求保護的發明或者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的技術方案之間,或者能否作為二者之間進行比較的中間橋梁。其次,要綜合分析本申請、補交實驗數據、最接近的現有技術,考察該補交實驗數據能否證明本申請的技術效果優于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如果本申請的技術效果優于補交實驗數據的技術效果,而補交實驗數據的技術效果優于或接近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的技術效果,則補交實驗數據能夠證明本申請的技術效果優于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如果本申請的技術效果優于補交實驗數據的技術效果,但補交實驗數據的技術效果明顯比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的技術效果差,或者不能確定其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在技術效果上孰優孰劣,則補交實驗數據不能證明本申請的技術效果優于最接近的現有技術。
審查員在依據申請人提交的補充實驗數據進行事實認定后,將以該事實為基礎進行后續的審查,并作出授予專利權或者駁回專利申請的結論。
四、結語
專利申請人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在申請文件授權方面關于補交實驗數據能否接受以及如何審查長期存在爭議。《專利審查指南》歷經近三十年的修改,補交實驗數據從供審查參考、到不予考慮、再到應當予以審查,一直到今年施行的申請日之后申請人為滿足《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第二十六條第修改內容三款等要求補交的實驗數據應當予以審查,這一爭議正在以顯著的方式逐步解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以及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專利審查指南》關于補交實驗數據的章節也將不斷完善,知識產權授權確權必將更加科學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