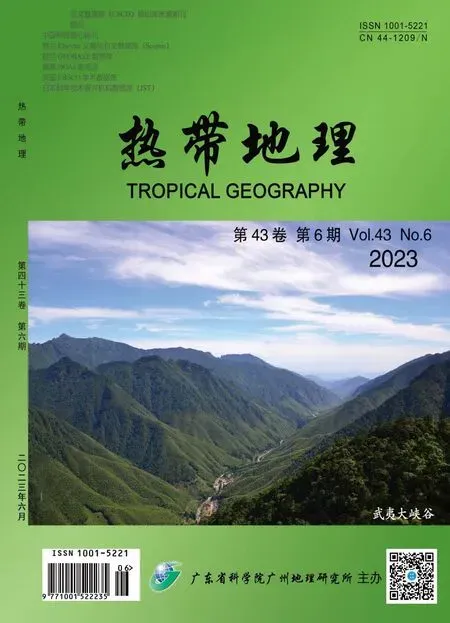背包旅行與身份構建:一名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自我民族志
孫 瓊,李 林,黃先開
(1.北京聯合大學 a.管理學院;b.旅游學院,北京 100101;2.北京工商大學 數學與統計學院,北京 100048)
“背包客”由英文backpacker 翻譯而來(解佳等,2020),指一類在旅行過程中以背包(通常指高過頭頂的背包)作為主要行李的特殊旅游者(Pearce, 1990;陳鋼華 等,2021)。與其他游客相比,在旅游動機上具有典型的逃避、求知、尋求刺激及自我身份再確立等特征(Pearce et al., 2007;Ooi et al., 2010; Hindle et al., 2015),在旅行中表現出突出的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Larsen et al., 2011;Tomazos, 2016)、追求自我發展與自我再認識(Canavan, 2018; Collins-kreine et al., 2018)等行為模式特點。由于背包客形成了獨特的群體風格并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和行為,他們通常被學者視為是社會建構中的一類特殊群體(Adkins et al., 2007;解佳 等,2020)。對大多數背包客而言,背包旅行不僅是一種旅行方式,更是一種自我身份的表達,其身份標簽包含了獨立、自由、冒險、自我轉變和個人發展的精神追求(Cohen et al., 2015;劉魯 等,2018)。目前,背包客身份建構相關研究被學術界視為背包旅行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余志遠,2014)。
受益于上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踐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人擁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旅行機會。進入90年代,背包旅行被視為一種充滿“異國情調”的旅游方式,在中國年輕人中開始流行(Zhang et al.,2018)。過去十年間,國內和國際旅行中的背包客數量顯著增加,背包旅行已成為當代青年的重要亞文化(余志遠 等,2022)。近年來,背包客群體人數在國內逐漸增多,但女性參與者仍是少數(Xu et al., 2021)。雖然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背包客行列中,但女性背包客大多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出現,其中已婚女性數量更是稀少。通過梳理“背包客身份構建”這一主題的文獻后發現,多數研究都將背包客群體作為一個整體展開分析(Zhang et al., 2017),很少關注其性別差異,對女性背包客群體及其身份構建的關注稀少。在為數不多的背包客旅游研究中,西方學者發現女性群體與男性群體在旅游模式上有明顯不同,她們往往將背包旅行視為暫時從煩瑣的日常生活中撤退的“中場休息”(Elsrud, 1998),并將其作為在遭遇個人危機(尤其是感情破裂)后重建獨立角色的途徑(Hillman, 1999)。考慮到中西方不同的社會情境及中西背包客行為的差異(Luo et al., 2015;朱璇,2018),西方的研究結論是否適用于中國仍有待進一步的檢驗。特別是中國已婚女性群體,他們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員,相較于未婚女性承擔著更多的家庭責任,他們在背包旅行中是如何實現身份構建,尚缺乏專門研究。基于此,本文將深入探究中國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身份構建問題,以期發現中國已婚女性背包客身份建構的根源和途徑,剖析家庭對其身份構建的影響,拓展背包客身份建構理論。
1 理論來源
1.1 自我民族志
自我民族志是一種自傳體形式的民族志研究,通過對意識、思想、情感和信仰等多個層面的“剝離”,系統地描述和反映個體的文化體驗(Ellis et al., 2011)。不同于書寫他人故事的民族志,自我民族志要求研究者既要充當“局內人”,也要成為“局外人”(Anderson et al, 2012),其獨特性在于將自我意識作為第一手經驗數據的來源(Chang,2016)。有學者指出:相較于其他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凸顯了自我的主體性,研究者通過描述個人層面的認知和實踐,強調了權力關系在塑造個體現實中的作用(吳建興 等,2022)。所以,自我民族志是一種情感喚起性敘事,呈現了高度個人化的特征,其利用個體經驗來探尋新理論,從學理角度重新思考個體生命和文化意義。
自我民族志的書寫多源自生活中的感悟或觸動。我的“感悟”是對已婚女性背包旅行代際傳遞故事的反思。有學者指出自我民族志與個人敘述的不同之處在于:1)可以向外部群體揭示內部群體的隱秘行為(He et al., 2022);2)將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形成理論貢獻;3)有意識地接受“脆弱”;4)喚起外部群體的同理心(Chang et al., 2016b)。自我民族志不應僅僅停留在“講述研究者個人的故事”,還應是研究者通過剖析自我經歷或體驗進而驗證或提煉理論,并對相關群體提出建設性意見(李方圓 等,2022)。在當下提倡多元研究方法的時代,自我民族志日益得到旅游學者的重視,但相較于國外學者,國內旅游學者對自我民族志的認識和使用剛剛起步(吳建興 等,2022)。自我民族志運用自傳式的描述方式,相較于傳統定性研究方法在旅游體驗等研究主題上更具深描的品質(Miles,2019),特別是在并不常見的旅游場景研究中更具優勢(Komppula et al., 2013),其提供了一個有價值、可持續的旅游體驗觀察窗口(費孝通,1994)。鑒于此,我將繼續深描我的故事,從學理角度反思我作為一個已婚女性背包客的歷程。
1.2 對已婚女性背包客和社會角色的再思考
1.2.1 背包客身份構建 背包客通常被學者們認為是一類社會建構的社區,群體風格獨特,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和行為(Cohen, 2011)。對于多數背包客來說,背包旅行不僅是一種旅行形式,也是一種身份表達。旅游學者提出背包客群體熱衷于通過身份標簽將自己與“大眾游客”區分開來,并將其旅行身份視為“意義創造”的重要來源(O'Reilly,2005)。背包旅行本質上是代表價值取向和社會分化的標志(Zhang et al., 2017)。長期以來,背包旅行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組織的旅行,其不僅具有靈活的旅行安排,還具有長期旅行、低預算、脫離常規、追求真實性和冒險性、愿意與他人互動的顯著特征,帶有明顯的獨立、自由、冒險、自我轉變和個人發展的理想特征(Elsrud, 2001; Noy, 2004;O'Reilly, 2005)。為了獲得和維持特殊的群體身份,背包旅行者必須至少遵循以上規范性特征中的一個,以區別于大眾游客。因此,背包客的身份建構一直被視為背包客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Cohen,2011; Currie et al., 2011)。Muzaini(2006)提出,背包客遵循規范性行為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在群體內確立地位和贏得聲譽,將背包旅行中的“偶然經歷”當作象征性資本,將背包客固定于社會建構的身份之中,他們在旅行中會重點尋求“原真性的旅游體驗”,進而采用多種策略來“尋找當地人”。關于冒險和冒險行為的敘述被認為是背包客在群體中獲得更高等級的另一個重要策略(Elsrud, 2001),說明旅行方式標志了旅行者價值取向,影響了社會分化。這種觀點強調了背包客的身份標簽區別于普通游客。與此同時,背包旅行被認為與普通旅游截然不同,是為獲得和維持等級制度中更高地位的場域,往往與男性主義、文化霸權和勢差等權威元素相關;背包旅行是維持群體中個人聲譽和地位,爭奪控制權的顯在具象。有研究認為,Muzaini 背包客身份理論僅關注“低預算、長期旅行、愿意與他人互動和白人男性”,而沒有考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可能產生不同的倫理觀念。民族和文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背包客身份建構的方式和形式(Maoz,2007),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區群體之間背包客身份構建的過程。此外,背包旅行的研究通常面向西方,研究人員主要關注“西方”背包客及其身份構建問題(Teo et al., 2006; Cohen et al., 2015)。Muzaini 的背包客身份構建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女性有待考究。
在中國,背包客被稱為“驢友”,與已知的西方背包客行為相比,具有顯著的不同。盡管中國背包客群體在過去十年中經歷了顯著增長,但該領域的研究卻相對遲緩。近年來,背包客作為一種重要的旅行類型受到了中國學者的關注,學者主要聚焦于背包旅行相關的動機和行為研究(Luo et al.,2015; Chen et al., 2020)。研究發現,中國背包客在年齡結構上與西方同行相似,且以男性為主;不同的是其在實際旅行中往往有較高的旅行支出,且背包實踐的成熟度較低,高度依賴互聯網(O'Reilly,2005; Ong et al., 2012)。與西方背包客一樣,中國背包客也面臨著制度化的困境,隨著背包融入旅游業,背包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消費的象征(Zhang et al., 2017)。這一制度化過程,最初源于背包客的實踐,不斷構建與“背包客”相關的意義,以及“背包客”作為社會身份的意義。雖然大量關于中國背包客的文獻已經開始了解其行為,但很少有研究關注背包客身份的社會構建問題。此外,迄今為止背包客的大多數研究基于客位研究方法,只有少數研究關注了中國背包客自身的意義建構(陳鋼華 等,2021)。Muzaini提出該理論時所處的社會語境與當代中國社會不同。中國家庭生活有著強大的母職傳統,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的“母職”是規定女性在父權制家庭中作為妻子必須承擔和履行的職責,并非著力于維護母性,而是一種權利與責任的規定。中國傳統對于已婚女性社會地位的印象已將其與“背包獨游者”的角色天然隔絕。已婚女性被認為應該以家庭為重,承擔相夫教子的責任,具備內斂、溫順和被動的特質,加重了已婚女性之于背包旅行的邊緣性,忽略了她們對自我價值實現和精神需求的追尋。因此,本研究認為,對已婚女性身份的刻板認知是阻礙其背包旅行的關鍵。由此,本研究運用自我民族志的質性研究方法進行理論溯源。
1.2.2 已婚女性背包客與社會角色理論 有學者指出,旅行在自我身份構建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決定了個體對身份、地位和所在群體的找尋和認同。已婚女性背包客渴望在獨自背包旅行中尋求自己的獨立定位,并通過背包旅行尋求挑戰,以打破傳統社會對個體的角色期望(Cai et al., 2019)。研究表明,即使過去和現在的背包客群體中不乏已婚女性的身影,其在主流話語中的地位也逐漸顯現(雷汝霞 等,2017),越來越多的已婚女性聲稱他們與“驢友”群體有密切聯系,但其在背包客群體中仍處于附屬地位。社會學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傳統思維模式強迫已婚女性的氣質、性格、職業及行為方式等必須符合所其所扮演的“已婚女性”角色(Park, 2019)。
角色是社會心理學研究者從戲劇中借用的概念,強調自我與“一般他人”的角色之間的相互關系,該概念與各個體在社會中的結構位置密切相關(Park, 2019)。社會角色是由一定的社會地位決定的一種權利義務、行為規范和行為模式,要求處在不同社會地位的個體做出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喬納森·H·特納,1987)。社會角色是社會結構對其結構網絡中的每一個具體節點的功能要求,它看似是把現實中的個體作為調節對象,實質并非針對個體,而是面向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功能(喬納森·H·特納,1987)。這種功能要求并非社會針對個人的規定,而是由個人在社會網絡的位置所決定(易偉芳,2015)。換言之,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社會分工、角色、能力以及身份、地位等不是由生理因素決定的,而是社會文化對不同家庭成員的期待和規范、資源和機會的分配,能力和特長的發展影響了社會對丈夫和妻子等社會角色的認知,形成了男女之間權力和地位關系的不平等,這種關系在文化習俗、教育、宗教、法律和政策等作用下得以鞏固和加強。究其根本,社會角色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權力關系。傳統的思維模式使女性在家庭關系中處于劣勢,依附于丈夫和孩子而存在。在社會角色理論下,男性被必然地推向社會,女性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應留守家庭,其行為模式須符合社會權力者的期許。而已婚女性“背包客”恰好是把屬于男性領地的“背包旅行”作為象征性資本,用以反抗傳統思維里的父權和夫權。回顧我的親身經歷,本研究認為,背包旅行是我作為一個已婚女性對自主和自我發展(即能力)的追尋與共鳴。正是這種“自主的追尋與共鳴”,使打破傳統社會角色認知、塑造新角色特征、實現自主發展成為已婚女性背包旅行的主題。此外,“場域”是自我發展抗爭的場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場域”不僅具有時空觀念上的意義,還關注了空間中的“位置”和“構型”(郭建斌,2008)。本研究將剖析不同場域下個人、家庭與群體的聯系以及消費型構編織下的社會角色認知及其運行機制。
2 敘事緣起:背包旅行的代際傳遞
2019年,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徒步旅行成為熱門旅游線路,我正在家中打包行李準備前往尼泊爾背包旅行,這次我選擇走安娜普爾納大本營線(Annapurna Base Camp),在路上徒步8 d。先生坐在沙發上一臉不高興地盯著我打包行李,看著我將睡袋、雨衣、登山扣、手電、充電器等旅行用品放入背包中,有一搭沒一搭地問我尼泊爾好不好玩,喜馬拉雅徒步旅行累不累,有沒有請向導等。看到我整理好的旅行背包,他淡淡地說,結了婚就不應再和小姑娘時候一樣獨自一個人跑出去玩,問我為何不干脆報個旅行團帶著老人、孩子一同出行,云云。我把之前我在各地背包旅行的照片拿出來給他看,無論是層巒疊嶂、無邊無際的龍脊梯田,抑或是深居西藏山南地區洛扎縣境內神秘的庫拉崗日圣湖,里面都充滿了普通旅游者不曾領略的風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讓我內心悸動,但這些在他看來卻不值一提。我不顧先生的反對,仍然在為人妻、為人母后堅持每年都要實踐一次“說走就走”的背包旅行。與先生的反對不同,我的母親看到我在婚后仍熱衷背包旅行,很是欣慰,并未責難我沒有與家人一同出游。
背包旅行的傳統可以上溯至我母親那一輩。母親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一個生活條件優渥的家庭,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母親的父親在機關工作,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母親不僅學習成績優異,還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一名大學生。母親畢業后從事與旅游相關的管理工作,一直非常熱愛旅行。70年代后期,受益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母親擁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旅行機會。同時,在90 年代,背包旅行被視為一種富有浪漫情調的旅行方式,中國女性變得比以往更加獨立,母親經常背包到各地旅行,成為國內最早的一批背包客。母親一直認為背包旅行不僅可以開拓眼界、增長見聞,還可以鍛煉自己的生活能力和應變能力。與父親結婚后,母親仍然堅持一有機會便和三五好友一同背包旅行。
母親熱衷背包旅行,在我很小的時候也帶我一同出游,稍大點還送我去參加專門的背包夏令營。因為能吃苦,又熟練掌握了一定的野外生存知識,我很快便鐘情背包旅行,并對人跡罕至的神秘之地充滿興趣。背包旅行成為我工作和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種休閑活動。從祖國西北的的喀納斯到西南的蒼山洱海,從法國的香榭麗舍大道到柬埔寨的吳哥窟,都留下了我背包旅行的足跡。隨著我成家添幼,父親和先生開始對我背包旅行略有微詞。父親認為“為人妻后,應當以家庭為重,哪里有自己跑去玩的道理”;先生認為閑暇時間我應優先在家照顧老小,盡可能少地離家獨自出行。全家只有母親一直支持我婚后堅持背包旅行。
這個背包旅行代際傳遞的故事開始讓我思考,為什么家庭會對已婚女性的背包旅行行為賦予特殊的闡釋和判定?我的已婚女性背包客之路又意味著什么?
3 家庭場域下的背包旅行
3.1 家庭背包旅行的起點
20 世紀50 年代,母親出生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女性強調獨立自主發展,母親有機會背包到各地旅行。但背包旅行在90年代的中國才開始興起,作為“舶來品”,其主要在年輕人中流行。從歷史文化層面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儒家思想也是中國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家思想下的旅游實踐強調主觀的內心感受,“樂因乎心,不因乎境”以及近游傳統、尚古意識、“與民偕樂”(喻學才,2004)。中國傳統的旅游觀念不同于西方鼓勵探險的旅游精神,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背包旅行作為一種旅游形式進入人們的視野也只是近十年的事情。在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使得家庭不僅是一個決策單位,也構成了家庭成員個人的決策環境,已婚女性在繼續教育、職業發展、社會生活等眾多領域的參與程度深受家庭決策過程的影響(吳帆,2014)。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想已婚女性多以溫順、文靜,以丈夫和孩子為絕對核心,甚至是缺乏個人主見的形象出現,所以已婚女性長期被排除在背包旅行之外。從社會現實來看,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無法為民眾提供良好的旅行基礎,在中國背包旅行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還需要獲得家庭的支持。幸運的是,自近代以來,中國民眾一方面出于對西方英雄浪漫主義生活方式的推崇,開始出現鼓勵已婚女性走出家庭通過背包旅行以獲得獨立人格的新興審美標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從性別平等的角度大力提倡提高已婚女性的家庭地位,號召“提升已婚女性的家庭權利意識和參與能力”(李超海,2013)。正是在家庭支持和中國社會文化觀念變遷的雙重影響下,母親得以成為一名背包客。不難看出,當時只有部分已婚女性可以背包旅行,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逐漸改善,更多的已婚女性背包客被納入大眾旅游時代的浪潮中。
3.2 家庭背包旅行的延續
研究表明,家長會帶孩子一同旅游或鼓勵孩子參加旅游,以從小培養孩子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的思想(鄧紹秋,2009)。這說明父母往往扮演著孩子參與旅游活動的引路人和資助者。在我的家庭中,母親扮演了這個角色,從而實現了家庭背包旅行行為的代際傳遞。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一個機關干部家庭。因為父母都是大學生,他們對我的教育比較重視,很早就鼓勵我多去參加旅游活動,在大自然中收獲知識,開拓眼界。我依然記得我第一次背包旅行是同母親前往距離北京348 km外的五臺山。我們坐長途大巴最先抵達臺懷鎮并一路搭車前往鴻門巖,沿著山路一直徒步攀爬,從中臺一路向西臺走去。由于我年齡小,速度慢,抵達西臺的時候已是晚上11點左右。當時的我又累又餓,詢問母親為什么要背包旅行。母親指著我們剛剛翻越過的中臺方向說道:當我站在浩瀚無垠的星空下,感覺自己是如此地渺小,任何煩惱都拋到了九霄云外,看著自己一步步走過的路,感受到了憑借自己的力量征服一座山的成就感。當時我的父母并沒有以“小姑娘不要一個人跑出去背包旅行”為理由反對我成為一名背包客,反而耐心地給我傳授各種野外生存知識和徒步技巧。他們從未要求我留在家中做一個溫順、文靜的女孩,而是鼓勵我繼續前往我不曾抵達的未知領域去探索。和母親一同背包旅行滿足了孩子渴望被關注和平等對待的情感需求,也成為一項家庭儀式。
母親鼓勵身為女兒的我背包旅行是希望女兒能夠傳承家庭的傳統,希望年幼的我能夠真正理解背包旅行的意義。學者鄭雄飛等(2022)提出:“個體或被動卷入或主動參與,根據所處的社會位置采取符合身份設定的行動,血緣共同體為集體行動提供情感和物質支持,也為個體行為提供角色扮演的舞臺與活動空間”。母親通過帶我進行背包旅行,希望女兒能夠像她一樣熱愛背包旅行,憑著自己的力量自主抉擇生活,構建屬于自己的“角色”。
3.3 家庭背包旅行的抗爭
重新回顧母親帶我背包旅行的經歷為反思家庭作為社會角色構建的舞臺掀開了一道豁口,我意識到家庭成員對社會角色的認知影響著背包旅行的參與實踐。雖然父親支持我婚前背包旅行,但對我婚后特別是為人母后的背包旅行活動予以堅決的反對。父親認為女性結婚后應扮演好一名“賢妻良母”的角色。自我民族志的敘述給了我反思父親態度的機會。這已不是簡單的“家長制”對已婚女性背包旅行的壓制,而是中國傳統社會對于已婚女性角色認知的真實寫照。夫妻軸一直是中國家庭關系的主軸(楊菊華 等,2014),妻子是丈夫身份的附屬,很難獨立作出人生規劃。父親的理由暗含了對已婚女性背包旅行的價值判斷。選擇獨自背包旅行意味著家庭需要承擔巨大的社會壓力和被人猜忌、非議的風險;即使成為一名著名的背包旅行者,身體已不再屬于家庭,而是變成群體內外部身份區隔的標志(樊友猛,2020),所以我不應該在婚后獨自背包旅行。父親是利用“在場”的家長身份壓制我婚后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抗。
從中國宏觀階層架構看,母親和我兩代人均是都市職業女性,擁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母親的個人經歷讓她認識到背包旅行的積極效用,在她看來,家庭不僅是背包旅行的起點,也是打破傳統社會角色認知構建新角色特征的支點。在家庭內部,背包旅行的代際傳遞是一種具有象征性的行為隱喻,家長對孩子的希冀和已婚女性對家庭意志的遵從構筑了結構的邊界。但子女背包旅行的“生殺大權”仍掌握在家長手中,子女能否獨自背包旅行,去哪里背包旅行,去旅行多少天,賦予背包旅行何種意義,在何時何地如何踐行背包旅行,都受到家長意志的影響。而家長的意志受到傳統文化對社會角色認知的影響,這也展示出傳統的角色特征對家庭影響的微觀圖景。從家庭與外部社會的互動來看,家庭承載了反抗社會傳統角色觀念的壓力。家庭的權力擁有者不遵循傳統角色規范是對傳統權力體系的反抗,將有助于子女打破社會刻板印象和偏見而實踐背包旅行。
4 同輩人場域下的背包旅行
4.1 背包客身份與自我抉擇
結婚后,背包旅行已成為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閑活動。一是因為通過背包旅行可以不受大眾旅行團線路安排的限制,前往少有人涉足的地域探秘,感受自然風光之美;二是因為組建了新家庭的我迫切希望可以自主決定個人的興趣和生活。
通過背包旅行,我建立了自己背包客的身份標簽。我會提前數月規劃我的背包旅行,選擇具有挑戰性的目的地,登錄各大背包旅行論壇搜集相關資料;一遍遍觀看背包客拍攝的旅途紀錄片,登錄論壇與驢友們討論最新的背包旅行裝備,感受著關于背包旅行的獨特魅力。從我居住的北京周邊開始,每逢假期我都會背包旅行5~7 d,自主選擇徒步的目的地,隨身攜帶一個小型數碼相機,沿途拍攝記錄當地的風土人情,并在我完成背包旅行后將我的旅行經歷整理成文字,配上圖片,發布在“驢友”論壇上。我會津津有味地瀏覽別人在我帖子下的評論,認真回答每一條留言。這種自主決定背包旅行目的地、成功完成具有挑戰的背包路線,并向他人成功傳授旅行技巧的經驗,讓我對前往更遠的地方背包旅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信心,強化了我的背包客身份標簽,增加了主觀幸福感。
作為已婚女性,我是朋友圈中的唯一一名背包客。一方面,我有與普通大眾旅行者截然不同的身份標簽,這無疑引來了很多異樣的目光和非議,其中既有男性的藐視也有女性的懷疑。正如已有研究指出,女性背包客很難獲得男性背包客的認可,還會遭受其他女性的責難,認為女性背包客的旅行行為是為了更方便其與陌生異性交往(Larsen et al.,2011)。但另一方面,背包旅行也是一個自我決定的過程。自決理論提出,三種特定心理需求的滿足將有效提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這三種心理需求分別包括:自主性(即參與反映個人興趣或價值觀的行為)、能力(即有效地從事有價值和具有挑戰性的追求)和關聯性(即與他人建立密切和令人滿意的聯系,感覺被接受)(DeHaan et al., 2014)。我利用背包旅行,通過自決,對傳統家庭觀念中以男性為核心的霸權進行反抗,向那些擁有更多象征性資本的人所定義的制度秩序發起沖擊,開啟了一場新的身份構建之旅。
4.2 社會身份與精神通約
隨著我生育子女,我已不再是剛結婚時那個特立獨行的小姑娘,而成為一名母親。由于我個人可支配的時間被各種家庭事務和孩子教育等占據,我可用于背包旅行的時間越來越短,頻率也顯著下降,因此我對長距離背包旅行的熱情逐漸冷卻。在我的三口之家中,我盡可能地履行好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角色,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和撫育孩子的事務。當我在網絡上看到越來越多的同齡人加入背包客的行列,足跡遍布國內外的知名線路,羨慕他們可以在連綿不絕的群山中徒步穿行,拍攝絕美的風景照片,這時我通常會保持沉默,不再瀏覽主頁信息。幸運的是,此時京郊游開始興起,每逢小長假,我可以抽出一天時間在北京周邊背包徒步,北京近郊的一日徒步旅行成為我的小小慰藉。
難道僅僅因為沒有充裕的旅行時間,我就簡單地喜歡上了短途的背包旅行嗎?以德里達為首的后現代解構主義者認為事物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先在的、不變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質,一切都是變動的、不確定的,而且與主體狀況相聯系,意義只存在于解釋者的解釋行為中,身份構建則是一個舊身份不斷分裂,新身份不斷形成的去中心過程(德里達,2001)。如果短途徒步旅行符合科恩背包客身份系統中的表面特征,是一種標簽化的特征,那么它所代表的獨立自主、冒險精神和英雄主義則是背包客身份的精神特征,是背包客標簽的內核。那么,這樣看來短途徒步旅行實際上是我希望打破身上帶有的傳統角色特征標簽,重新奪回生活自決權、構筑新身份的解釋行為。在短途徒步旅行本身的巨大魅力和生活福祉追尋的雙重作用下,我成了一個徒步背包旅行的愛好者。因經常在北京周邊小眾旅游景區徒步,我還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齡朋友。因此,精神化的背包旅行通約性幫助我完成了這場新身份的構建之旅。
4.3 身份認同的掙扎
與同齡人的交往使我經歷了關于背包客和已婚女性身份認同的掙扎。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個體開始認識到自決是身份構建的重要手段。我開始主動規劃每年的時間,盡可能地在春節前擠出兩周時間進行每年一次的背包旅行,從素有北京“百慕大”之稱的門頭溝鐵陀山,到甘肅張掖的喀斯特地貌——七彩丹霞,再到世界著名文化遺產地——柬埔寨吳哥窟都留下了我背包旅行的足跡。回顧我的新身份構建之旅,不論是以背包旅行為由自主掌控生活的行為,還是降低背包旅行頻率,都是主體面對傳統社會角色刻板認知時的策略。如果主體處于關系場域中較高的位置、擁有更多的象征性資本,其可在整個群體關系中處于核心,并重新定義新的群體身份;但當主體處于整個群體的邊緣地位,那么主體可能放棄自決權,而去遵從大多數人的抉擇,以求融入新的群體。是選擇賦予背包旅行特殊的意義,通過自決掌握生活的“遙控器”,不再扮演傳統觀念下的已婚女性角色,同時塑造新的社會角色特征,實現主觀幸福感的提升;還是選擇以短途背包作為自己的私人空間,向傳統的群體身份認知妥協,這取決于主體所處的位置和對個人生活福祉的追求。身份認同掙扎背后的社會角色固有認知,決定了同齡人關系的能指和實踐。
5 旅游消費場域下的背包旅行
5.1 國內旅游消費的出行自由
2010 年后,國內旅游消費迎來“井噴式”發展,新婚不久的我擁有了向往已久的名牌背包旅行設備和更便捷的國內出行機會,我從家長手中名正言順地接過了旅游出行的“指揮棒”。我可以自主決定在國內各大城市和著名景區的背包旅行線路。這一階段,我熱愛上了國內山岳型背包旅行活動。和對短途徒步旅行的熱愛一樣,喜歡山岳型背包旅行活動是源于構建背包客新身份和賦予女性新社會角色特征的需求。從黃山絕美的蓮花峰、嵩山主峰峻極峰到武當山金頂,都留下了我作為一名女性背包客的印記,無不是我在國內旅游消費黃金時代的狂歡。有學者指出,國內大眾走馬觀花式的旅游“就是一個收集照片、收集符號的過程,是對某特定景點意義符號的生產與消費”(Urry,2011)。與此同時,男性在背包旅行中各個方面都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人們將女性背包客塑造為“桀驁不馴、特立獨行、充滿誘惑和性感的”(蔡曉梅 等,2016)。女性背包客也相應處于邊緣地位。但2005年當代女作家芭芭拉·赫吉森在《女人旅行三百年紀事(No Place for a Lady)》里面記述了98歲的著名女性旅行家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在中國的旅行故事,她直言:“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樣死去該多么美好”(芭芭拉·赫吉森,2005)。那些本該待在家中的已婚女性,已經開始沖破牢籠,脫下裙裝穿上褲裝,在旅行的同時開始學習獨立思考,變得獨當一面、勇敢無畏。已婚女性背包客渴望能夠沖破長期以來男性和家庭對其背包旅行的阻礙以及女性背包客不被重視的傳統。此刻的我已不再滿足于以背包客來構建身份,而是以熱愛一項男性主導的活動來打破傳統社會角色觀念的禁錮。
出于對背包旅行的熱愛,2009年我第一次背包旅行進藏。這讓我徹底認清了我對徒步旅行的偏愛。由于直接乘坐飛機抵達拉薩,沒有逐漸適應海拔的提升,加之對西藏向往已久,抵達目的地后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背包旅行,甚至最后引發了嚴重的高原反應,不得不提前終止旅行返回。在我看來,淺嘗輒止的國內大眾旅游“打卡”遠不如一次短暫的深度背包旅行體驗重要,所以我開始在北京周邊進行短期背包旅行。當時的手機信號還沒有現在便捷,經常會造成家人與我聯系不便,此舉惹惱了我的父親和丈夫。這僅僅是關于背包旅行嗎?這是對禁錮在身份上枷鎖的反擊。國內的大眾旅游消費象征著權力和資本,同時也是一種反擊手段。國內旅游消費時代的到來讓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旅行便捷,我可以在國內自由規劃我的旅行交通、時間,海量的旅行服務可供我選擇。至此,我徹底投入到了背包旅行活動中,這是對傳統權力擁有者壟斷旅游資源的強烈“反抗”。
5.2 國外旅游消費的參與自由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出境旅游蓬勃發展,背包旅行由過去的國內大眾旅游向國外深度出境旅游轉換,個性化旅游產品和服務的出現給背包客帶來了出國領略“異域風情”的旅行體驗。面對陌生的異域他鄉,我得以釋放之前小心翼翼的身份焦慮和處心積慮構建的社會角色特征,實現全身心地享受背包旅行的過程。我會在攜程上提前預訂好特價機票,利用馬蜂窩論壇提前聯系當地的向導和司機,咨詢有關當地旅行線路的問題,將沿途旅行的照片和游記發表在博客里。我發現,越是前往與國內生活環境不同、人跡罕至的國外小眾景點并拍攝秘境般的風光或當地風土人情的照片,就越有可能在群體中受到關注,掌握更多的話語權。為了盡可能多地前往國外小眾景點,擁有在背包客群體中更高的權威,我幾乎投入了我的全部業余時間和金錢,我一有空閑就要查閱國外最新的背包旅行線路并輾轉前往徒步,購買昂貴的攝影器材,前往毫無徒步價值的景點只為在博客中發布更多吸引人的照片。逐漸地,我的私人生活被背包旅行所反噬。消費水平的提升使得國際背包旅行成為可能,人們擁有了更多的旅行自由,可以前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旅行。然而,姚延波等(2021)在分析旅游消費時提出,現代的旅游消費從過去更多關注景觀對象,逐漸轉向一種具有炫耀性質的消費行為,越來越多的旅游者喜歡在旅行途中或旅行結束后,將自身旅游體驗或見聞向其關聯用戶呈現并與之互動,而忽略了在旅游中對真實(本真性)的尋找。由此可見,國際旅游消費浪潮的興起驅使我們不斷前往人跡罕至的新奇小眾景點,拍攝各種綺麗的自然風光大片,被卷入這種“消費驅動的被迫旅游”中,而忽略了在旅行中尋找本真性,去感受當地真實的社會文化風貌和生活樣態。
5.3 意義賦予的爭奪
基于對我個人背包旅行經歷的反思,我減少了對背包旅行不必要的消費。盡管我仍會出國進行背包旅行活動,偶爾也會和母親一同背包旅行,但是炫耀性的定制化消費行為幾乎戛然而止。我努力阻止消費作為中介物的僭越。我從當時那個迫切渴望借助背包旅行打破傳統束縛的小女孩,到現在已為人母的旅游學者,背包旅行已成為我社會資本積累中至關重要的因素,而消費只是一種手段,是背包旅行的附屬品。我認為我與背包旅行的關系應該回歸到追尋旅行本身樂趣,滿足內心自我幸福感。作為旅游研究者,我殷切希望獲得意義自治,我對背包旅行的認知不應止于群體的標簽行為,也不是消費本身,更不是我所期盼構建的某種社會角色。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證明自己作為學者的獨立性和作為背包客的反思性,這是背包旅行消費符號能指意義的退場。
但是真的就這樣退場了嗎?打開我的購物車,近5年間,我一共購買了數十件與背包旅行有關的產品,從防沙圍巾、登山杖、保溫瓶到狼眼手電,僅是登山背包我就有5個,戶外旅行產品是我最常購買的產品類型,我會以類型豐富的背包旅行產品擁有者來彰顯我是一名專業的背包客。我時常反思,即使我已經擁有了足夠的背包旅行產品,為什么還要不斷地購買這些并不必需的商品?米德曾說:“自我是社會互動的產物,是通過‘扮演他人的角色’來反思性地構建的”(Morrow, 1935)。一方面,我希望獲得新的身份構建,另一方面,在個性化旅游消費的慣性下,我仍不遺余力地穿梭于國外的小眾景區,塑造我特立獨行的已婚女性背包客身份。現在的我和當年那個身份焦慮的小姑娘并沒有差別。大多數時候我會被貼上“與眾不同”“離經叛道”的標簽。我的經歷印證了“自我是通過‘扮演他人的角色’來反思性地構建的,通過與他人的互動,個人學會與他人所扮演的角色相適應,通過這種方式構建和獲取身份意義”(李方圓 等,2022)。我所樹立的這些身份標簽暗示了人們將背包旅行行為歸屬于男性范疇,還將對已婚女性社會角色的刻板印象強置于背包客的想象中。“不在場”的刻板角色認知強化了已婚女性背包客的邊緣地位,這恰恰證明了我對社會角色和消費統制的反抗不成立。
5.4 傳統社會角色認知和媒介主義的消費牢籠
國外定制化的背包旅行并非大眾消費模式的延伸。消費者可以通過便捷的交通網絡自主選擇想要前往的目的地,這充分顯示了國內旅游消費時代的大眾性、聚合性特征,其聚合的對象是海量的旅游消費信息。國內旅游消費時代,背包客旅行的自主性有所提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背包客們又迎來了國外旅游消費時代。國外旅游消費的本質特征是定制化、展示和信息交互,它的出現填補了國內旅游消費時代產品種類、信息交流的匱乏(胡林,2017)。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背包旅行中。在諸如京津長城段和四姑娘山畢棚溝這類初級背包旅行線路中,大眾旅游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背包客的性別均衡,因為已婚女性和各種社會階層均可參加。但在夏特古道和喀納斯大環線這種高級背包旅行線路上,參與者多來自核心的背包客群體,彼此之間大多相熟,熟人網絡反而強化了已婚女性背包客的邊緣地位,少有人參與其中,因為已婚女性自身可能以社會普遍的角色認知來構建自己的身份標簽。此外,社交媒體作為一種新型傳播媒介,在旅游發展中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在潛移默化改變著旅游者的消費模式,使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的行為發生著明顯變化(Amaro et al., 2016),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旅游者分享旅游體驗的圣地,成為人們“曬”旅游的秀場。現代旅游作為一種具有炫耀性質的消費行為,是社交媒體的熱門分享內容。社交媒體在傳遞背包旅行炫耀性符號意義的同時,消費則收割人們的金錢和關注度。社交媒體和消費主義使得社會角色特征和自我炫耀成為這一階段的顯性邏輯。
6 結論與啟示
回顧我作為已婚女性的背包客之路。母親對我背包旅行的支持源于其自身對背包旅行的認知和體驗影響,背包旅行的代際傳遞實際上通過母親的個人行為愛好和情感鏈接對子女的旅行行為產生作用,其本質上是母親通過構建背包客身份,對傳統的已婚女性社會角色認知的反抗。對于傳統角色特征的打破和對新的社會角色的構建,始終貫穿在我的已婚女性背包客體驗之中,已婚女性的身份天然地被認為與背包客相隔絕,在不同的旅游消費場域中,已婚女性通過背包旅行反抗傳統社會觀念強加在其身上的刻板角色印象。民族志學者Ellis 等(2011)提出“文化的文本頓悟”這一理念,故本文的自我民族志敘事反映了已婚女性背包客的困境。泰格和倫德爾(Teghe et al., 2005)指出,幸福感是指過好生活或過好生活所需的實踐和過程,是一種以心理和社會文化需求為中心的狀態。我的背包旅行文本對于幸福感的追尋凸顯了自我價值實現對當代已婚女性的重要意義。
6.1 社會角色特征的重構是構建已婚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徑
本研究敘事包含了社會經濟發展、信息技術提升和個人人生階段的變換、禁錮與反抗,伴隨著作為已婚女性背包客的每一段經歷。在這一過程中,我充分展演各種各樣的身份和角色,實踐著對父權、夫權、消費主義和媒介等的反抗,我仍然堅持在生活中自我抉擇。旅游是一個典型的場域,通過旅行者自己來探尋生活的意義(Sharpley et al.,2011)。后現代語境中,傳統和現代的框架不斷消解,我所面對的禁錮也因語境而不同,但對于傳統社會角色認知的打破是貫穿之中的永恒主題。正如社會角色理論研究所指出的,個體如同“演員”,必須按照劇本要求扮演不同角色,個體的行為也必然受到群體社會生活的規范和制約(奚從清,2010)。本研究自我民族志敘事最大的理論貢獻在于發展了對社會角色塑造永恒性認知,指出與社會角色塑造相伴的永遠是抗爭,這是構成現代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徑。由于對新社會角色特征塑造的動態性和日常性,加之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已婚女性可能不得不接受某些傳統社會角色的認知,與某些身份特質“和解”,但打破傳統社會角色繭房的“在場”是已婚女性追求自決的過程。
以往有不少學者指出,根據“形式”這種外在的客觀標準來區分背包客和其他類型的游客不甚有效(Larsen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7, 2018;Dayour et al., 2017),更重要的是通過內在的心理特征對背包客與其他游客群體進行有效的區分(Zhang et al., 2017, 2018;劉魯 等,2018;Chen et al., 2020)。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人們通過“自決”獲得反映個人興趣或價值觀的行為自主性,擁有從事有價值或具挑戰性行為的能力,并由此與他人建立密切聯系,進而在所從事的活動中獲得幸福感(Sedikides et al., 2019)。已婚女性背包客正是通過背包旅行這種獨特的方式,通過自決,用實際行為打破傳統社會觀念下的角色桎梏,掌控自己的旅行消費決策、融入背包客群體,塑造新的社會角色,進而實現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6.2 消費主義下生存需要追尋幸福感
本研究經歷了背包旅行的代際傳遞,呈現了自我抉擇和跨階層的精神通約,在抗爭中完成身份構建和社會角色重塑,是對主觀幸福感的追尋,因為這種不可調和性具有洛佩茲(Lopez et al., 2017)所說的“自主和自我發展在整個領域產生的共鳴”。在這個消費高度發展的時代,人們與消費生活高度勾連,個體陷入了新的身份構建困境。但每個個體可以通過控制旅游消費的程度來調整自我的卷入程度,構建自我的消費認知。旅游是一種具有炫耀性質的消費行為(姚延波 等,2021),人們通過自我抉擇在國內和國際旅游消費市場中選擇分配。背包旅行相較于一般旅行的時間更長且行程更具彈性,更注重旅行過程中的社會交往,且活動的參與性更高(Pearce et al., 2007; 2009),可以獲得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陳鋼華 等,2021)。這是久在消費禁錮中重返自由的一種“真實”行為,體現了在現代消費社會中自在生活的可能。所以,人們應該通過自決來提升幸福感,并尋求內心的安寧,延展生命的價值,這也是給身處現代消費社會中的當代人的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