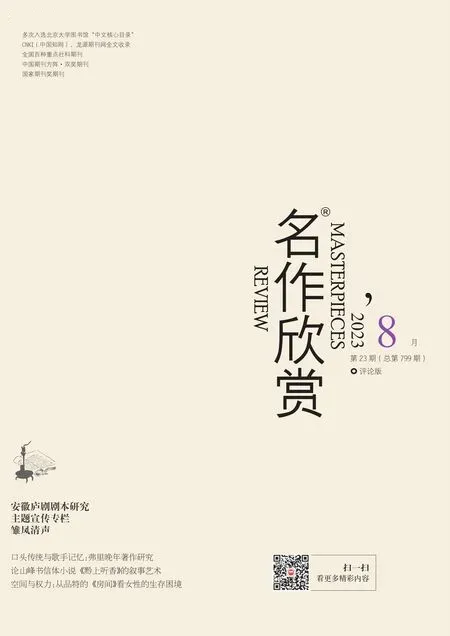病態審美
——白居易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梁嘉懿[寧夏師范學院,寧夏 固原 756000]
在歷代與大疫的斗爭中,中國人民一直以來都表現出對生命的高度尊重,這背后折射的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強烈的生命意識。事實上,生命意識一直以來都是人類最為普遍的意識之一,生命是文學產生的基礎,文學是生命的反映。簡單來說,“生命意識是對生命懷有一種強烈的自覺性意識,它表現為對生命自覺地關懷和熱愛。”①自幼體弱多病、生性敏感引起了白居易的生存恐懼,在生命短促的死亡陰影下顯示了極強的自我關切意識。在這種生命意識的強烈觀照下,其詩中出現了大量的衰老書寫、身體書寫,白居易對個體細微變化的關注展示出了其豁達的生命觀。
一、衰老書寫
白居易現存的2916 首詩中,詩題(包括小序)和詩句中出現“病”字的共323 首,404 處,分別占詩歌總數的11.1%和13.9%。②可見對疾病的感知之敏感,以及自我關切意識之強烈。白居易在16 歲寫下《除夜寄弟妹》的詩,詩中云:“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③適值盛年,正當青春時期,就嘆息自己的“病容”,且比過去更加嚴重,舊病之沉、新年之喜、羈旅之思涌上心頭,對健康之痛尤其切膚。后又在《病中作》中感嘆:“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18 歲就對自己不及時養生、保養身體而悔恨,可見其身體素質極其不好。自16 歲在《除夜寄弟妹》中第一次涉及“病容”一直到其離世,疾病書寫貫穿了白居易的整個創作生涯。身體羸弱、病痛纏身,雖不致殞命,卻相伴一生,足以見得這些小病小痛帶給白居易的痛苦。其詩中的疾病書寫多種多樣,如,眼病、腰痛、肺病、肱傷、頭痛、頭暈、風眩、耳聾、風濕、脫發、手痹、足疾,以及不明原因慢性病等。
疾病纏身首先給個體帶來的是衰老意識,衰老是個體無可阻擋的時間腳步,是生命必然面臨的終極命題。陶淵明曾經感嘆日月推遷“念將老也”,白居易詩歌中有大量造成詩人身體病痛的直觀書寫。這些疾病不僅給白居易帶來了生理上的不適,同時也對其心理造成了一定影響,一些無傷大雅的小病小痛被擴大到整個生活,心理學上把這種行為稱之為“自暗示”,“自暗示就是自己向自己暗示一種觀念,使他實現于動作”④。在這種心理暗示下白居易多次以“病身”入詩,如“無勞是病身”(《彭蠡湖晚歸》),“病身無所用”《病中書事》),“思量老病身”(《羅子》),“病身初謁青宮日”(《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新茗分張及病身”(《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病身不許依年老”(《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零落唯殘兩病身”(《歲暮病懷贈夢得》),“寂絕無人問病身”(《病中得樊大書》),“白發新生抱病身”(《重到城七絕句·高相宅》),“一葉舟中載病身”(《舟夜贈內》),“倚石攀籮歇病身”(《上香爐峰》),“病身佛說將何喻”(《病中詩十五首·罷灸》),“杖策人扶廢病身”(《強起迎春戲寄思黯》),“憂我貧病身”(《寄元九》),“便是衰病身”(《西原晚望》),“病身知幾時”(《村居臥病三首·其三》),等等,達二十余例。當一個人留意到自己發蒼、視茫、齒落、耳聾等容貌上的衰老變化,并能感知到這些身體上的變化帶給自己的“病身”之時,就反映了其對待衰老的高度重視和關注,但無論是哪一種意象都充分體現了白居易對身體的關注,對個體生命的關懷。
白居易詩歌中對于衰老的書寫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喜歡在除夕夜嘆老,這部分詩中出現了大量的有關于年齡的數字書寫。“他把紀歲時、紀氣血、紀一時之事結合起來,成為詩歌日常化編年書寫的代表。”⑤白居易將自身的身體狀況、一時之瑣事融入詩歌中的日常化書寫,這背后是惜時惜命強烈生命意識的體現。
除夕夜本是闔家歡樂,燈火通明,辭舊迎新的美好夜晚。詩人卻異常焦慮,感嘆時光易逝。歸結原因是因為除夕具有重要的時序意義,意味著一年的結束和新一年的開始。人人都害怕衰老,更何況是本就體弱多病的白居易。心理學中把這種現象稱為元擔憂。英國心理學家艾德里安·韋爾斯(Adrian Wells,1995)將擔憂分成Ⅰ型擔憂和Ⅱ型擔憂(元擔憂)。Ⅰ型擔憂是對特定情境的擔憂,是事件擔憂。Ⅱ型擔憂是在Ⅰ型擔憂基礎上形成的,其特點是個體對擔憂有明確的認識。有關元擔憂與焦慮交互作用關系的研究發現,長時間的焦慮導致元擔憂出現,元擔憂導致人們擔憂敏感性增強,使個體更多地注意擔憂信息,促使其產生更強的焦慮。⑥簡單來說元擔憂就是因為自己本身擔憂而擔憂。在除夕夜這樣的節日氛圍渲染下,本就體弱多病的詩人變得更加敏感,對眼前流逝的光陰也表現出格外的珍惜,體現在詩文活動中就是對年齡刻意的書寫。如,“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除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除夜寄微之》),“火銷燈盡天明后,便是平頭六十人”(《除夜》),“三百六旬今夜盡,六十四年明日催”(《除夜言懷兼贈張常侍》),“七十期漸近,萬綠心已忘”(《三年除夜》)。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白居易在中年后,對年齡增長問題的關注,四十八歲的除夕夜,白居易因為“老添新甲子”而“病減舊容輝”,面對明天就要四十九歲的自己,悔悟過往;五十二歲的除夕夜,白居易嗟嘆自己如今“鬢毛白毿毿”可依舊一事無成,心有不甘;五十九歲的除夕夜,白居易想著火銷燈盡之后自己就是六十歲的人了,陷入失眠;六十三歲的除夕夜,白居易感嘆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就在今天結束了,明天自己就要六十四歲了,借酒消愁;六十七歲的除夕夜,白居易感慨自己七十將近,已是家中最年長的人,孩童嬉戲打鬧,后代依次來舉杯祝酒,不悲不喜,此時白居易的心態較年輕時更加平和。在歲月更迭間,詩人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體的變化,頭發越來越少,牙齒越來越稀疏,身體越累越孱羸,看著歲月的消逝,詩人憂心忡忡無法安睡,這時便不由得感嘆“病眼少眠非守歲,老心多感又臨春”(《除夜》)。除夕夜失眠覺少不是因為守歲,而是因為新一年到來帶來的年齡焦慮。從這些除夕詩中可以看出詩人對自身衰老,生命流逝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詩人極強的生命意識。
二、身體書寫
中國傳統身體觀一直以來都堅持身心合一的觀點。正如《老子》所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⑦可見身心合一和苦樂同在一直都是先哲無解的命題,人類的身體作為有血有肉的生理組織,必然會受到來自外界和自身的共同影響。身體是人存在的根本,是主體思想的寄寓之處。在白居易的詩歌中有大量的身體符號書寫,甚至包含身體中各種各樣的器官。通過對白居易詩歌中出現的身體符號進行分類整理,發現其結果之豐富,種類之全面:
(1)軀體名詞:身、體、驅、形、骸、胸、臂、部、背、腰
(2)內臟名詞:心、肝、脾、肺、膽、腸
(3)頭部名詞:頭、首、腦
(4)面部名詞:臉、面、顏、頸、頤
(5)五官名詞:眼、耳、睛、齒、頭、牙、咽、喉、舌、眸、眉、耳、鼻、口、舌、腭、目
(6)四肢名詞:手、股、肱、指、掌、肘、臂、肩、足、腳、肢
(7)體液名詞:涕、淚、血、汗、脂
(8)體表名詞:皮、肉、肌、膚、乳
(9)體毛名詞:鬢、毛、發、須、髭、髯、髻
(10)骨骼名詞:骨、髓、骸
身體也是文學中不可或缺的表現要素,也很早就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表現對象之一。⑧從上古時期《彈歌》中簡單描述生產生活的歌謠開始,再到《詩經》《楚辭》中對愛情,美人的描寫,一套中國化的身體審美書寫范式就形成了。如,《衛風·碩人》用“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⑨來展示美女之神韻美。與之不同的是白居易因為自身多病羸弱,恐懼死亡。常以“衰鬢”“腰瘦”“白須”等意象入詩來暗示自身形象,形成了一種病態的身體審美觀。如下表:

白居易詩歌身體書寫所體現的這種病態審美觀念與傳統儒家“文質彬彬”的審美理念背道而馳。除了以“衰鬢”“腰瘦”“霜毛”等詞入詩之外。白居易還多次在詩中提及“老丑”一詞。如,“白發郎官老丑時”(《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趁伴入朝應老丑”(《初到洛下閑游》),“漸覺詠詩猶老丑”(《贈夢得》),“三嫌老丑換蛾眉”(《追歡偶作》),“漸覺花前成老丑”(《感櫻桃花因招飲客》),“年貌又老丑”(《隱幾贈客》)。白居易對于自身的身體書寫形成了一種自怨自艾的審丑美學風格。將衰病的體貌客體化,是自我觀照,自我審視,內省思考的一種體現。同時,白居易將自身衰老的真實狀況如實記錄在詩歌創作中的現象,顯示了其極強的自我關切意識。
白居易對于身體“年貌老丑”的自我嘲謔,自我調侃使得身體書寫發生了全新的變化,促進了身體美學由審美向審丑的轉變,顯示了一種不同于傳統傷春悲秋生命感知的豁達。
三、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是人類生活的本質問題,只有堅持生命至上原則,才能在此基礎上去探討其他問題。嘆時傷生、憂己思人、處病感懷一直是古代文人關注的重要話題,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內容則是文學對生命的表現。生命意識亦是白居易詩文中的重要表現對象,自幼體弱多病使他對人的疾病、身體、衰老等問題表現出極度的關注。
從《與元九書》中“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書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可以得知,二十歲的白居易便患有眼疾,因為科舉考試,作息紊亂,年紀不大,所患疾病種類繁多,因此白居易在后續的生活中展示了對個體生命極強關切的意識。為了讓自我生命得以延續,不因為疾病而早逝,白居易極其注重養生,寫下了大量的養生詩。這些詩歌中有對前人養生經驗的批判,也有自我養生實踐經驗的總結。《思舊》一詩典型概括了白居易的養生觀念。詩中舉韓愈、元稹、杜甫、崔玄亮的例子,揭示了服食丹藥對于身體的損耗,進而反襯自己不食丹藥老命得以延續。接著又說少壯之時被嗜好與欲望所牽制,不注重飲食,傷了精氣神,這些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人的壽命。“且進杯中物,其余皆付天”的感嘆也展現了白居易任憑造化,適性自得的通達和淡泊無欲的養生觀。
白居易的養生觀念主要體現在飲食養生方面。《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⑩,《禮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見食物是人類生存的重要物質基礎。白居易詩歌中提及的飲食可以概括為適量飲酒、粗茶淡飯。其飲食詩中多次提及喝粥。如“粥美嘗新米,袍溫換故綿”(《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融雪煎香茗茶,調酥煮乳糜”(《晚起》),“先進酒一杯,次舉粥一甌”(《新沐浴》),“空腹一盞粥,饑食有余味”(《閑居》),“留餳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雞毬餳粥屢開筵,談笑謳吟間管弦”(《會昌元年春五絕句·贈舉之仆射》),“黃耆數匙粥,赤箭一甌湯”(《齋居》),“酥煖薤白酒,乳和地黃粥”(《春寒》),“饑聞麻粥香,渴覺云湯美”(《七月一日作》),“何以解宿齋,一杯云母粥”(《晨興》),等等,從這些詩篇中可知粥不僅能起到充饑的作用,也可以制成黃耆粥、地黃粥、胡麻粥和云母粥等藥膳粥調理疾病,達到養生的作用。
綜上所述,白居易在養生方面頗有研究,有批判有繼承。在“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唐代,即使體弱多病仍然度過了人生75 個春秋。
四、結語
對于文學作品的研究,一部分從文學內部進行研究,另一部分從文學外部進行研究,如從社會學、歷史學、藝術學等的角度。二者結合當為一條行之有效且全面的研究路徑。這些跨學科研究的興起開拓了文學研究領域,但這種跨越的力度還不夠,還需要踏出文史哲這一領域。作家作為社會中的一個個體,其家族命運、身體變化必然會影響其心理狀態。心理狀態的變化會直接體現在作家的文學創作中,體現在作品中就是一種生命意識。
白居易詩歌語言的淺顯平易,很可能與其自幼體弱多病有關。唐代詩人中不僅僅白居易在詩歌中涉及疾病、身體、衰老三方面的書寫。王績、駱賓王、陳子昂、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孟郊、李賀等人都有所涉及。因此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我們可以開辟出一條疾病與風格之關系、身體與風格之關系、衰老與風格之關系的探索之路。將古代文學研究置身于不同的文化領域,從而促進古代文學作品的研究。
①郝素玲、魯興軒:《〈大地〉中的生命意識》,《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第93—97頁。
② 呂國喜:《論白居易閑適詩中的“病”》,《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83—86頁。
③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注》(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75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朱光潛:《變態心理學派別變態心理學》,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45頁。
⑤ 周裕鍇:《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43頁。
⑥ 鄭希付:《中學生元擔憂與一般焦慮》,《心理學報》2002年第3期,第284—288頁。
⑦ 湯漳平、王朝華譯注:《老子》,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9頁。
⑧ 龐明啟:《“剝落”的“老丑”:宋詩衰病書寫與身體審美轉向》,《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0—27頁。
⑨ 周振甫譯注:《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頁。
⑩ 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282頁。
? 李慧玲、呂友注譯:《禮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