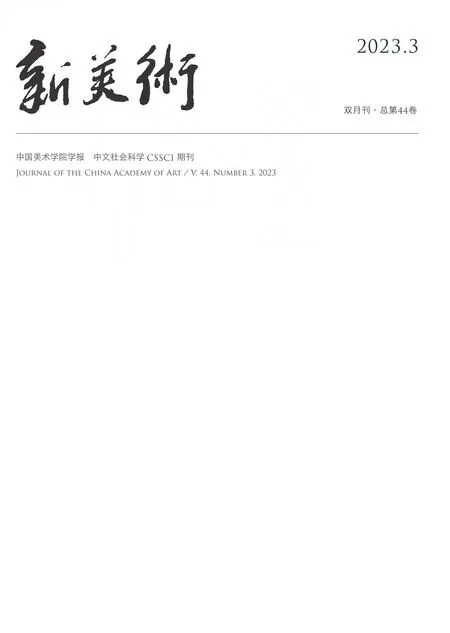平山郁夫作品中的光影建構(gòu)
王曉黎
平山郁夫是日本近現(xiàn)代繪畫(huà)史上被譽(yù)為“五山”之一的重要畫(huà)家,源于“玄奘精神”和敦煌藝術(shù)的滋養(yǎng),作品傳承日本繪畫(huà)的風(fēng)格,注重光影、色彩和寫(xiě)實(shí)技法的運(yùn)用,融合東西文化和思想,形成沉郁、嫻靜且富有東方審美意蘊(yùn)的現(xiàn)代風(fēng)格。本文通過(guò)闡述日本畫(huà)的平面性、裝飾性和朦朧感的特點(diǎn)來(lái)論述平山郁夫?qū)θ毡井?huà)的繼承,力圖剖析宗教美術(shù)思想與平山郁夫作品光影建構(gòu)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一步分析逆光、投影等西畫(huà)光影觀察法在其作品中的運(yùn)用。
一 日本畫(huà)平面性、裝飾性、朦朧感的傳承
日本在繪畫(huà)上善于向中國(guó)、向印度和向西方學(xué)習(xí)。如陳振濂所言:“(日本)作為本國(guó)繪畫(huà)的本體性不強(qiáng),反過(guò)來(lái)也就表明接受的寬容度大,因?yàn)樽晕乙庾R(shí)不根深蒂固,所以各種方法都可以借鑒來(lái)為己所用。”1陳振濂,《維新—近代日本藝術(shù)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shù)史比較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42 頁(yè)。源自中國(guó)的水墨畫(huà)、南北宗和文人寫(xiě)意畫(huà)發(fā)展而來(lái)的日本畫(huà)在變遷中,經(jīng)歷江戶時(shí)代的狩野派、琳派、四條派、浮世繪等發(fā)展階段,隨著明治時(shí)代(1868—1912)與西方交流的增多,以日本美術(shù)院和東京美術(shù)學(xué)校(今東京藝術(shù)大學(xué))為依托,形成“日本畫(huà)”和“西洋畫(huà)”并存發(fā)展的局面。“日本美術(shù)之父”岡倉(cāng)天心和芬諾洛薩以復(fù)興傳統(tǒng)日本繪畫(huà)為理念,呼吁“重振東洋美術(shù)”,同時(shí)創(chuàng)造“新日本畫(huà)”,勸說(shuō)畫(huà)家把西方繪畫(huà)的空間表現(xiàn)和光的表現(xiàn)植入到日本畫(huà)中,橋本雅邦、菱田春草、橫山大觀、小林古徑和下村觀山等畫(huà)家都積極投入新日本畫(huà)的探索。
日本畫(huà)在革新的同時(shí),保持其自身的鮮明特征:平面性、裝飾性,和朦朧美。日本的繪畫(huà)和工藝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對(duì)裝飾美感的追求普及于社會(huì)各階層。平面性和裝飾性存在于早期日本畫(huà)的發(fā)展中,尤其是琳派,琳派俵屋宗達(dá)和尾形光琳的畫(huà)尤其強(qiáng)調(diào)畫(huà)面的平面性,為凸顯主體對(duì)象,覆蓋不需要的因素,背景一律用金色(金箔或金泥)覆蓋,產(chǎn)生華麗的裝飾效果;同時(shí),構(gòu)圖既追求單純平面,又對(duì)細(xì)節(jié)進(jìn)行刻畫(huà),顯示舍棄之美和細(xì)節(jié)之美。相對(duì)弱化線,運(yùn)用明亮的色塊平涂,這種處理方式是抽象和具象的結(jié)合,平面化、單純、韻律、形式化,從而增強(qiáng)視覺(jué)沖擊力和形式美感。
日本畫(huà)在衍進(jìn)的過(guò)程中繼承包括朦朧法在內(nèi)的中國(guó)繪畫(huà)的風(fēng)格,中國(guó)藝術(shù)著意虛無(wú)和空靈的審美理想,體現(xiàn)“天人合一”的美學(xué)追求,為表現(xiàn)“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氣韻”和“意境”,作品中往往呈現(xiàn)出淡遠(yuǎn)、虛靜、朦朧的審美意象。橫山大觀、菱田春草和高山辰雄等畫(huà)家的作品正體現(xiàn)了朦朧美,他們?cè)趧?chuàng)作中削弱了傳統(tǒng)的墨線,在某些單獨(dú)的色塊或兩色塊相交接的邊緣采用虛接過(guò)渡法,類似國(guó)畫(huà)墨跡的湮暈,以表現(xiàn)光和空氣,使畫(huà)面彌漫著薄霧感、朦朧感,清幽的意象與朦朧模糊相融合,體現(xiàn)一種靜態(tài)的審美觀照方式,富有優(yōu)雅靜謐的東方浪漫主義情調(diào)。
平山郁夫的作品從《佛教傳來(lái)》《入涅槃幻想》(圖1)等佛教題材創(chuàng)作到《寂光》《羊群暮歸圖》等沿絲路采風(fēng)作品,以及《平等院》《唐昭提寺》(圖2)等日本庭院山水的描繪,都較好地繼承了日本畫(huà)的裝飾、平面化處理和朦朧美的特征,營(yíng)造出寧?kù)o、高雅、古樸的東方審美意境。他所處的社會(huì)背景適逢二戰(zhàn)后日本全面“西化”與日本民族意識(shí)覺(jué)醒相交集,是日本急速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時(shí)期,日本文化中引進(jìn)了西方觀念,平山郁夫就讀的東京藝術(shù)大學(xué)設(shè)立日本畫(huà)專業(yè)和西洋畫(huà)專業(yè),在專業(yè)學(xué)習(xí)上東西兼具。其畫(huà)學(xué)淵源師古,但不泥古,作品較少有其恩師前田青邨的影子。作為“東京美術(shù)學(xué)校”派之一的前田青邨繪畫(huà)風(fēng)格屬于典型的“和樣”,色調(diào)明麗、線條謹(jǐn)細(xì),平山郁夫作品中強(qiáng)烈的明暗對(duì)比、對(duì)光的表達(dá)顯然有別于恩師的傳統(tǒng)工筆重彩。他在《悠悠大河》中闡述自己大學(xué)期間研讀哲學(xué)和文學(xué),在佛畫(huà)和古典藝術(shù)中汲取的營(yíng)養(yǎng),包含西洋美術(shù)。2平山郁夫,《悠悠大河》,楊晶、李建華譯,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8年,第119頁(yè)。平山郁夫經(jīng)年累月的追隨玄奘足跡沿絲路采風(fēng),從而使他的畫(huà)既有對(duì)傳統(tǒng)日本畫(huà)的繼承,又有對(duì)西洋美術(shù)、敦煌壁畫(huà)以及阿旃陀石窟壁畫(huà)等中亞風(fēng)格的借鑒。

圖1 [日]平山郁夫,《入涅槃幻想》,昭和36 年(1961),180.7 cm × 226.5 cm

圖2 [日]平山郁夫,《唐招提寺》,昭和45 年(1970),50.0 cm × 65.2 cm
平山郁夫早期的作品呈現(xiàn)出表現(xiàn)主義特征,賦予圖像象征的含義。強(qiáng)調(diào)抒寫(xiě)內(nèi)心世界,在相對(duì)抽象的佛教題材中注入個(gè)人意志,產(chǎn)生“移情”的表征,揭示一種內(nèi)在的心理需要,體現(xiàn)畫(huà)家的主觀感情和內(nèi)心世界,以營(yíng)造具有“表現(xiàn)主義”意味的圖式表達(dá)的渴望,更具精神性。早年的人生磨礪是其創(chuàng)作的契機(jī),二戰(zhàn)時(shí)廣島原子彈爆炸造成的痛苦使他尋求抵達(dá)精神彼岸,來(lái)自身心的痛苦渴望被救贖。《佛教傳來(lái)》《入涅槃幻想》等作品顯然帶有戰(zhàn)后的創(chuàng)傷和隱隱的傷痛感,在題材上放棄現(xiàn)實(shí)世界,放棄對(duì)自然的模仿,以鮮明的主觀色彩和強(qiáng)烈的明暗對(duì)比創(chuàng)造“幻象”,在“幻象”中完成主觀精神的內(nèi)心體驗(yàn)。
二 宗教美術(shù)與光影建構(gòu)
平山郁夫的繪畫(huà)緣起于宗教,通過(guò)東西宗教美術(shù)的比較研究獲得啟示,認(rèn)為佛教、絲綢之路和東方傳統(tǒng)是日本畫(huà)發(fā)展的契機(jī),他畢生的繪畫(huà)創(chuàng)作也正圍繞這三方面來(lái)實(shí)踐探索。他從大量宗教美術(shù)和以宗教畫(huà)為主題的富有裝飾感的畫(huà)毯中獲得啟示,在畫(huà)面處理方式上適當(dāng)?shù)剡\(yùn)用西方繪畫(huà)的光影要素塑造二維空間,對(duì)形象的捕捉、感知呈現(xiàn)鮮明的個(gè)性特征。他圍繞絲綢之路的采風(fēng)創(chuàng)作反映其對(duì)自然山水和風(fēng)土人情的熱愛(ài),在對(duì)自然物象的描繪中感受宗教體驗(yàn)。平山郁夫的宗教情感是其靈感源泉,立足于東方的宗教美術(shù)探索是指引他前行的一道神光,勾連著東方意象審美、二維空間處理和深厚的禪宗思想。
宗教美術(shù)與光影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光被賦予象征性,用以表達(dá)宗教精神,東西方有著驚人的相似。在佛教中,佛陀發(fā)光是佛神性的表現(xiàn),佛光意為佛的智慧,是源自心靈的力量,是超乎一切力量的一種光。在西方宗教中,光同樣具有象征作用,魯?shù)婪颉ぐ⒍骱D吩凇端囆g(shù)與視知覺(jué)》闡述:“在圣經(jīng)中,光明象征著基督、上帝、美德、真理和救世主,而黑暗卻象征著妖魔與邪惡。”3魯?shù)婪颉ぐ⒍骱D罚端囆g(shù)與視知覺(jué)》,滕守堯、朱疆源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中世紀(jì)哥特式教堂彩色玻璃窗正是利用光與古希臘神話里的太陽(yáng)神阿波羅密切聯(lián)系,彩色玻璃鑲嵌成圖案或主題故事,經(jīng)陽(yáng)光照射,透過(guò)玻璃的光線投射到幽暗的教堂內(nèi),產(chǎn)生裝飾、宗教、神秘、詩(shī)意和圣潔的氣息,象征了上帝的到來(lái),如步入純凈的天國(guó),瞬間從世俗之中升華到崇高的境界。
光影并非中國(guó)畫(huà)和日本畫(huà)的聚焦點(diǎn),確切地說(shuō)是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畫(huà)。古代的日本美術(shù)是以初唐美術(shù)為基點(diǎn),日本畫(huà)早在奈良和平安時(shí)期向中國(guó)畫(huà)追摹學(xué)習(xí),東方繪畫(huà)的總體特征是注重表現(xiàn)情感和人格,具有主觀和精神指向,注重形線之美,不完全寫(xiě)實(shí),也不完全抽象,忽略物象的凹凸,通過(guò)二維平面塑造一個(gè)空靈的意境,表達(dá)一種對(duì)自然生命的體悟和超然胸襟。二戰(zhàn)后,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日本畫(huà)逐步與中國(guó)畫(huà)拉開(kāi)了差距,在繪畫(huà)中引進(jìn)西方的透視法、質(zhì)感畫(huà)法、明暗法等,弱化以線造型,講究光影,再現(xiàn)眼睛看到的三維空間,與西方繪畫(huà)產(chǎn)生了一定的融合。利用光影豐富畫(huà)面的視覺(jué)形象成為改造日本畫(huà)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這種趨勢(shì)下,平山郁夫?qū)で笥袆e以往的日本畫(huà)圖式,他立足宗教美術(shù),運(yùn)用西方的光影建構(gòu)探索精神層次的繪畫(huà)語(yǔ)言。平山郁夫的作品對(duì)西方光影運(yùn)用經(jīng)歷了兩個(gè)階段:一、早期追求特殊的光——逆光的運(yùn)用。如《袛園精舍》、《入涅槃幻想》《求法高僧東歸圖》等,這一時(shí)期的光具有象征作用,與精神緊密聯(lián)系。這“金色的光”是佛的象征,是一道點(diǎn)亮精神的靈光,體現(xiàn)莊嚴(yán)的宗教精神。二、中后期普遍光和反射光的運(yùn)用,如《東方的黎明》《法隆寺金堂》等作品,畫(huà)家從特殊光轉(zhuǎn)向普遍光、反射光和穿過(guò)半透明物質(zhì)的光,追求畫(huà)面的寧?kù)o、平和和優(yōu)美。隨著大環(huán)境的驅(qū)使,宗教的式微,作為重表現(xiàn)和象征意義的特殊光的運(yùn)用也逐步削弱,平山郁夫從追求強(qiáng)烈視覺(jué)沖擊力的畫(huà)面效果,轉(zhuǎn)向追求內(nèi)心的寧?kù)o悠遠(yuǎn)、作品呈現(xiàn)優(yōu)雅詩(shī)意的東方情調(diào)。
三 特殊光和自然光等西方光影觀察法的運(yùn)用
平山郁夫的代表作《佛教傳來(lái)》是以表現(xiàn)玄奘肩負(fù)崇高的使命西行印度求法為主題,表現(xiàn)高僧種種苦行后的開(kāi)悟,眼前一派生機(jī)盎然、充滿活力的場(chǎng)景,是表達(dá)畫(huà)家受白血病折磨內(nèi)心渴望獲得新生和光明。以和尚、黑白馬、和平鴿和植物作為畫(huà)面的主要構(gòu)成,樹(shù)葉、白馬和人物的膚色等大量運(yùn)用色塊的平涂,抽象化處理了人物的臉、手和足部,以金線象征性地勾勒人物衣紋,以虛接法營(yíng)造一種朦朧清新詩(shī)畫(huà)的情調(diào),體現(xiàn)出濃濃的裝飾風(fēng)格,實(shí)現(xiàn)了裝飾、抽象和象征的結(jié)合。平山郁夫說(shuō)這幅畫(huà)“舍棄以前具體寫(xiě)實(shí)的作畫(huà)手法,采用新的畫(huà)法,我試著把眼、鼻、口浸潤(rùn)在模糊的狀態(tài),著意表現(xiàn)其高于形體的精神上潛在的東西。畫(huà)形體也不用線條,而用相互融合的顏色搭配來(lái)表現(xiàn)。”4平山郁夫,《平山郁夫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07 頁(yè)。日本評(píng)論家河北倫明評(píng)論這幅畫(huà):“在獨(dú)特的群青主體的色調(diào)中,浸潤(rùn)著朱、金、白諸色的光澤,那老成練達(dá)中蘊(yùn)含著的勃勃生機(jī)、清新靜寂、高爽情懷,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5同注4,第5 頁(yè)。
《入涅槃幻想》刻畫(huà)釋迦涅槃入寂,眾弟子哀切地隨侍四周,白鴿飛舞,佛光流瀉,單純以金色、黑色和灰色營(yíng)造出的莊嚴(yán)肅穆氛圍,表現(xiàn)方式是繼《佛教傳來(lái)》的進(jìn)一步提煉,在內(nèi)在精神的意象表達(dá)中逐步融入對(duì)光的初步探索,光影強(qiáng)化氛圍的表達(dá),將裝飾、抽象和象征風(fēng)格推向極致,畫(huà)風(fēng)和圖式具有開(kāi)創(chuàng)意義。
《袛園精舍》(圖3)刻畫(huà)在印度舍衛(wèi)城中袛園精舍內(nèi)佛陀布施傳教的場(chǎng)景,和《建立金剛心圖》等作品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對(duì)光的探索,較多地運(yùn)用特殊光逆光,渲染光影,使畫(huà)面富有節(jié)奏和韻律,充滿神秘氣息。佛和菩提樹(shù)的背景以金色渲染,弱化人物臉部、衣紋和結(jié)構(gòu)的處理,它們依舊保持平面感和圖案化,大面積的菩提樹(shù)葉以塊面與線性元素相結(jié)合,極具表現(xiàn)力。畫(huà)家著意表現(xiàn)佛光照耀的神秘氛圍,強(qiáng)化戲劇性,光具有象征和啟示的功能。這一時(shí)期圖式中強(qiáng)烈光線的運(yùn)用并沒(méi)有刻畫(huà)投影和表現(xiàn)空間,延續(xù)日本畫(huà)的朦朧感,雖工尤寫(xiě),有意表現(xiàn)意識(shí)中的內(nèi)在精神。平山郁夫橫跨歐亞兩大洲的絲綢之路采風(fēng)中收藏了不少犍陀羅浮雕(圖4),其佛傳題材作品在圖式上與古印度犍陀羅浮雕存在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居中的面向觀者端坐的佛陀”或“涅槃的佛陀”“菩提樹(shù)”“信徒的體態(tài)、衣紋”等都有一定的形態(tài)相似性。

圖3 [日]平山郁夫,《袛園精舍》,昭和56 年(1981),六折屏風(fēng),171.0 cm × 362.0 cm

圖4 犍陀羅浮雕,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shù)館
平山郁夫多次描繪的《平等院》(圖5)以相對(duì)寫(xiě)實(shí)的筆調(diào)描繪夜晚寧?kù)o的日本庭院,鈷藍(lán)色的天空,灰藍(lán)色的湖水,虛淡的遠(yuǎn)樹(shù),古樸的樹(shù)木掩映著主題建筑鳳凰堂,沉穩(wěn)、凝重的畫(huà)面透露著東方審美的詩(shī)性和靜謐美。屋檐、遠(yuǎn)樹(shù)、地面、灌木叢和光等大量地運(yùn)用虛接法表現(xiàn)朦朧的意境,似籠罩在薄霧中,鳳凰堂大殿透出來(lái)的普遍光以及水面的反射光在這里顯得柔和又含蓄,光暈感以粉質(zhì)顏料厚涂,透出部分底色,形成色彩的疊加,具有眼睛即時(shí)看到的逼真感,這道光具有禪宗的靈韻。相類似的《唐昭提寺》《凈琉璃寺》《法隆寺金堂》等都運(yùn)用了逆光、漫射光和穿過(guò)半透明物質(zhì)的光增加畫(huà)面的靈動(dòng)和宗教氣息。

圖5 [日]平山郁夫,《平等院 》,昭和55 年(1980),41.0 cm × 53.0 cm
《寂光》(圖6)則描繪了中東絲綢之路采風(fēng)的某個(gè)場(chǎng)景,在伊朗伊斯法罕的伊斯蘭教馬斯吉德寺院內(nèi),寺院土黃色的圓屋頂,厚重的圓柱和視覺(jué)中心虔誠(chéng)的蒙著黑色面紗的女人,構(gòu)成異域風(fēng)情的純潔世界。在畫(huà)面右側(cè)普遍光的照耀下,圓柱的邊緣被模糊,光與影相互成就,光線與明暗賦予了宗教感。圓柱與陰影也因色彩的深淺變化產(chǎn)生了空間透視感,柱子和屋頂?shù)倪吘壗Y(jié)構(gòu)線完全弱化,以豐富的色塊作為銜接,不著過(guò)多的具象刻畫(huà),厚重的肌理質(zhì)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圖6 [日]平山郁夫,《寂光》,昭和46 年(1971) ,72.7 cm × 52.7 cm
《羅馬的黃昏》(圖7)更加忠實(shí)于自然和視覺(jué)效果,運(yùn)用西式的觀察和表現(xiàn)技法刻畫(huà)羅馬黃昏的穹頂和夕陽(yáng),光線感減弱,普遍光夕陽(yáng)的暖黃色彌漫整個(gè)畫(huà)面。畫(huà)家基于印象派觀察法,捕捉色彩,抓住光線稍縱即逝的印象,表現(xiàn)即時(shí)的色彩感受,以黃紫色調(diào)為主,穹頂?shù)倪吘夛@得模糊,有近實(shí)遠(yuǎn)虛的空間感,在普遍光影響下昏黃的天空和遠(yuǎn)處的穹頂顯得肌理層次豐富,富有油畫(huà)的厚重質(zhì)感,這里的光不再具有象征性,它是真實(shí)世界的媒介。《東都洛陽(yáng)白馬寺》(圖8)是平山郁夫西行追隨玄奘足跡采風(fēng)創(chuàng)作的作品,白馬寺和樹(shù)木隱匿在漫天的橘色中,在富有透視和縱深感的布局里,光影中的色彩產(chǎn)生變化,反射光影響下的天空、樹(shù)葉、塔身的色彩失卻了固有色,是畫(huà)家提煉的混合色,此時(shí)的畫(huà)家重視寫(xiě)生,光影作為視覺(jué)的中介,把世界看成了光影。

圖7 [日]平山郁夫,《羅馬的黃昏》,昭和60 年(1985),21.0 cm × 22.0 cm

圖8 [日]平山郁夫,《東都洛陽(yáng)白馬寺》,昭和51 年(1976),65.2 cm × 90.9 cm
綜上所述,平山郁夫?qū)獾奶幚砻黠@具有西方繪畫(huà)的特征,通過(guò)對(duì)光影強(qiáng)調(diào)和渲染,以和諧的色彩營(yíng)造出或強(qiáng)烈或?qū)庫(kù)o優(yōu)美的畫(huà)面氛圍,探索東方繪畫(huà)在二維空間上的延展性。前期在平面繪畫(huà)中引入歐洲中世紀(jì)宗教美術(shù)的光影感,利用特殊光逆光營(yíng)造出具有表現(xiàn)主義特質(zhì)的繪畫(huà)程式,富有象征意味,以強(qiáng)烈的明暗對(duì)比增強(qiáng)視覺(jué)感受,傳遞一種精神寄托。中后期較多地運(yùn)用普遍光、半透明的光營(yíng)造寧?kù)o悠遠(yuǎn)的氛圍,部分運(yùn)用印象派的畫(huà)法,使其“失去”固有色,著以眼睛即時(shí)感知的色彩,從表現(xiàn)內(nèi)心世界轉(zhuǎn)向探索可見(jiàn)世界,重視寫(xiě)生,作品體現(xiàn)出一種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19 世紀(jì)的日本畫(huà)壇,平山郁夫和東山魁夷、高山辰雄、加山又造、杉山寧(即所謂的“五大山”)一起完成了對(duì)西方繪畫(huà)的吸收和融合,對(duì)光影、透視、明暗技法的運(yùn)用以及繪畫(huà)材質(zhì)上的改進(jìn)縮小了東西方繪畫(huà)的本質(zhì)差別,完成了日本畫(huà)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轉(zhuǎn)型后的新日本畫(huà)光與影的關(guān)系相對(duì)曖昧,不具有鮮明的空間意識(shí),體現(xiàn)出折中主義的特征。現(xiàn)代日本畫(huà)則是具象表現(xiàn)和抽象表現(xiàn)相結(jié)合,仍然追求圖案式的平面效果,注重裝飾趣味,展現(xiàn)出新日本畫(huà)的深沉厚重之美,保留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精神,體現(xiàn)優(yōu)美、抒情、傷感、朦朧的風(fēng)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