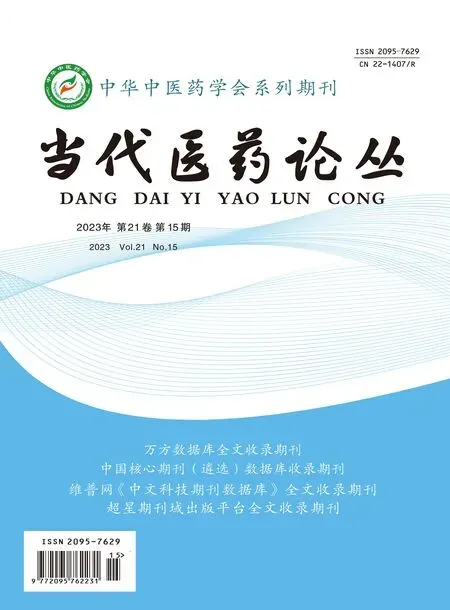外周血淋巴細胞/單核細胞比值在預測多發性骨髓瘤患者預后中的應用價值研究
趙海軍,張麗翠,張 玉,魏 瑜
(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檢驗科,新疆 石河子 832000)
多發性骨髓瘤(multipe myeloma,MM)是臨床上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主要臨床特點是分泌單克隆免疫球蛋白的漿細胞異常增殖。MM 占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的10%,本病患者占全部癌癥患者的0.9%[1]。臨床上針對MM 患者主要以藥物治療為主,常用的藥物有蛋白酶抑制劑、免疫調節劑等[2]。近年來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MM 的治療方案也更加多樣化,然而本病仍無法治愈,臨床只能通過治療延長患者的生存期,提高其生存質量。MM 患者的治療受到全球醫學界的關注,在新修訂的國際分期系統(revised 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R-ISS)中[3],將一些實驗室指標作為MM 患者治療效果和預后的預測指標,其中就包括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bsolute lymphocyte count,ALC)與 單 核 細 胞 計 數(absolute monocyte count,AMC)比 值(ALC/AMC ratio,LMR)[4]。國外的臨床研究顯示,LMR 是影響MM 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5]。本文就LMR 在預測MM 患者預后中的應用價值進行探討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20 年1 月至2022 年12 月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62 例MM 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病情符合《中國多發性骨髓瘤診治指南(2015 年)》[6]中關于MM 的診斷標準,且患者分為有癥狀和無癥狀兩類;(2)臨床資料完整,并能夠積極配合研究;(3)患者及其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并自愿參與。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惡性腫瘤;(2)既往治療中接受過化療;(3)既往有其他免疫藥物治療史;(4)中途因不可抗力因素退出研究。62 例MM 患者中,有男性患者33 例(53.23%),女性患者29 例(46.77%);中位年齡為64 歲(年齡范圍:54 ~74 歲),其中年齡≥65 歲者有17 例(27.42%);MM 分型:免疫球蛋白G(IgG)型41 例(66.13%)、免疫球蛋白A(IgA)型14 例(22.58%)、輕鏈型7例(11.29%);Durie-Salmon(DS)分 期:Ⅰ期11例(17.74%)、Ⅱ期10 例(16.13%)、Ⅲ期41 例(66.13%);R-ISS 分期:Ⅰ期13 例(20.97%)、Ⅱ期21 例(33.87%)、Ⅲ期28 例(45.16%)。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資料,并查閱相關病歷,對患者的性別、年齡、DS 分期、R-ISS 分期、血紅蛋白(Hb)、β2-微球蛋白(β2-MG)、血肌酐、乳酸脫氫酶(LDH)、骨髓漿細胞比例、LMR 等臨床資料進行收集、整理。隨訪及預后評估:對患者進行隨訪,隨訪方式主要為門診及電話隨訪,統計患者的5 年總生存(OS)率及無進展生存(PFS)率。OS 時間指從患者發病起至其死亡時間或末次隨訪時間;PFS 時間指從患者發病起至疾病進展或死亡的時間。觀察MM 患者LMR 閾值的分布情況,根據患者的LMR 將其分為高LMR 組與低LMR 組,比較兩組的5 年OS 率與PFS 率。對影響MM 患者預后的因素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MM 患者LMR 閾值的分布情況
根據ROC 曲線,將ALC 1.24×109/L 作為其最佳界值(AUC 為0.549、敏感度為70.38%、特異度為44.52%),據此將患者分為高ALC 組(≥1.24×109/L)和 低ALC 組(<1.24×109/L),例 數 分 別 為40 例(64.52%)、22 例(35.48%);外周血AMC 的最佳界值為0.60×109/L(AUC 為0.641、敏感度為33.78%、特異度為83.29%),據此將患者分為高AMC 組(≥0.60×109/L)和 低AMC 組(<0.60×109/L),例數分別為44 例(70.97%)、18 例(29.03%);外周血LMR 的最佳界值為3.60(AUC 為0.599、敏感度為41.00%、特異度為41.00%),據此將患者分為高LMR 組(>3.60)和低LMR 組(≤3.60),例數分別為39 例(62.90%)、23 例(37.10%)。
2.2 LMR 與患者預后之間的關系
按照國際骨髓瘤工作組制定的療效判定標準展開判斷,療效分為完全緩解、部分緩解、穩定、進展。對患者化療4 周后的療效展開評估,本研究的62 例MM 患者中,44 例患者治療有效,有效率為70.97%。所有患者均能接受隨訪,將其納入生存分析中,結果顯示高LMR 組的5 年OS 率為84.62%(33/39),低LMR組 的5 年OS 率 為56.52%(13/23),組 間 差 異 明顯(P<0.05)。高LMR 組的5 年PFS 率為76.92%(30/39),低LMR 組的5 年PFS 率為30.43%(7/23),組間差異明顯(P<0.05)。
2.3 影響MM 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分析
以5 年OS 為預后良好,展開單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年齡患者的5 年OS 率差異不顯著(P>0.05);不同DS 分期、Hb、β2-MG、血肌酐、LDH、骨髓漿細胞比例、LMR 患者的5 年OS 率差異顯著(P<0.05)。詳見表1。

表1 影響MM 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分析[例(%)]
2.4 影響MM 患者預后的多因素分析
將經單因素分析后有顯著差異的因素納入到多因素分析中,再將性別和年齡這兩個常見影響因素同時納入多因素分析中,結果得出,DS 分期 Ⅲ 期、LDH >245 U/L、β2-MG ≥5.5 mg/L、Hb ≤110 g/L、LMR ≤3.60 是導致MM 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詳見表2。
3 討論
惡性腫瘤在發生、發展的過程中,會伴有免疫系統的改變,炎性反應使大量白細胞聚集并凋亡,這對患者機體的抗腫瘤免疫應答反應有嚴重的影響,進而使腫瘤細胞數量大幅度增加。淋巴細胞、單核細胞是人體內重要的免疫細胞,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7]。外周血ALC、AMC 及LMR 是一類相對容易獲得的免疫檢測指標[8],且檢測費用較為廉價,對患者造成的經濟壓力較小,患者更容易接受。現階段,臨床上關于LMR 與腫瘤相關的機制并不十分明確,這與患者治療前的免疫抑制、免疫缺陷、機體對淋巴細胞的依賴性等均有很大關系[9]。而MM 的發生與機體免疫功能缺陷密切相關,雖然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MM 患者在病情進展的過程中,會出現局部或全身免疫微環境的改變[10],其中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均參與了腫瘤的發生、發展,對二者及其比值進行測定有助于評估患者的預后,包括5 年OS 率與PFS率[11-12]。本次研究選取的指標均與臨床密切相關,可以很好地評估MM 患者的治療效果及預后。本研究中,高LMR 組的5 年OS 率為84.62%(33/39),低LMR組 的5 年OS 率 為56.52%(13/23),組 間 差 異 明顯(P<0.05);高LMR 組的5 年PFS 率為76.92%(30/39),低LMR 組的5 年PFS 率為30.43%(7/23),組間差異明顯(P<0.05)。此外,本研究還發現,DS 分期Ⅲ期、LDH >245 U/L、β2-MG ≥5.5 mg/L、Hb ≤110 g/L、LMR ≤3.60 是導致MM 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見,LMR 是MM 患者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P<0.05)。這是因為,LMR 可以有效反映MM 患者體內抗腫瘤細胞的增殖、擴散能力[13],LMR 較低者體內抗腫瘤免疫應答被抑制,腫瘤細胞惡性增殖活動加快,故其預后較差。同時,ALC作為適用性免疫效應細胞,其功能被抑制可導致機體對腫瘤細胞等有害因子的抵抗力減弱,這類患者更容易出現感染等情況,導致其預后不良[14-15]。
綜上所述,LMR 在MM 患者的預后預測中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可為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