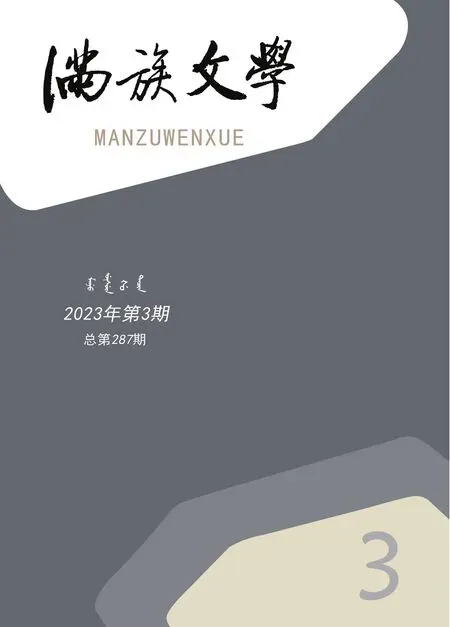琴 心
孟紅娟
一
殘陽從寬闊的江面上褪去,漸漸隱入對岸的叢林。在江邊守了一天的釣翁已收竿回家。天色已暗,山上的杜鵑獨自在暮色中燦爛。七里灘的潮水已退,江水汩汩,緩緩而淌。不知何時,一彎淡月在寬闊的江面上升起。月色清幽,靜靜地照拂著睦州的山川民居。這是一個江清月靜的夜晚,三山塔上的鐘聲鐺鐺鐺地響了數下。
宋景佑元年(1034)的一個春夜,睦州郡所內,燭火通明。四十六歲的新任知州范仲淹邀請幾位幕僚好友與僧人來公署小聚。幾杯薄酒下肚,諸位心情暢快,一致邀請范仲淹撫琴助興。
此次雖被貶睦州,但范仲淹一路行來,心情隨著景色不斷變化,舟行陸替,行程中留下不少詩作,尤其是睦州清麗的山水,激發了他疲憊已久的心。酒助雅興,范仲淹在眾人注視的目光中,走到琴桌前,抬頭望了望窗外的明月,月兒如勾,月色清幽,時不時有淡淡的片云飄過。范仲淹微熏的臉色泛著紅光。仆從在琴旁點了一支細香,輕煙裊裊,范仲淹定神回憶了白天去探訪過的嚴子陵釣臺,然后端正身姿,調整心緒與呼吸,對準徽位,彈起他一生中最愛的曲子《履霜操》。
曲音憂傷卻堅定。
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親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擔任右司諫。當時仁宗與郭皇后不和,偏聽偏信,決定廢后。而范仲淹認為“郭后無故不可廢”,結果被仁宗皇帝一紙詔書,貶到睦州,這是范仲淹人生中的第二次被貶。
景佑元年(1034)正月,范仲淹帶領家眷離開汴京,其間經過穎河、淮河、錢塘江和富春江。那天,他們的船正行淮河上,遭遇狂風大雨,波浪翻滾,差點把船掀翻,坐在船上的妻兒嚇得紛紛抱怨行程艱難。面對妻兒的埋怨,范仲淹自信地認為自己對國家一片忠誠,不會像屈大夫那樣有葬身汨羅的下場。想到這段驚險的經歷,他寫下了《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詩,講述了他在自然旅途中遇見的風險,其實也是他人生仕途上風波迭起的反映。在各種兇險的波浪和風險面前,范仲淹始終以積極豁達的心態面對,“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折射出他關愛別人,拯救他人的品行和風范。
四月中旬的江南,春意正濃,楊柳依依,草木清新,花含笑,水潤媚。范仲淹經過三個多月和三千多里水路的長途跋涉,終于疲憊地到達了令他向往已久的嚴陵之地。
睦州一帶,雖然山多地薄,人口稀少,但自然風光似詩如畫,孕育了眾多的文人雅士,還誕生了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睦州詩派”,僅唐朝就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等大詩人。這里的山水和人文,都是他心里仰慕的。
赴任之初,他心中郁積著諸多不解和愁懷,心想自己好心相諫,卻被奸臣所阻。然而一路行來,尤其是到了富春江嚴陵勝境,所有被貶的不快和郁結都被這里的明山秀水一一化解了。于是,到桐廬郡后他便以樂觀的心態一氣呵成寫下了《出守桐廬道中十絕》,這里的江山云水,這里的滄浪溪水,這里的鱸魚白鳥,都讓人素心悠然、怡身養病。這十絕,是他在桐廬郡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的真實寫照,他慶幸自己與這一方水土有緣。因而,到任不久,便給恩師晏殊寫了一封信,信中描寫了桐廬郡的自然奇勝,以及他在桐廬郡與幕僚章抿、阮逸和僧人、野客等寫詩彈琴、樂而忘形的生活狀態。書信的字里行間充溢著飽滿的情感,逸興高遠,絲毫不在吳均的《與朱元思書》之下。
“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齋中偶書》)研《易經》,操古琴,是范仲淹的兩大終身愛好。無論在桐廬郡還是其他地方,這兩大愛好始終跟他不離不棄。今晚,月夜下飲酒彈琴的雅興,正是《與晏殊書》和《齋中偶書》詩的生動還原。
收回那野馬般跑遠的思緒,范仲淹將目光聚焦在古琴上,又彈了一遍《履霜操》,輕靈的泛音仿佛嚴陵溪的潺潺清流和泠泠春水;上行下行,靈活的走手音恰似嚴子陵的高風。有人評價范仲淹,以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名垂千古,又以《履霜操》一曲盡得千年風雅。
在桐廬郡任職期間,范仲淹除了修建嚴子陵祠堂、做澤惠鄉民的好事,在公暇時間賦詩彈琴外,還游覽烏龍山,探訪方干故里。他以這里的山水為對象,寫了氣勢非凡的《瀟灑桐廬郡十絕》。十首詩的每首都以“瀟灑桐廬郡”開頭,春茶、畫樓、隱泉、清潭、蓮花……這里的“神仙境”,充分陶冶了范仲淹的性情,桐廬更因范仲淹有了一個響亮的前綴詞——“瀟灑”。
詩言志,琴言心,瀟灑桐廬郡,使范仲淹這位憂國憂民的政治家詩興大發,也令他琴意更濃。
二
夜已深,諸人盡興而歸。
清澈的月光透過窗戶,照進范仲淹的臥室,落在他的枕邊。范仲淹躺在床上,思緒萬千,今晚的琴酒雅興,讓他興奮得失眠了,想到從汴京來桐廬郡的日日夜夜,盡管時間不長,但這里的山水和人文足以讓他頻頻咀嚼。哼著《履霜操》的旋律,就著清亮的月色,他輕輕打開青壯年時代愛琴、學琴、賞琴的記憶之門。
范仲淹兩歲,父親范墉因病去世。他們孤兒寡母,生活陷入困境。母親只得帶著他再嫁到山東淄州長山縣令朱文翰家,取名朱說,直到他入仕那年,才奉母命還范姓,改回姓名。
二十歲那年,范仲淹曾遠游陜西,結識了鄂縣(今河南睢縣西北)名士王鎬。
“王鎬善琴,其清而賢,隱而未出。平日里襲白衣、跨白驢,枕琴籍書,縱飲浩歌,優游云泉,有嵇阮之風。”他欣賞、羨慕王鎬襲白衣、跨白驢的魏晉風度,并因王鎬結識了河南汝南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寶、浙江臨海精于易學的道士屈元應。他們四人各有所長,但都愛好和精于古琴。那段時間,他們朝暮相處,彈琴弦歌,生活雖苦,但因為有琴,精神卻無比自由快慰。他一生愛琴,自稱“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得益于跟他們的交往。
二十一歲時的范仲淹,在長山附近的醴泉寺讀書。他認為一個人非刻苦不能有成,每天只煮一盤粥,凝結后分成四塊,早晚拿兩塊粥凍,夾著幾根切碎的咸菜吃,這樣的生活一直過了將近三年。他的《薺賦》詩流露了獨特的志趣:“陶家翁內,腌成碧綠青黃,措入口中,嚼生宮商角徴。”對范仲淹來說,無論走到哪里,茶飯可以不思,但琴劍必須隨身。他在《和楊畋孤琴詠》里表達了對琴的喜愛:“愛此千里器,如見古人面。欲彈換朱絲,明月當秋漢,我愿宮商弦,相應聲無間。自然召南風,莫起孤琴嘆”。或許,琴是他與天地溝通的最好方式。
兩年后,他到應天府書院(今河南商丘)讀書。應天府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校舍宏偉,藏書數千卷。這里的學習環境令范仲淹如魚得水,不思晝夜。五年的刻苦攻讀,終于列榜。其間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有詩書琴畫相伴,卻樂在其中:
“白云無賴帝鄉遙,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風鳥,薄才猶可賦鷦鷯。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鐘期恨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
這是他丁母憂期間,應恩師晏殊之請,執掌應天書院時寫給晏殊的詩。詩句連用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伯牙巧遇知音鐘子期、左思賦詩山苗蔭澗松等典故,來表達他貧賤益奮不移安邦之愿、窮且彌堅不墜青云之志的胸懷,他以顏回那種直面人生、笑對苦難的精神鼓勵自己。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四十歲時,在晏殊的推薦下,榮升為秘閣校理,負責宮廷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實際上是皇帝的文學侍從。期間,他有機會與館閣文臣、當朝琴藝第一的宮廷樂師崔遵度結識,并師從崔遵度學琴。
學琴期間,他曾向崔遵度請教,如何彈出感人至深的曲子。崔遵度說:“清厲而靜,和潤而遠”。崔遵度的這一回答,成為日后決定中國琴風的千古名言,清雅和潤、靜遠淡逸,定下了中國古琴的基本風格。至明末清初,江蘇常熟有虞山派出,抉漢唐以來中華琴學之精微,倡導“輕微淡遠”之旨,崇雅黜俗,凡琴上取躁急之聲、有重濁之情者,不合淡遠之旨、無有輕微之意,便不合雅正之道,非古琴之“正音”。就此而言,箏笛琵琶之高亢、嘹亮、急促和華麗,與清虛曠遠、淡中有味的古琴音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經過思索,范仲淹終于理解了“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歟”。這也正是他的琴道觀。
北宋琴家朱長文的父親朱公綽是范仲淹的高足。任過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的朱長文,對范仲淹特別敬慕,他說:“君子之于琴也,發于中以形于聲,聽其聲以復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務多趣巧,以悅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彈雖少,而得其趣蓋深矣。”君子撫琴,在于中正平和,而非取悅他人,范仲淹雖然技藝一流,但彈奏的琴曲并不多,他對琴理的領悟非常深刻。
范仲淹一生只彈《履霜操》一曲,此曲足以撫慰他屢屢受傷而不屈的心靈。
這是一首什么樣的曲呢?蔡邕《琴操》記載:“《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伯奇被逐出家,清晨履霜,自傷無罪,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故事中的伯邦實可惡,伯奇令人同情。伯奇用琴聲表達自己的心聲。
魏晉大琴家嵇康在《養生論》中云:“撫琴若心自適,無弦亦可。”相傳陶淵明不會彈琴,卻要長年在家中放一把無弦琴,每逢酒酣意適,輕輕撫摸,無聲勝有聲,不失為靈魂的寄托。我以為,范仲淹彈《履霜操》也同此境,白日辛苦,人事復雜,靜夜撫琴,熱一爐檀香,于裊裊青煙中體味清虛曠遠之境,身體得以暫歇,心靈得以超越。
嚴陵灘邊月色皎,范公府內花含嬌。因操縵《履霜操》曲而失眠的范仲淹,枕著月光,將青少年時代的成長道路及自己對琴的癡迷情懷梳理了一遍,逝去的一幕幕跟琴曲一樣,沉靜曠遠,總是適時地蕩漾在他內心深處。如今已是中年的范仲淹,有緣瀟灑在桐廬郡的釣臺、千峰、白云、清溪和滄浪里,對生命、國事和琴道又有了更深的感悟。
三
夜寂靜,天光微明,范仲淹仍無睡意,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遭貶的經歷。那是他在任睦州知州前幾年的天圣七年(1029),由于上書劉太后還政于仁宗,結果被貶到陳州(今河南淮陽)做通判,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波折。
憶起在陳州任地方官時,他曾在一個仲秋之夜聽當地一位高僧真上人彈琴,并作詩《聽真上人琴歌》。詩中,他以一個知音者和藝術家的手筆,聲情并茂地描繪了真上人豐富多彩、優美傳情的琴聲:“隴頭瑟瑟咽流泉,洞庭蕭蕭落寒木。此聲感物何太靈,十二銜珠下仙鵠。”琴聲在他內心掀起強烈的共鳴,不禁淚如雨下,“伏羲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詩中,他還從一個被貶之臣的博大胸懷和政治家的視角發出了響亮的呼喊:“乃知圣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興亡哀樂不我遁,坐中可見天下心”,富于哲理的感慨和呼喊折射他心憂天下、愛民萬物的政治家形象和海納百川的胸懷,這無疑是他作為一位政治家在音樂思想領域的獨見,難怪后人贊他不愧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偉人。
有人讀了《聽真上人琴歌》,如此高度評價:“前有白居易‘江州司馬青衫濕’,后有范仲淹‘我聞遺音淚如雨’。”
回憶自己賞琴、愛琴、彈琴的一幕幕,范仲淹覺得自己更喜歡在琴曲中思古。他在《鳴琴》詩中寫道:“思古理鳴琴,聲聲動金玉。何以報昔人,傳此堯舜曲。”堯舜二帝是遠古時期的圣人,他們的德行受世人尊敬。《呂氏春秋·察賢》:“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后人用“鳴琴”稱頌地方官簡政清刑,無為而治。《鳴琴》詩恰恰反映了范仲淹崇古且追求中和之道的價值取向,事實上這正是他多年為政之道的心聲。
宦海人生,風云多變,他將自己的政治思想融于琴學理論,將音樂同治世之道、人生志趣聯系在一起。他在《與唐處士書》中提出了“琴不以藝觀”的思想。文中說:“蓋聞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以后,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后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可見,他所推崇的是上古的、也是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他反對后世傳者的“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反對把古琴當作“藝”來對待。他認為崔遵度琴藝最值得稱道的是“清靜平和,性與琴會”,只有琴與人合,人與音合,音與弦合,才能進入超凡脫俗的境界。
范仲淹所反對的這種琴藝,正是藝人琴,尤其是唐代以來的藝人琴。他的這個觀念,影響極為深遠,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在復述這個命題,堅持古琴不是樂器、琴樂也不是音樂的觀點。
其實,范仲淹的琴樂理論與他的政治觀點是同頻共振的。他主張“儒者報國,以言為先”,他認為“治樂同治世,治樂尤治心”。他作詩“奏以堯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顧我亦依依。月有萬古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歌,憑月為知音”。其心灼灼。因而在他的為政生涯中,他總是不斷上書朝廷,希望校正時弊,但是屢言屢貶。然而,無論仕途如何坎坷,他總能胸懷坦蕩,自適自安,因為他知道曲高則和寡,他相信自己“此心良可歌”,希望與先輩,唐朝宰相范履冰那樣,跟天地自然、古琴、以及象堯舜一樣的有德之人引為知己。
不出其然,他在睦州待了不到半年,便改任蘇州知州。第二年,因在蘇州修建水利有功,被召回朝廷任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升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可是后來因《百官圖》一事得罪了丞相,出為饒州(今江西鄱陽),那是他第三次遭貶。
四
生命就是一首悲歡交響曲。
這夜,失眠的范仲淹慶幸自己雖沉浮于宦海,但生命中總有一些知音伴隨,共同的志趣讓他們彼此相知相契,這足以填補生命中的缺憾和失意。他向來把與名士交游、與知己論道、與隱士唱和看做人生的樂事。他曾說過:“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黃。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
躺在床上,他在心里默數著生命里的一個個琴中知音,除青少年時期交游的王鎬、周德寶、屈元應這幾位研道的琴友和恩師崔遵度及高僧真上人外,還有處士唐異和隱士林逋等人。
范仲淹曾問崔遵度,當朝還有誰與崔公志同道合,誰的琴藝可與他比擬。崔說非唐異處士莫屬。范仲淹敬佩唐異的琴藝,更崇仰他“厭入市朝如海燕,可堪云水屬江鷗”的高潔。
枕著如水的月光,范仲淹繼續回憶與唐異的交往。他曾寫信給唐處士,期望得到唐異的傳授。在《與唐處士書》中,范仲淹除了闡述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等琴理外,還慨嘆秦以后琴道散失,而他所在的大宋,“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他為自己尋到能學琴與琴道的老師,快樂如孺子。而唐異也敬重范仲淹,請他為自己的詩集作序。兩人以文相通,以琴相友,最終結成了知交。
范仲淹交友有自己的準則,那就是“惟德是依,因心而友”。一個個人物從他眼前晃過,唐異是崔遵度推薦給他的知交,他還十分欽慕當朝隱士林逋。
林逋比范仲淹大二十一歲,后人稱他和靖先生。林和靖幼時刻苦好學,通曉經史百家。長大后,曾漫游江淮間,后隱居杭州西湖,結廬孤山。
天圣三年(1025)前后,范仲淹曾懷著仰慕的心情給林逋寄贈過詩作。林逋回贈《送范寺丞》,詩中,林逋把范仲淹比喻為漢代的司馬相如和位卑敢于進諫的“仙尉”梅福,流露出欽佩和期許。有了詩作往來后,在興化任職的范仲淹便幾次去杭州孤山,即便《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還要再去,當他再訪林逋時,正值孤山天氣放晴,草木蔥籠,上岸后即見到“碧嶂淺深驕晚翠,白云舒卷看春晴”。從冗雜的宦海來到明凈的孤山,范仲淹感到內心澄澈敞亮,仿佛“尋仙入翠屏”。那天,他們一起撫琴飲酒論詩賞鶴,縱談古今,忘了身在何處。
其實,范仲淹的知交琴友中,還有后來的僧人音樂家日光大師。仁宗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由鄧州(今河南鄧州市)移知杭州,這是范仲淹經歷了抗敵西夏的勝利,又經歷了“慶歷新政”的失敗,罷去參知政事之職,知鄧州三年后。這時,離他在鄧州作《岳陽樓記》已兩年多時間。
范仲淹到杭州后,去天竺山尋訪了一位已經十多年不下山的故交、僧人音樂家日光大師,還聽了他的演奏。日光圓寂后,范仲淹踐約為這位和尚作了一篇《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在“塔記”中,范仲淹稱贊日光大師沉穩自如的音樂演奏:“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纎失,徽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這是一流演奏家所特有的風度。范仲淹的這篇“塔記”,實為借日光大師“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樂進一步闡明自己“琴不以藝觀”的音樂理論。
由此,想到我平時練琴,徽位總是拿捏不到位,尤其是十八、七九、七六、六二、五六等弦位,常有偏差,自然很難奏出山泉泠泠般的琴音,為此老師曾教我用西畫的平面透視法來準確定位。可以想象,范仲淹平日操琴,肯定受過日光大師的影響,他彈《履霜操》曲,厚重而不粗糙,輕靈而不虛飄,快速而不急促,遲緩而不松弛。同時,范仲淹這篇塔記本身,也是一首旋律優美、韻味醇厚的“天竺琴歌”。
對范仲淹來說,沒有琴,人生與生活都是不完整的。富春山白云悠悠,富春江碧水長東,范文正公琴心可鑒,范履霜,琴心中飽含著的憂樂正時時洋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