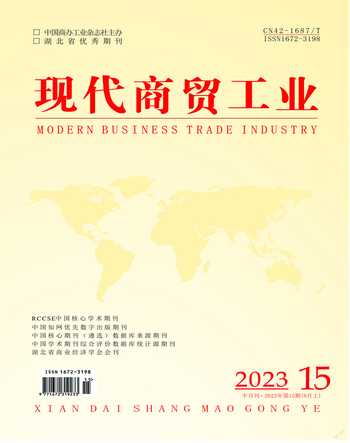“知假買假” 藥品消費的懲罰性賠償研究
藍天駿 王依婷 張雅靜
摘?要:“知假買假”是懲罰性賠償制度出現以來不可避免的伴生問題,關于“知假買假”行為的具體性質及其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討論,自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后就從未停止。由于藥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其產品的安全性要求更高,因此我國司法領域對“知假買假”藥品消費的懲罰性賠償一般持肯定態度,但由于其缺少高位階的立法支持,故仍需從法律證成與適用邊界兩個角度進行制度完善。
關鍵詞: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5.055
1?問題的提出
懲罰性賠償是一項起源于普通法系的較為特殊的賠償制度,但由于其與大陸法系傳統民事賠償體系的“同質補償”基本原則相悖,因此在我國引進該制度的初期就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自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首次對懲罰性賠償進行規定后,經歷了三十余年的探索發展,雖然我國關于該制度立法選擇的討論已趨于同一,大多學者都肯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但司法實踐中關于懲罰性賠償的具體適用仍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亟待完善。消費者保護領域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起步最早、研究最多的領域,在發展過程中,陸續在商品房、食品、藥品等領域分別細化出了具體的規范。藥品安全是與人民健康息息相關的基礎性民生工作,根據黨的二十大提出的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要求,積極探索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既是黨和國家對法學研究提出的任務要求,也是法學領域利用自身優勢對國家治理進行的積極探索。與懲罰性賠償制度誕生相隨的是實踐中不可避免的“知假買假”亂象的產生,基于此,本文欲對“知假買假”藥品消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肇始、現狀及未來進行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適用肯定的法理依據是什么。
第二,“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適用的現狀如何及存在哪些問題。
第三,“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規則的完善路徑是什么。
2?“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適用的正當性基礎
2.1?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的理論價值
2.1.1?彌補了民刑二分體系產生的立法空白
傳統的侵權責任體系以填補損害為核心,并不具有懲罰侵權人的職能,只有在侵害發生后,才能要求侵權人在其造成的損害的限度之內承擔責任。在制售假藥侵權行為中,如果嚴守傳統侵權責任法的實際損害限度,會導致制售假藥行為因為違法成本極低而無法得到有效的遏制。雖然《刑法》中也有生產、銷售假藥罪等相關罪名對嚴重的制售假藥行為進行規制,但與構成侵權相較,構成犯罪的門檻較高,一些尚未入刑的較嚴重的制售假藥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的規制。對比其他普通商品,藥品與消費者的生命權、健康權聯系密切,在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因此在藥品消費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理論,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可以有效地填補一般侵權損害賠償與刑罰之間的空白,對制售假藥行為形成連續性的規制。
2.1.2?豐富了賠償制度的內涵
由于一般侵權損害賠償僅僅可以實現矯正正義,并不關心藥品生產者、銷售者同藥品消費者之間的地位與資源差異,因此,只能產生恢復藥品消費者受到制售假藥侵權前原狀的作用,但不能預防或懲罰制售假藥行為。在藥品消費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理論,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豐富了侵權賠償制度的內涵,除了填補損害外,還通過懲罰、報復制售假藥行為,產生了預防和遏制潛在的制售假藥行為的效果,并在矯正正義的基礎之上堅固了分配正義的實現,體現了私法邊緣公法化的大趨勢。
2.2?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的實踐價值
2.2.1?凈化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發展
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一方面,通過“特別嚇阻”增加了制售假藥行為人的經濟負擔與違法成本,使其因懼怕承擔更大的賠償責任而不敢再為同樣的行為,通過“一般嚇阻”使制售假藥行為人外的其他人不敢為類似的不法制售假藥行為,降低了制售假藥行為發生的風險。另一方面,通過較高的訴訟回報,激勵更多的主體參與到制售假藥治理當中,加大了打擊制售假藥不法行為的力度。最終實現多管齊下,促使藥品制售主體合法合規地從事經營活動,凈化了藥品生產、銷售市場的環境,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經濟發展。
2.2.2?推進法治進程
傳統的產品質量侵權糾紛中,由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較高,維權收益較低,許多消費者都選擇了息事寧人,放棄了通過法律途徑進行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久而久之,助長了制售假藥者的囂張氣焰,不利于藥品消費領域的法治進程推進。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使被侵權人更為積極地尋求法律救濟,維護自身的利益,促進了藥品消費者法治觀念的形成,提升了藥品消費領域的法治化程度。
3?“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3.1?“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現狀
3.1.1?立法現狀
《藥品管理法》第144條第3款規定了制售假藥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但在該法中并未明確規定“知假買假”的性質及其是否應受該條保護。實踐中肯定“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的最直接的依據源自2013年通過的司法解釋(以下簡稱《食藥糾紛解釋》的第3條,該解釋規定制售假藥行為人不能以藥品購買者明知藥品存在問題為由進行抗辯。2017年公布的最高法工作文件(以下簡稱《2017年最高法意見》)對前述司法解釋的第3條的政策考慮與適用范圍等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與明確,指出由于藥品直接關系到購買者的身體健康,是具有特殊與重要安全性的消費產品,因此法院不能因購買者“知假買假”而不予支持購買者的主張,但這種特殊政策不宜推廣到食品、藥品外的其他領域。2021年《食藥糾紛解釋》進行修正時,該解釋第3條并未發生變動,體現了最高法對“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仍持肯定態度。
3.1.2?司法現狀
在裁判文書網以“知假買假”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共有判決書6915份,其中2012年5份,2013年19份,2014年87份,2015年391份,2016年709份,2017年1759份,2018年1363份,2019年750份,2020年877份,2021年645份,2022年304份。對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2013年《食藥糾紛解釋》頒布后至《2017年最高法意見》頒布前相關案例數量逐年遞增,從側面證明了對“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的肯定極大地促進了購買者積極維權,甚至催生了職業打假現象。2017年之后,在最高法的要逐步遏制通過職業打假謀取不當利益的主張指導下,“知假買假”相關案例的數量開始逐漸回落,至2022年,全年僅有304份,雖然數據受到了疫情等環境因素的影響,但也反映了目前嚴格限制“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司法態度。
3.2?“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的問題
3.2.1?缺少明確的“知假買假”藥品購買者獲取懲罰性賠償權利的規范文本法律證成
之所以“知假買假”藥品消費者獲取懲罰性賠償權利一直飽受爭議,很大程度上源于當前關于其正當性的理論證成大多從經濟法的價值保護體系入手,缺少必要的規范文本法律證成。“知假買假”藥品消費行為中出售藥品者是否需要承擔法律上規定的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民事法律基礎是傳統買賣合同中的出賣人的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民法典》在第613條中規定了出賣人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排除,并且未規定例外情形。體現了在傳統民法理論上,買受人的“不明知”是出賣人承擔義務的前提。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3條第1款也排除了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前已知瑕疵且瑕疵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的情形,借鑒了民法上的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排除規定。
《藥品管理法》第144條規定了藥品生產銷售領域承擔賠償責任的前提是“給用藥者造成損害”,法條中使用了“用藥者”而非“購藥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藥品管理法》的立法初衷是為了保護真正意義上的藥品消費者,而非一般的藥品購買者。
《食藥糾紛解釋》第3條肯定了“知假買假”藥品購買者有獲取懲罰性賠償的權利,但并未明確指出其高位階的法律依據是什么。解釋第3條運用了“購買者”代替了解釋第2條中的“消費者”,說明司法機關也認為“知假買假”主體并不具有消費者的身份,那么其經濟法規范文本正當性基礎也受到了動搖。民法規范文本中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排除例外的空白,與經濟法規范文本中消費者主體資格的限制邊界,導致了“知假買假”藥品購買者獲取懲罰性賠償權利缺少明確的規范文本法律證成。
3.2.2?對職業打假藥品購買者的惡意訴訟缺少必要的規制
“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根據主體的不同,可以進一步細分為普通消費者的“知假買假”藥品消費同職業打假人的“知假買假”藥品消費。如果說《食藥糾紛解釋》第3條對普通購藥者的“知假買假”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支持,還在打擊制售假藥行為的必要限度之內,職業打假藥品購買者同樣不加限制的適用該條規定是否合理則難免令人懷疑。《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規定了消費者具有主體資格需以其購買使用行為目的“為生活消費需要”,不具有此目的的購買者并不具有消費者的身份,也不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與調整。職業打假人已完全脫離了消費者的本質,若不對其加以必要的規制,可能會在實踐中出現職業打假人對假藥生產消費者多次重復惡意訴訟的現象發生,與藥品消費領域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以維護市場良好秩序、節約司法行政資源的初衷完全背離。
4?“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路徑
4.1?完善“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證成
德國在規定出賣人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排除時,雖未直接規定例外情形,但根據法條可以推導出“出賣人在標的物的風險轉移前具有將已知的瑕疵進行排除的義務”的例外,即出賣人有此義務但未履行時,即便買受人明知權利具有瑕疵,也不影響其繼續主張權利。我國臺灣地區在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排除例外的探索道路上走得更遠,曾在判例中指出“負責補正”出賣者在出賣標的物時若未履行補正之義務,買受人的明知與否不影響其主張權利,即買受人明知的情況下,也可以依據應補正者未補正請求出賣人繼續承擔責任。我國的民法體系中,應參照域外的經驗,引進瑕疵擔保義務排除例外情形,在《民法典》第613條中增加相關規定,使《食藥糾紛解釋》第3條具有明確的民事高位階的法律依據。此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3條也應進一步細化,明確該條第2款經營者同購買者間具有“品質約定”義務時,如未在交付商品時補正商品的瑕疵,仍應向“知假買假”者承擔相應的責任。在高價的經濟法規范文本中留有“知假買假”者獲取懲罰性賠償的余地,避免法律一刀切的否定模式帶來法律規定的不周延,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也無法適用“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礎上,《藥品管理法》的第144條的“用藥者”也應更改外“購藥者”,為《食藥糾紛解釋》第3條提供必要的經濟法依據。
4.2?完善“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邊界
我國的藥品消費領域的消費者權益遭受侵害時,既可以尋求私力救濟,也可以尋求公力救濟,與之相適用,我國的藥品消費者的訴訟維權途徑也可以分為由當事人或其近親屬提起的侵權訴訟,或由檢察機關、消協代為提起的公益訴訟。在這種二分的訴訟模式下,當事人自行起訴主張懲罰性賠償取得的懲戒與預防制售假藥的作用應該是十分有效的,否則會徹底打破公法與私法的壁壘,造成傳統法律體系的崩塌。針對購買假藥當事人自身而言,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功能仍應以補償其損失為主,這就直接否定了職業打假藥品購買者的惡意訴訟行為。故在承認《食藥糾紛解釋》第3條必要性的前提下,還應對“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邊界進行進一步的明晰,例如可以通過設定職業打假人的內涵,排除職業打假藥品購買者利用規定多次重復惡意訴訟行為的合法性,避免藥品職業打假人通過惡意訴訟謀取不正當利益,擾亂藥品制售市場的秩序,對經濟與社會造成不良影響。
5?結語
當前實踐中制售假藥的現象仍屢禁不止,“知假買假”者在打擊制售假藥工作中發揮出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若想要規范“知假買假”行為,使懲罰性賠償制度在藥品制銷領域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需具備細致的適用規則與合理的處理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現有的藥品領域“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從形式主義上看,仍缺乏必要的合理性與精確性支撐,從功能主義上看,制裁功能又與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的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存在著利益博弈。因此,有關部門既要從形式上也要從功能上對現有制度進行進一步完善,尋求“知假買假”藥品消費懲罰性賠償適用的最優解。
參考文獻
[1]胡文濤.知假買假行為懲罰性賠償適用研究[J].海大法律評論,2020.
[2]葛江虬.“知假買假”:基于功能主義的評價標準構建與實踐應用[J].法學家,2020,(01).
[3]應飛虎.禁止抑或限制?——知假買假行為規制研究[J].法學評論,2019,(04).
[4]李仁玉,陳超.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法律適用探析——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條的解讀[J].法學雜志,2015,(01).
[5]尚連杰.“知假買假”的效果證成與文本分析[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01).
[6]王承堂.職業打假人起訴資格的規制邏輯[J].法學,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