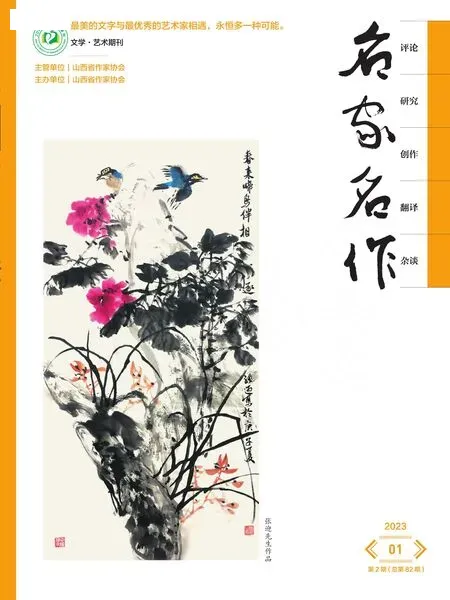剪不斷的中國結——《灶神之妻》中的中國儒家孝文化思想
張嘉寧
一、引言
善于描寫母女關系的譚恩美作為第二次文學發展浪潮中涌現出來的佼佼者。“借助處女作《喜福會》而聲名鵲起的譚恩美無疑是一個旗幟性人物。”(劉向輝,郭英劍,2020) 繼開山力作《喜福會》之后,她又推出另一扛鼎之作《灶神之妻》,仍然續寫了母女關系的文化情緣。《灶神之妻》序言部分所說:“這些三四十歲的作家代表了第二代華裔美國人,他們在美國本土長大,受正統美國教育,用地道的英語寫作。但是,由于中國血統,由于從長輩那兒潛移默化地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他們不約而同、自然而然地把目光集中在華人命運上。”(凌月,1992)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對譚恩美的創作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她的作品無不彰顯出儒家文化的客觀性表征, 儒家文化是她創作的源泉,是母女間關系的維系,是儒家文化的再現。
二、儒家文化的基本核心思想
儒家是人倫之道、人倫之學、人倫之教。儒家學說的核心就是人,所以我們要以天倫定人倫,以人倫效天倫。自儒家學派誕生之日起,孔子就以仁為核心,義與禮為兩翼,仁、義、禮相輔相成形成穩定的邏輯架構;“仁”的核心是“孝”,目的是為了“和”,因此,“孝”可以說是儒家文化的靈魂。“孝”文化作為“仁”的起點和根本思想,它不僅傳承了中華文明的傳統,更深入到“仁”學的理論體系中,從自然血緣的概念提升到社會道德的高度,不僅建構起儒家思想觀念的主要框架,也對未來的儒學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后世發展的儒學也大都以仁、義、禮為準繩,沿用至今。誠然,儒家思想中所體現出的孝文化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內涵,正如“百善孝為先”所體現出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體系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從一定意義上說,儒家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和代表。”(何中華,2020:5)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核心價值觀念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生相隨、互為表里。
三、《灶神之妻》中的孝文化思想
“孝”集道德觀、人生觀、宇宙觀為一體,是傳統儒家思想的首要觀念和核心要義,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基、行為規范之首而備受推崇。梁漱溟認為,“說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沒錯。”“百善孝為先”,表明孝文化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所占據的不可動搖的“霸主”地位。正如《孝經·圣治章》所云:“曾子曰:‘敢問圣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中國傳統倫理體系的起點,在某種層面上可以說沒有孝文化就沒有中華傳統文化。孝不僅貫穿于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歷史,而且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道德體系之中。“所謂‘八條目’與‘三綱五常’,莫不以孝義為起點,從孝義而演繹生發出來。”(肖群忠,2001)譚恩美身為華裔,自然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對中國文化有割舍不斷的深厚感情,儒家文化早已深入其骨髓。《灶神之妻》中孝文化是多維度呈現的,是儒家文化與時俱進、包容并蓄的結果,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母題再現。
(一)終身大事:孝的“婚煙”維度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的一個主要表現是遵從父母的意志,實現父母的心愿。”“儒家強調子女思想與行動應該受父母控制,其理論根源在于‘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之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親事,中于事君,終于立身。”(金學品,2016)儒家傳統文化認為,父母給予子女生命,子女應該無條件地服從父母,對父母盡孝,但是這種“孝”更傾向于一種補償性行為。贍養父母、光耀門楣也是孝的一種道德體現。《論語·學而》強調了子女的“孝”與父母之間的“道”的關系。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意即父親在世時,要看子女內心的志向是否符合父親(或母親)的期望;父親去世后,要看子女的行為是否符合父親(或母親)的遺愿;即使父母不在了,也能夠長時間遵守父母的遺訓,實現他們的心愿,這就是儒家所宣揚的“孝”道。
孝文化的表現在《灶神之妻》中是多層次和多維度的。對于父母包辦婚姻的遵從,據《魏書·王寶興傳》:“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自中國古代以來,包辦婚姻便已存在。特別是“娃娃親”在封建時期蔚然成風,完全剝奪了男女自由戀愛的權力。中國自古就有“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的說法,子女不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是忤逆和大不孝。在小說的第三章節“魚死了三天”部分,女主人公薇莉就面臨同樣的遭遇。“我本來要嫁的那人家境并不富裕,但有教養,溫文爾雅。我虛歲16 時,沒見過他本人就拒絕了他家的求親,這是因為我聽信了大嬸嬸的話。”因為女主人公薇莉早年喪母,她的終身大事便落在了她大嬸的肩上,她大嬸要為她找一個門當戶對的如意郎君。所以,全權掌握薇莉的婚姻自由,如果她大嬸覺得不好,那便是薇莉的不喜歡。薇莉是沒有自由去挑選自己的心上人的,如果她母親仍然健在的話,她母親的做法也勢必會和薇莉的大嬸如出一轍,因為她大嬸就是她已故母親的化身和代言人。特別是在第二十五章節“寶寶的婚禮”部分,塔莎和“我”母親的對話證明了違背父母的婚姻安排而付出的“大不孝”代價。新娘的稀奇古怪,甚至異類,都是因為她違背了母親的話,沒有遵從父母的旨意而理應付出的大代價,新娘不被他人所接納,就是她違背家長所受到的懲罰。
封建家長制和父母包辦婚姻制是儒家文化的一個客觀性表征,子女要聽命于父母,侍奉父母,順服父母,不可違背父母的意愿。特別是當“我”的母親妄想自己選擇丈夫時,她的叔叔大為不悅:“給她帶來麻煩的,是她只為自己著想。”因為“我”母親的行為與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馳,是母親為了愛情而結婚的愚不可及的幻想。而關于“我”和“花生”誰先結婚的問題則更是體現了父母之命不可違的強制性。“你聽你媽媽說,我最大,得最先結婚。我只有服從。”從儒家思想來看,婚姻不僅是子女的人生大事,也是父母的頭等大事,因為子女是家族延續香火的載體,是光宗耀祖的希望。他們應該遵從父母的婚姻安排,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是儒家孝文化的體現,因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二)立人之本:孝的“教育”維度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儒家孝文化不僅體現在婚姻上,更體現在中國人十分重視的教育大事上。教育不僅可以讓子女有立命之本,更是實現成功的手段。中國人歷來重視光宗耀祖、光耀門楣之事。《孝經》曰:“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子女應當在學業和事業上均取得成功,成為一個自強、自立、自信的人,為父母增添光彩,因為他們的成功也是父母的成功,他們的成功會給祖上帶來無上的榮耀,這也是孝的最高目標。“來自儒家傳統文化下的母親們一方面認為做母親的有責任教育好子女,另一方面也認為女兒的生命就是自己生命的延伸。”(金學品,2016)在名為“距離”的章節,珠兒謀得了一份幫助智力遲鈍的兒童培養說話能力的好工作。身為“語言教師”的她在幫助與自己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殘障兒童恢復語言的同時,毫無疑問會更加傾向于培養智力正常的兒童說話,因此她的兩個孩子似乎如魚得水,很快在語言學習方面便超出了正常的兒童。而她的孩子果然沒有讓她的母親珠兒失望,特別是女兒塔莎,“她這么大的孩子大都只能用兩個字的短語。她的確聰明。”無需贅言,女兒塔莎的語言天賦和超乎常人的智力給她帶來了極大的鼓舞和震撼,讓她對女兒的未來更是充滿了期待和憧憬。而“我”母親的“幻想戀人”魯也是通過教育而平步青云的典范,他的建樹定會讓他的窮苦家庭榮光倍增。他實現了父母對他的期許,做到了對父母和祖上的孝,樹立了一個儒家文化中的典型的“大孝子”形象。
(三)血脈之根:孝的“中國性”維度
自古有“落葉歸根”之說,即“比喻事物總有一定的歸宿,多指客居他鄉的人終究要回到家鄉”(江藍生等,2012)即便“我”的母親未能回到中國,可她的心卻始終未敢忘國,她的言行舉止無不流露出中國的痕跡,而“我”也選擇接受來自母國的文化,認可自己的中國文化屬性,尊重母親的文化本源,尊重自己的中國母親,這正是儒家孝文化維度的體現,所謂“父母之命不可違”便是如此。小說《灶神之妻》對于中國文化的描寫俯拾皆是。在“杜奶奶的葬禮”部分,從來沒參加過中國式葬禮的我也隨母親一起去參加了杜奶奶的葬禮儀式。當寶寶給我們一人一個箔包糖和一小紅包吉利錢的時候,我因為不懂它的寓意而說:“我沒有參加過佛教葬禮。”而母親回答道:“這是為了保險,以防你在這里受到驚嚇。”母親在這里顯然是用了中國的風水學說來教導我,讓我明白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對從來沒有聽說和見到的做法,我沒有任何抵觸和反駁,而是選擇接受了這次洗禮。婚禮上的陌生習俗仿佛一顆小小的火苗,點燃了我從未意識到自己身體里潛在的中國文化。因為不頂撞父母便是孝,我對于母親的中國思想是默認和支持的,特別是當母親在講中國財神爺的故事時,我對中國風俗的好奇表明自己對中國文化的好奇,推動著我不斷發現和探索中國文化;這也表明我尊重母親的中國式思維,遵守儒家的孝道說。漸漸地我也相信了中華傳統文化所宣揚的“運氣說”,并以中國人的思維告訴我們她(母親)的命是怎么回事。
即便沒有母親在身邊諄諄教導,我仍然在繼續學習中華傳統文化,我尊重母親的中國屬性和儒家思想的孝。“我”雖然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但我對中國母親所一直推崇的傳統儒家文化早已全盤接受,變得越來越具有中國味,越來越具有儒家弟子的風范。“父母之命不可違”,父母的思想亦不可違,這正是儒家孝文化的道德操守。“我”因為中國母親而接受儒家文化,因為儒家文化而踐行了孝,可以說,儒家文化于“我”于母親同等重要,早已深入骨髓,難舍難分。
四、結語
《禮記·郊特牲》認為:“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儒家文化教導我們要遵從父母的意愿,孝敬父母、報答父母。譚恩美雖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但對于中國、對于儒家文化不甚了解。她和她母親之間的愛恨糾纏正是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對抗最后走向融合的文化景觀。儒家文化對譚恩美來說是不可否認的存在,她的骨子里、血液里都是儒家文化的紅色基因。可以說,沒有儒家文化的影響,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譚恩美作為第二次華裔美國文學發展浪潮中的巨匠,通過回憶和母親的種種往事將儒家文化重現,使其找到自身的中國屬性。正如張龍海教授所說:“他們身上的中國性成為其他生活的支點。”譚恩美身上所體現出的儒家文化表征正是她中國文化屬性的體現,她與中國儒家文化有著剪不斷的情緣。華裔美國作家因其身份具有的雙重性而被賦予寫作的多重視角,這一獨特性使華美作家可以自由地游離于東西方世界之間,因此,沒有一位華裔作家可以完全擺脫東方或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而譚恩美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