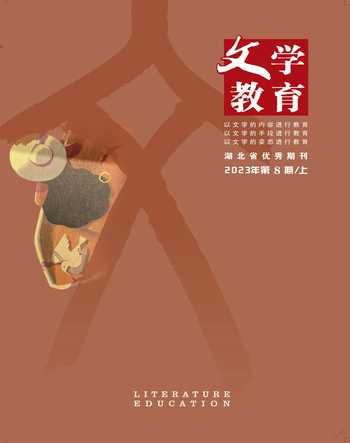從《活著》看余華小說創作風格的轉變
范琴 時曙輝
內容摘要:20世紀90年代,余華小說《活著》的發表代表著其創作風格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既體現在敘事內容上又表現在敘事策略上。從敘事內容方面來看,作家在題材上實現了從復仇題材到苦難題材的變化;在敘事主題上由性惡論轉變為性善論。就敘事策略而言,余華的小說語言從血腥轉向溫情;敘述動作發生了由顯在敘述者向隱在敘述者的改變。
關鍵詞:余華 《活著》 創作風格
1992年,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的發表在中國文壇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其早期的小說帶有較為鮮明的先鋒實驗色彩。從《活著》開始,小說實現了從先鋒向寫實的變化,這種變化既體現在由題材和主題思想的變化而帶來的敘事內容的變化,也體現在由語言和敘述動作的變化所帶來的敘事策略的轉變。從敘事內容上來看,小說在題材上關注更多的是人的苦難生存,在主題思想上贊美人性之善;從敘事策略上來看,小說在語言描寫上發生了從血腥向溫情的轉變,在敘述動作方面,隱在敘述者代替了早期小說中顯在敘述者的敘事特點。
一.敘事內容的轉變
《活著》作為余華創作風格轉變的標志性作品,小說在題材的選擇上和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他消解了早期作品中冰冷的復仇題材,在筆調上趨于緩和,開始關注苦難,尤其是底層民眾的苦難;同時從對人性惡的關注轉向了對普通百姓所流露出的美好人性的書寫。余華在敘事內容上的不斷創新影響了他以《活著》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向現實主義的轉向。
(一)從復仇題材到苦難題材
余華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復仇是其小說的一大題材,如《鮮血梅花》作為余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之子阮海闊在其母親的要求下踏上了為父報仇的漫漫征程;《現實一種》中更是徹底顛覆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人倫常理,作者在不動聲色之間向讀者展示了家人之間互相折磨、互相殘殺的復仇行為;《難逃劫數》中東山和妻子露珠之間由前期熱烈的愛轉變為后來的兇狠復仇:丈夫東山用煙缸砸倒了妻子,隨之邪惡般地將妻子的腦袋像西瓜一樣劈開了......在復仇行為面前,親情亦或者愛情似乎都顯得無足輕重,復仇題材的書寫成為了余華早期小說寫作的一個突出特色。
而到了90年代的長篇小說,作家余華在寫作觀念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題材上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活著》一書顛覆了昔日的人的殘忍復仇,他開始轉向底層民眾的苦難訴說,這也是余華從先鋒實驗向現實書寫的標志。
《活著》中,余華以福貴為中心,主要描寫了老人福貴艱難而又坎坷的一生。年輕時的福貴是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但是他的家產也在日復一日的賭博中敗光;在父親的幫助下還完賭債,而父親在上廁所時離開了人世,父親的離去使福貴一家失去了主心骨;老丈人得知福貴敗光家產后,不久便把女兒家珍接到了娘家,妻子的離開使原本一地雞毛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后文的描寫中,福貴的家庭更是遭遇了一連串的重大變故,苦難的基調越來越明顯,色彩越來越濃厚。雖然妻子家珍經歷一番波折之后重新回歸了家庭,但美好的生活似乎與福貴之間顯得那么遙不可及。福貴上城為母求醫,卻遇上了國民黨征兵,身體健壯的福貴就不可避免地被官兵拉去前線打仗。打仗的艱辛和危險是不言而喻的,但福貴歷經了千難萬苦之后平安地回到了家中。可這時的家庭與福貴離開之前是大不相同的:母親早已離開了人世,女兒鳳霞因小時候生病沒有得到及時醫治成為了聾啞人。一連串的打擊如雨后春筍,一茬接著一茬,苦難并沒有因為來得太過頻繁而有絲毫停止的痕跡。時間如白駒過隙,無論是女兒鳳霞還是兒子有慶都在茁壯成長,福貴一家的生活看上去過得越來越紅火,越來越有希望。然而余華在不斷賦予福貴希冀的同時,痛苦和苦難也在悄悄來臨。后來的有慶因積極響應學校獻血的口號,在輸血的過程中卻因醫生判斷失誤而死。這時全家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女兒鳳霞身上,聾啞的鳳霞經過媒婆介紹后,終于和城里的女婿二喜喜結良緣。生活仿佛從苦難的最低點重新回到了希望的道路上來,但是人的一生似乎逃脫不了生命的意外和反復無常。女兒鳳霞終究也沒有逃脫悲慘的結局,她在醫院分娩時因大出血去世;兒子有慶和女兒鳳霞的接連去世,使作為父母的福貴和鳳霞很難接受這樣的事實,本身體弱多病的家珍在接二連三的親人去世的打擊下,便更加弱不禁風,最后妻子家珍也永遠地離開了丈夫福貴。《活著》中,余華把苦難娓娓道來的同時卻又展現得淋漓盡致,不禁使人感慨人生來似乎就注定不平等的現實,人生就如同麻繩一樣專挑細處斷。后來的女婿在工地干活時,因工友的操作失誤,過早地葬送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福貴的家庭早已在不斷的生死離別前變得面目全非、支離破碎,原本幸福的家庭卻只剩下了年幼的孫子苦根和年老的福貴。苦根的幸存似乎與苦難成為一種人生常態時是格格不入的,不久之后,孫子苦根便因偷吃大量豆子而被撐死。雖然苦難不斷,但是福貴全都默默地承受了下來,頑強地活了下來,生活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著。生活是線性向前的,所有暫時的痛苦悲傷、快樂喜悅,終將成為回憶的一角。[1]可以說,福貴身上既有苦難的存在又有活著本身的深刻意義。苦難的書寫在《活著》中成為了一個鮮明的特點,苦難題材是余華從冰冷的復仇題材由內向外的鮮明轉型。
以《活著》為重要的分水嶺,余華在后期寫作中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了對苦難題材的寫作偏向。《許三觀賣血記》開頭關于四叔與許三觀的對話就在一定程度上悄無聲息地奠定了全書的苦難氣息。如四叔回答許三觀的問題時說道:“什么規矩我倒是不知道,身子骨結實的人都去賣血,賣一次血能掙三十五塊錢呢,在地理干半年的或也掙那么多”[2]。從此之后許三觀踏上了賣血的漫漫征程,他用自己的鮮血度過了接踵而至的難關。《兄弟》中宋凡平為了保護家人慘死、母親李蘭因病重而死以及宋剛的變相“自殺”等,都是底層民眾難以言說的生活苦難。甚至是一經出版就飽受爭論的小說《第七天》中,文中對苦難的渲染也一直未曾中斷,如養父患淋巴癌、伍超賣腎......苦難題材的呈現成為了余華在后期作品中的底色。
(二)從性惡論到性善論
余華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他在早期的文學寫作中受到了西方作家以及西方思潮的影響,形成了與傳統寫作背道而馳的創作方法。在敘事內容的寫作上更是受到了波德萊爾《惡之花》、卡夫卡《變形記》等西方作家對“審丑”的藝術表現的影響。余華在“審丑”寫作上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對人性丑態的揭示,他早期的文學寫作就像一個赤裸裸的屠宰場,向讀者展示的是血腥、死亡和人性之惡。
從成名作品《十八歲出門遠行》開始,余華就寫了十八歲的“我”在人生旅途的一次經歷:“我”用小聰明換來了免費搭車,但汽車拋錨,路人都在搶奪車上的蘋果,而“我”選擇幫助司機阻止行人搶奪蘋果,但這一善舉卻受到司機無情的嘲笑,最后的結果卻是“我”的行李也被司機偷偷拿走,只有“我”成為了整個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性惡論就像一顆種子早早地種在了余華的作品之中,深刻地影響了其早期先鋒小說的敘事內容。再如《死亡敘述》中更是毫無保留地展示了人性之惡:多年前的“我”在山路開車時意外撞死一個男孩,而時隔多年后的“我”再次回憶這段經歷時,“我”卻好像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撞人事件的嚴重程度和“我”在回憶時的冷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者雖然寥寥幾筆,卻把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充分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些作品無不體現出余華對人性惡的深刻揭示。
到了90年代,我國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大眾文學快速占領市場,加之余華本人社會閱歷的豐富,這些都使余華對人文精神的理解發生了改變,他逐漸消解了早期小說中關于人性之惡的主題,在敘事內容上轉為表現人性之美的書寫。
“文學就是人學”,文學的實質就是一個不斷探索人性的過程。如著名京派作家沈從文30年代出版的《邊城》,雖已時過境遷,但仍然受到廣大讀者喜愛的主要原因正是他對人性的挖掘。余華也不例外,在余華90年代以《活著》為代表的轉型寫作中同樣能看到他對人性的探索,深刻地表現出了他對人性之善的肯定。
《活著》通過塑造許多善良美好的人物形象,從而傳達出作家余華對人性美好光輝的贊美之情。如《活著》中,福貴家的顧工長根替福貴一家干了一輩子的活,死前還特意交代家人把舊綢衣交給曾經的少爺福貴,好讓少爺在死前還可以穿綢衣再風光一回,為了少爺福貴可以體體面面地離開人世,這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細節卻彰顯出人性的光輝。再如福貴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父親、母親和妻子都一直鼓勵他,讓福貴堅信人只要活在世上,貧窮并不可怕的事實。正是家人之間難能可貴的親情和家人對富貴的寬容,使他能夠忘掉過去,重新開始。后來福貴誤打誤撞被抓當兵期間,家珍并沒有拋棄一家老小,而是默默地照顧老人和孩子等待丈夫回家。正是家珍善良無私的行為促使從戰場上幸還的福貴重新擁有了熱愛生活的勇氣。兒子有慶更是乖巧懂事,每天利用放學時間喂羊,因心疼母親做鞋辛苦便光著腳往返于學校和家之間。在縣長夫人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有慶更是義無反顧地為她輸血,最后因醫生失誤導致失血過多而死。但當福貴和家珍得知縣長是曾經的戰友春生時,二人并沒有歇斯底里的怨恨和責罵。無論是親情還是友情,余華都深切地表現出了他對人性之善的謳歌。作家余華在小說的后半部分花費了一定的筆墨描寫鳳霞的生活:鳳霞在媒人的幫助下找到了人生歸宿,女婿二喜非常疼愛鳳霞,二人的生活非常甜蜜。在女婿二喜得知鳳霞懷孕之后,她便受到了丈夫無微不至的照顧。文章這樣寫道:二喜總是先上床喂飽蚊子,就是為了讓妻子安心睡覺。余華對鳳霞和二喜二人的生活細節的描寫,不僅表現出作者對愛情的禮贊,更是表現出他對人性之善的真實寫照。縱觀全書,無論是親情、友情還是愛情,書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散發著人性的光輝,余華在這部小說中所宣揚的人性之善是對人性之惡的反叛,余華對美好善良的人性的肯定正是他對性善論的肯定。
《活著》在敘事內容上的變化,深刻地影響了余華的其他小說的創作風格。如《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多次為家人的賣血經歷、《兄弟》中林光偷偷給兄弟李光頭錢財以及李光頭發家致富后花重錢為林光治病、新作《文城》中難得可貴的情義和人性的淳樸等,這些作品都能表現出余華對人性之善的生動寫照。
二.敘事策略的轉變
《活著》是余華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一度被看作是余華小說風格轉型形成的標志性作品。作為余華的經典小說,《活著》在敘事策略上表現出了獨有的藝術技巧,作者在語言上采用了與前期小說中截然不同的溫情的語言描寫。此外,從《活著》開始,余華在敘述動作上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小說的敘述動作發生了從作家作為顯在的敘述者到隱在敘述者的變化。
(一)從血腥的語言到溫情的語言
余華在醫院的成長經歷和作為牙醫的工作經歷,使其最初以先鋒的姿態登上中國文壇。他的前期作品常常帶有許多血腥場面,給人一種殘酷的壓抑感,暴力、血腥的語言描寫則是余華在前期小說的重要的寫作標簽,字里行間處處透露出冷酷的冰渣子。如《現實一種》中,余華寫皮皮對堂弟摔死時的反應:他發現從腦袋里流出來的血就像盛開的花朵一般。作家把孩子對鮮血的無知反應和鮮血流淌出來時的視覺刺激聯系在一起,不禁讓人不寒而栗。再如后文寫醫生們解剖山崗尸體時的快感:金黃的肉體脂肪,里面分布著一個又一個的紅點:皮膚的連接處一點點地被解剖刀切斷,醫生撿起像破爛一般的皮膚。醫生解剖尸體的場景是殘忍的,作家余華更是通過血腥暴力的語言使殘忍的場景更加慘不忍睹。不僅是《現實一種》,其他小說中也可以看到余華對血腥的語言描寫的偏向。如《一九八六年》,文中為了突出“文革”的慘狀,作家在作品中運用了大量的既血腥又暴力的話語,文中把人的頭顱和瓦片相提并論,頭顱的掉下就像瓦片從房屋掉下一般,似乎沒有一點值得惋惜的余地。更使人難以置信的是,作家把頭顱溢出的鮮血比喻成鮮艷的線條。血腥的語言描寫以及語言所帶來的視覺上的“盛宴”似乎成為了余華在早期小說中津津樂道的寫作方式。余華曾經坦言,80年代的自己似乎迷戀上了暴力,而作者正是通過大量血腥的語言構建了層出不窮的暴力場景。
法國著名文學家羅蘭巴特認為,文學的生命在于作品的語言藝術,由此可見語言對一部作品的影響之大,而小說的語言風格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作家的創作風格。《活著》區別于余華前期作品的不同之處也在于語言上的溫情簡潔。福貴的一生是多難的一生,但余華卻在福貴的回憶式敘述中充滿了溫情的語言描寫和緩和的敘事語調。如年少貪玩的福貴敗光家業后,作為妻子的家珍卻對丈夫福貴說道:“只要你以后不賭就可以了”[3]。敗光家產本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但妻子家珍的反應確實是如此的平靜,語言又是如此的溫和。后文關于福貴回憶家人離世的場景時,讀者在余華的字里行間更能體現出他對溫情的語言描寫的偏愛。如福貴和家珍得知兒子因救縣長夫人而死,而縣長恰恰是曾經的戰友春生時,二人并沒有撕心裂肺的指責和謾罵,相反夫婦二人一直用安慰親人般的語調鼓勵春生要勇敢地活下去,活著不僅為了自己,更是為了“我們”。再如福貴微笑地回憶家珍死亡之后的場景;“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凈凈,死后一點是非都沒留下,不像村里人有些女人,死了還有人說閑話”[3]。無論是昔日的榮華富貴還是今日的家道中落,亦或是親人的不斷離世,都是作家筆下無法掩蓋的沉重話題,然而余華卻采用溫和平靜的語言藝術,讓讀者在感受福貴的苦難人生時仍能心如止水般的平靜。語言的溫情描寫不僅代表了余華轉型后的一種敘事策略,更是豐富了作品的精神內涵,使余華的小說散發出更大的藝術魅力。
《活著》的發表,成功地影響了余華90年代及其現今的小說的敘事策略,如作為《活著》的姊妹篇《許三觀賣血記》,無論是許三觀與根龍一次次的賣血討論還是三年自然災害“嘴巴炒菜”的語言安慰,在血和淚的故事中依舊流露出溫情的語言敘述。長篇小說《兄弟》中,余華同樣用溫情的語言記錄了李光頭和宋剛兄弟二人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的經歷,不僅使作品透散發出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同時重構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二)從顯在敘述者到隱在敘述者
縱觀上世紀80年代文學創作的社會環境,西方的浪漫主義、人文主義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傳入,廣泛地影響了以余華為代表的一批以先鋒小說享譽文壇的作家,他們樂于在作品中表現作家的聲音,讀者在他們的作品中能夠明顯地捕捉到作家作為一個顯在的敘述者從而推動情節的發展。
如《現實一種》中,當皮皮虐待堂弟感到索然無味后,轉而站在窗前觀察窗外的景物,文中的景物描寫細致到幾片樹葉在風中搖動都可以交代得清清楚楚。仔細閱讀這個敘事段落,讀者很明顯地發現這里的觀察者不是幼孩,而是年輕作家余華的敘事聲音。在經典的敘事文學中,作品中人物的情緒、態度、觀點都是由敘述者所控制和安排的,無論作品中有多少人物、多少個聲音,都是來自同一個敘述者的安排。[4]作為20世紀初發表的第一部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此部小說已經顯露出作家在敘述動作上調整的跡象。作家的視角隨著內容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我”始終作為故事的出發者和敘述者。小說借主角孫光林的成長波折,從少年孫光林的視角側面表現成人世界的自私和冷漠。但不可否認的是,少年的孫光林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洞察到成人世界的人情冷暖,而余華在此部小說中所展示出來的近乎真實的冷漠的成人世界,讓讀者更加清晰地覺察到作家余華作為一個顯在的敘述者操控敘述的行為。
到了《活著》,作家在敘述動作上的調整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同時對后期的小說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活著》中,作家作為敘述的主體退到幕后,使故事的敘述更加接近人物本身,這也就意味著作家從早期顯在的敘述者到后期隱在的敘述者的敘述變化。《活著》是余華在敘述上充分體現了“敘述的力量”的一部作品——在《活著》中,余華的小說敘述從此前更多想表達作家自己的聲音,轉而開始更多地發出人物自己的聲音。[5]從《活著》開始,余華逐漸認識到小說人物的重要性。小說中一共記錄了福貴的五次回憶,幾乎所有的回憶和故事的發展都是在福貴和下鄉采集民謠的“我”二人之間的交談中進行的,而這五次回憶也幾乎構成了文章的全部內容。如小說開頭寫“我”在民間采集歌謠時遇到了正在田間耕作的福貴,二人便開始交流。二人交流的開始也是福貴講述自己一生經歷的開端,福貴首先通過回憶少時的富裕生活和后來家道中落的原因,從而一步步地推動情節的發展。從開頭關于福貴向“我”傾訴心聲的這段情景描寫,讀者便可以看出作家把敘述的話語權交給了小說人物,自己僅僅充當故事的聽眾。再如關于記錄福貴被抓當兵期間,他的家庭所遭遇的一系列變故:母親離世、女兒鳳霞因生病成了聾啞人......作家展開福貴的這段人生經歷時也是讓人物自己發聲,書中寫道太陽已經夕陽西下,而“我”一直在樹蔭下坐著的緣故是福貴的講述還沒有結束。余華通過人物回憶和對話的方式讓作家隱藏在人物背后,與此同時把小說人物從故事的背后推到故事的前臺,使人物形象更加飽滿,讓人物平等地表達自己,這正是作者在后期寫作中所追求的隱在敘述者的敘事策略。
繼《活著》之后,《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小說在敘述動作上的調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活著》的影響。如《許三觀賣血記》中通過人物與人物之間大量的對話把小說人物推到幕前,通過自己的嘴交代自己的事。《兄弟》中,無論是了不起的宋凡平、聰明狡猾的李光頭和帶有弱性色彩的宋剛還是油腔滑調的陶縣長、坑蒙拐騙的商人周游等,作家把話語權交給了人物本身,從而較好地代替了前期小說中作家操控人物的敘述方式。可以說余華在敘述動作上的調整是其小說不斷創新的結果,作家退到幕后,把小說人物推向幕前的敘事策略也使其作品更加具有敘述的力量和魅力。
總而言之,余華小說的寫作風格以《活著》為重要的轉折,這種轉折將敘事內容和敘事策略與現實主義完美融合,給90年代的文學藝術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同時《活著》糾正了余華早期先鋒文學的偏頗,為日益蛻化的先鋒文學提供了很好的寫作范例,為作家余華及當代文壇的發展提供了一條文學解放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李可欣.向死而生——試論余華小說的死亡意象[J].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1(01):79-84.
[2]余華.許三觀賣血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
[3]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2、166-167.
[4]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6.
[5]劉艷.心理描寫的嬗變:由“心理性”人物觀到“功能性”人物觀的敘事演變——以余華《活著》為例[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6(05):3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