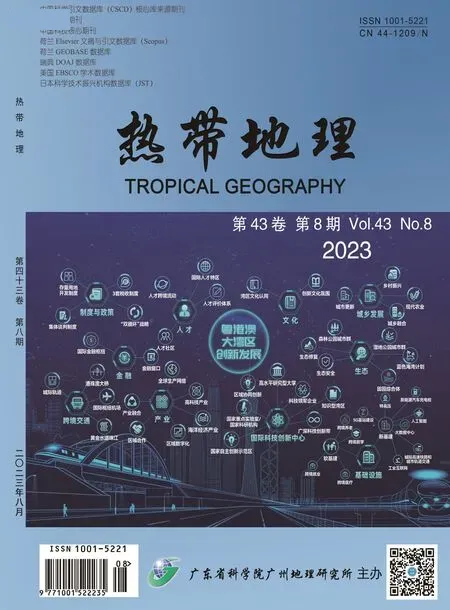基于空間封閉度的城市通風廊道構建
——以衡陽縣城為例
向艷芬,鄭伯紅,郭 睿,江燚晗
(1.中南大學 建筑藝術學院,長沙 410075;2.江西省國土空間調查規劃研究院,南昌 330008)
城市通風廊道是以提升城市空氣流動性,緩解熱島效應和改善人體舒適度為目的,為城區引入新鮮空氣而構建的通道。在快速城鎮化發展中,通風廊道可以有效減緩城市熱島,驅散城市空氣污染等城市氣候環境問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要求“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環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同年中國氣象局提出構建城市通風廊道的規劃技術指南;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聯合頒布了《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等,2016)。目前,城市通風廊道建設已經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作為推動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的戰略舉措之一。中國南方城市普遍處于夏熱冬冷的特殊氣候背景,構建城市通風廊道十分必要。
城市通風廊道的研究始于德國斯圖加特的城市空間布局研究,陸續在不同城市展開,至2016年,對中國17個省區的36個城市共進行了63項城市通風廊道專項規劃或相關研究(Ren et al., 2018)。根據研究手段的不同大致分為3類:一類是基于實測數據的理論分析,如早期的斯圖加特和卡塞爾、東京都和旭川的城市風環境研究(趙敬源,2010;任超 等,2013),該類研究數據采集工作量較大、不易獲取,且數據易受變量影響無規律變化。二是利用風洞實驗,如通過風洞實驗分析了加拿大渥太華、美國紐約等城市風環境(Williams et al., 1992;Plate et al., 1999)。雖然實驗易調節自然條件且結果精確,但在方案修改階段周期長、費用高,不易開展。三是計算機模擬,即利用計算機進行數值模擬,常用的技術有CFD、GIS、RS等,如用CFD軟件研究了東京、香港、臺南等城市與風環境的關系(Ashie et al., 2009; Wong et al., 2010; Ng et al., 2011;Hsieh et al., 2016),模擬結果可行性較高、發展前景大,但需要驗證軟件的可行性、時間周期較長,研究尺度受限。
近年來,香港、長春等城市利用CFD與GIS的集成、GIS 與實測數據或形態學理論等綜合手段,展開通風廊道的規劃與建設研究(Chen et al., 2011;Chang et al., 2018),但多基于大尺度的城市,且多為專題研究,對中、小尺度的城市規劃建設指導性不強。此外,依據CFD等復雜模型所提出的相關策略,存在城市尺度模型內容復雜、建模結果跟不上快速的規劃過程、評價指標過于單一難以落地等問題(Germano, 2007; Ng et al., 2011; Yuan et al.,2014;史兵 等,2017)。在當前國土空間規劃背景下,面對量多面廣和空間形態相較單一的中小城市,需要一種更加便捷的方法用以指導城市通風廊道的建設。
城市規則建模是一種語義建模方法,即采用一系列計算機語言將現實世界的信息轉換為邏輯信息,并根據規則決定模型的生成,是一種可以快速反映城市風貌的建模方法。常見的城市建模方法大致可分為4類(駱燕文 等,2017):1)基于二維數據資料(如規劃圖紙等),利用AutoCAD、Sketch-Up等軟件建立城市三維模型,這是使用最廣、精確度最高的一種方法;但耗時較多,數據的時效性存在不確定性,工作量較大,難以滿足三維空間深層次的研究應用。2)激光掃描,利用激光掃描儀或機載激光雷達掃描獲取城市建筑模型數據,該方法能快速、精準獲取相關數據;但數據量較大,模型生成時間長,成本較高。3)使用航天影像或數碼攝影,根據建筑物的特征提取相關數據,該方法獲取速度最快,展示信息最真實;但模型不易修改,存在信息不完整的問題。4)規則建模,能快速構建三維城市模型,允許創建和分析替代方案,適用于規模較大、對細節要求較低的模型,常用的軟件有CityEngine 和ArcGIS。與傳統的建模方法不同,城市規則建模更擅于靈活有效的建模,模型包含多方數據,允許創建和分析多方案,適用于城市的已建和新規劃區域(Trubka et al., 2016)。但當前少有研究將城市規則建模與城市通風廊道相結合,而城市的通風廊道往往影響城市的空間形態布局(盧飛紅,2016),因此,在以優化城市通風廊道為目的的空間形態布局中應用規則建模技術具有現實意義。
在城市規則建模中,本文提出構建空間封閉度綜合評價模型以計算城市的潛在通風廊道。空間封閉度初期作為描述單體建筑內部空間封閉程度的概念,但在研究城市風環境的大尺度下,可將其定義為城市三維空間內的封閉程度,即城市空間對風流動的阻擋程度。城市空間的封閉度受垂直要素的高度、密實度和連續性等方面影響,可理解為受建筑的城市形態特征影響。相關研究(Grimmond et al.,1999; Wong et al., 2010)證明,地表建筑物、自然植被的粗糙度和開敞空間影響城市風環境,其中建筑的城市形態特征對城市通風廊道的構建影響最大。Grimmond 等(1999)在研究中證明建筑的形態特征可由形態學方法計算,即可通過城市下墊面的粗糙元形態特征定量估算。國內外相關學者總結了許多形態特征的量化指標,如Chen等(2011)在ArcGIS中以粗糙度指標論證城市幾何形態與風環境的關系,并證明迎面面積密度、天空開闊度等指標可用于評價城市風環境的變化,其他學者相繼應用該類指標開展研究(Yuan et al., 2014;Wicht et al.,2017;李廷廷,2017;Ren et al., 2018)。Kanda 等(2013)提出了同時考慮迎風面積系數、頂面積系數、平均建筑高度、最大建筑高度和建筑高度標準差的形態學計算方法;唐玉琪等(2020)以上海徐家匯地區為例,論證了該方法可估算建筑形態特征且差異較小。部分學者利用粗糙度指標與GIS中的最小成本路徑定義城市通風廊道,并利用CFD軟件論證結果的可行性(Wong et al., 2010;Hsieh et al.,2016;Peng et al., 2017;申鑫杰 等,2020)。可見城市風環境的評價指標選取由單一向綜合轉變,研究方法轉向更為快捷、精準,尺度也傾向人行空間。
因此,本研究試圖運用GIS技術與城市規則建模的方法,構建城市潛在通風路徑,深入分析城市空間封閉度與通風廊道之間的關系,綜合空間封閉度影響因子構建城市潛在通風廊道,以期為改善丘陵型的中、小城市風環境提供借鑒。
1 研究區域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衡陽縣城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區域,地形有起伏,海拔為32~255 m,相對高度<200 m,坡度較緩和。城區地勢周邊高、中間低,湘江支流——蒸水河貫穿東西。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外圍山體有屏蔽作用,致使盛行風的滲透較弱,大氣污染物疏散存在問題。縣城建成區面積為15.6 km2,主要集中在老城區與西渡區;建筑多為4~6層,新區建筑規劃以7~10 層為主,城區周邊為大面積綠地(圖1)。

圖1 衡陽縣城城市鳥瞰圖Fig.1 City aerial view of the Hengyang county
根據《建筑氣候區劃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技術監督局,1994),湖南省全境屬于夏熱冬冷氣候類型,夏季炎熱潮濕,需加強城市自然通風以提高人體熱舒適度;冬季則正好相反,因冬季風寒冷干燥,需要規避寒風入侵。衡陽縣四季分明,夏熱冬冷,受山體影響,氣候變化更甚。由國家氣象信息中心提供的衡陽縣臺站近30 a氣象數據統計可知,城區冬季盛行東北風,平均風速1.5 m/s,夏季盛行南風,平均風速2 m/s;7 月平均氣溫最高(30.2℃),極端最高溫達41.3℃,1月平均氣溫最低(6.7℃),極端最低溫達-4.8℃。在7、8 月中,平均有34 d是35℃以上的高溫,其中有連續幾天超過40℃。受多變氣候與起伏地形的共同影響,湖湘傳統民居在布局上往往選擇依山傍水以形成宜居的小氣候區域,在建筑設計上夏季隔熱通風,冬季防寒納陽(萬艷華,2010;張蒙,2017)。
1.2 研究方法
首先基于城市的基礎地理信息數據規則建模,再根據空間封閉度影響因子構建綜合影響評價模型,并對衡陽縣的現狀和規劃模型(圖2)進行評價,然后通過PHOENICS對現狀與規劃模型進行數值模擬。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比GIS 與數值模擬2種途徑下的結果,以及驗證實測風速值,提出衡陽縣夏熱冬冷氣候區內的通風廊道設計策略。

圖2 衡陽縣城總體城市設計規劃方案Fig.2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scheme of the Hengyang county
1.3 空間封閉度因子的空間數據集構建
上文分析了城市風環境研究中的評價指標運用,現有的研究多依據單一指標劃定,而史兵等(2017)指出單一指標評價難以滿足精細化的城市建設,應選擇更全面的指標研究風道與城市的內在關系。根據文獻(Kanda et al., 2013;Yuan et al.,2014;Hsieh et al., 2016;Wicht et al., 2017;李廷廷,2017;Ren et al., 2018;唐玉琪 等,2020),分析選擇5個較為成熟的參數,分別是:建筑物迎風面積密度(Frontal Area Density, FAD)、天空開闊度(Sky View Factor, SVF)、絕對粗糙度、建筑高度均值、建筑密度。其中,FAD(Hsieh et al., 2016;Wicht et al., 2017)受建筑幾何形態影響,能考慮地形的變化,但在評價人行高度處的風場變化時存在不足;SVF(Chen et al., 2011;劉勇洪 等,2017)反映人行高度處的城市幾何形態,可彌補FAD指標的不足。本研究選用方形柵格劃分地塊,與其他劃分地塊的方法相比,規則劃分有利于開放空間的數據展示(Man et al., 2010; Ng et al., 2011),因此要選擇能描述規則地塊整體情況的指標,以選用能表示城市空間內幾何形態的絕對粗糙度和表示地塊內建筑物覆蓋率的建筑密度和建筑平均高度,下文將概述5個指標的概念及計算公式。
SVF指在建筑圍合的城市空間中,人們視線所及可看到的天空范圍。Gal 等(2009)認為柵格計算SVF 更適合大尺度、多數據的城市地表開闊度。SVF的計算公式為(劉勇洪 等,2019):
式中:γi為第i個方位角時的地形影響高度角;n為計算的方位角數目。由于SVF 值越大越有利于通風,在綜合計算時,SVF以負值進行計算。
FAD 表示單位面積內城市建筑迎風面積密度,反映城市風的滲透性(劉勇洪 等,2019)。數值越大表示該區域對風的阻礙越大;相反阻礙越小,通風能力越大。計算公式為(Ng et al., 2011):
式中:λF(θ,z)表示特定風向θ處的迎風面積密度;A(θ)proj(△z)為面向θ風向的建筑物總投影面積;θ為風的不同方位的方向角度;AT為研究區域的地塊面積;△z為投影面積高度方向的計算范圍。λF(z)表示整個城市冠層的形態平均值;P(θ,i)表示第i個方位的風向年均出現頻率;n表示氣象站統計的風向方位數。
絕對粗糙度(Hm)可表示城市幾何形態(陸面、植物、水體)的粗糙度,Kondo等(1986)發現城市結構可通過氣流中障礙物的絕對粗糙度來降低地面的平均風速,計算公式為:
式中:Ai是i號建筑的占地面積;hi是i號建筑的高度;Aj是研究區域的非建筑物占地面積。
建筑密度(D)指研究區域內的空地率和建筑密集程度,數值越大表示該單元內的建筑物覆蓋率越大,阻礙也越大,計算公式為(Grimmond et al.,1999):
式中:Ai為i號建筑的占地面積;AT為研究區域的地塊面積。
建筑平均高度(Hˉ)表示研究區域內建筑物高度的變化,數值越大表示研究區域內建筑高度變化小,風的滲透力越小,計算公式為(張海龍,2015):
式中:Hi是i號建筑的高度值;n是研究區域內的建筑數量。
1.4 空氣封閉度評價模型構建
考慮到各影響因子的特性和代表性,采用序關系法(G1-法)賦予各指標權重系數,以此構建評價模型。相比層次分析法,G1-法無需構建判斷矩陣及一致性檢驗,大大減少了計算量(王學軍 等,2006;王偉武 等,2019)。5個影響因子分為:FAD(X1)、SVF(X2)、絕對粗糙度(X3)、建筑密度(X4)、建筑高度均值(X5)。按照指標對通風影響的重要性進行排序分級:X1>X2>X3>X4>X5,根據相對重要程度的比值對rk進行賦值,設定r2=X1/X2=1.2,r3=X2/X3=1.4,r4=X3/X4=1.4,r5=X4/X5=1.4,權重系數Xm的計算為:
則X1/X5=3.292 8,X2/X5=2.744 0,X3/X5=2.352 0,X4/X5=1.960 0,(X1+X2+X3+X4)/X5=9.396 8。因此,各評價因子的權重系數為:X5=(1+10.349)-1=0.096 2,X4=X5·r5=0.134 7,X3=X4·r4=0.188 6,X2=X3·r3=0.264 0,X1=X2·r2=0.316 5。根據各影響因子的權重值建立綜合評價模型,即:
式中:i為城市通風潛力的影響因子編號;n為城市通風潛力的影響因子總數;βi為第i個影響因子的單因子評價值;Xj為j因子的通風潛力權重值(X1+X2+X3+ ┉ +Xn=1)。
1.5 數值模擬中邊界條件的設置
選擇PHOENICS 軟件對潛在風道進行模擬驗證,其中,風廓線指數α依據地表面粗糙度分區(日本建筑學會,2007),賦值0.27;對規劃紅線范圍內的建筑及山體建模,建筑物每層賦值3 m,以最低的河流高程為初始高度,按照等高線數值進行拉伸建模。在PHOENICS中使用3層嵌套的六面體網格,選擇廣泛用于低速湍流的標準k-ε湍流模型;流入邊界的風向選擇東北風(冬季)和南風(夏季),10 m高度風速為2 m/s;建筑和地形表面邊界為光滑壁面,流出邊界使用零梯度條件。研究區的建筑高度不超過100 m,綜合考慮地形高度變化,將計算域邊界高度調整為3倍的模型最高高度,在150 m高度范圍內網格大小設為3 m,超出該范圍的網格大小逐漸增加。
2 結果分析
2.1 空氣封閉度現狀與規劃的對比
由于研究范圍內有一定高差變化,在計算影響因子時加入地形高度,即以研究范圍內的蒸水河面為參考水平面,高度計算為相對地形高度加上建筑高度,如圖3所示。按縣城總體規劃的紅線范圍,基于1∶1 000 的CAD 地形圖計算城區內現狀建筑的影響因子,并在ArcGIS 中以50 m×50 m的單元尺度轉為柵格圖,各影響因子空間數據集見圖4。

圖3 受地形影響的天空開闊度計算原理示意Fig.3 The calculation principle of Sky View Factor

圖4 空間封閉度因子分布Fig.4 Distribution of the spatial enclosure index
圖中紅色表示數值越大,對比分析FAD值,夏季區域小于冬季,冬季數值較高是因為建筑遮擋寒風的緣故。不同風向下FAD高值分布在城區西部與南部,如解放西路西段,由于該路段建筑密集,密度值較大;東部、北部建筑的整體密度較低,迎風密度值較低,通風潛力非常好。規劃方案中,新區建筑的FAD通過優化策略能得到有效控制,整體數值降低,其中高值區域集中在老城區與新區中規劃的居住區,即單位柵格內建筑密度與體量較大的區域。老城區的SVF 值有所增加,驗證了老城的優化措施能有效改善城區的天空可視度;新城出現局部低值柵格是因為單體建筑過大,也間接造成建筑的絕對粗糙度、密度、迎風面積密度等數值偏大。
SVF值中紅色區域表示低值區,數值越低表示天空可視范圍越小,現狀的低值區域集中在城區內建筑密度較大的區域,如船山廣場片區的新正街等,但規劃方案的老城區低值有所改善。新區內規劃了大量的工業廠房和高層居住建筑,擴大了計算單元內的建筑占比,導致地塊的建筑密度和絕對粗糙度的增大。
2.2 LCP與現狀風速云圖對比
利用GIS 中的最小路徑(LCP)生成綜合影響評價的路徑,得到潛在通風廊道,為了驗證路徑的準確性,將其與PHOENICS 的模擬結果進行對比。LCP 依據GIS 中50 m×50 m 的分辨率進行計算,沿規劃紅線每50 m 設置了共290 個起始點進行計算。圖5-a、c、e、g 表示綜合評價疊加LCP,LCP 選取成本值較低的路徑作為風道路徑。

圖5 現狀(a、b、c、d)與城市規劃(e、f、g、h)方案通風潛力對比Fig.5 Comparative of the city ventilation potential of urban planning schemes
圖5-b、f是中性流條件下的夏季風速云圖。夏季風的路徑中,南側為阻擋較少的農田用地,風口較大、風道多,但受城區北側山體的影響,大部分南向來風被阻擋。由于蒸水河河面較寬敞,在西側也形成一道沿河的風道,城區內部受阻較多,風沿建筑高差或道路方向走勢;城區東側的風道基本沿山體布局,大致為南北向。PHOENICS中的靜風區基本無潛在風道,風速值較大區域風道較多。
圖5-d、h是冬季風速云圖,北側有較多山體阻擋,風道路徑難以貫穿,潛在路徑較少,南側不受阻擋,風道較多。西側老城區仍受山體阻擋,僅有2 條沿主干道形成的風道,在南邊沿蒸水河匯聚。圖中顏色對比明顯,潛在路徑與顏色變化趨勢一致,能與云圖中顏色偏紅的區域相重合。
2.3 潛在風道驗證
根據上文挖掘的潛在通風廊道,在夏、冬季各1 d進行風速測量,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分別選擇南風日和東北風日,以此驗證潛在通風廊道和PHOENICS 模擬結果(Ng et al., 2011;李廷廷,2017;張弘馳,2020)。南風向分別沿清江路、海英大道和蒸水河西段3條城市道路,用便攜式氣象觀測站Kestrel 5500 進行風速測量,共布置55 個測量點;東北風向分別沿保安路、新正路和洪山路,共布置50個測量點,如圖5-b、d所示。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在道路兩側布置測量點,測量時間為T 10:00-16:00,儀器每10 min記錄1次數據。
表1 的實測結果與LCP 的計算結果基本吻合,表明了LCP分析的可信度,也證明了空間封閉度綜合評價的方法科學可行。實測通風路徑的平均風速皆高于對比點,說明所選風道的通風效果較為顯著,尤其在大型交通路口或是較大的城市廣場附近,觀測點風速值較大;蒸水河西段的風速遠高于其他風道,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寬闊平坦的空間通風效果相較于高低起伏的建成區更佳。

表1 夏、冬季潛在風道數值對比Table1 Comparison of measured values of urban ventilation corridor in summer and winter
2.4 風環境優化策略
規劃方案將城區分為5個風貌區——城中的傳統生活風貌區、城西的西渡歷史風貌區、城東的濱水休閑風貌區、城南的田園景觀風貌區和城北的高新產業風貌區。其中,傳統生活風貌區為老城區,建筑體量較大,以中、高層為主;西渡歷史風貌區嚴格控制開發強度,建筑體量較小,以低層建筑為主;濱水休閑風貌區展示新城形象,建筑體量較大,以中高層建筑為主;城南組團多為居住用地,以板式中高層居住建筑為主;城北組團建筑體量較大,以工業建筑為主,建筑多為1~2 層。圖5-f、h為Phoenics軟件模擬得到的人行高度處云圖,結合城市通風廊道的構建類型和作用空間,將通風路徑分為一級廊道和二級廊道,一級廊道貫穿大型生態綠地,可為城區內提供風源;二級廊道則串聯綠地系統、道路系統等,作用于城市內部功能空間,表2 羅列了規劃方案中8 條一級通風廊道和14 條二級通風廊道。基于不同等級的廊道空間采取不同的優化策略,即從風口、開敞空間、水域、道路及建筑布局5個方面提出風環境優化策略,完善規劃方案并利用綜合評價模型進行驗證。

表2 衡陽縣城一、二級城市通風廊道匯總Table 2 The summary tabl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urban ventilation corridors in Hengyang county
分析現狀可知,風口地帶布置了污染性的工業,如服飾工業園、機械工業園等,影響城市內部的空氣質量。在規劃階段,調整風口地帶的土地利用布局,規劃控制新建工業園的開發強度和建筑布局,轉移有污染性質的企業,將工業用地遷移至下風向,在工業區外圍布置綠化隔離帶,并增設監測站點。
現狀風道體系中,大多數道路與主導風向呈夾角,城市整體綠化連續性不足,公共空間較少,未形成網絡結構,部分區域建筑密度大,導致風難以滲透。因此在規劃階段將串聯水體、綠地、公共空間及道路元素構建風道體系,結合《衡陽縣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加強與城市綠地的有機聯系。通過擴大綠地面積、增加立體綠化及綠地數量、降低下墊面的粗糙度等,拓寬風口風道、增加通風載體,構建城市綠網。在風口區域,可建設大面積楔形綠地,植被由防護林改為低矮的喬灌木,便于風的進入。建筑布局方面,老城區通過拆除通風節點處的老舊建筑,降低建筑密度,打破連續的建筑界面,改善地塊內的通風情況。拓寬街道的天空可視域面積,使街道兩側的建筑高度呈梯度變化,優化建筑布局形態,提高街區的滲透率。
圖5-e、g展示了規劃方案的風道路徑,在不同主導風下的潛在通風路徑皆與Phoenics云圖中的風道相似,再次證明利用ArcGIS 構建的綜合評價模型可得到適用的通風廊道,雖在對比分析中受研究尺度的約束,局部街區未形成風道,但不影響整個城區風道的建立。
3 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種由空間封閉度構成的多指標綜合影響評價模型,以衡陽縣城為例,利用GIS中的LCP構建夏、冬季主導風向下的潛在通風廊道,并對比了CFD數值模擬中的風速云圖,結果顯示,風道的分布基本是沿城市主干道,多為連接城市公共空間的道路,但在北部城鄉結合處由于道路系統的不完善、路幅狹窄的原因導致通風性能較差;風向多為密度較高的老城區趨向低密度建筑、公園綠地等城市公共空間,但由于道路與風向呈夾角、廊道系統的連續性不足,導致部分通風廊道的走向與整體的方向有一定偏差;亦或是由靠近城區外圍趨向郊區農田、蒸水河面等自然生態區域等。
本研究選擇了迎風面積密度、天空開闊度、絕對粗糙度、建筑密度、建筑平均高度5個空間封閉度影響因子,該指標不僅考慮了城市地形的影響,還能表征切割后地塊的整體差異性。單一的評價指標未能覆蓋所有的風道要素,對比不同指標數值的空間分布差異,發現單一標準未能準確評估,而多因子綜合評價涉及更多影響要素,其評價結果相對更可行。因此在城市規劃方案中,針對不同的城市空間類型進行優化,通過調整風口的用地布局及布局形態、開敞空間的網絡化布局及要素選擇、濱水空間的城市三維形態和廊道路徑下的建筑布局及高度控制,并利用多因子綜合評價證明優化策略的有效性。因此,在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的前提下,規劃方案可依據綜合評價模型指標調整城市道路、開敞空間、建筑結構等要素的空間布局,還可在控規層面加入地塊的經濟指標,多尺度協調風道的構建。
本研究論證了空間封閉度評價模型在中國典型夏熱冬冷氣候區的可行性,為城市的通風廊道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該方法不僅能快捷有效的評價及修改規劃方案,為基于氣候特征的城市風道量化研究提供技術支撐,還能為地方政府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設管理及動態監測方法,有利于控制性詳細規劃階段指標的約束與落實。同時,本研究仍需深入開展,后續將在不同氣候區內驗證模型的有效性,完善評價模型;并耦合不同尺度下的風道研究,補充城市不同尺度下的風環境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