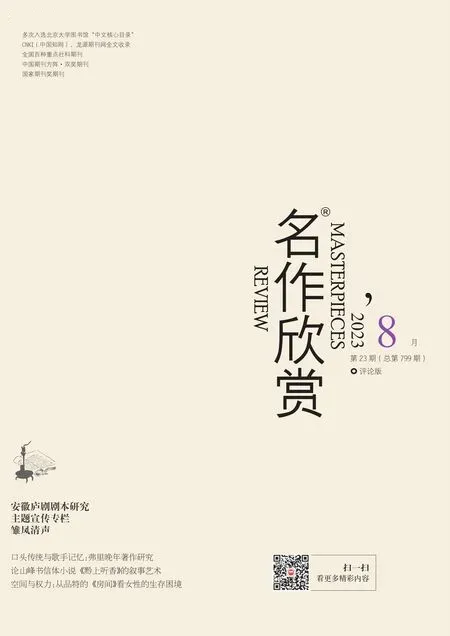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詩經》的經典范例及可能解讀
——以《周南·關雎》為例
⊙溫左琴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州 350007 ]
我們無法確知《詩經》各篇的生成年代,無法確知《詩經》各篇具體在訴求什么,吟詠什么,但我們可以確知《詩經》的組合、編撰及其最后成書成經必有其內在規律或約定俗成的認定準則。正如我們讀者面對《詩經》時所必然會有的閱讀期待與經典范例。說到底,作為儒家五經之首,《詩經》不單應具有經學上的道德規范,更應具有詩學美學上的獨異品性,或就是作為詩教之可能的文學性、審美性。就此,我們以《周南·關雎》為例,做具體解讀,垂范整個《詩經》閱讀。
周南,應在今西安南部的渭水流域;召南,應在洛陽以南直至長江的廣大地區。合之,就有可能是今日的江漢流域。方玉潤《詩經原始》有言:“竊謂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詩皆周南詩多,故命之曰周南。何以知其然耶?周之西為犬戎,北為豳,東則列國,惟南最廣,而及乎江漢之間。”也即《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是十五國風中最有可能發生在南方也最有可能帶有異域風情且對楚辭產生深遠影響的作品。事實是,周南與召南作為周王朝的兩個不完全統治區,似乎先天就具備產生其他文化的特質。本部分所要探究的就是以周南、召南為代表的南方文化,在不同于中原文明、黃河流域文明的同時,又是如何被納入整個民族文化體系,成為今天我們所能聽到的《詩經》中最響亮的聲音,甚至代表其至美的文學典范及整體的抒情范式,成為《詩經》中的最高審美標準。
面對《關雎》,有以下問題:
1.《關雎》作為三百篇之首,有沒有為全篇定調?或者說,它該傳達給我們怎樣的情緒?我們是否可以由此想象并圈定《詩經》的歌詠范圍?
2.該篇選自《周南》,是否具有地方特色?或者說,它的地域色彩明顯嗎?以它為代表的“周南”“召南”的存在,會不會使得《詩經》整體風格不統一以至于成為《詩經》中的異類?
3.是否特指貴族青年?其他階層的男子也有此種類似情感的流露和追求嗎?
4.是“求之不得”只能寄托于想象的愛戀嗎?
5.經學家的詠“后妃之德”固不足道,但產生此種解讀的話語體系又是如何長期運作的?
6.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評定可靠嗎?此種表述和經學家的“后妃之德”,何為表,何為里?
7.此篇的“比興”之體,單單是為愛情主題服務嗎?“比興”之外,該篇是否還有理趣?或者說該篇是否能上升到一定的理想、信仰層面?
其實,上面所有問題,可歸結為一問:《關雎》,僅僅是愛情主題嗎?顯然,主題的確定或可能性,真能解決上面所有問題。本文即以此著力,對其進行古典釋義與現代闡釋,以期在今日層面上更好地了解《詩經》的深刻內涵和可能意蘊。具體步驟如下:
首先,我們對《關雎》做文本細讀,看看能不能在細讀中解決上述問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鳥兒彼此和鳴聲。未見其鳥,先聞其聲,或者叫先聲奪人。我們只從對疊詞的字形、發聲看,就覺得它應該是一種簡單、親切,又非常悅耳、動聽的聲音。這有可能是抒情主人公的當下情境:聽到鳥兒歡叫,心悅之,循聲尋找,果然在水中小洲上發現了一對相親相愛的鳥兒。可為什么是“一對”?相傳“雎鳩”雌雄相依、情義專一。故此刻即便有成群的鳥兒在歡叫,我們也只認為它是唱給它親愛的另一只。也正因此,有了下面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所心心念念的她,應是“窈窕淑女”,這個“窈窕”耐人尋味。今日我們對它的理解,或者對女性審美的“窈窕”之感,似乎只來自它的字形:裊裊娜娜,風行水上,無形中有一種女性之美。簡單點,粗俗點,就是要瘦,要身材好,這是今日女性審美的基本前提。但古漢語中的“窈窕”二字,卻大有講究。揚雄曾言:“美心為窈,美狀為窕。”王肅云:“善心為窈,美容為窕。”不管古人究竟是以何為好?以何為美?我們卻能肯定他們都在強調一種內心的良善,或者是道德美、品質美。再加上后面毋庸置疑的“淑”之美善,那真是把這種心靈的美、內在的美擴展到極致。也正因此,這樣的女子才是世間最美好的存在。而只有這樣的美好,才配得上君子或像“我”這樣有德行有修養的人。這可能是男主人公的當下自況,更可能是一種自我期許,或就是他的審美標準和道德信仰。我們來看這個“逑”字,除伙伴、配偶之外,我們為什么不能把它當作一種理想的存在,一種值得我們不息追求的美好愿景?
就此,我們重新來審視這起首兩句的修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毋庸置疑,這么多年來,人們都把它看作是興句形象,同時又有比的意味,借以引出后面的“窈窕淑女”。似乎“雎鳩”只是他物,而后面的“淑女配君子”才是所詠之題。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反其意用之,我們認為“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才是整篇、乃至整本《詩經》的歌詠對象:美好事物的存在,即便不在眼前,但也永存于我們心中,且值得我們不息追求,即“永以為好”。此種感覺或信念,源于我們的日常經驗,因為此種雌雄相依、從一而終的鳥兒確實存在,就在水中,就在小洲上。由此自然引起我們的追慕企羨,而我們此刻最能想到的人世間的美好,恐怕就是那與我們匹配的人兒。
順著這個思路,接下來的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不僅落實了前面的美好或追慕,更在說明:這,僅是人世間諸多美好的一種。說到底,所謂“窈窕淑女”在此語境中,其實就是在進一步解讀前面的那種美好。而“君子好逑”就是這所有語意在句中的落腳點,或者就是這整個文本的語義中心。這起首四句,本身就是互文。“窈窕淑女”,不只作為君子的好“逑”而存在,更是回答了前面所暗示的何以為美、何以為好的最高標準:即形神俱美、俱好,或內外統一的美和好。就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該篇主題并非僅僅是求偶,而應是對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熱愛、追慕與求索。求偶、戀愛只是它的“形”、它的“殼”,借助于這種表象,它真正要生發的其實是那種內在的對美好生活、理想人格的追求,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執念。而這,才應是整本《詩經》的綱領所在、吟詠范圍,或者說是精神氣質、傳世的動力與意義,說到底就是核,就是后世所說的風骨。試想,在那樣一個書寫極度艱難的時代,我們祖先若不是為了保留他們的此種內在精神活動,這種對美好生活的企羨,對人類精神所能達到高度的不息求索,怎么會反反復復地這樣世代詠唱或抒寫?而今日的我們,所能做的恐怕仍是重新認識、激發且傳遞。畢竟經典的存在,不僅在于它的過去,更期望在現在以至未來勃發它的新生命,這也是兩千多年前孔子的“述而不作”在今日的應有之義。
以上為該篇的第一樂章,概括來說,就是由眼前、現實所見所想的美好,自然過渡到夢境以及理想中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下面就該具體展開求索過程,自然也是順著君子追求淑女的自然流程展開。然而,我們突然發現,她于“我”,不止有現實的距離,更有心靈的阻隔。甚至可以說,此刻,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更無法感知“我”的熱情,“我”該怎么辦?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前兩句,再次做比,同時起興。同樣既可以是眼前所見,更有可能是心中所想。眼前所見者,契合前面所托出的水中小洲、鳥兒和鳴的人間勝境。但此刻的情感基調卻明顯發生變化。若前面是自然、永恒、歡欣的,那么,此刻應有很多的不確定。且看這“荇菜”是如此參差不齊,隨水漂流,“我”對它的采摘肯定會非常艱難,甚至盲目,亦如“我”思念的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對她的想望就像夢幻泡影,“我”的一切努力很可能就是徒勞。也正因此,主人公突然心生迷離恍惚之感。的確,美好的事物總是乍隱還現,欲走還留,總是值得我們不息求索,日思夜想。它在眼前,更在夢中。難以求索,悲哀莫名,此即是孔夫子所謂的“哀”。我們再看下文,看看作者究竟有沒有絕望,有沒有“傷”。
這幾句,同樣是由眼前、現實再到理想、夢境。在此過程中,作者同樣為我們營造了如夢如幻的審美境界,我們隨之亦迷思亦恍惚,卻又苦痛愁悶、憂心如焚。但是,畢竟有了目標,有了努力的方向,我們看主人公如何逾越?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幾句,由“求”引發,詳寫“求之不得”的苦痛、悲哀。句子、語詞重復的同時,情感也得到強化。“悠哉悠哉”不只極寫時日漫長,憂心如焚,更有一種心身俱困、堅貞不渝的狂想與迷思。如果說前面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還在給我們營造夢境,那么,眼前這幾句卻已回歸現實,概括呈現夢想變為現實的道路,何其遠,何其苦!而情緒也隨之變得低回、郁積。并且該章的韻腳也很有特色,“得”“服”“側”的入聲協韻,于情感上同樣讓我們產生嘶咽難言之感,或者說,它的音和義就是同步的,而詩句的意義也正是在這種自然的詠嘆屏息中產生。我們再看下一章: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這一樂章的前兩句,再次做比,借物起興。在語意重復的同時,我們更看到情感振起的可能。前之“流”,此之“采”,雖簡單變換,我們卻在時間延續、空間轉換的同時,明顯感受到后種行為的簡單、有效。“采”說到底要比“流”更有目的性,更帶主動性。看來,作者在追求美好的路途中,終于摸索到了規律,終于要得其門而入。換了“君子淑女”的語境,就是“我”對她的情誼,她已知曉,且已回應。我們就像那彼此相和的鳥兒,已是你有情來我有意。“琴瑟”作為古典樂器,自然是淺彈低應、曲意深幽,但加一“友”字,突然就覺得此種情意已紛紜蒸騰,奔流不息,甚至久久纏繞不忍散去。我們突然明白,古典詩學中所指的詩歌最高境界——以瞬間達永恒,此刻已然應驗。
這一樂章,應是寫愛情的成熟或理想的豐滿。是的,“我”對她的追慕一如既往,然而,“我”只能用最適合她的方式讓她知曉。為了和她匹配,“我”必得自我提升,跟上她的節奏。李義山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亦可佐證此種情感的珍貴與瞬間的難以把握。可見,理想與現實,“我”與她,自古以來,就是一種艱難的遇合。這是理想求索過程,更是自我精進之路。因其目標專一,因而感人至深。但是,終于,我們感覺到了,且已不再是抒情者的獨奏或狂舞,而是由另一方不斷加入,并最終形成非常和諧的二重奏、雙人舞。情深義重,靈犀點點,我們所能想到的人世間的美好,或已呈現。接下來,主人公應是要急不可耐地分享此種人生盛況: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前兩句,再次重復,呼應上兩章的同時,似乎已昭示我們:理想終于實現,人生真已圓滿。是的,總有那么一天,“我”會到達她的小洲,與她相遇,我們因此會成為天底下最幸福的那一對。此為“芼”之意,亦為“樂”之遇,更是“我”對這個世界的宣言:永以為好,也即生生世世,我們都在追求美好,并將成就美好。這最后一章在承接、呼應前面樂章的同時,再次直指主題,再次強化“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永恒之感。這樣肯定、樂觀又積極的情緒與追求,難道不是《關雎》為整部《詩經》奠定的情感基調與價值取向。孔夫子的“哀而不傷”由此亦已應驗。因為只有希望存在,理想高揚,人類才會生生不息。而我們不永在此種自我精進與求索的路途中?
就此,筆者認為:
1.《關雎》所營造的這種對美好事物的不息追索,對“何以為好”的叩問和反思,對“永以為好”的祝福與期待,正是《詩經》的主旋律,或歌詠范圍,或就是人類精神所能達到的最大自由,亦是我們今日研究《詩經》,并以“永以為好”命名此種人類精神的應有之義。
2.該篇選自國風中的《周南》,除了南方多水多琦思外,它所描摹的種種情感或境界,是不分民族、地域,具有共同性的,因而能夠打動所有閱讀者。就此,把它放在三百篇之首,也不會以偏概全,更不會把我們帶偏,相反,是一種“何以為好”的典型范例。
3.至于是否特指貴族青年,則明顯是前人的誤讀。此種情感,不分階層,應是人們普遍的理想追求。我們完全不必因其君子淑女、琴瑟鐘鼓這些所謂的階級地位表征,就對追求者的身份進行設定,以致局限該詩的深刻內涵和可能引起的審美體驗。
4.前人所謂“求之不得”只能寄托于想象的愛戀也不足道。在現實中,此種求索,哪怕真的沒有實現,但在精神層面,不只作者,不只抒情主人公,就是我們讀者也經過了這樣的精神歷險。誰說,理想的實現、美好的感覺,就只能在現實生活中呈現?況且,該篇確實是完整描摹了愛情、理想的求索,以及最后真的實現,真已圓滿的過程。
5.至于經學家本就荒唐的詠“后妃之德”固然不值得我們討論,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到產生此種解讀的話語體系,不只過去,就是現在也仍然存在。這就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道德先行、意識形態論。我們應該了然,對于藝術、對于美,我們絕對不能以自己的主觀臆想隨意強加它什么主題,或什么功用。它的美,它的好,首先應是符合藝術形成的機制以及我們閱讀時美的形成與生發的自然過程。
6.至于孔子的“《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表述和經學家的“后妃之德”的評定,其實無所謂表里,不過是在孔夫子“溫柔敦厚”的傳統詩學和經學家經世致用思想的主導下,對《關雎》或《詩經》的一種意識化解讀或政治化、工具化的應用。這是特定時期的行為,但很可能會形成思維定式,甚至代替我們的審美,這是需要我們特別警惕的。
最后,我們要回答的是,該篇通篇“比興”,是否單單為愛情主題張目?當然不是,并且,生活中并不存在這樣單純的手法。至于該篇,“比興”之外,真有理趣,是真已上升到對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認定與求索。
但是,由此,我們不能不想到,以《關雎》為代表的 “周南”“召南”部分,在彰顯《詩經》最高思想內涵和藝術成就的同時,就其表現手法或審美品質而言,確實是一種異質的存在。我們明顯感覺到,若單純地以《詩經》所謂現實主義表現手法去解讀它,很難得其門而入。我們發現其中有太多縹緲的情緒或美感,執著的追求與叩問。我們雖不能證明以它為代表的江漢流域文明此時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文化,但至少我們看到《詩經》在傳播或成書的過程中,一種新的風尚或審美正在形成。就此,我們能不能這樣設想,以“周南”“召南”為代表的《詩經》中的一些篇章,其實已開啟《楚辭》的先河,它預示著南方文明、長江流域文化的到來。它的空靈深透、淑女君子的遇合,事實上已被屈原“香草美人”之喻發展到極致。由此,我們不能不慨嘆: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新的時尚與審美,已在舊有傳統或習俗中孕育成長,而我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與熱望,卻始終如一。此為“永以為好”的應有之義,“何以為好”的可能指向,更是《關雎》的開宗明義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