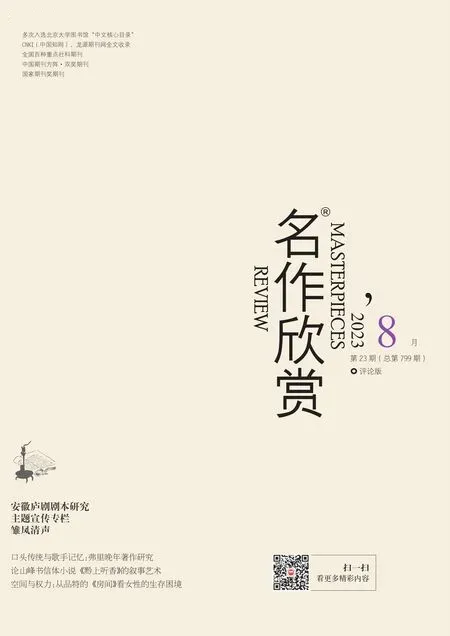宋代文賦結尾對漢賦的傳承與轉寫
——以蘇軾文賦為例
⊙俞冰越[上海師范大學,上海 200233]
一、“勸百諷一”:漢大賦至駢文的書寫傳統發展到宋代
(一)“勸百諷一”
“勸百諷一”指的對象是漢代的大賦,而宋代的文賦體系更類似于漢代后期的抒情小賦。“勸百諷一”一詞語出《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①此處揚雄指出,司馬相如的賦雖然有諷諫之意,然奢靡之辭過多,諷諫的意味則被削弱了。顏師古同樣注云:“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
故而之后“勸百諷一”意為諷諫文章的效果適得其反,形成這種諷諫力度不夠的現象是因漢賦(尤其是漢大賦)的寫作過程中,文章主體往往規模宏大、氣勢恢宏、結構精細,作者使用上千言敘述文章主體部分——奢靡迤邐的部分最容易寫出氣勢,故而文章的主體從諷諫轉為對迤邐的描述,諷諫力度被削弱,在最后的“說理”部分則比起文章主體強度減弱不少。
但“諷一”的結尾仍然是漢賦當中不可剝離的書寫部分,如果去除“諷一”,則文章不夠流動,只有文辭華麗卻繁重的主體部分,故而結尾對全文書寫的反撥和勸諭需要起到足夠有力的收束作用,一掃前文的綺麗,以此漢賦的評價標準中仍然將結尾視作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
(二)“攝意”:蘇軾文賦的特點
漢賦向后發展,隨著朝代的更替逐漸出現了變化。魏晉隋唐時期將大賦的繁華迤邐融入駢文四六體的寫作當中,全篇強調對仗工整,聲律鏗鏘有力,氣勢恢宏。
唐代初期,駢文仍然被視作文賦書寫的主體部分。自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后駢文才逐漸出現衰退傾向,中唐時期因安史之亂而出現國力衰落,藩鎮割據、宦官弄權,但貞元后社會再次趨于穩定,“中興”不僅僅體現在經濟方面,文化上則體現在古文運動的興起方面。自初唐陳子昂提出“復古”,隨后出現取法于兩漢的主張延續至今,韓愈等人的提倡時機恰好迎合了文化“中興”的需要,因此古文運動順勢而發。其作為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本質上是為了復興儒學,因此試圖改變駢文的繁復華麗,強調自然質樸的散文語言,“古”在于推行古道,“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②。通過對簡練、明晰的辭義闡釋來學習古人的治世之道,因此語言的表意作用被高度重視,即出現了對于文章“載道”作用的高度推崇。然而在韓、柳離世后的后繼者缺少如其二人的文章深度,因此古文運動逐漸失去活力,在唐代詩賦取士的情況下駢文再次復興于晚唐,直至宋代初期仍然存在,不僅在文賦領域極為興盛,連言志的詩歌都受到極大的影響,西昆體的盛極一時恰恰說明駢文的受眾群體之廣泛。
直到宋代,歐陽修等人領導的第二次古文運動才逐漸使得散文的發展更勝于駢文。由于古文運動的再次興起并持續的時間足夠長到對一代文風進行調整,宋代文賦的整體風格相較前代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轉。其中不乏傳承,又相較于漢賦變得更加清麗,篇幅短小,往往詠物,或托物言志。歐陽修的《秋聲賦》開創了宋代文賦寫作風格的基調,而宋代另一位文賦方面的領導者蘇軾的文賦寫作不難看出有《秋聲賦》的巨大影響。蘇軾的創作中仍然有繼承部分漢賦的模式化:文章前部的描述洋洋灑灑,重在氣勢與感受,抒情至文賦結尾,立意將前文的恢宏氣概一收而攬,統率全文——這與漢代傳統的“勸百諷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但漢賦的寫作由于過度強調文學性和抒情性,對故事的敘述性較弱,然而蘇軾因個人的寫作風格與當時文壇所倡導的真摯的特色,相較漢賦則更為強調文賦寫作過程中的“立意”。其佐證可在《容齋隨筆·東坡誨葛延之》中見到:“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后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③蘇軾用集市的買賣用以錢“攝”物作為比喻,引申至寫作當中,強調立意的重要性,只有先“立意”后以意攝文,才能胸中有意,憑此將“散在經史子集內”的天下之事囊括于胸中,最終胸有成竹。
故而蘇軾的文賦雖然與漢賦有明顯的傳承與相似之處,但不似漢賦“勸百諷一”所帶來的后遺癥:頭重腳輕。相較漢賦,蘇軾文賦的結尾對全文的收束力度往往極大,與前文所埋下的線索一以貫之,或者用短短一兩句將前文營造的氣息一掃而空,給人帶來留白的余韻,回味無窮。這一部分特色則由《秋聲賦》發展而來,蘇軾將其繼承發展并融進個人的創作特色中。
此外蘇軾的文賦選擇也在題材上更加日常化,如《老饕賦》《菜羹賦》《酒隱賦》都從自身經歷出發,強調日常生活瑣事都能作為文章主題,與漢賦對駢文的藝術性推崇截然不同。甚至創作目的如《后杞菊賦》中所云“作以自嘲,且解之云”④,僅僅作為記事的用處。他對文賦題材的選用相較于前代更加日常,但宋代的文賦特點恰恰在于能從日常之中發掘足以感慨之物并“為之記”。即使是簡單的主題,在結尾處仍然能提取出感慨之理,達到收束全文的作用。
宋代將前代文賦中的迤邐繁重改為清麗自然,其中多數依托于兩次古文運動的影響,但也同時存在上書皇帝以求認可的文賦,如周邦彥所作《汴都賦》模仿大賦,以許多古文奇字來體現自己深厚的文學功底,連翰林學士都難以盡數認全,只為使神宗皇帝對自己稱贊王安石新政的文賦感到喜愛。然而這種因莊嚴的朝堂公務而要求的語言儀式僅僅占了宋代文賦的一小部分,正如宋代文賦的整體傾向于清新、自然、日常,這樣炫技作用的文章多單純用以體現學識并求取公務方面的作用,并非寫作的主體傾向。尤其足以作為佐證的是,蘇軾也有仿照漢賦格式所填的《秋陽賦》,但盡管運用了漢賦格式,其情感的表達仍然與漢賦常見的形式有所區別,重在個性的抒發。
二、結尾的說理性篇幅與余韻設置
從結尾的角度而言,對于漢賦“勸百諷一”的批評源自文章過于頭重腳輕,繁華迤邐的書寫壓過了說理部分,不足對文章的主體部分形成強有力的反撥。而宋代的文賦將傳統一變,在前文的書寫中就少有重于駢體書寫的部分,結尾處的說理被當作重點進行描繪,在篇幅上與漢賦形成較大的差異,也從較為直觀的方式上解決了漢賦主要被詬病的問題。
在《秋聲賦》中可見宋代文賦結尾對全文的統攝作用,雖然是常見的主客問答形式,但結尾處卻顛覆了往常的套路化書寫。由于“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⑤,歐陽子在夜晚做出秋風蕭瑟恐怖的感慨,這段文章主體部分的書寫方式較為近似于漢賦的書寫形式,然而特殊之處在于作者在歐陽子長篇的感慨、抒情后僅用一句“童子莫對,垂頭而睡”消解了前文全部的抒情感慨。
通常的主客問答模式往往是抑客揚主,以“主”說服“客”作為文章的結尾——蘇軾文賦也往往以此形式展開,然而本文中消解了常見的駁、應、從的問答形式。“主”的長篇大論是否有說服“客”,其實在童子睡去的結尾中徹底不再被作者看重。甚至更進一步思考垂頭睡去的“客”是否有聽見“主”的感慨,其實也在陷入沉睡的結局中無法得到解答。全文的最后一句“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體現歐陽子的無奈與無人理解,唯有寂寞的蟲鳴伴隨著他的輕嘆,全文不再存在“主客問答”的形式,被“客”從交談結構中的離去、消失所解構。“主”作為文章主體而進行的大篇幅論述在最后只剩一句無奈的嘆息,將過往的慣常套路一掃而空。因此最后一句結尾雖然十分短小卻極為精悍,強有力地收束了全文對“秋聲”的論述,融于一聲嘆息,又富有余韻。
蘇軾的文賦也繼承了《秋聲賦》的寫作風格:結尾對前文的統領能力極強,同時強調結尾的余韻。蘇軾的主客問答形式往往出現在通篇靠后的位置,以主客的問答方式結尾,又為結尾的余韻設置前文的呼應,故而收尾使用的篇幅往往不止最后一句或最后一段。最能體現此點的是《后赤壁賦》的“道鶴合一”的收尾:《后赤壁賦》以蘇子夢到道士問他赤壁之游的感受,忽然意識到道士或許就是之前見到的孤鶴,而詢問后夢醒,“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后赤壁賦》是接連《前赤壁賦》對人生思考的探索,而最終“道鶴合一”以及夢醒的結局將所有夢中之境唐突地切斷——道士是誰?“道鶴合一”有怎樣的寓意?當初為何孤鶴會“飛鳴而過我”?一切的疑問都由于最終夢醒的結局被徹底切割,作者帶領讀者感受到的滿腔困惑無法得到任何的回答,消解了作者之前在登赤壁過程中的惶惶然之情,徒留下對道士不知所蹤的淡淡枉然。
《前赤壁賦》也是如此,盡管看似“客喜而笑”是一個彼此心意相通的結局,作者卻特意添加最后一句用以帶來余韻:“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客之前對“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產生惶然的情緒,蘇子用“吾與子之所共適”寬慰了他,但東方既白后的天明會是如何?在二人推杯換盞直到大醉一場后,明日的客是否已然豁達,還是在困頓中徹底忘記了昨晚的對話,所有對未來的展望被蘇子以一句“不知”帶過,給二人的探討增加了一絲可玩的余韻。
從篇幅的角度同樣能注意到兩篇文賦的結尾有相似之處:《前赤壁賦》從“蘇子曰”開始對前部分客人的愁思進行辯駁,以此收尾;《后赤壁賦》則在游覽赤壁的文章主體段就已然見到“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這一段與收尾的“夢一道士,羽衣蹁躚”形成呼應。兩篇文章的收尾都從主體段已然埋下伏筆,作者特意地鋪墊是為了讓結尾的收束顯得短促有力,不會出現拖沓和冗長的情況。
從中可以看出宋代的文賦與漢賦相比對結尾更加重視,篇幅的占比相對來說較大,說理力度也更強,尤其強調最后的結尾能留給讀者較強的可玩性與讀后余韻。
三、蘇軾文賦中兩種不同的結尾收束類型
蘇軾文賦中的結尾主要可分為兩種常見的收束類型:一種以主客問答形式為文章主體,往往以“抑客揚主”作為收尾;而另一種對日常性的事物書寫,強調最后自己從事物身上獲得的感受,從而“為之記”。
(一)“客笑”:主客問答模式的收尾方式
蘇軾文賦常以主客問答形式作為文章的主體,故而收尾也以主對客的觀點進行辯駁并將客說服,以“客喜而笑”作為結局。最具有代表性的則是《前赤壁賦》的結尾:“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而除《前赤壁賦》的“客笑”之外,仿照漢賦格式所填寫的文賦《秋陽賦》同樣以主客的方式進行書寫,借用西漢時的子虛、烏有兩位人物形象,表達作者個人的情感。此處“主”為“居士”,“客”為“公子”,以“公子拊掌,一笑而作”為結局。《黠鼠賦》中也是如此,但此處作者卻轉而一筆,將自己置于“客”的位置,蘇子的感慨也因“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而幡然醒悟,最終“余俛而笑,仰而覺”。此處蘇子作為“客”的身份,被心中的聲音(主)說服,笑著讓童子提筆記下此事,盡管看上去與原模式有很大差異,卻仍然是“客笑”的主客問答模式的收尾。
除去“客笑”的結局之外,也有單純以主的反駁作為收尾段,省略了最后客人認同的部分文章。如《后杞菊賦》以序介紹自己為何做此賦的理由,而文章的主體部分只有序言中未曾出現的“客人”言語:“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與作者的辯駁:“先生聽然而笑”,即使未曾出現最后客人認同的部分,但蘇軾還是保持著在自己文賦收尾時“笑曰”的一貫風格。“客笑”的“笑”是被“主”的說法說服,解開心中憂慮而笑,“主笑”是游刃有余、輕松自如地回答之笑。盡管笑的對象不同,表達的整體情緒卻是相同的。
(二)“為之記”:因日常事務獲得感悟
日常事務的感悟最有代表的作品是《老饕賦》《菜羹賦》等從題材選用上就較為日常的文賦,往往結尾處作者會強調自己從此事務上獲得了怎樣的感悟,故而“為之記”。
如《老饕賦》中,作者用一個頗有禪意的結局收尾:“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將對美食的書寫轉為對人生的理解,將俗物雅化,體現士人的“禪意”。從食物中體會禪機,最終達到“海闊而天高”的人生感悟。
《菜羹賦》中也是類似的收尾方式:作者感慨“忘口腹之為累,以不殺而成仁”,將食用菜羹的意義高尚化,使得日常的瑣事具有哲理上的韻味,最終引發作者的一聲嗟嘆。
這兩篇文賦都將瑣碎事物提升到哲理的高度,并為之記,時來源于宋代文學常見的題材擴展和審美轉型,對個人日常生活的關注使視角個人化,又從個人的事物中體現出新的書寫趣味,形成了宋代文賦對詠物以及托物言志的題材拓展。
①〔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07年版。
② 王水照:《傳世藏書·集庫·總集》(7—12),《全唐文》(1—6),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948頁。
③洪邁:《容齋隨筆·中華國學文庫第四輯》,中華書局2015年版。
④ 〔宋〕蘇軾:《蘇詩全集校注·第十冊·文集一》,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唐〕歐陽修:《歐陽修選集》,陳新、杜維沫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