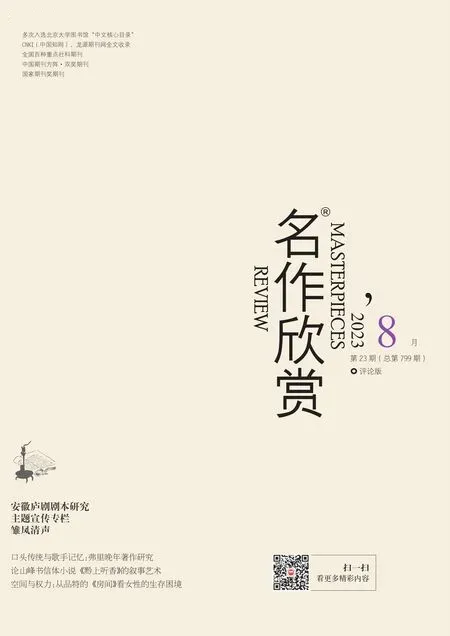融合與逃離的悖論
——遲子建小說《煙火漫卷》中的哈爾濱敘述
⊙李新艷[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1;河南師范大學 河南 新鄉 453007]
哈爾濱是遲子建小說寫作中鐘情的敘述對象,《起舞》《白雪烏鴉》《黃雞白酒》等多部小說都以哈爾濱為敘事背景展開敘事情節和敘事人物的書寫,同時對這座城市的民俗風情、歷史文化做了多維展現,哈爾濱也成為遲子建文學創作中建立的一個鮮明的地理坐標。
從繁花似錦的大興安嶺山脈——北極村到美輪美奐的現代大都市——哈爾濱,遲子建起初對這座城市是有隔膜的:“我背離遙遠的故鄉,來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我尋求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陽光空氣離我的生活越來越遠……”①歷經多年的寓居與寫作,遲子建對哈爾濱的感情也逐漸濃厚,“我是1990 年來到哈爾濱的,至今生活已經30 年了。你想,30 年孕育一個生命,如果你有一個孩子,他從出生到30 歲,都要娶妻生子了。我對哈爾濱,從最初的隔膜到現在已經水乳交融了。”②既確證了對于哈爾濱之前的“隔膜”情感,又強調了現在的“水乳交融”狀態。我們相信,30 年的時間,憑借獨特的敏銳性和豐富的情感性,遲子建對哈爾濱這座城市的人、事、物已十分熟悉,但是否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呢?作者對這座城市有著怎樣復雜而隱秘的感情呢?細讀文本,我們發現小說字里行間特殊的空間敘事和隱含的感情宣泄與其所說的“水乳交融”存在著裂隙與矛盾,一定程度上來說,哈爾濱敘述,在文學層面和精神層面都呈現出有意融合與無意逃離的悖論。
一、榆櫻院:城市空間的邊緣書寫
對于哈爾濱,遲子建在創作《煙火漫卷》時認為:“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暢快淋漓的文學表達。”③學術界對該小說的解讀也集中于城市書寫,認為“對城市的聚焦,是遲子建在《煙火漫卷》中的一個重要轉變”④,“這部作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敘事,而是真正的以城市為中心的敘事”⑤,“顯示出遲子建對哈爾濱城市書寫獨特‘地方路徑’的發掘”⑥,“帶有城市傳記的意味”⑦,等等。然而我們發現,《煙火漫卷》的敘事空間和敘事對象雖是哈爾濱,但作者真正關注的地理空間是位于都市但更接近鄉村的道外。從地理空間來說,哈爾濱分為三個區:南崗、道里和道外。南崗是政治中心和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作者在小說中很少提及或一筆帶過;道里有一條繁華的中央大街,作者著墨雖多于南崗,但介紹更多的是富有特色的老建筑;作者最為傾心的是道外,無論經濟條件、物質條件都比較落后的“棚戶區”。小說中一個重要的敘事空間——榆櫻院,就位于道外。
榆櫻院的建筑風格屬于半中半西、半土半洋,歷史成因要追溯到20 世紀初中東鐵路興起時。哈爾濱“深藏在現代高樓下,看上去破敗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⑧,可見,遲子建對榆櫻院的敘述是要突出它所隱藏的歷史故事。榆櫻院既是一個地理空間,上演著人們生活中的悲歡離合,又是一個意象,其獨特的歷史背景隱喻了哈爾濱這座城市的滄桑經歷,厚重過往。這樣的建筑有很多,《起舞》中老八雜的半月樓,《黃雞白酒》中玉蘭街的紅磚樓,如今它們的意義不僅僅是居住或使用,更是了解歷史、銘記歷史的窗口和印記。哈爾濱從開埠、中東鐵路修建以來,成為貫通東西、互通貿易的大都市,形成了獨具異域特色的老建筑:熱鬧的斯大林公園、富麗堂皇的圣索菲亞大教堂、猶太老會堂改建的音樂廳,它們與榆櫻院形成了鮮明對比,“城市現代性和殖民性交融在一起使‘哈爾濱敘事’成為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審美的試驗場”⑨。隱沒于其后的城市歷史景觀是一個城市最醒目的名片,更能彰顯一個城市的魅力和生機,是一個城市永葆生機的靈魂。遲子建對于哈爾濱文化歷史的詮釋并非考古學式的單線條描繪,而是將之與城市中的人融為一體,將宏大的歷史與現實當下巧妙結合。以榆櫻院為原點,以劉建國、于大衛為半徑形成的關系圓中,所涉及的主要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流淌著多民族的混合血液,背負著父輩、祖輩錯綜復雜的歷史命運。他們在血緣上呈現了混血的特點,在家族上匯聚了多國的因素,劉建國、翁子安、雜拌兒等下一代的個人命運與哈爾濱這座城市的命運息息相關,“既內在于20 世紀中國革命史的話語體系之中,也同時兼具多國政治力量碰撞和文化風格雜糅的特征”⑩。哈爾濱在融合多民族多國家的文化精神過程中,也形成了既風情萬種又滄桑隱忍的城市性格。
“歷史學家們試圖用概念系統解釋城市,作家們卻借助于想象系統。”?文學中的城市書寫應當是客觀敘述和主觀想象雙重建構作用的產物,既有現實意義的居住行為和居住經驗,也有精神層面的城市心態和歷史意識。遲子建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來自于父親心酸艱難的生活經歷以及感傷沉重的回憶講述,這影響了她對這座城市的主觀印象,也為她書寫這座城市打下了灰色沉重的敘事基調,“是一座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這種認知很早就有,《白雪烏鴉》中傅家甸抗擊鼠疫的悲情歷史;《起舞》中“半月樓”濃縮了哈爾濱的傳奇歷史。遲子建專情于哈爾濱,感興趣的不是它經濟發達的中心區域,而是城市邊緣地區及隱沒于光怪陸離背后的城市歷史景觀,貌似城市卻非城市,貌似現代卻非現代,這其中也隱含著作者內心對這座城市歷史的回望及當下的猶疑。
二、普通人:城市人物的裂隙闡釋
“城市想象的核心要素是城與人。”?“城”是“人”的繁衍生息之所,“人”是“城”的精靈。在敘述這座城市中的人時,作者的目光也并未停留于公司白領、精英等成功人士,而是仔細打量最不起眼的那群普通哈爾濱人,甚至是非哈爾濱人。“道外舊時叫傅家甸,打魚的,種地的,趕車的,賣柴的,開客棧、貨棧和錢莊的,經營燒鍋、火磨和茶莊的,應有盡有。”?榆櫻院作為重要的敘事場景,其住戶除老郭頭是哈爾濱人外,其他如街邊擺攤的中年男女、來拜師學藝的小劉父子、從青黛河畔來尋夫的黃娥都是從外地到哈爾濱的外來人或者說城市的邊緣人,他們為了生存或更好地生活而徘徊掙扎于城市之間,被這個歷史豐富的城市所包容,但同時也存在著較大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榆櫻院也成為連通城市和鄉村、城里人和鄉下人、現代文明和鄉村文明的中間地帶。
對于這些人,作者的敘述態度是平和、樸素的。小說既客觀暴露了人性中的現實主義、功利主義、金錢主義等負面因素,全景式描繪了城市社會中市民階層的人生眾生相,也多維度展現了人性深處普通市民的善良寬容與堅忍溫情。面對失子之痛,于大衛夫婦并未將劉建國視為仇人,謝普蓮娜至死沒有埋怨過他一句;劉光復彌留之際,黃娥為了滿足他到松花江游泳的愿望,不僅為其打來江水,還擔心冰涼的江水恐怕激著病人而為其暖水;進城買菜的老夫婦把黃娥撞傷了,雖然一窮二白卻不逃避責任,盡其所能來賠償……在這個幾乎被城市遺忘的地方,在這些都市人所不屑的“底層”那里,我們看到埋藏于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這是這群在城市生活中歷經挫折傷痛的人淺唱低吟譜出的一首人情曲,其中蕩漾的是滿滿的、溫暖的人間煙火氣,這種氣息,久經內化,可以反過來成為人的道德佐證。作者有意將她心中最期待的那種美好與現代都市隔離,退回到人群的最深處,通過徘徊在高樓大廈之外、奔波于城市大街小巷的人群來詮釋人性的本真和美好。
遲子建一向對人性有著敏銳的感知力,對生命、命運有著深刻的敬畏心。重癥室里嘀嘀鳴響的呼吸機“對不擔心醫療費用的患者親屬來說,是生命最動人的音符;而對家境貧寒的患者來說,呼吸機就是點鈔機,沉重的醫療費巨石一樣壓著他們”?,一語中的,十分深刻。作者愿意相信人性的美好并在作品中去實踐這種信仰。劉建國對突如其來的“兒子”雖百般反感,但仍然操心他們的衣食住行;黃娥無意中氣死了丈夫,愿以死來補償;劉嬌華退休后仍不辭辛苦為出獄人員安排就業。作者總有一種能量,讓我們在人性的黑暗中看到那隱藏的一絲善意,讓我們在生命的絕望中看到那掙扎的一線希望,也許這就是人性最美好的地方,也是人間煙火最迷人的地方,讓我們對這個世界仍抱有美好的期待和向往。無論城市或是鄉村,真正的生活都是撥開五光十色后顯露的最本真的、最庸常的日子,這樣的日子是普通的也是最能打動人的。“有時閱讀自己以前的作品,從最初的滯澀生疏一直到現在的巧對成熟,很多東西都在變,但有一點是沒有變的,那就是我始終關注日常性的東西。”?遲子建就是懷著對生活的滿腔熱愛之情,與日常生活進行質樸的交流,總是在灰暗與沉郁的同時,能夠發現生活的陽光與溫暖。老八雜匯聚了城市的各色人等,他們總是在凌晨四五點就從家里出去,晚上帶著一身臭汗回家,用歌聲來驅散一天的疲憊(《起舞》);陳青娘家在城郊的一處貧寒之地,回家需要多次輾轉大巴車、公共汽車、報廢車改裝的面包車才能到達(《第三地晚餐》);秋冬季節糊窗縫、腌酸菜、喝黃雞白酒《黃雞白酒》)。作者將哈爾濱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刻畫得細致入微,生活在其中的人并沒有在物欲極大豐富、追求現代時尚的社會環境中就妄自菲薄,反而都在體味自己生活中的快樂和滿足,這也許是他們的生活哲學,卻也反映出作者的生活觀念。
三、松花江:城市之外的想象之地
“城市不只是一個物理結構,它更是一種心態,一種道德秩序,一組態度,一套儀式化的行為,一個人類聯系的網絡,一套習俗和傳統,它們體現在某些做法和話語中。”?城與人具有某種文化同構關系,城市經濟的急劇發展,必然會在自然、文化、人文等方面有所體現和反映。作者來到哈爾濱的時間正處于一個時代變更、社會變革的轉折期,她在感受城市發展所帶來的便捷與摩登外,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壓力和問題,這影響了她對現代化的理解。“如果現代化是讓人過同一種模式的生活,如果現代化是讓人遠離對人的心靈有撫慰的生活,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是真正的野蠻!”?就像《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大規模的森林開發問題,《晚安玫瑰》中的婚戀觀問題,《群山之巔》中的環境破壞問題,《煙火漫卷》中也透露出作者對城市現代化過程的反思。
小說中,劉建國家的“樓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建造的,所以多年以來歷經了水電煤氣、暖氣的改造工程,以及電話、有線電視和光纖的入戶。”?城市改造既給市民生活帶來極大便利,又展現了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卻也“給這樓‘掛腸破肚’,弄得它傷痕累累”?。劉嬌華家附近的馬家溝以前“是一條充滿浪漫情調的清水河”?,后來“由于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建筑規模不斷擴大,生活污水和垃圾激增,加之氣候變化,這條河遭受污染,幾度干涸,成了城市排污口,河水變得渾濁,散發著刺鼻的氣味”?。當三十年后作者再回望這段過程,不僅僅局限于簡單記錄生活的日常,也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更是要通過對生活的重新想象和刻畫,打開一條能洞悉當代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開辟一條深思過往和將來的精神向路。
雖然作者一直強調在寫哈爾濱這座城市,但小說中仍能捕捉到她試圖逃離城市、回歸鄉村的想法,然而身體的逃離并不實際,其實是內心的一種渴望,著意逃離與回歸之間,一個重要的空間意象就是松花江。作者除了對“松花江”進行了較多的自然描述外,還將“松花江”打造成心靈的救贖之地。劉建國所犯的愚事是在松花江邊驚醒,下決心再次來到興凱湖畔,找到那個孩子并彌補過錯,這既是他最后身體的落腳點,也是靈魂的落腳點。黃娥為了彌補當年的過錯想在安置好兒子后去陪伴丈夫的亡靈,在給孩子寫的“哈爾濱記事”中,記錄最多的是松花江。劉光復死后,劉建國和妹妹用松花江水為其凈身,骨灰撒向松花江。在他們凈化靈魂、尋找生命救贖之地的時候,共同的方向都是松花江。如果說榆櫻院是所指,那么松花江就是能指,是作者城市之外的想象之地,心靈的救贖之處。現代文明雖然筑起了高樓大廈,但是筑起的文化壁壘使得傳統生活離我們漸行漸遠,環繞在城鄉之間,無法縫合它們之間的差異,既有物質層面也有隱形層面,看不見摸不著的,揮之不去又時時纏繞于人們心中,從而試圖在鄉村中來縫補生命的殘缺之處。然而,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又怎能完全逃離城市,重返自然呢?鄉村可能是城市人的一種假想和心靈歸宿,作者試圖以自然的溫情來增加城市的溫度,來為現代城市當中焦慮、茫然的人們找尋一條凈化心靈的途徑。人對自然抱有虔誠的敬畏之心,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是一種對抗人與人之間不和諧的方式。“地域決定著人的存在,地域給人們一種身份認同感、集體歸屬感、時空確定感以及內心寧靜感。”?文學地域主義從地域出發,但又超越了地域,它從地域中獲得素材和啟示,傳達的是終極的人文關懷。大自然是遲子建生長的地方,也是她鐘情的地方,更是她心靈的歸屬地,她一次次在文學中抒發著對這片土地的留戀之情。
遲子建是一個對人生懷有善意、對人性充滿信任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總是以一種淡定的、徐緩的敘述語氣道來她所要講述的故事,又總是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批判。在當代作家當中,她突破“現代化”的重重障礙和誘惑,回望傳統文化的品質和精髓,正視現實社會,反觀現代文明的內容和形式,實在是非常難得的。
①遲子建:《原始風景》,《人民文學》1990年第1期。
② 吳銘:《城市煙火孕育蓬勃生機》,《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0年9月28日。
③?遲子建:《〈煙火漫卷〉創作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戴文子:《哈爾濱的“人間煙火氣”》,《方圓》2020年第20期。
⑤⑩崔慶蕾:《煙火中的城市抒情、反思與批判——讀遲子建長篇新作〈煙火漫卷〉》,《小說評論》2021年第3期 。
⑥ 張海玉、于京一:《試論遲子建城市書寫的“地方路徑”——以〈煙火漫卷〉為中心》,《百家評論》2021年第2期。
⑦ 李永東:《誰來為城市署名——評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煙火漫卷〉》,《文學評論》2021年第5期。
⑧?????? 遲子建:《煙火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04頁,第56頁,第6頁,第23頁,第23頁,第162頁,第163頁。
⑨ 于小植:《“城市主體”建構及其限度——論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煙火漫卷〉》,《文學評論》2021年第6期。
? 〔美〕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
? 楊凱芯、李永東:《別處的北京想象》(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 遲子建、周景雷:《文學的第H地》,《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4期。
? 〔美〕張英進:《中國現代文化與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時間與性別構形》,秦立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遲子建、郭力:《現代文明的傷懷者》,《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
? 劉英:《文學地獄主義》,《外國文學》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