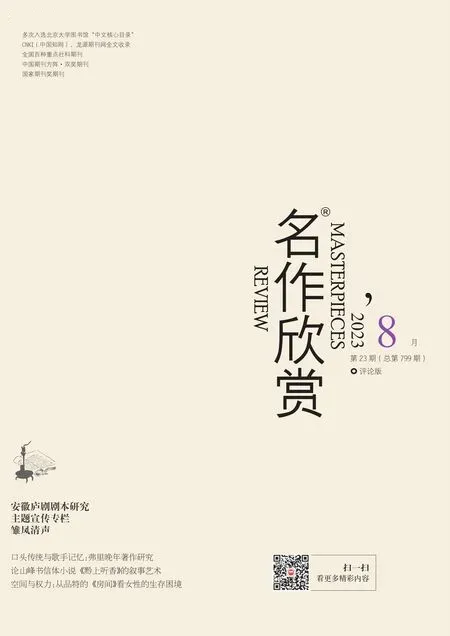論唐詩中的男性演奏
⊙徐航[安徽師范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
唐朝是音樂與詩歌的黃金時代,關于唐詩中涉樂詩的范圍,陸群《唐代詠樂詩研究》限定為:“以音樂作為主要或重要審美對象,通過對樂器、樂聲、樂工、樂曲、樂事等音樂題材和聽者感受的描寫,藝術地表達音樂感染力的詩歌作品。”①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將唐詩中的男性演奏詩界定為:“以男性表演的音樂作為主要審美對象,并側重于音樂描寫的詩歌作品。”據此爬梳《全唐詩》,所得男性演奏詩共有七十余篇。因“藝人”通常泛指以樂舞表演為生的群體,而此類詩歌中出現的演奏者包含了詩人、隱士、僧侶等各種身份,階層較復雜,故而統稱他們為“男性樂人”。
學界對唐代涉樂詩研究翔實,但對于男性樂人少有關注。筆者通覽描寫男性演奏的唐詩,發現它們雖數量有限,但樂人的階層分布多元化,詩人與演奏者之間不僅有看客與藝人的關系,還有很多是朋友、師生、同僚等,相較于摹寫女性表演的詩作,詩人在描寫這一類音樂表演時往往少了一份輕佻,在“聲色”之間更加傾向于對“聲”的描摹,淡化了“色”的比重,情感意蘊也呈現出豐富性。這種獨特的描寫藝術賦予了詩歌怎樣的風格特色?其中又蘊含了詩人怎樣的創作心理?本文將通過形象描寫、環境描寫、音樂描寫三個方面進行深入探究。
一、形象描寫
唐詩中對男性樂人的形象描寫篇幅十分有限,這與觀看女子表演的唐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說后者是惟妙惟肖的西洋畫,如“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艷,醉舞雙眸斂鬢斜”(萬楚《五日觀妓》),那么前者就是著意于留白、傳神的中國畫,詩人往往只臨摹男子的輪廓或一個部位,留出大量的空白,讓讀者在感受音樂時展開對表演者形象的想象。
《詩經》中用“手如柔荑”引發人們對莊姜美貌的千年遐想,唐詩中也對男性樂人的手青睞有加。如李白《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云:“《白雪》亂纖手,《淥水》清虛心”②,這位“閑坐夜明月”、獨奏“悲風調”的幽人隱在夜色中,只留一雙玉手在月光下舞動,一暗一明,一隱一言,詩人視角的聚焦,也帶動讀者欣賞重心的傾斜,而夜色背后的留白,更是給這位隱士的形象增添了神秘莫測的余韻。顧況的《李供奉彈箜篌歌》在寫李憑的箜篌表演時也多次寫到“手”:“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弦中指撥”“腕頭花落舞制裂,手下鳥驚飛撥剌”“左手低,右手舉,易調移音天賜與”“手頭疾,腕頭軟,來來去去如風卷”“指剝蔥,腕削玉,饒鹽饒醬五味足”“爇玉燭,點銀燈;光照手,實可憎。只照箜篌弦上手,不照箜篌聲里能”,詩人慨嘆玉燭“只照箜篌弦上手”,實際上詩人留給讀者一窺樂人形象的“貓眼”里也只有一雙“箜篌弦上手”,透過此眼,可以看見演奏的起伏跌宕,表演的始末都在對“手”的描摹中層層推進。詩人以生動細膩的手部動作描寫串聯整首詩歌,最后又以燭火下的手部特寫收束全篇,以點帶面,音樂表演的形與藝得到完美融合,觸發讀者對演奏者其人其術的無盡遐想。
除了手部描寫外,唐詩中亦不乏其他匠心獨運的男樂人形象描寫,但它們無一例外都體現出詩人對細節的捕捉,對留白藝術的追求。如李宣古《聽蜀道士琴歌》在描寫琴師時僅勾勒出一彎朦朧的背影:“更深彈罷背孤燈,窗雪蕭蕭打寒竹”,窗欞外雪打寒竹,燭火下人影伶俜,不必再從“顏如雪”談到“淚如珠”〔白居易《夜聞歌者(宿鄂州)》〕,只此一條寒夜竹窗下的瘦影,已予人無限凄惶迷離之感、人生踽涼之悲,這是唐詩中男性演奏的描寫以無充有、言近旨遠藝術的典型表現。再如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僅以“紫髯”“綠眼”兩個詞對異域的男樂人形象做了簡潔而傳神的刻畫,“紫髯”“綠眼”是異域男子最突出的形貌特征,也是與中原人差異最明顯的地方,這既是對“胡笳聲”演奏者的交代,也是“聲最悲”的由來,詩人通過樂師的形象描寫對所處環境做了無聲的交代。《古詩十九首》中說:“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③,異域的樂聲在陌生的環境里更顯凄愴,而點到為止的人物描寫卻給全詩帶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暗示性韻味。
袁枚云:“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唯虛空。詩人之筆,列子生風。離之欲遠,即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水,斯名應龍。”④唐詩中的男性樂人是面目模糊的,他們不作為單獨的欣賞對象而受到精細的描摹,對他們的刻畫往往是為了配合音樂的表現,此類描寫既完成了虛空、留白的藝術架構,在音樂詩中不喧賓奪主,又能于虛處“即之彌工”起到交代人物情況、烘托音樂氛圍、串聯演奏過程、暗合詩人意志、引發讀者遐想等作用,虛實相生,最終完成涉樂詩中的“中國畫藝術”。
二、環境描寫
在男性音樂表演的環境描寫上,很多唐詩在時間、意象、氛圍等方面表現出極高的相似性,具體體現在兩點:清幽感、距離感。從時間安排上來說,在對表演時間作了交代的30 首男性演奏詩中,有27 首的時間是在夜晚,占比高達百分之九十。在詩歌意象搭建上,“風”出現35 次、“月”出現28 次、“云”出現25 次、“竹”出現13 次,其余出現頻次較高的物象還有“雪”(11 次)、“煙”(10 次)、雨(7 次)、“霜”(6 次)等,同時,概括氛圍的“清”字在這些詩中一共出現了35 次,令人不禁感嘆:男性演奏詩中世外之境真多!
詩人們常用“夜”“月”“燈”“夕”等字眼向讀者暗示音樂表演背景的暮色沉沉,如:“明月搖落夜,深堂清凈弦”(鮑溶《秋夜聞鄭山人彈楚妃怨》),“曲終月已落,惆悵東齋眠”(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邊州獨夜正思鄉,君又彈琴在客堂”(項斯《涇州聽張處士彈琴》),“空堂半夜孤燈冷,彈著鄉心欲白頭”(薛能《秋夜聽任郎中琴》),“月落江城樹繞鴉,一聲蘆管是天涯”(張祜《聽簡上人吹蘆管三首》)等。如此眾多的夜間演奏,不能不讓人懷疑:這究竟是單純的時間巧合,還是詩人有意為之?
韓愈在《山石》中曾抱怨夜間的觀賞:“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⑤,而夜間的音樂演奏卻是更為動人的,齊己《秋夜聽業上人彈琴》就曾剖白道:“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常建《聽琴秋夜贈寇尊師》亦云:“琴當秋夜聽。”另外,夜本身就有清幽、冷寂的況味,方回云:“道途晚歸,齋閣夜坐,眺暝色,數長更,詩思之幽致,尤見于斯”⑥,上述詩中亦透露出“岑寂”“獨夜”“惆悵”等心理感受,這些無疑都是詩人們有意將時間安排在夜晚的佐證。最后,不妨從逆向角度再看那些描寫白日演奏的樂詩,竇庠《留守府酬皇甫曙侍御彈琴之什》:“青瑣晝無塵,碧梧陰似水。”陽光的透射下連塵埃也不見,蔥蔥梧桐樹下投影似水幽幽。劉禹錫《和令狐相公南齋小宴聽阮咸》:“座絕眾賓語,庭移芳樹陰。”室內鴉雀無聲,時間在芳樹的影子里靜靜流逝。可以看到,即便將時間切換到白日,詩人還是在反復強調“清幽”。因而,時間上的夜只不過是詩人寄托情思的載體,在那濃厚暮色中化不開的是詩人內心對清幽、孤寂情境塑造的追求。
從意象使用上來看,“月”“云”“竹”“雪”“風”“煙”“雨”“霜”等意象在詩中頻頻出現,以其自身的冰清玉潔為音樂表演營造出清冷幽雅的意境,如“竹林高宇霜露清”(韋應物《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月照竹軒紅葉明”(司馬扎《夜聽李山人彈琴》)、“晴碧煙滋重疊山,羅屏半掩桃花月”(溫庭筠《郭處士擊甌歌》)等,“月”“云”遙遠、“風”“煙”縹緲、“雨”“雪”“霜”亦是冷不可親之物,詩人們或許正是想利用這些意象營造出疏離感,傳達“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訊息,將演奏者與讀者拉開距離,絕不似女性表演詩中如可聞見脂粉香味、牽住飛舞霓裳那般親近。著名美學家朱光潛說:“創造與欣賞的成功與否,就看能否把‘距離的矛盾’安排妥當,‘距離’太遠了,結果是不可了解;‘距離’太近了,結果又不免讓實用的動機壓倒美感,‘不即不離’是藝術的一個最好的理想。”⑦唐詩中對男性音樂表演的距離安排不可否認地為演奏環境帶來了肅穆與高潔感,讓此類詩歌與一般的靡靡之音、尋歡作樂的音樂想象拉開了距離。
三、音樂描寫
男性演奏中的音樂表現是詩人摹寫的重點。方扶南《李長吉詩集批注》曰:“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詩足以驚天,李師足以泣鬼,白詩足以移人。”⑧其中的“驚天泣鬼”之作皆為男性演奏詩,可見唐詩輝煌的音樂描寫成就。誠然,“時間不存在可替代品,這使時間在音樂形式推動內部構建力量時具有唯一性”⑨,而詩中的音樂描寫在千載之下仍能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這與其真摯、細膩的修辭表現不無關系。
通過比喻來達到耳目通感在中國文學中很早就有先例,如《禮記·樂記》:“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孔穎達《禮記正義》:“聲音感動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狀如此。”⑩唐詩在表現男性演奏時也運用了大量的動態比喻,如“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李白《月夜聽盧子順彈琴》)、“十指宮商膝上秋,七條絲動雨修修”(薛能《秋夜聽任郎中琴》)等,這與唐詩中的一般涉樂詩并沒有太大區別,真正能夠凸顯男性演奏特點的是在比喻之中對力感把握的追求。
張祜《楚州韋中丞箜篌》:“千重鉤鎖撼金鈴,萬顆真珠瀉玉瓶。”運用貼合音質的“鉤鎖”“金鈴”“真珠”“玉瓶”作比,詩人尚覺不足,還要加上“千重”“萬顆”來擴大聲勢,再用強力的“撼”、流動的“瀉”使聲音震動起來、流瀉開來,整條充滿力感美的動態流程一齊構成音樂的喻體,令讀者耳中頓時鈴聲大作,玉瓶翠響。這種在音色之內揣度力感的音樂描寫,在“泉”字上體現得最明顯。“泉”是男性音樂表演詩中使用較多的喻體,常常呈現出不同的音樂風格,如“泉迸幽音離石底,松含細韻在霜枝”(方干《聽段處士彈琴》)是擊石迸濺的泉水,聲音靈動跳躍;“鶴警風露中,泉飛雪云里”(竇庠《留守府酬皇甫曙侍御彈琴之什》)是高處飛流的泉水,其聲縹緲空靈;“寥寥夜含風,蕩蕩意如泉”(鮑溶《秋夜聞鄭山人彈楚妃怨》)是波動蕩漾的泉水,其聲輕柔宛轉;“灑石霜千片,噴崖泉萬尋”(齊己《聽李尊師彈琴》)是自崖上噴涌而下的泉水,其聲洪大激昂;還有“朱絲弦底燕泉急”(賈島《聽樂山人彈易水》)的急促、“花咽嬌鶯玉漱泉”(楊巨源《聽李憑彈箜篌二首》)的清脆等,“泉”被賦予了豐富的生命力,同一個喻體,詩人通過對力感的揣摩,打破固定思維,使其承載了千變萬化的音樂演奏,可見唐詩中男性演奏音樂描寫的細膩、生動。
四、結語
綜上所述,唐詩中對男性演奏的描寫特點可以大致概括為:人物描寫的留白、環境描寫的幽寂以及音樂描寫的生動細膩,呈現出與一般追求聲色的樂詩不同的風貌。筆者認為導致男性演奏詩呈現出以上特征的重要原因是:情勝于欲。
唐朝,尤其到了中晚唐時期,音樂演奏更加傾向于女性,以至于“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歐陽炯《花間集序》)?,而在男性演奏詩中出現的樂人,身份大都為文士官員、僧侶道士,他們與詩人之間不再是簡單的奏樂者與賞玩者的關系。平等的地位打斷了詩人狎褻、獵奇的眼光,階級與身份上的親近又讓詩人更容易流露出真實、深沉的情感,因而對他們演奏的敘寫往往淡化形象的描摹,以清幽冷寂的環境襯托演奏氛圍的肅穆或樂人品質的含霜履雪,又時時透露出詩人細膩真摯的情感,如劉禹錫《聞道士彈〈思歸引〉》:“仙公一奏思歸引,逐客初聞自泫然。莫怪殷勤悲此曲,越聲長苦已三年”,夢得本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豁達,但《思歸引》“一奏”,“初聞”就令他泫然淚落,可見此樂的感發力量。再如鮑溶《秋夜聞鄭山人彈楚妃怨》:“容華能幾時,不再來者年”對年華易逝的深悲、項斯《涇州聽張處士彈琴》“邊州獨夜正思鄉,君又彈琴在客堂”對故園的思念等,無不蘊含著深摯動人的情感。《呂氏春秋·仲春紀·情欲》:“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唐代男性演奏詩中的情理壓倒了追摹聲色的欲望,又因情感的節制而呈現出留白、距離感等特性。
由上可見,唐代男性演奏詩雖從屬于樂詩,但因樂人的身份、詩人的情感態度、詩歌描寫的側重點等條件的不同而在普遍性中蘊含著特殊性,在對唐宋涉樂詩詞研究浩如煙云的文獻中,針對男性演奏者的研究寥寥無幾,這對此類詩歌而言乃不貲之損,對于唐宋文學的整體研究亦有畸輕畸重之弊。本文通過對男性演奏詩中較為直觀的一角——描寫藝術的挖掘,嘗鼎一臠,探討此類詩歌的獨特性,期待學者們關注這一群體、這類詩歌,從而推動學界對唐代涉樂詩更全面、清晰的認識。
①陸群:《唐代詠樂詩研究》,長沙理工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② 徐昌州、嘉訓編著《古典樂舞詩賞析》:“盧子順,生平不詳,是個隱者,他身居山林,淡泊寡欲,胸懷高潔。”
③曹蔚文、李至琳、周雙立:《兩漢文學作品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頁。
④ 〔清〕袁枚:《續詩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9頁。
⑤ 宗傳璧:《韓愈詩選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頁。
⑥〔元〕方回:《瀛奎律髓》,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301頁。
⑦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
⑧ 吳戰壘:《唐詩三百首續編》,安徽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頁。
⑨ 李京澤、李思琦、季惠斌:《以音樂美的體驗解決“美的本質”問題》,《當代音樂》2022年第9期,第38—40頁。
⑩ 李學勤:《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8—1149頁。
? 周嘯天:《古文鑒賞》,四川辭書出版社2019年版,第591頁。
? 高誘注:《呂氏春秋》,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