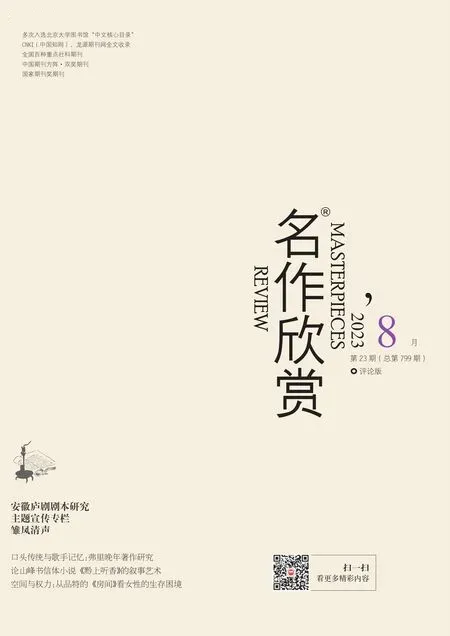羅迪·多伊爾《微笑》中主人公的幻化與創傷
⊙張云繡 田祥斌 [廣州理工學院,廣州 510540]
羅迪·多伊爾(Roddy Doyle)是當代愛爾蘭最杰出的小說家,他善于用其敏銳的洞察力捕捉愛爾蘭社會存在的深邃問題,特別是對青少年成長過程的細膩觀察以及青少年心理世界感受的細致描寫方面深有造詣。1993年,羅迪·多伊爾以兒童視角敘述的小說《帕迪·克拉克哈哈哈》獲得布克獎,他的作品大多以都柏林普通人的生活為主題,富有溫暖的人文主義情懷。多伊爾小說創作的語言簡潔而又生動,能給讀者帶來無限的想象。
小說《微笑》出版于2017 年,是多伊爾關于兒童成長的一部心理小說。該小說以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幻化的維克多(Victor)的悲慘人生展開,講述兒童心理問題是如何影響著他們的未來。兒童時期,菲茨帕特里克因被校長性侵后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蛻變為與菲茨帕特里克截然相反的人格幻化者——維克多,這種雙面人格持續了38 年。在故事中,羅迪·多伊爾借兩個矛盾人格的相遇,逐漸揭開主人公維克多的面紗,暴露出當代校園中普遍存在的性侵和暴力。通過校園內的倫理道德淪喪敘事和主人公的心理變化,揭示了青少年成長歷程中心理健康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著名作家、評論家邁克爾·紹布稱贊道:“多伊爾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創傷后帶來的傷害,還要盡可能地去感受它們。這是他迄今為止最勇敢的小說,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小說。” 評論家們一致認為,無論是細膩地觀察,還是令人膽戰心驚的心理懸念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微笑》都成功地撼動了人心。本研究從心理分析角度,試圖探討維克多微笑背后的心理創傷對青少年人生的毀滅性影響。
一、維克多的回避創傷與再體驗苦難
心理創傷是一種損害心理健康的精神疾病,通常是由自然或人為災難引起的強烈情緒反應。小說中維克多的心理創傷當然是源自人為因素,為了躲避不堪回首的過去,幻化后的維克多是個小有名氣的政治記者,喜歡寫小說,是中年離異的正常男人。但菲茨帕特里克的突然出現打破了他原有的平靜生活,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奇怪男人,以他中學同學的身份出現,不斷地揭開他的傷疤,喚起維克多在學校里被男校長性侵17 次的痛苦回憶。雖然維克多極力掩藏創傷事件的存在,編造了新的身份,試圖走向新的人生,但隨著不堪回首的過去侵襲而來,維克多也不得不面對真正的自己。真實自我的閃現,以及揮之不去的噩夢,證明了維克多從未擺脫創傷事件的創傷巨痛。
維克多通過38 年的回避試圖營造自己的“桃花源”,逃避現實世界給他心理帶來的傷害。根據心理分析:“回避癥狀(Avoidance)體現在受害者試圖在生理和情感上遠離創傷。創傷事件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如壓倒性的恐懼、害怕和焦慮,這些情緒反應可持續終生。因此,對創傷事件的回避可以暫時緩解痛苦。”維克多為了緩解創傷的痛苦,選擇逃避不堪回首的過去,幻想創傷事件沒有在自己身上發生,這正是一種心理創傷的回避癥狀。
維克多創傷的回避行為主要體現在雙重自我。為了躲避創傷事件帶來的傷痛,菲茨帕特里克將自己幻想成另一個他——維克多,一個沒有遭遇過性侵的正常人。事實上,少年兒童往往弱小脆弱,“無法擺脫權威的壓迫。他們只能躲在幻想世界里,假設自己是別人,哪怕只能緩解一分鐘的痛苦”。然而美夢再美,終會醒來。38 年后,菲茨帕特里克以維克多的同學的身份現身,并主動回憶起他們的學生時代。然而,即使維克多假裝不認識菲茨帕特里克,甚至排斥,尤其是極力逃避菲茨帕特里克不斷提到的往事,但他無法真正抹去這段陰霾。
為了盡力回避過去的創傷,現實中忍氣吞聲、唯唯諾諾的維克多一反常態地編造故事,試圖減輕過去受到傷害的程度,他堅決否認自己被校長性侵的事實。在幻想世界里,信誓旦旦地宣稱他曾被猥褻過一次,而他勇敢地在廣播中揭露了校長惡劣的犯罪行為。即使面對菲茨帕特里克的一再揭開傷疤,他依舊拒絕承認殘酷的事實。這正是一種暫時緩解傷痛的表現,但這種持續性的回避行為,是當事人不能直視深處的心理問題。游離在正常生活之外而遺失了真實的自我,也就始終無法治愈傷痛。
回避痛苦的過去是害怕再體驗帶來更重的創傷。正如凱茜·卡魯斯所述:“創傷是對嚴重的突發性或災難性事件的經歷,其中對事件的反應通常會延遲、不受控制地重復出現幻覺或其他侵入性現象。” 在《微笑》中,心理創傷的再體驗也給維克多帶來了毀滅性打擊。即使回避,他也無法完全避免縈繞腦海的痛苦記憶,這種延遲的反映和重復出現會持續傷害受害人。正如赫爾曼提到的再經歷癥狀那樣:“即使經過很長時間,受到創傷的人也會不斷想起創傷事件,就如同他們在不斷地重新體驗,尤其是體驗當時的感受和情緒。創傷就像一道符咒,反復出現在受害者的意識中。”38 年里,維克多一直在逃避創傷的陰影,但即使躲進了幻化世界,他也無法完全忘記那些創傷事件。恰恰相反,反復體驗創傷事件如影隨形,無孔不入地侵入維克多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擊潰他的精神世界。
創傷事件不斷入侵維克多的夢境,百般折磨著他。就算時隔多年,創傷事件的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中,噩夢一次又一次地將他拉回被校長性侵的場景。刻畫在腦海中的受害細節總是歷歷在目,比如被性侵時教室的地板、校長的大手等,這些頻頻重演的創傷經歷使他一直無法走出陰影,嚴重阻礙了他的成長。
在現實中,創傷性記憶反復入侵,嚴重影響了維克多的生活。菲茨帕特里克的多次出現,讓維克多不斷陷入糟糕的回憶中。在故事的尾聲,菲茨帕特里克打破了維克多的幻想世界并告訴他:“我是你,維克多。”此外,菲茨帕特里克揭露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校長不只是騷擾你——我,我們。不止一次,他并沒有就此止步。一次,兩次,一共十七次。他強奸了我們,維克多。”不僅如此,菲茨帕特里克還向維克多詳細地描述了不堪回憶的遭遇,壓倒性的恐懼感也隨之而來。痛苦記憶的不斷入侵,使維克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駭人的感受和情緒,痛苦的記憶摧毀著他的理智。
這正是小說要昭示的,心理問題頻發,必須深入研究心理創傷問題,更多地關注心理創傷這種無形卻傷害力巨大的心理疾病,幫助更多人走出創傷的陰霾。
二、維克多心理創傷的成因與警示
《微笑》中,導致維克多心理創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學校、個人性格和他的家庭三個方面。維克多的心理創傷雖然沒有造成身體傷害,但痛苦的經歷卻比身體的傷害還要嚴重,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陰影,這既有直接成因,也有間接因素。
從影響的程度和持續的時間可以看出,校長的性侵和維克多性格的自我壓抑是導致維克多遭受心理創傷的最直接原因。維克多的創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就讀的學校校長對他的性侵造成的。“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大多數教師與受害者在學習生活中經常見面和相處,受害人通常會對加害主體有類似于家中長輩的尊敬、信任和崇拜。” 作為學校的管理者,校長與維克多接觸頻繁,對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加上家長對兒子的不關心,維克多成為校長“合適的學生”,然后以“教摔跤”的借口在放學后留下他,并實施了猥褻、施暴、強奸等罪行。他深知維克多不會揭穿他這些齷齪的事,竟然肆無忌憚地威脅維克多:“你長大了能與我作對了!”弱小的維克多哪敢反抗,因此釀成了人生悲劇。
作為管理者的校長是權力擁有者,也是虐待狂,用暴力的手段體罰學生是司空見慣的行為。維克多說過:“校長曾經在教室門前抓住道克并毆打他,只因他認為道克在傻笑。”“工作特點與傳統道德觀念的影響,受害人基本上不能也不會對其產生反抗意識,在其受到侵害后也不敢告訴家長,而犯罪行為人正是因作案的低風險、低成本,才肆無忌憚地對受害人進行持續的加害行為。”正因為如此,校長在學校內可以隨意虐待毆打沒有反抗能力的維克多。利用職權辱罵虐待學生,游走在無人看管的不法之地,這也導致維克多不敢向身邊人揭發校長的此種暴力行為。
維克多的自我壓抑是導致他形成心理創傷的又一直接原因。小說中,維克多是一個敏感的男孩,很容易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自從經歷了創傷事件后,他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情緒之中,從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在三十多年的自我壓抑中,特別在糾結于是否要揭穿校長的罪行時,維克多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維克多內心十分渴望站在眾人面前揭露校長的惡行;另一方面,維克多既害怕丑事敗露,也畏懼校長的報復,始終不敢向任何人吐露真相。然而,在他的心里依舊渴望身邊人能注意到他的異常,希望同學們能問他為什么放學后留在學校,希望媽媽能發現他內褲上的血跡。但不幸的是,沒人注意到他的反常之舉。最終,維克多郁結于創傷事件,陷入自我壓抑的牢籠中,加深了他的心理創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校長作為惡行的始作俑者,在陽光下得意洋洋地對受害者進行施暴,而作為受害者的維克多卻一直生活在黑暗的陰影中,無法解脫。
導致維克多心理創傷的間接因素在于親情缺失和肆虐的校園暴力。一方面,他的母親從未經受過教育,沒有運用正確的方式培育維克多。而且母親忙于家務和照顧妹妹,無暇顧及維克多的生活和學業。她不僅不知道維克多在學校被性侵的事情,就連三年的校園暴力她也毫無所知。另一方面是維克多缺乏父愛。為了養家糊口,父親外出謀生,缺少對孩子的陪伴。在《微笑》中,維克多對他父親的描述是:“我不認識他。我每天都看到他的照片,但我聽不到他的聲音,也想象不到他在廚房的樣子。”在維克多的成長過程中,父親對他幾乎沒有任何關心,所以維克多對父親沒有具體的記憶。更糟糕的是,父親在他被性侵的過程中因病住院,這無疑給了罪犯更多的機會。無論是母親的疏忽,還是父親的親情缺位,都間接地使維克多成為校長的獵物,陷入生活的陰霾。因此,維克多心理創傷的加劇與長久沒有得到正確的治療,他的父母難辭其咎。
校園暴力和老師的不作為是導致維克多心理創傷的又一間接原因。在充滿敵意和暴力的學校里,學校的不當管理、教師責任心的缺乏和學生之間的霸凌都對維克多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在學校里,教師對學生毫不關心。維克多的男法語老師墨菲老師(Murphy)在課堂上對維克多說“我無法抗拒你的微笑”。在同學眼中,墨菲課堂上唯獨對維克多說這句話,而且言語里面似乎含有一種超越師生關系的情感,因為墨菲的稱贊,致使維克多遭受了持續三年的校園暴力。更糟糕的是,老師們對校園暴力視而不見。“老師們從不介意暴力,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插手此事。”維克多遭受校園暴力的三年,沒有一個老師站出來阻止這種惡劣行為。很明顯,這些教師沒有任何的職業道德和同情心,在他們眼中,學生只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弱勢群體,從來都不需要尊重。面對敵對的學生和老師的失職,維克多在學校備受身體和心理的煎熬,一步步將他從陽光大道拖進惡魔的深淵。
維克多的心理創傷是多方面的,有直接因素,也有間接因素。校園生態失衡,親人關愛缺位,教師漠不關心,這都是導致他悲苦數十年的源頭。如果能給予受害者足夠的關注,及時發現異常行為和心理問題,就能從源頭上預防或進行心理治療。這表明,處在成長關鍵時期的孩子,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都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愛護。
三、心理創傷的雙面人格
在《微笑》中,心理創傷對維克多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他,現在卻成了一具黯淡無光的軀殼。由于不可抗拒的創傷事件的發生,他對前途喪失信心,人生觀扭曲。弗洛伊德描述這種現象為受害者對創傷性災難時刻的執著,不知道如何掙脫,因此與現在和未來完全脫節。心理創傷導致維克多成為一個沒有夢想和靈魂的行尸走肉,形成現實與幻想之間的沖突,最后達成現實與臆想世界的和解。
赫爾曼在《創傷與復原》中說道:“創傷事件破壞了受害者對世界安全性、積極價值觀和準則的原有認知,所以受害者往往會在創傷事件中感到內疚和自卑。”由于無法抗拒的創傷事件的發生,維克多對前途的信心徹底消失,人生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心理創傷扭轉了維克多的人格,他本可以成為一個樂觀善良的人,但真實的他卻萎靡傷感,沉浸于匪夷所思的幻想之中。起初,維克多是一個簡單而敏感的小男孩,對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滿希望。經歷創傷后,他內心變得悲觀、黑暗,尤其體現在他歪曲的想象中。只是一間重新刷墻的出租屋,他卻想象有人在那里被謀殺,墻上還留著血,并且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情況下,編造了他鄰居是妓女的故事。此外,菲茨帕特里克的衣服反映了他對生活的負面看法。他總是穿著“那件側面有口袋可以裝獵槍彈和死兔子的襯衫”。無論是外表還是內心,都透露了他是一個沮喪的悲觀主義者。
心理創傷摧毀了維克多的前途與成就。維克多曾對未來充滿信心,但菲茨帕特里克卻對自己的生活充滿消極和困惑。在學校時,維克多愛好合唱與寫作,他上過大學,是小有名氣的政治記者,正在寫一部關于愛爾蘭社會的小說,他是一個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目標滿懷期待的人。然而,在現實中,菲茨帕特里克卻變成了漫無目的的行尸走肉,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并有閱讀障礙的人。他沒有任何目標或職業規劃,也失去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從以上分析來看,維克多向往美好的生活,比如愛好、工作、夢想和家庭,而真實的他卻一無所有。因為心理創傷,他變成了一個與自己的期待截然相反的人。
心理創傷隔絕了維克多的情感表達和人際交往。維克多可以與身邊人正常交往,他有一個慈愛的母親和親密的朋友,與著名主持人瑞秋結婚并育有一個兒子。恰恰相反,菲茨帕特里克不善于交際且行為古怪。38 年來,他一直沉浸在創傷事件的傷痛里,與家人斷絕聯系,沒有任何朋友,無法正常與他人交流,整日獨來獨往,沒有目的地徘徊。因為無法進行男女交往和正常性生活,所以他一開始就拒絕了瑞秋的約會邀請,他將自己置身于一座孤島,與外界完全脫節。
維克多和菲茨帕特里克作為兩個截然相反的矛盾體,反映了現實與幻想的沖突。心理創傷如排山倒海般入侵維克多的人生,讓一個原本小有成就的人變成了獨來獨往的行尸走肉。
雖然主人公具有雙面人格,但現實中的菲茨帕特里克和幻化的維克多最后得到和解,這源自菲茨帕特里克的出現,維克多不得不面對自己丑陋的過去。赫爾曼提到:“受創傷的人需要了解過去,才能重新掌控現在和未來。因此,對心理創傷的認識,要從對歷史的重新發現開始。” 過去與現在的沖突雖然讓維克多難以接受,但正是菲茨帕特里克的出現導致現實與幻化的沖突,才讓維克多最終接受了現實,治愈了自己。
菲茨帕特里克和維克多之間的碰撞讓他發現了自己不完美的過去。故事的最后,菲茨帕特里克突然出現,他大膽地告訴維克多:“我就是你,維克多。我就是你變成的樣子。”并詳細地告訴維克多,他的大學、他的工作和他的前妻與兒子都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最終,維克多最難以接受的曾被校長性侵17次的事情也被爆出。終于,維克多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菲茨帕特里克,“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了。不是一面鏡子,也不是雙胞胎,我就在那里。”在他們的沖突中,維克多回到了不堪回首的過去,發現了他真實的自我。
最后,維克多接受了被性侵的事實,并對菲茨帕特里克說:“謝謝你告訴我。”對維克多來說,盲目回避只能暫時地緩解創傷帶來的痛苦,反復的噩夢和菲茨帕特里克的多次現身表明幻想終究無法脫離現實。相反,接受真實的過去,可以讓維克多煥然一新,真正擺脫創傷帶來的傷害,勇敢地走出創傷的陰霾。
小說昭示,心理創傷是可治愈的。盡管維克多試圖回避創傷事件并擺脫創傷帶來的傷害,但創傷的惡魔卻一直形影不離。神奇的是,當維克多鼓起勇氣面對它時,惡魔卻被他所打敗,逃之夭夭。
四、結論
在《微笑》中,多伊爾形象地刻畫了被心理創傷毀掉人生的主人公。雖然校長的性侵只持續了一段時間,但維克多因創傷事件造成的心理創傷卻不斷影響著他的生活,使他成了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孤島。雖然幻化為維克多而回避創傷記憶,暫時緩解了他的痛苦,但無盡的回憶重現讓他筋疲力盡。而治愈創傷的唯一方法是勇敢地直視創傷,逆流而上,這樣創傷的惡魔才會被打敗。
多伊爾通過兒童的視角觀察了童年時期的創傷經歷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生活,以及要怎樣面對創傷,呼吁大家要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多伊爾用他充滿人文情懷的文字,為弱勢群體奔走呼號,這也是小說家的初衷。